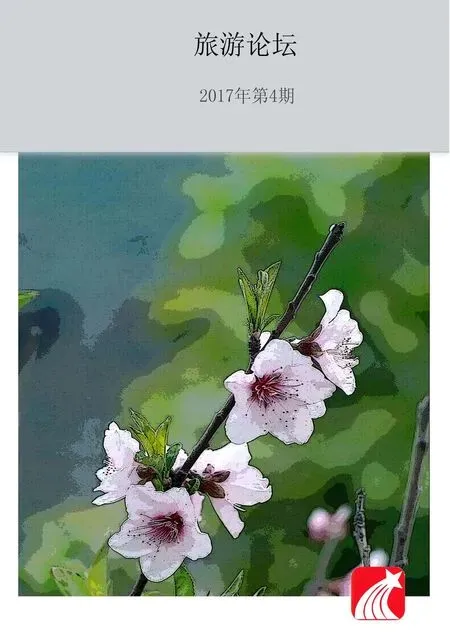论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来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朱江勇
(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旅游文化研究】
论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来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朱江勇
(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是晚清时期西方来华女性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她的来华游记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多重性。从肮脏、破败、毫无生气的中国形象,美丽、伟大、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以及女性旅行者视角、旅行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等几个方面来论述立德夫人笔下来华游记中中国形象的多重性,对认识当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来华游记;中国形象
0 引言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构筑于西方文化中的一种话语体系,其文本表现是西方传教士、商人、文学家等在历史著作、游记、书信、纯文学作品或哲学著作关于中国的记述,始于蒙元时代《柏朗嘉宾蒙古纪行》与《鲁布鲁克东行记》对“契丹”的描述,随后《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成为当时将中国盛赞为“人间天堂”的经典性著作。但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的变化发生不同演变,18世纪中期西方开始丑化与贬斥中国,如当时风靡欧洲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指出中国是“棍棒统治”的专制帝国;19世纪中期是西方否定中国形象的高潮阶段,这时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专制、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人士不断增加,众多西方来华人士中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群体,她们的身份比较复杂,有女传教士或外交官、传教士以及商人的家眷,还有旅行家、画家、摄影家和作家等,她们在著述、翻译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西方来华女性很多把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写成各种著作来塑造中国形象,其中很多为游记作品,有研究者统计“晚清民初几十年间,西方来华女性相继出版的游记作品达60余部”[1]3,代表人物有伊莎贝拉·伯德、康斯坦丝·卡明、艾米丽·坎普、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萨拉·康格等,其中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颇具代表性。
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Mrs.Archibald Little,1845—1926),原名阿丽霞·海伦·乃娃·毕维克(Alicia Helen Neva Bewicke),是英国商人、冒险家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te,1838—1908)的妻子,因而她习惯被称为“立德夫人”,国内研究者或译者将她翻译为“阿绮波德·立德”或“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她的丈夫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曾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被清朝授予从三品官衔,他是第一位闯进中国西部的外国人和第一位驾驶轮船通过三峡的人,长期居住在四川,开办重庆贸易公司,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学者气质的商人、冒险家,他的许多游记作品如《中国五十年见闻录》《穿越长江三峡》《峨眉山之游》《云南之旅》等写得生动有趣。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随丈夫在华生活时间长达20年(1887-1907年),她凭借在中国旅行、考察和社会活动的亲身经历,以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为署名著文并发表有关中国题材的英文著作有9部:The Fairy Foxes: A Chinese Legend(《狐仙:一个中国传奇》),Shanghai: Kelly &Walsh,1890;My Diary in a Chinese Farm(《中国农村日记》),Shanghai: Kelly &Walsh,1894;A Marriage in China(《中国婚事》),London: F.V. White,1896;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走近中国:我所见到的中国人》),London: Hutchinson & Co.,1899;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穿蓝色长袍的国度》),London: T. Fisher Unwin,1901;Out in China(《在中国》),London: Trehere,1902;Li Hung Chang: His Life and Times(《李鸿章:他的生活和时代》),London: Cassell &Co.,1903;Guide to Peking(《北京指南》),Tientsin: Tientsin Press,1904;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我的北京花园》)。在当时,立德夫人享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美誉,她作品中的游记非常受欢迎。本文以她的来华游记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她游记作品中的多重中国形象。
1 肮脏、破败、毫无生气的中国形象
18世纪中叶,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开始退潮,转而憎恶与丑化中国,其实质是西方势力增长后要为自身的殖民扩张提供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西方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在承认中国历史悠久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停滞,欧洲的传教士、旅行者在中国发现了普遍的贫穷,此时欧洲人犹如大梦初醒。1793年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是西方中国形象衰退的重要转折点,马嘎尔尼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乾隆皇帝的华夏中心主义在这次碰撞中水火不容,马嘎尔尼看到的是一个“停滞的中华帝国”。
“旅行家往往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视野去‘发现’世界的,‘眼后’的既定观念决定了‘眼前’所看到的东西。”[2]14立德夫人所处的年代是西方中国形象最黑暗的时期,她接受的关于中国的观念必然受时代影响,她的游记作品涉及中国大江南北,在她笔下不仅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县城与乡村的卫生状况等物质条件,而且官员、百姓的精神状态与思想,或是体制都有毫无生气的一面。如《首访北京》写了北京没有化粪池、没有下水道的肮脏卫生状况,毁灭人性的科举制度,脸色带灰毫无表情而羸弱的候补道台,面色苍白、头上长着脓疮的小孩,被驯服、思想保守落后、贫穷又抵触任何改变命运的努力的老百姓,她感叹说:“举目四望,发现周围的一切既让人感到无奈,又令人厌恶。这样的北京真是可怕!”[3]4《从引航镇到大沽口》在作者通过炮台大门时,看到中国“士兵们衣帽歪斜、毫无士气,军官们穿着褪了色的蓝紫色长衫、面露愁容,完全没有军人的气势”[3]11。《上海》中上海旧县城最恶名昭彰的特点就是脏,尤其是人们麻木地使用汇聚了各处污水的河流(立德夫人称之为“污水沟”)的水洗衣服、做饭、饮用,因此导致人们受霍乱的折磨。《烟台八月》说中国房屋旁边的排水沟散发着恶臭与污秽的程度可以和北京一较高下,“中国的城镇又脏又乱,有着中国独有的气味,如同蚂蝗一样紧追着不放——那是饿肚子时最不想闻到的。”[3]19
19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核心是鸦片,鸦片成为当时联系中英两国现实与想象的一种媒介。在现实中,西方通过贸易与战争制造了一个鸦片中国,在观念里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抽鸦片的中国形象,因而中国在西方殖民话语中被描述为“鸦片帝国”或“中国就是一个抽鸦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非理性与愚昧、病态堕落与专政暴政、贫穷与混乱。鸦片和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麦思都在鸦片战争前夕已经看到鸦片给中国带来触目惊心的景象,他说:“中国人早逝、多病、饥馑,都是鸦片造成的。而且可以肯定,这种毒药每年还在摧毁大批的人。任何有感情的人,只要一想到这种悲苦与堕落均来自鸦片贸易,都会不寒而栗。”[4]74立德夫人在中国生活的年代,离第一鸦片战争已有半个世纪,但是鸦片的祸害依然在中国各地肆虐,从重庆到乐山的路上,她发现那些肥沃土地旁生活着的是面色苍白的村民,“这些男人们全都躬着身子,似乎不光身子空了,连肋骨都被掏走了。他们手里大多拿着一个小盒子……这是专门用来吸食鸦片的。”[3]69在四川丰都城,她也见到一望便知是吸鸦片导致脸色很差的人群。
鸦片与抽鸦片,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毒品与陋习,立德夫人承认源源不断的鸦片是令中国人变得麻木不仁的罪魁祸首,也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行为对中国的危害,提出必须关注英国方面的动向,但是她闭口不谈鸦片战争,也没有呼吁英国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
2 美丽、伟大、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
西方长时期存在着作家、哲学家们在书斋里想象中国的事实,如中世纪被称为“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按照当时西方一般想象来描绘中国,他的《曼德维尔游记》将中国虚构为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的国家,伏尔泰也在《风俗史》中赞誉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清明的政教。晚清时期的西方来华游记大多数是依托于作者在中国的旅行亲身经历写成的,因而对中国的描写变得更加具有真实性,尤其对中国风俗描写更加细致,对中国人的认识更加深入。但有趣的是,坐在书斋里的作家、哲学家对中国观念上的旅行,其中国形象是清晰确定的,而那些亲历中国的旅行者,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反而是模糊、多重的,立德夫人游记中的中国形象正是这样具有多重性:并非完全黑暗或者完美,而是呈现出黑暗或完美,抑或在两者之间飘忽不定。
晚清来华旅行者们看到中国肮脏、破败、毫无生气的同时,也看到中国的美丽与伟大,同时他们也预感中国这头睡狮正在孕育着变革的力量逐渐清醒,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也落于他们的笔端。
描绘美丽的中国风景是许多西方来华游记的一个共同特点,立德夫人笔下的中国风景令她赞叹,无论是中国的城市、海滨胜地、寺庙陵墓,还是中国各地乡村山野都有美丽的景色。如北京城的春色:“登楼放眼四望,美丽的北京城尽收眼底。满城皆树,嫩绿色中隐现皇宫的金顶……山上遍布亭台楼阁,屋顶闪烁着绿色、金色和最令人着迷的孔雀蓝色……更远处是清晰可见的西山,衬着被风吹过的黎明的天空,美丽得难以言表。”[5]65-66上海花园里花卉四处绽放,色香各异,呈现在眼前是“万紫千红总是春”,“香港的公园很漂亮,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与空中台阶。而上海的公园却镶嵌在苏州河与堤岸间,园内小桥颇具观赏性,上面行人络绎不绝,下面小河蜿蜒流淌,水面上浮过快速汽船、颠簸的小艇、张着深色帆布的轻舟与平底船。这一切组成一幅流动的全景图。”[5]9重庆夏天的农村生活有酸甜苦辣,但是风景和体验都美妙极了,“宁静的夜空,银河低垂,月儿向西沉去。田野沉浸在一片诱人的寂静当中,白天看起来参差不齐的水稻,在夜幕的掩映下竟然平整而美丽。我们站在山顶,边呼吸格外新鲜的空气,边数天上的星星:牛郎星、织女星……”[3]77
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历史起点是1250年前后的蒙元时代,当时描述中国的“程式化”套用语有:“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君权强盛”“政治安定”等,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指出,蒙元时代欧洲发现中国成为旧世界最有意义的发现。当时欧洲人“更多的是去中国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的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6]135。尽管晚清来华旅行者观念中的中国已不再强大,但是他们眼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仍然让他们感慨万千,立德夫人在《海滨胜地》中写到她被长城的魅力所折服,望着蜿蜒起伏的雄伟长城,立德夫人如痴如醉地说:“中国所谓的‘万里长城’——即至少3000英里,据说花了十年才建成,而且建得如此坚固,历经两千多年而城墙依旧,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5]272-273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遭受到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打击,但作为西方来华旅行者的立德夫人,她在中国各地看到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韧性仍然散发着光芒。如在《春日宁波》写塔郎山附近当地人对她的热情、好客、友好;在《中国西藏的夏日之旅》中看到既让她产生怜悯之心又让她钦佩不已的坚韧、负重的汉族背盐人,也看到兴奋的藏族人,藏族男人们个个英俊潇洒,女人们则全都红润快乐,他们的行动都非常敏捷。在立德夫人看来,眼前中国是不可预测的、表面上屈服但从未真正屈服的、强健而健康的中国。
旅顺之行是立德夫人在华旅行的最后一站,当时旅顺被俄国占领,这次旅行结束时,立德夫人坚信在今后的几年里可以看到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如一个俄国人对她所说的“50年之后,中国人一定会成为远至贝加尔湖的主人”那样,她说:“中国人正在寻求科学之道……等我们下次旧地重游,也恐怕会面目全非了……本书只是一个小小的、对在中国的众多大好河山之中度过的悠闲时光的纪念。”[5]117
3 女性旅行者视角中的中国形象
国外学术界对清末民初来华女性游记作家这一群体关注主要从本国文学和文化背景出发,除了对她们的作品进行介绍外,还从形象学、殖民主义、历史话语、女性主义等视角切入,代表作有苏珊·苏瑞的《东方化的女性主义:立德夫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史景迁的《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专门列有“女性观察者”一章,重点考察了晚清5位来华女性出版的日记、信札等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尤其是她们笔下对中国妇女的描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景迁考察的5位女性不包括立德夫人,笔者认为她以女性旅行者视角描绘的中国妇女和中国形象同样具有代表性。
西方的女性游记研究认为,女性旅行者是“变化的观察者”,她们通过模仿男性化行动到异地旅行,试图实现自我逃离本国的社会规范,她们的游记有着区别于男性创作的独特研究价值[1]8。从女性视角来看立德夫人的来华游记,最大特点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细腻观察和热心关注、帮助中国女性。在中国旅行期间,她看到逆来顺受的中国女性遭受缠足的痛苦,而强行缠足不但没有美感,而且导致无数中国女性失去健全的双脚,甚至导致一些幼女失去生命。立德夫人呼吁废除女性缠足,1895年她和其他9位在华女性成立“天足会”,并不遗余力地到处演讲,足迹遍及武昌、汕头、厦门、福州、杭州、苏州,以及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她呼吁废除这种摧残女性的陋习,还为此拜访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大臣,最后慈禧太后下了让官员劝止缠足的诏令。立德夫人作为一个西方女性,克服重重困难去唤醒千千万万的缠足妇女,她大声疾呼:“中国妇女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和他的母亲一样。自从缠足在中国盛行之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世景仰的男人。人们不禁大声呼喊‘他在哪里?’”[3]191—192立德夫人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第二个观音菩萨”。
立德夫人还以女性旅行者的视角对中国女性有独特细致的观察,一方面为中国女性的现状(如受缠足、吸鸦片之害)痛心不已,如立德夫人发现不少通商口岸的中国女性堕落,她们喜欢抽大烟、散流言、开派对、喝酒、玩牌,尤其是身体孱弱的女烟鬼依然通宵达旦地吸烟,“女烟枪们从烟榻上站起来,眼睛放光,面颊潮红,激动得语无伦次。慢慢地,她们脸色转黄,面露病态,郁郁不乐。她们似乎对吸烟片不以为耻,就像英国酗酒的女人对酒一样。”[7]81但另一方面,立德夫人也不乏褒扬中国女性的美丽、热情,如她经过四川万县的时候,看到船上的美丽的女子,“她们大部分有着红扑扑的脸庞,娇羞而美丽,大眼睛水灵灵的……这里的妇女格外美丽。”[3]61她在上海乡下旅行时,经过一户正在举行婚礼的人家,那些怀里抱着打扮得精致漂亮的婴儿的女宾客热情地拉着她的手要她进去做客;在立德夫人的眼中,接受福音的中国人最可爱,那些来教会学堂听课的女孩子们长得眉清目秀,脸庞红扑扑的,眼睛里透着机灵劲儿;在苏州,立德夫人为苏州女性的美丽惊叹不已,她认为苏州女性之美是艳丽而不显妖媚,苏州女性的穿着打扮要“比中国西部妇女的衣服合体得多。袖子紧贴肩膊,露出小臂,而不像一般的中国服装那样,袖子一直垂到手腕那里”[3]189。
4 旅行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旅行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移动与碰撞,旅行者带着自身的文化在异乡与另外一种文化接触,产生旅行中的跨文化交流。立德夫人在她的游记中处处体现跨文化的视角,如她习惯于将中国某一处风景与其他国家风景相比较:《春日宁波》中雪窦山的杜鹃花令她的惊喜油然而生,山坡上全都铺满了红彤彤的杜鹃花,它们就像在英国花园里一样娇艳动人,竞相开放。在她眼中雪窦山午后的景色简直可以和意大利北部的风光媲美,“塔郎山能让人想起英格兰约克郡荒原上的春天,因为它是峡谷中的一片高地,环境与天气情况都让人觉得舒适愉快。”[3]39雪谷与塔郎山之间的山谷简直就像圣约翰斯哥特城堡,令人流连忘还,五陵谷则像麦德罗的维尔佩拉索山谷,也像日本的一个山谷,只是比日本的小巧但不乏雄浑。《烟台八月》中她写道:“在烟台,很多地方都能让我想起霍利赫德……同烟台一样,霍利赫德的大海也是湛蓝湛蓝的,海拔高度大概与烟台的小山持平……烟台南部那些青黑色的山峰雨量就少得多,同霍利赫德比起来,简直就像是来自阿拉伯沙漠,似乎从上帝造人那时起就没有下过雨。”[3]15—16重庆在立德夫人的眼中则像是魁北克、里昂或爱丁堡,她说:“重庆像魁北克省一样,处于两江交汇处。它大小与里昂差不多,外形与爱丁堡有几分相似,城墙高耸”。[7]33
不仅是面对风景,她还对旅行途中看到的种种现象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九月的芜湖》写一个寺庙胖胖的弥勒佛很像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个爱吹牛的福斯塔夫;《温塘》是写她在四川重庆东北温泉旅行的经历,温泉对任何人都是免费的,她立刻想到:“英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如画的动静,却不允许人们擅自入内,因为它们通常属于某个有钱人,而那里恰恰是他私人住宅的范围。中国不是这样,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开放的。”[3]139对中国人的日常打扮,立德夫人看到中国人的衣服宽大,两个胳膊都行动自如,不像英国人的衣服穿或者脱都得又拉拽又挺胸缩肩,很是费事。对颜色的敏感度也体现在穿衣服上:“中国年轻有钱的少爷,总是穿得很艳……伦敦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则不同,穿的衣服往往是纯色的。”[3]155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体现在对中国这个失败的国家与民族异类化,异类化的方式表现为将中国漫画化与丑化[8]101。如把中国人称为“中国佬”,嘲笑中国男人留辫子、女性裹小脚、全民穿着蓝布袍,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就是挤满东方大地的呆滞愚钝、残暴冷酷的蚁民。在带着跨文化的视角看彼时中国的现状,立德夫人在描写中国肮脏、破败、毫无生气时,不断地流露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如她认为在华传教士或西方人对中国来说都带有“救世主”的意味,而且中国在很多地方有进步几乎是得益于西方人。如《烟台八月》中她说:“在欧洲人的作用下,烟台成了一个超级俱乐部——富有、凉爽、通风效果良好,最大的特点是思想开放。这一切都得益于那些出过力的欧洲人。”[3]18在烟台的传教士们还做一些具体改变中国的事情,如引进肉质美味的梨、葡萄,还有土豆,但是他们最想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些传教士们被立德夫人看成是具有极大献身精神的男女,在她看来教义在中国获得认可的话,中国或许会像美洲人一样进入文明时代。
5 结语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一种跨学科的深度观念史研究,它是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基础上,我们了解、理解、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目的与意义就是认识西方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即西方文化中关于中国认识的那一部分。而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具体文本构筑恰好始于西方旅行文学,即《柏朗嘉宾蒙古纪行》《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关于“契丹”的介绍,因此从西方旅行文学切入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很有意义。
古今中外大量的旅行文学作品内容的开放性、形式的流动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加之旅游学科研究的交叉属性,决定了旅行文学必然会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旅行文学具有跨文化性和跨学科性,也使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旅行文学的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旅行文学笔下的旅游目的地其实是一个超越现世时空的浪漫之地,它既在现实世界中,又不是那个“真实”的地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不仅是旅行文学文本的产物,而且是旅行者经验的产物,因为旅行者的想象颇具意义;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指向,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指向,不管旅行文学文本的写作环境与现实关系如何,都是以想象或表现的方式构筑一种内心的目的地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文学的研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尤其重要。
立德夫人作为晚清时期来华颇具代表性的亲历中国的旅行者,她的来华游记讲述了作为一个外国人十多年来在中国城市、乡村的所见所闻,细致地描绘了不同地方的风俗民情,深入地挖掘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她的游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多重性。本文从肮脏、破败、毫无生气的中国形象,美丽、伟大、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以及女性旅行者视角、旅行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等几个方面来论述立德夫人来华游记中中国形象的多重性,对认识当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1] NIE H.A study of British women's travels in China in 1840-1911[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2012.[聂卉.1840—1911年英国女性来华游记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2.]
[2] WANG Y S.Western image of China(book one)[M].Beijing:Unity Press,2015.[王寅生.西方的中国形象(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3] LITTLE A.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M].CHEN M J,trans.Nanjing:Yinlin Press,2014.[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M].陈美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4] MEDURST W H.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M].London:Jonh Snow,2b,Paster Noster Row,1838.
[5] MRS LITTLE A. 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M].LI G Q,LU J,trans.Beijing:Beijing Library Press,2004.[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我的北京花园[M].李国庆,陆瑾,译[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6] HUDSON.Europe and China[M].LI S,WANG Z Z,tran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5.[赫德逊.欧洲与中国[M].李申,王遵仲,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7] LITTLE A.Intimate China[M].YANG B,FENG D,et al,trans.Nanjing:Nanjing Press,2008.[阿绮波德·立德.亲密接触中国:我眼中的中国人[M].杨柏,冯冬,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
[8] ZHOU N.Second human[M].Beijing:Academy Press,2004.[周宁.第二人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潘岳风] [责任校对:连云凯]
OntheChina’sImageoftheTravelNotesofMrs.ArchibaldLittleinChina
ZHU Jiangyong
(GuilinTourismUniversity,Guilin541006,China)
Mrs. Archibald Little was one of female western representatives who paid a visit to China from the we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r travel notes in China built up multiple China’s images. The images from being dirty, dilapidated, and lifeless to attractive, great, and hopeful, as well as from the female traveler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be into the western China’s image at that time.
Mrs. Archibald Little; travel notes in China; China’s image
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2015年)课题:“晚清时期西方旅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TYETP201550)
2017-02-19
朱江勇(1976- ),男,江西瑞金人,文学博士,桂林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戏剧与区域文化、旅行跨文化研究。
ZHU J Y.On the China’s image of the travel notes of Mrs. Archibald Little in China[J].Tourism forum,2017,10(4):113-119.[朱江勇.论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来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J].旅游论坛,2017,10(4):113-119.]
F592.9
A
1674-3784(2017)04-01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