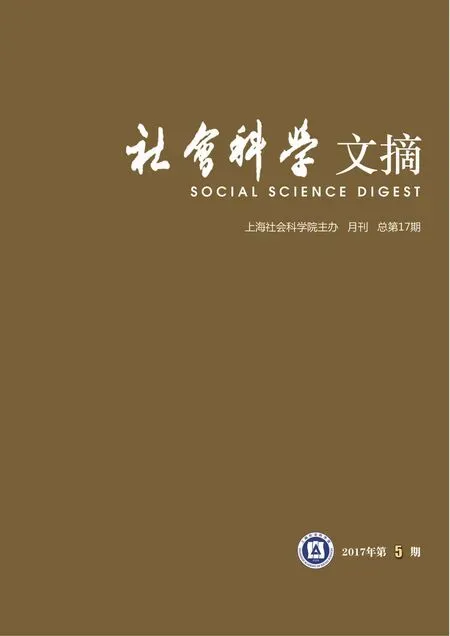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的性质
——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
文/陈民镇
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的性质
——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
文/陈民镇
郭沫若在判定商代是否为奴隶社会时,首先确定农业在商代占主导地位,然后证明主要农业生产者是“众”,进而认定“众”为奴隶,并得出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结论。郭氏认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众”与“民”均为奴隶,一些学者沿承其说,将传世文献以及甲骨卜辞中的“众”、“民”一概视作奴隶。郭氏从社会生产的主导成分出发判定商代是否属于奴隶社会,确是一条可行的途径。问题在于“众”是否是当时的主要农业生产者?“众”是否如郭氏所认定的属于奴隶?
卜辞所见“众”、“民”的身份
殷墟所见人殉、人牲以及卜辞中的“众”、“民”,均被郭沫若视作商代的奴隶,这也构成殷商奴隶社会说的两大支柱。然而,关于卜辞中“众”和“民”的具体涵义,学界向有异辞。甲骨文的“众”作,郭沫若认为其字取日出时众人相聚而作之意,并以此为“众”表示奴隶的重要证据,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有学者虽认同郭氏的字形分析,但将“众”理解作商代的自由民。甲骨文中是否有“民”字,尚存争议。西周早期金文中已有“民”字,如大盂鼎所见、何尊所见,论者或以为像草芽之形,系“萌”的本字(如林义光、商承祚便持此说);郭沫若则认为像刃刺目之状,亦表示奴隶。甲骨文中的“民”字尚不明晰,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以来,不少学者将甲骨文中的“”释作“民”。不过,总体卜辞所谓“民”字尚无充分材料可供讨论,其义尚不明了。而“众”则有较丰富的材料,学者的讨论也更为充分。
学界对“众”的认识,向来存在较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众”究竟是奴隶还是平民,或者说是奴隶还是非奴隶。在郭沫若的基础上,陈梦家、王承祒、王玉哲、王贵民、杨升南等进一步论证“众”为奴隶。针对这种说法,许多学者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众”并非奴隶,当是自由民、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族内农夫之类的身份(笔者统一视作广义的“平民”),张政烺、赵锡元、于省吾、赵光贤、朱凤瀚、金景芳、裘锡圭等均持此说。两派学者所依据的卜辞材料大同小异,但由于史学观念及古文字释读理解的分歧,所得出的结论亦迥然相异。
按照郭沫若的思路,殷商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本,而“众”则是这一农业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如“众”从事与农耕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涉及“田”、“裒田”、“耤”、“尊田”等。上述行为一般被认为与耕种有关。但并非没有疑义,如也有学者主张“田”系祭祀田祖,与耕作无涉。果其如此,参加祭祀的“众”便很难说是奴隶。“裒田”、“尊田”则确与耕种有关,“耤”或即籍礼,但从卜辞看更有可能指普通的耕作。
再如“众”与商代重要粮食作物黍也有联系,如:“壬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冏。”商王与“众”一同参与冏地的劳作,这实际上已非单纯的农业生产。有学者认为该行为说明商王亲自对奴隶劳动进行监督,徐喜辰、岛邦男、裘锡圭等则指出这是商王偕同“众”参加籍礼。岛邦男将“众”与《国语·周语上》籍礼所见“百吏庶民”相联系,极有见地,但他将不少明显与籍礼无关的辞例比附籍礼,招致学者批评。裘锡圭则全面分析了冏地与籍礼的关系,进一步说明“王往以众黍”并非商王监督奴隶耕作,而与籍礼有关。清华简《系年》首章强调籍礼之于王朝兴替的意义,有学者据此指出商代可能并无籍礼,而是商周因革之际周人的制度创造。出于文体性质的特殊性,卜辞未必会明确标示冏地生产的礼仪背景。与冏地有关的仪典即便不同于周人的籍礼,但至少也具备商王亲自参与以及将所获粮食用以祭祀神祇的特征,性质与籍礼有叠合之处。如若“众”是奴隶,商王偕同奴隶参与此类活动是难以想象的。
从卜辞看,除参加劳动生产外,“众”也参与商王组织的田猎、征伐等活动,殷商的族众与军事组织本就关系密切。耐人寻味的是,在动用“众”进行军事活动时,尚且需要“气”这种表示征求意见的、相对平和的方式。当“众”有灾祸时,商王会进行卜问,甚至举行相关祭仪。于省吾曾指出,卜辞未见杀“众”以当人牲,也从没有以“众”用来赏赐的例子。以上现象,均可佐证“众”并非奴隶。卜辞中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众”的人身被占有,或可以买卖和杀戮;“众”并不符合奴隶的一般特征,卜辞材料反而说明“众”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过去的一些误解往往来自对卜辞的误读。如卜辞所见“众人”,由于一些学者将“读作“屠”,故认为“众人”可被任意屠杀。然而,“众人”可以被屠杀并不能证明其一定是奴隶。更何况所谓“”实际上不从“余”,读作“屠”并无确据。再如论者将卜辞所见“丧众”解释作奴隶逃亡,于省吾、裘锡圭已澄清“丧众”只是与战争有关,所谓“雉众”亦当作此理解。可见,关于卜辞中的“众”可以被任意屠杀或受压迫逃亡的解释都是不可靠的。文字学与训诂学的研究澄清了过去辞例理解的疑啎,倾向于说明“众”并非奴隶。
持“众”非奴隶说的学者认为,在商代,家族人数中绝大多数的平民族人才是少数宗族贵族的主要压榨对象,前者正是“众”的主要来源。这可以得到考古发掘的一定支持。平民在殷商社会中占很大比重,如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除发现12座大墓和250个祭祀坑,还发现1200多座小型墓葬。学者相信,这些小型墓葬主人是殷代社会的平民,即“众”。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商王朝进入成熟王国阶段后仍以族氏为社会基本单元,同一墓地的墓葬主人是本族平民,过去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没有提供商王朝存在众多奴隶从事社会生产的证据。但所谓“本族平民”的成分未必单纯,殷墟墓葬中所谓平民的成分比较复杂,未必与王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羌人等外族战俘有很大一部分被献祭,但羌人也有转化为士兵和劳动者的线索,因此并不能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步融入殷商的平民阶层。
卜辞中的“众”很难说是奴隶,这自然对殷商奴隶社会说不利。但“众”是否为殷商的主要农业生产者?“众”之外的农业生产者重要性如何?均需进一步讨论。卜辞所见“臣”、“妾”、“仆”、“奚”、“刍”等,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人身自由,且参与社会生产,他们是否为奴隶?他们在商代的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何?如果他们是奴隶,能否说明殷商属于奴隶社会?目前学界对这些人群的研究并不充分,他们在殷墟的墓葬中也难以找到相应的材料。而且,甲骨卜辞,文辞简质且文体特殊,虽是共时的、直接的史料,但所包含的信息毕竟有限。即便当时存在大量奴隶,这些奴隶的存在情形和生活状态也未必作为“国之大事”成为卜辞所关心的对象。因此,卜辞是探索殷商社会形态的重要史料,却并非决定性的史料。
清华简商书所见“众”、“民”的身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近年来公布多篇与《尚书》有关的文献,其中第1辑的《尹至》、《尹诰》以及第3辑的《傅说之命》(即《说命》)三篇均可归入“商书”。清华简商书出现“众”与“民”的关键线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商代的“众”、“民”问题,但目前尚缺乏讨论。《尹至》、《尹诰》中涉及“众”与“民”的文句有:
(1)余微其有夏众不吉好,其有后厥志其丧,宠二玉,弗虞其有众。民允曰:“余及汝偕亡。”(《尹至》)
(2)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咸曰:“曷今东祥不彰?”(《尹至》)
(3)夏料民入于水,曰:“战!”(《尹至》)
(4)夏自竭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无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翦灭夏。(《尹诰》)
以上为夏之“众”、“民”。在(1)中,“有夏众”与“有后”相对举,二者为“民”与“君”的关系。后文叙及“弗虞其有众”后马上言及“民允曰”,“有众”与“民”、“有民”其义实一。在(4)中,“有民”、“民”与“众”交替使用。在上述辞例中,“众”、“民”涵义相近,且“众”、“民”与夏王的关系极为微妙。“众”、“民”是“守邑”的根本,因夏王“弗虞其有众”、“自竭其有民”、“作怨于民”,便与夏王“离心”,这被视作商人灭夏的关键。再如:
(5)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尹诰》)
(6)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尹诰》)
(7)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予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尹诰》)
以上为商之“众”、“民”。(6)先曰“民”,后曰“众”,文意相承,系同义互置的关系。从商王立场而言,只有顾及“众”、“民”的感受,使其受益,才能得到“我众”和“远邦”的拥戴。“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指的是将夏人的财富施与“众”、“民”,使他们获得商人灭夏的实利。这里的“众”、“民”,显然是指商王的子民或族众。
在《尹至》、《尹诰》中,或曰“众”、“有众”,或曰“民”、“有民”,无论就商而言还是就夏而言,涵义均大致相同。他们为君王所倚重,他们是否拥戴君王,攸关政权的稳固与否。虽然“众”与“民”在具体使用时侧重点可能存在微妙差异,但总体而言,《尹至》、《尹诰》中的“众”与“民”均指一般民众,这与卜辞所见“众”的涵义大体一致。
《说命下》出现了4例“民”,未见及“众”:
(9)其又廼司四方民,丕克明。(《说命下》)
(10)汝亦惟克显天,恫怀小民,中乃罚。(《说命下》)
(11)余丕克辟万民,余罔坠天休,式惟三德赐我,吾乃敷之于百姓。(《说命下》)
在《说命下》中,君王的职责在于“司四方民”、“辟万民”,同时还要时刻“虞民”、“恫怀小民”。值得注意的是,(8)的“弗虞民”与前文(1)《尹至》的“弗虞其有众”可相参证,仍强调不关心“众”、“民”会招致祸端,同时进一步说明“众”与“民”意涵相当。但(9)所见“四方民”、(11)所见“万民”的说法,似乎说明“民”的外延更广。(10)所见“小民”,与清华简《保训》诸篇所见“小人”,“民”、“人”近同,《说命上》出现两次的“邑人”也相当于邑内之“民”。虽然卜辞中的“民”尚不明晰,但西周以来的金文和传世典籍基本上都可与上述辞例相验证,表示一般民众,而无所谓奴隶之义。
《尹诰》、《说命下》诸篇体现出的思想,颇有后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意味。若传世商书与清华简商书有一定依据,那么涉及敬天保民、安民利民、重农裕民、慎罚宽民、柔远能迩等精神的重民思想在商代已有一定发展,周人敬德保民的观念当非无源之水。如果商代已有成熟的重民思想,当时“众”、“民”的身份也可以得到进一步落实。夏大兆、黄德宽鉴于《尹至》、《尹诰》出现重民思想而判定它们晚出,这沿承了自王国维以来将重民思想视作殷周分界的“常识”。廖名春则将《尹诰》所体现的重民思想视作孟子思想的源头,程浩强调清华简商书保留了商代的可信史料,并据《厚父》指出至少在周初民本思想即已比较成熟,宁镇疆对此有进一步探讨。李守奎指出:“我们是根据孟子的民本思想推定之前该思想的不存在,还是根据其前面的思想推定孟子思想的来源,这个问题事关重大,需要我们慎重对待。”诚然。不少学者将“天”、“德”、“民本”等观念视作周人的专利,重要依据是它们在卜辞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但由于卜辞的文体具有特殊性,未必能反映商人的全部精神世界。断言商代便有发达的重民思想,为时尚早;先入为主地将重民思想视作周以后才出现的内容,下意识地认为商人是“神本”,周人是“民本”,从而抹煞了早期文献的价值,亦不足取。重民思想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表现,并且需要结合中国早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政治思想、宗教观念等因素加以理解。
余论
通过上文分析,殷商奴隶社会说的一大支柱,即“众”、“民”系奴隶,在新材料面前遭到不小的冲击。但即便这一支柱不成立,仍不能遽断殷商非奴隶社会,因为殷商奴隶社会说尚有其他支撑。如若殷商王朝并非奴隶社会,并不等于中国同时期其他区域没有进入奴隶社会,也不等同于商代之前或之后没有经历奴隶社会。
商代之前的社会形态,论者要么轻易对号入座,要么置之不顾。随着相关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商代之前社会形态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充分的资料,但尚待充分发掘。无论是理论建构、文献记录、考古实物还是人类学的调查,均有其长处,也存在各自不可避免的缺陷,故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尤为必要。目前而言,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整合还是非常不够,这也是奴隶社会问题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撰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宗旨在于写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无论是侯外庐、张光直还是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孜孜于这一“续写”的尝试。郭沫若虽也意识到“中国的古代发展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尽相符”,“不否认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特殊性”,但始终坚持西周或殷商属于奴隶社会的观点。随着论辩的深入,不少学者开始质疑郭沫若的看法,即便是一些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学者,也逐渐认同奴隶社会多样性的存在。如徐中舒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的特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还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不能简单地按照欧、美社会情况硬套。”如果中国的商朝以及其他时期并不存在典型的奴隶社会,如果中国文明的发生与早期发展经历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路径,那么是否可能预示着中国的奴隶社会属于另一种类型?这已然涉及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理解社会形态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这便要求我们从中国文明的实例出发解答“中国路径”。如若忽略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进程中多样性的存在,“不仅使得历史上千差万别的现象变成无法解释,而且使得历史的统一性也变成无法认识”。
唯物史观不是提供给后人的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在误读马克思经典理论、脱离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主张商周奴隶社会说,恰恰是违背唯物史观的表现。中国学者一度受欧洲中心论和特定政治语境的拘囿,往往存在误读或者盲从马克思经典理论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理论的情形。近30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排斥宏大叙事,忽视对历史理论的建构,有走向碎片化的倾向,故有学者近来呼吁“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西方理论,我们不能自我设限,而应该在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和推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摘自《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原题为《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