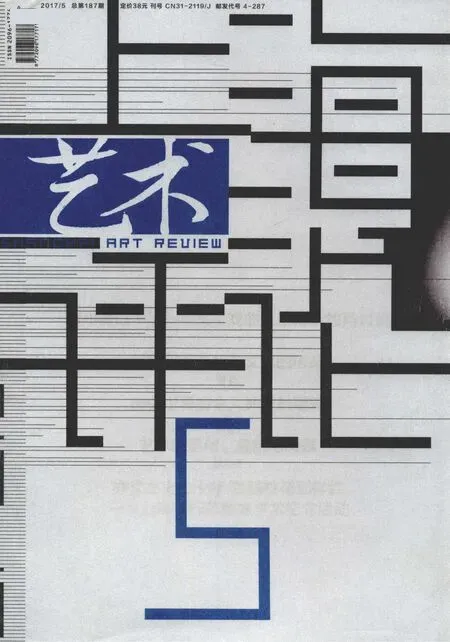经典,如何重读?
——论传统戏曲文本的当下搬演
张之薇
经典,如何重读?——论传统戏曲文本的当下搬演
张之薇

《哈姆雷特》立陶宛OKT剧团
公元1616年,中国明朝万历年、英国查理一世时代,一个名叫汤显祖的隐居文人与一位名叫莎士比亚的编剧写手都在这年溘然长眠。显然,他们逝世于同年是一个偶然,但这个偶然却使得400年后的2016年,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让他们的相遇成为必然。历经400年时光的淘洗,两个本无关联的人,却因为他们同为剧作家的身份,因为他们同样穿越时空的经典剧作,而被拿来,让他们相遇。
于是,2016年,东方的汤显祖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在国内的戏剧重镇——北京,交相登场,应接不暇。从开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以《亨利五世》《亨利四世》吹响纪念莎士比亚的号角开始,立陶宛OKT剧团的《哈姆雷特》、德国邵宾纳剧院的《理查三世》、波兰克拉科夫老剧院的《李尔王》、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威尼斯商人》等等,纷纷在京上演。而与之相对应,2016年国人纪念汤显祖最大的动作无疑是上海昆剧团将汤显祖传世的《临川四梦》创排,并于当年7月在国家大剧院接连四日上演,这绝对堪称近年来戏曲界少有的盛事。紧随其后的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重新创排的《南柯梦》(上下本),以及一些根据汤显祖作品改编的话剧、小剧场戏曲等也接连上演。由此引出一个话题,400年前,或者更久远的传世剧作,我们究竟该如何搬演?经典文本,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该如何与当下对接?以及究竟该如何让我们的戏曲经典融入世界戏剧的大环境中?
搬演经典,中外观念不同
在西方,经典文本虽然在精神表达上具备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特点,但是由于时代的隔膜,恐怕传世经典的搬演在后世大多都无法避免原创文本与独特阐释相结合这一环节,也就是说,经典附着着阐释的乐趣,而在当代西方批评的语境中,这可能是经典最大的乐趣。所以,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宣称“作者死了”,实际上就是挑战原创作者的绝对权威地位,此思潮也影响了戏剧界,即剧作家地位开始被撼动。随之,“残酷戏剧”代表人物阿尔托更是在《名著可以休矣》一文中狂言“旧时代的名著对于旧时代是有用的,但对于我们则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用最接近的、最直接的、与当代感情风尚相适应的、能为人人所理解的方式说已经说过的东西,去说还没有说过的东西。”一些反叛传统的导演对经典的搬演很热衷,就是因为经典中蕴含着重新被阐释的巨大空间。在他们看来“作者”已死,接下来可以狂欢的是作为“读者”的他们。而在汉斯·蒂斯·雷曼的《后戏剧剧场》中,更是把文本视为和剧场“姿态、音乐、视觉要素相平等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文本话语与剧场话语之间的裂痕是很大的。它们可以明显不一致,甚至可以毫不相干。”在西方,剧场与文本的关系不是依附与融合,而是充满矛盾的张力,有的时候甚至是分裂的。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北京戏剧舞台上,立陶宛OKT版的《哈姆雷特》是一个现代化妆间里在镜像魔阵中徘徊的王子;我们看到了德国邵宾纳版的《理查三世》是通过一只垂悬的“麦”让中世纪的暴君走进当下;我们看到了波兰克拉科夫老剧院带给观众的是一场李尔缺席的《李尔王》。反之,英国皇家莎士比亚、环球莎士比亚剧院对莎士比亚经典文本中规中矩的搬演,反倒显得缺少乐趣。看得出,当代对经典文本的重构与创造是国外先锋导演很强烈的创作倾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剧场是独立的”这一观念,是基于经典可以通过再阐释让当代人审视自我这一前提。
而搬演中国的经典,尤其是戏曲文学经典,面对中国戏曲这一载体,我们的态度和方法与西方导演有着大不同。区别于西方戏剧缘起于对理性精神的求索和对“酒神”精神的崇拜,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净化与洗涤灵魂;戏曲则不然,娱乐性、观赏性、民间性是其本源,几百年来形成的唱、做、念、打一整套表演体系在宋、元、明、清、民的历史长河中与文学的位置此消彼长,直至最终占据了比文学更核心的位置。而客观地说,中国戏曲之于世界戏剧的最大贡献,一定首先是其表演艺术,之后才是文学上的。这就决定了面对中国戏曲经典文本,表演的意义比重新阐释的意义大,传承的价值更多时候是在思想性之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际,上海昆剧团能够将汤翁久不上演的“四梦”全部创排出来,的的确确是昆曲界、乃至于戏曲界一件难上加上、功德无量的大事。因为它通过上演不仅仅完成的是对汤显祖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对上昆传承机制的夯实。
据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记载,清末时上海昆曲上演情况,汤显祖“四梦”之《还魂记》(《牡丹亭》)能够上演的折子为:《劝农》《学堂》《游园》《堆花》《惊梦》《离魂》《冥判》《拾画》《叫画》《问路》《吊打》《圆驾》;《紫钗记》能够上演的折子为:《折柳》《阳关》;《邯郸记》能够上演的折子为:《扫花》《三醉》《番儿》《云阳》《法场》《仙圆》;《南柯记》能够上演的折子为:《花报》《瑶台》。这份材料是根据清末的《申报》和《字林沪报》等戏目广告整理而出的,大致记录了晚清苏州昆班以上海为中心的演出情况,当时的昆曲虽属强弩之末,但也有七八百出折子戏可以经常上演。但是,今天,纵然如上海昆剧团这样传承有代的国内最顶尖昆曲院团,也只有近300出折子戏可以上演。昆曲剧目传承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传一代,少一半”,而昆曲折子戏的失传失掉的倒不在于唱谱,更不在于文本,而是在于其精微细腻的表演脉络,诸如唱做规范、技艺要点、行当绝活等。正如俞平伯曾言:“尝谓昆曲最先亡者为身段,次为鼓板锣段,其次为宾白之念法,其次为歌唱之诀窍,至于工尺板眼,谱籍若俱,虽终古长在可也。”这就是以表演为本位的昆曲艺术最大的现状,对“身上的事”的抢救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如昆曲这种具有深厚传统积淀的古老剧种,恢复、整理、传承,使之能演,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
上海昆剧团“临川四梦”:以恢复整理为原则的文本搬演
上海昆剧团担此大任,让经典“四梦”全本上演,就是出于对昆曲经典文本的恢复、整理、传承。不过他们对“四梦”采用的方法也是有区别的。《牡丹亭》,这部在乾嘉时期,就以折子戏形式频繁上演的剧目,上昆仍旧直接以折子连缀的形式搬演。事实证明,经过数百年舞台锤炼,并流传至今的这些经典折子,依旧在审美享受上是最值得称道的。以《游园》为起,以《惊梦》《寻梦》《写真》《离魂》为承,以《拾画》《叫画》为转,以《幽媾冥誓》为合,在积淀深厚、细腻完备的表演面前,原本五十五出的“全本”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全本”真正的要义在于还原昆曲最精纯的表演,让演员的唱、念、舞成为舞台上的本体,也成为观众欣赏的主体,这样对于《牡丹亭》这样耳熟能详的文本恐怕是最佳的表现方式。我们看到了三代杜丽娘和三代柳梦梅的代继传承,看到了闺门旦、花旦的动静相宜,以及昆曲巾生除了文雅之外的痴与狂,看到了昆曲演出史上最经典的曲牌中所蕴含的情与景在演员身上的体现,看到了在一出折子戏中演员怎么通过表演将人物的情感层层推进,等等。不过,略显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标榜“全本”的《牡丹亭》搬演,还是没有跳出昆曲即才子佳人的生旦戏模式,著名的《冥判》一折并没有出现。试想,如果在生旦行当的静戏之余,也有昆净行当的热戏对比,这部凝聚昆曲表演精髓的“全本”《牡丹亭》可能更能体现昆曲艺术的多维性。
而与《牡丹亭》不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这三个剧目,由于在舞台上搬演的机会几乎绝迹,加之大多观众对它们的故事与情节远没有达到非常熟稔的地步,所以,从文本上进行重新整理改编以便在时间长度上适应当下,同时在舞台呈现、演员身段、唱念上进行重新创造则成为了主要创作方法。这三部戏分别聘请了王仁杰、张福海、唐葆祥对其进行整理,他们均在遵循汤显祖原著基本内容的原则下,对情节进行了适度删减,对唱辞的精简也是搬用与创造两结合,让叙事节奏加快,虽然,有时有跳跃之感,但保留一个完整故事主线的原则在这三部戏中是一致的。从舞台呈现上看,虽然三部中都有少数的折子戏曾被演出,但是几乎不见于当今舞台,因此,“全本”需要在遵循昆曲身段规范下重新创造,梨园中人谓之,捏戏。从“案头”到“场上”,实际上始终是昆曲全本戏搬演时面临的必要转化,尤其是在乾嘉之时,折子戏大盛之后。据陆萼庭言:“当昆剧折子戏盛行时期,梨园搬演家从来没有冷落过全本戏,相反,多方探索,力图重振新戏的时代雄风,因为他们深知这是一种具有坚实群众基础的演出方式。”当时的梨园,对全本戏的搬演,有如《精忠记》《铁冠图》这样“借全本之名,展示折子戏之实”的“百衲本”;也有如《白蛇传》这样根据传奇《雷峰塔》(蕉窗居士作)完全改写的梨园本;也有从著名曲家作品中选取合乎梨园标准的剧目进行加工,如将李渔的《凰求凤》经过改删压缩,按照梨园讲究戏剧性、热闹、好看、新奇、有熟套剧场效应等特点进行搬演。以此对照,上海昆剧团对“临川四梦”从“案头”到“场上”的这个创作过程,似乎略显拘谨,除《牡丹亭》之外的“三梦”基本遵循原作,以压缩为主,在舞台旨趣上也以文人雅趣为主,虽然在根据曲文唱词将昆曲身段与行当结合,与人物结合,与情景结合,展现昆曲载歌载舞的特点上完成得很不错,但是却难说这三部戏在未来能否有留得下来的折子。今天,我们排“全本”是为了什么?一定是为了上演,为了流传,这恐怕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如果过度追求文人雅趣,反之忽视梨园标准,可能结果会事倍功半。

上海昆剧团“临川四梦”之《牡丹亭》(摄影:祖忠人)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桃花扇》:“一戏两看”式文本搬演
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全本”《桃花扇》搬演方法值得借鉴。从2017年4月开始,江苏省昆版全本《桃花扇》开始巡演,他们打出的宣传语“一戏两看”很惹人眼球。怎么两看?一看为全本,二看为折子戏专场。分两天上演,两者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而“全本”的演出方式很是别致,开场幕前曲,由不同的演员穿着水衣登台演唱孔尚任《余韵》中的套曲【哀江南】,古朴的空舞台上既是演员也是角色的他们,以不同行当分别吟唱着这套凭吊兴亡之曲,在致敬先贤之余,也将王朝易代、残山剩水的巨大悲凉感清晰地传达出来。“全本”《桃花扇》以【访翠】【却奁】【圈套】【辞院】【寄扇】【骂筵】【后访】【惊悟】【余韵】九场贯穿全剧,将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与“舆图换稿”的大时代相沉浮,最终落脚到那扇“推不开的门”上。这扇“推不开的门”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编剧张弘对孔尚任笔下人物的重新解读。在张弘看来,被道士棒喝的李香君与侯朝宗二人“双双入道”为自觉自愿,其仅为躯壳的不团圆而已,那么相较躯壳的不团圆更令人悲哀的是精神的不团圆,所以,让那扇门永远地定格在那里,门内的人早已物是人非,心境全无,无颜面对自己的小爱,而门外的人却依旧心存期盼,情爱弥新,这种相爱之人精神上的咫尺天涯或许更具悲剧性。笔者很是赞叹张弘面对经典并不亦步亦趋,敢于大胆改编的胆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扇“门”是张弘想象出来的,想象面对国破朝亡、大厦将倾之际文人们的心境究竟是怎样的?而这种想象是与300年前的文人共鸣之后,注入当代文人精神的创造,颇值得玩味。
看罢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版“一戏两看”《桃花扇》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整新如旧”。舞台上并没有看到当代技术对昆曲的僭越,所有的呈现仿佛都是传统昆曲的本来面貌,但实际上在清末的昆曲演剧史上《桃花扇》却并没有什么流传下来的折子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竟然都是新创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以折子戏的样式上演的,这就保证了它未来的存活度。出现在折子戏专场中的【侦戏】【寄扇】【逢舟】【题画】【沉江】,是从“全本”的关目中撷取捏成的,是完全尊重昆曲表演规范的。这五个折子虽然在行当的侧重点上不同,但是在趣味、人物、情感、表现上却是昆曲表演艺术的完美集萃,是“全本”之上的又一次绽放。如果说“全本”中所有场次都是紧紧围绕主线人物而推进的,那么折子戏则是对“桃花扇底”明末群像人物的一次聚焦。如“全本”中【惊悟】一场,可视为主角侯方域心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在折子戏专场中转变为以史可法为主角的【沉江】一折。由柯军饰演的史可法,扎着白靠亮相,发挥他文武老生的唱工和武戏功底的优势,将一个穷途末路的英雄在面对江山无主时,生无可恋的悲情倾泄而出。在这一出折子中,舞台上虽没有江却分明让观众看到了“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的波涛;舞台上也没有马,观众却分明能感受到仰天长啸、直奔江心,追随主人而去的白龙驹。一出精湛的折子,一定是人物、情感、唱做、技艺齐头并进的,【沉江】就是这样一出戏,而且它在全本中的位置绝对不可或缺。
柯军中英版《邯郸梦》:跨文本式搬演
无论是上海昆剧团还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大致还是在一个传统的“文本至上”的观念下进行创作,即以恢复、整理、改编为主要目的,创作者尽量隐没在大师身后,不仅是客观愿望,也是主观要求。这固然是昆曲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我们,在世界戏剧大环境中的中国,戏曲经典文本的价值难道就到此止步了吗?怎么样让戏曲这门中国的艺术瑰宝,打开与世界戏剧对话的门?我们可以像西方当代诸多导演那样,大胆挑战经典剧作的“作者”权威,通过对文本的拆解与重构,让创作主体勇敢地从大师身后走向身前,让经典说创作者主体自己的话吗?由此,我惊喜地注意到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作为个体,在经典文本与当下对接的一些探索。
2016年9月首演于英国伦敦圣保罗教堂的《邯郸梦》(由柯军和英方导演利昂·鲁宾联合执导),是作为导演和中方主演的柯军借助昆曲这门中国最古老戏曲艺术的一次世界发声。该剧由中国的昆曲演员和英国的戏剧演员,采用中英文双语的方式联袂出演。柯军选取了汤显祖的《邯郸梦》中【入梦】【勒功】【法场】【生寤】四个片段为主体,并将莎士比亚经典名著,如《麦克白》《李尔王》《雅典的泰门》《辛白林》等片段适时恰当地出现在卢生的“邯郸梦”中,或交错进行,或同台相望,或彼此交集,或重叠复合。这是一场奇妙的剧场体验,同处一个场域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从隔膜中迅速打通,透过对自己本国经典片段的熟知,观照了“他者”的深意。于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渴求、欲望的发酵,宦海的沉浮,以及将死之人对权力的态度,这些人类共通情感的生命体验,借助不同戏剧载体、不同戏剧语言、不同戏剧美学的方式相互映照,最终形成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戏曲的剧场样式。
这里有拼贴。在西方后戏剧剧场艺术中,拼贴并不罕见,但把这种方法用在戏曲创作中却不多见。柯军“汤莎会”的《邯郸梦》不仅有迥异戏剧形式和风格的拼贴,也有戏曲与西洋音乐的拼贴,甚至还有中英文两种语言的拼贴。该剧幕前曲由英国小提琴家查理·西姆演奏小提琴曲,由中国作曲家孙建安将《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只乐曲变奏杂糅,无缝对接,在婉转悠扬的旋律中两国演员相继登场。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首先在音乐中相和,形成对话,预示了接下来一生与权力纠缠的卢生和400年前莎士比亚笔下的各色权倾一时人物的邂逅。“汤莎会”《邯郸梦》中拼贴观念贯穿始终,“片断化”“互异性”的后现代美学观念支撑全剧。当穷困潦倒、对权力功名怀有极大渴望的卢生借来一枕“入梦”,踏梦而来的却是《麦克白》中三个有预言能力的女巫吟诵着莎士比亚著名的《Double Trouble》,实际上也是预示了权力这朵“恶之花”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是对贫穷还是富贵,都令人迷醉。而当卢生在崔氏的金钱开路下,荣登金科状元,并被封为御史中丞,兼领河西陇右四到节度使,挂印征西大将军时,一段麦克白夫人怂恿麦克白弑君场面出现。和卢生在妻子崔氏的帮助下获得权力一样,麦克白对权力的攫取正是通过夫人的蛊惑、诱导和帮助获得的。这样的异质同构无处不在。卢生征战沙场却被人陷害,从而遭遇云阳法场之祸,刽子手为他摆下囚筵,而此时出现在舞台上的则是《雅典的泰门》“设宴”中最经典的台词,从泰门口中说出:“瞧这过眼的浮华,她们跳舞,她们像疯婆子,人生的荣华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胡闹,我怕现在在我们面前跳舞的人有一天将要把我放在他们的脚下践踏。”于是泰门的白水宴席登场。顿时,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利害与残酷被恰当地表达了出来。而那一盆泼在宾客身上的水,也冷冷地浇在了卢生心头。
拼贴不是无端的堆砌,拼贴是在经典文本拆解之后的重构,经典在这里仅是创作者的材料,通过打破、颠覆、重建,凸显创作者主体的当代意图。从这一点看,柯军和利昂导演的这版跨文本的《邯郸梦》是与西方当代剧场艺术观念相通的。正如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曾言:“每一种文化表现的是内在图谱的一个不同的部分,完整的人类的真实状态是统一的,而戏剧就是能够把这块巨大的拼图集合为一体的地方。”
《邯郸梦》在观念上区别于传统戏曲之处还表现于,将“在场性”作为戏剧的重要样式,所谓“正在演”与“正在看”。舞台的样式是一个类似中国三面观舞台的空间,乐队位于舞台正后方,两个改良后的大红“守旧”和蓝色氍毹构成一个场域。开场,主演柯军穿着水衣从观众席登台,像一个局外人进入,在乐曲声中邀请英方主演从下场门上场,二人当众点亮舞台前的两只蜡烛。烛火熹微,烛火也晃动,这烛火仿佛是400年前的两束光,也仿佛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灵魂借着400年前的烛火照耀今人。烛火在此是有意义的,点亮、启蒙、相互映射、流芳千古。接着,两位主演下场装扮,中英两国其他演员悉数登场面对面坐在舞台左右的两侧,在接下来的演出中他们既是演出者,也是观看者,同时也是检场人。而在结尾处,当卢生“邯郸梦”醒,甘愿被度脱之后,卢生将自己的衣冠脱下,留在舞台,此时卢生又变回了演员柯军,他缓步走进观众席,英方三位演员上场将卢生的衣冠捧起,东西方戏剧的交会在此画上圆满的句号。
戏剧样式突出“正在演”和“正在看”是对“剧场是独立的”这一现代戏剧观念的确认。而“正在演”这一属性在戏曲中并不稀奇,因为对于戏曲而言,假定与虚拟是其最大特性,有时戏曲表演的形式也是表演的内容。但在西方传统的幻觉主义舞台观念下,内容即文本,内容即生活,所以,“正在演”常常是隐藏的。不过,莎士比亚,这个曾被伏尔泰称为“喝醉酒的野蛮人”,却是与中国戏曲“扮演”的观念灵犀相通的。在2016年9月的英国伦敦圣保罗教堂中,柯军和利昂导演的《邯郸梦》让中国和莎士比亚的舞台“扮演”的观念彼此碰撞。除此之外,“正在看”也是该剧有意识强调的。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前主任阿诺尔德·阿隆森曾经讲过,我们现在的戏剧可以没有剧本,没有舞台,没有布景,没有灯光、没有道具,没有服装,甚至可以没有演员,那么剩下什么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呢?只有观众,只有观看这个姿态。此话听起来甚为极端,但是却可以窥视出,国外后戏剧剧场艺术中,观众至高无上的地位,“观看”被视为戏剧的本质。《邯郸梦》中每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观看的角度不同,“看”与“被看”时时共存。在卢生将死之际向高公公提醒功劳簿,希望荫袭子孙时,李尔王分封场面出现,卢生与李尔直接对话,甚至最后合为一体。他们都是父亲,他们也都是权力的传递者,但中西方权力传递的方式又是那么不同,一个是施予以求身后的荣耀,一个是施予以求现世的回报。这都是通过舞台上所有的“看”与“被看”清晰表达出的。
无论是上海昆剧团,还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抑或是柯军,都在试图尝试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探索传统戏曲与当下的关系,至于探索的方向和路径是否正确,需要时间来检验。而笔者以为,对经典的重读,本质就是如何将经典“现代化”的问题,这其中有外壳层面的,也有内涵层面的。马泰·卡林内斯库曾经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言:“真正的现代化在任何领域都是同创造性(解决现存问题的首创方式,想象、发明等)相联系的,它排除了模仿”。关于中国戏曲“现代化”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戏曲理论家张庚就曾在他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中做出过探讨,他说:“改革旧剧的工作,在目前绝不仅仅是舒舒服服地接受技术遗产,而且要改造旧剧伶人的一般的观念和对于戏剧的观念。”是的,观念,创造性的观念其实是目前国内戏曲人最为缺乏的,而笔者以为在精湛继承戏曲表演传统的前提下,观念的突破在戏曲界绝对值得珍视。
1. 安托南·阿尔托《名著可以休矣》,载自杜定宇编《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242页。
2. 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44页。
3.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见“附录:清末上海昆剧演出剧目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347页。
4. 俞平伯《燕郊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193页。
5.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54页。
6. 彼得·布鲁克《戏剧是重新拼贴的世界地图》,《戏剧》2003年第2期,总第108期。
7.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曾经有致辞人的话,表达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观念。“让我们就凭这点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大的想象力吧。就算在这团团一圈的墙壁内包围了两个强大的王国:国境和国境(一片紧连的高地),却叫惊涛骇浪(一道海峡)从中间一隔两断。发挥你们的想像力,来弥补我们的贫乏吧——一个人,把他分身为一千个,组成了一支幻想的大军。我们提到马儿,眼前就仿佛真有万马奔腾,卷起了半天尘土。……凭着那想像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挤塞在一个时辰里。”,《莎士比亚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41-242页。
8. 李亦男《后戏剧剧场》译者序,载自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ii页。
9.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371页。
10. 张庚《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载自《张庚文录》(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243页。
作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