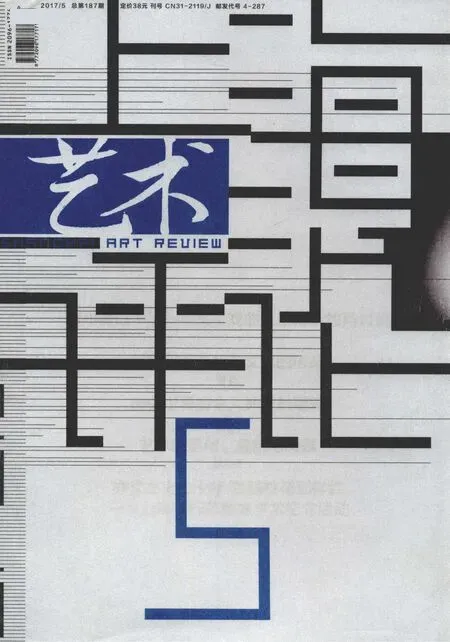寻找乌托邦:男人的故事—关于《战狼Ⅱ》的讨论
王 杰 高有鹏 周晓燕等
寻找乌托邦:男人的故事—关于《战狼Ⅱ》的讨论
王 杰 高有鹏 周晓燕等
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战狼Ⅱ》于2017年7月2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后引发热议,该片具有国际化视野,值得讨论,但我既不想从主旋律的角度去解读它,也不想简单质疑它,毕竟这两极均不是讨论理论问题的角度,我希望能把电影和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经历融合起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讨论角度。
高有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天是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来讨论《战狼Ⅱ》格外有意思。《战狼Ⅱ》通过叙述非洲撤侨的故事,表明中国在国家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之后,天下意识得到了复兴,这对现在中国国内相对狭隘和扭曲的民族主义而言,是一种文化矫正和修复,也是对中国梦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王杰:现在都在讲人类的起源,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
高有鹏:是,这就是寓意,其中的寓意就是拯救人类的天下意识,这种天下意识表现在《战狼Ⅱ》中就是“我救的不仅是中国人,是所有应该被救的人”。《战狼Ⅱ》所表现的中国人的担当具有合理的民族主义特征,不像美国的特朗普所提出来的白人至上,白人至上是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英雄神话从《战狼Ⅱ》重新出发,英雄主义的梦想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一种复制,影片与大禹治水、盘古开天等典型的神话一样具有拯救天下的情怀和浓郁的神话主义特征,可以说,《战狼Ⅱ》把超越现实和超越人的主体这样的理论问题放大到一种极致,形成一种对人的心灵的震颤作用。
王杰:《战狼Ⅱ》把“中国梦”具体化了。
高有鹏:中国梦就是中国的神话英雄主义,或者叫中国神话主义的再生,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要对这个梦想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应答,而《战狼Ⅱ》就是对中国梦的一种全新的应答,它具有一种放大中国梦的视角,把中国梦放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去表现,回归中国神话中的天下情怀,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警醒人们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平台、民族的胸怀关系密切,并促使反法西斯文学的世界格局渐渐地融合于我们的身心,启迪更多人思考“文艺如何使国民性爆发”等问题,毕竟,当代文艺作品若只谈本民族的危难和责任,就太狭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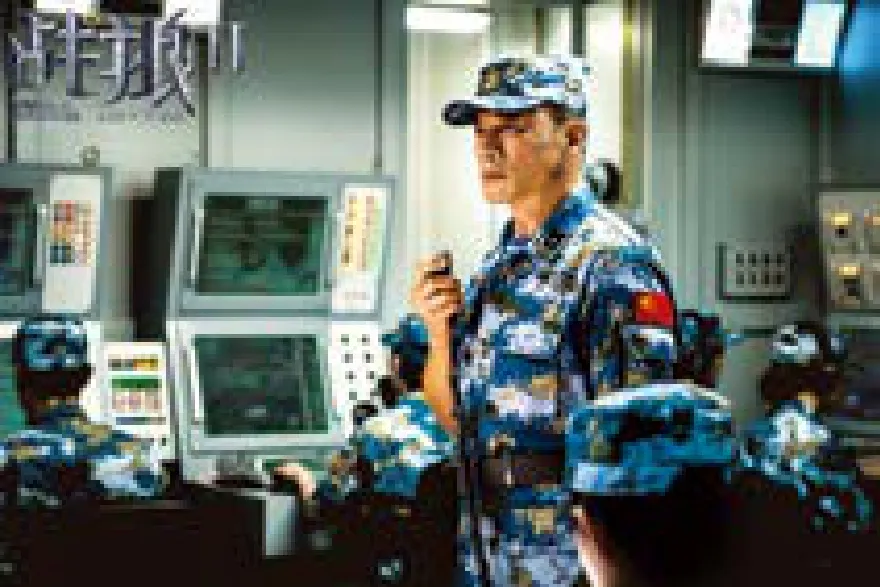
电影《战狼Ⅱ》
王杰:高老师把《战狼Ⅱ》放在全球化这个文化背景下讲,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有意思了。今年,主旋律电视剧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和主旋律电影《战狼Ⅱ》一开始均不被看好,但后来都引起热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怎么来解读?我认为,高老师从神话角度去解读,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但神话是一个大的思维,我们还得把它再具体化。我想通过《战狼Ⅱ》同《刺客聂隐娘》《血战钢锯岭》《老炮儿》等其他电影的比较来谈谈切身感受。我认为可以把《战狼Ⅱ》归入中国武侠类型片中,武侠片是中国功夫片的一种形式,而中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类型片就是功夫片。功夫片的特征就是“打”,“打”贯穿全剧。《战狼Ⅱ》主张“把对手打回去”,这跟《血战钢锯岭》《皮绳上的魂》和《刺客聂隐娘》所主导的放弃抵抗,主张非暴力主义是不同的。我认为不抵抗主义和非暴力主义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也有它的弊端,或者说有它的意识形态根源。我觉得《战狼Ⅱ》主导的“把对手打回去”的理念,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其基本理念是对现代性、二元对立、历史悖论等的辩证态度,这是一种超越了抵抗和放弃的辩证态度,有一种新的东西在里面,把中国人自甲午海战以来的郁结表达和释放出来了,触动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痛点,这也是《战狼Ⅱ》在国内票房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其实,2015年上映的《老炮儿》也是在“打回去”上触动了观众的这个点,只是《老炮儿》的格局不如《战狼Ⅱ》大;从神话学的角度讲,《老炮儿》还公开祭出乌托邦,即聚义厅,但可惜他就没有像高老师刚才讲的,它不是放在一个天下的大格局中来叙事。叙述历史既要大框架,又要放到具体的实践中间,对此,我觉得《战狼Ⅱ》是一个比较好的个案,它能够把这种大的问题,小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因为,如果光有大的问题,没有把小的问题呈现出来,电影最后可能也不会成功。
张永禄(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聚焦讨论《战狼Ⅱ》,一是为什么吴京以前的片子没有受到大家关注,而现在《战狼Ⅱ》能够成为现象级影片,这50多亿的票房是谁贡献的?第二,《战狼Ⅱ》中的民族主义问题。《战狼Ⅱ》的火爆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促成的,比如中印对峙,八一建军节军演,再加上暑假档期。据大数据观察,《战狼Ⅱ》的国内主要观众群聚集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次是重庆、成都,再者是杭州、武汉,尤以年轻女性偏多。从都市女性情感结构角度分析,我觉得《战狼Ⅱ》呼应了都市情感结构中寻找男子汉的一种情感,它切合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毕竟,这几年来银幕上小白脸形象,文弱形象太多了,而吴京是学武术出身,后来又去中国特警队训练了两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真打,而且玩枪动作很到位。另外,《战狼Ⅱ》尽可能贴近现代都市女性的情感需求,比如为了寻找爱情去冒险,很生活化,到了叙利亚遇到朋友受难,他讲究江湖义气拔刀相助,所有的切入点和老百姓的日常情感很切合,再后来,又因为他朋友的妈妈在工厂里面,他既救了朋友的母亲,同时也完成国家任务,把民间情感和国家正义情感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家国同构,达到了高老师说的天下情感的高度,展现了国际主义情怀,大格局地表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担当。
王杰:就阳刚形象塑造而言,我认为跟《战狼Ⅱ》对抗的是满屏“小鲜肉”的《建军大业》,这两部片子都是八一前放的,原来大家看好的是《建军大业》。
高有鹏:阳刚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一脉相承,比如《北方的河》《黑骏马》《平凡的世界》里都有,所以我认为《战狼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自然衔接,它把因急于建设意识形态的新话语而断裂的文化又衔接了起来,把100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被压迫,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的情感释放了出来。
王杰:中国功夫片中的男主角总体上还是阳刚的。其实,我觉得现代性对男性具有一定的压迫性,毕竟工具理性的要义就是服从,一级一级地服从才能保证高效,但如果一个男人完全以服从为第一,他的阳刚之气肯定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张永禄:所以,脱下了军装以后的冷锋就开始实施对抗,观众看了就解气,把受现代性规则压抑的这种无意识的情绪通过观影释放出来,另外,《战狼Ⅱ》是把热兵器和冷兵器结合得很好的一部动作片。
王杰:之前的很多中国武侠片是往前追述的,好像觉得古人就能超越现实,包括候孝杰的电影《刺客聂隐娘》用的唐传奇题材,其实要回到过去是回不去的,可是,吴京他转过身来了,他搞的是最先进的技术。不过,我觉得《战狼Ⅱ》中有一个冷兵器,就是毒箭,一旦射中立马就死,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夸张,有这么毒吗?可能也需要这种设计,不然过渡不了这个环节,同时,也印证了神话是奇迹,有奇迹才有神话。
王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编辑):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中国强大了,人民因为国家的强大而得到了实惠,从这方面讲,电影是正能量的,接触到了我们内心想看到的东西。我希望拍第三部的时候,感情戏上面可以更细腻一点。第二,影片中换枪声,爆炸声非常密集,显得很嘈杂,虽然这样可以把情节节奏带动得很快,扣人心弦,但好的电影还是应该张弛有度,可以借助更多的音乐舒缓节奏,比如在山洞里治疗那一段的音乐《风去云不回》就很好,可惜这样的声像组合并没有贯穿全片。第三,我希望在第三部中看到主角冷锋性格的成长,他不能始终是一个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应该像三号人物,那个公子哥一样,在影片中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第四,非洲的国家形象呈现过于混乱和落后了,在这方面可以处理得更高明些,虽然这在神话领域还是可以说得通,但全片毕竟还是立足于现实,讲的主要是当代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同样的,对强拆情节的设计也存在类似为推动剧情发展而设计痕迹过于明显的情况,现实生活中挖掘机绝不会嚣张得架到军属头上的,现在的中国应该不会让英雄这样流血又流泪的事情发生的。
周晓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战狼Ⅱ》的成功是题材的成功,并非艺术形式的成功,也就是说,影片止步于激发观众单纯、原始和自然的爱国情感,太多打打杀杀场景和大喊大叫的声音,这种过于直露的情感是非理性的,有较为明显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并不是高级的艺术作品所需要的审美情感。不过,从声像组合的艺术性角度而言,《战狼Ⅱ》中,吴京亲自演唱的电影推广主题曲《风去云不回》舒缓细腻,缓解和冲淡了由题材所激发起的观众的兴奋激情,观众的紧张情绪在简单、空灵、舒缓的吉他旋律,以及冷锋和龙小云的亲密爱情的幻象中得到缓解,这种声与像的艺术加工形式,有些类似托尔斯泰所推崇的“像写鲜花那样去写死刑”的形式创作手法,引导观众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单调的自然情感的“既紧张又平静”的混合情感,使大面积蔓延的、没有节奏感的自然情感得到了短暂的控制、回旋和缓解,产生了审美情感和艺术性;只可惜,影片中类似这样的声像蒙太奇并不多,客观上削弱了电影的艺术性。
高有鹏:作为一个神话主义的实验,《战狼Ⅱ》满足了大家的大国情怀和天下意识,自有它成功的地方,但在民族主义表达方面,自觉不自觉的流露了某种极端化情绪。比如说工厂主对中国工人的态度,以及他马上纠正说这个非洲孩子也是我们要保护的,有意识地把它纳入正义,但又掩盖不了中国人至上的思想,一开始就进入了民族主义的悖论之中,可如何克服的,电影无能为力,所以又加上了另一个情节,让一个非洲的孩子来当一个符号,去稀释这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当然,民族主义还是需要的,因为情感利益所在,只是利益是有条件的,需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寻找英雄或者男子汉是人类文明对自我超越的一种神话主义表达,这种“寻找”在每个时期都会出现,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战狼Ⅱ》向我们提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警惕自我膨胀,对民族主义可能产生的负面因素,不能放松警惕,毕竟民族主义带有爆发性和非理性因素,我们不能仅仅从民族利益出发和从情感利益出发而把它给绝对化。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战狼Ⅲ》如果不进行很好的文化修复的话,很难再成功,毕竟它与电影《007》系列不一样,《007》走的是人的个案路线,是人的犯罪,而生活中人的挫折和犯罪以及情感缺失等一直在发生。总之,《战狼Ⅱ》可以看做一种从简单的审美到高度的审美精神文化的的美学过渡,也许,真正显示大国情怀的,很可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生活中朴素的情感和事件,这也是《战狼3》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电影《战狼Ⅱ》
王杰:是的,谍报人员和特种兵还是有区别的,对特种兵而言,只有打才有戏,一旦纯比拼智慧的时候,特种兵就用不上了,所以,相对而言,《战狼》的空间还是小一点。而《007》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断地换人,所以我觉得《战狼Ⅱ》应该是公司的品牌,而不是吴京的品牌,如果变成吴京的品牌,空间就太小了。
张永禄:所以它在美国的票房就不高,基本是国内观众作出票房贡献。好莱坞电影的成功首先是编剧的成功,好莱坞每年大概花50亿美元去全球购买故事,把这些故事进行组合,然后再竞选商品思路,所以,一部片子从编剧到制作都是很长时间的。
王杰:好莱坞的类型片理论已经很成熟了,吴京也是按照这个来做的。但无论如何,《战狼Ⅱ》还是提出了一些值得中国文艺理论和创作领域去共同思考的一些问题。
石甜(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博士生):神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你要相信它,才能实现它,即神话有灵,信则灵。我在国外听到有一些国外的评论说中国参与了对非洲的新的掠夺,这部片子给出的回答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所以那个小孩管吴京叫干爹,这个也可以看作一种话语的转换。因为在英语和法语当中干爹通常是教父的形象。
胡漫(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我主要从批评的有效性这个方面谈谈,我之前认为豆瓣还是比较客观的,从这部片子发现也不是这样,受资本的冲击,豆瓣并未能够远离资本的运作,不过,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豆瓣有几个非常棒的影评家对这部电影不置一词,其实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只不过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读,这又使我在大数据下谈批评有效性的时候,又有一点信心了。还有一个我想谈的是主旋律艺术,“文革”时期,全民推崇主旋律文艺,“文革”过后,作品的艺术性占据了最高点,主旋律作品不仅少有市场价值,评论界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一直到了几年之前,情况还仍然是这个样子。而这几年,中国的民族情绪高涨,当然,民族主义现在在世界大范围内都是一个新的高潮,不仅在中国。我觉得,应该是开始反思民族性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的民族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反思的精神,或者说只是被这种世界民族主义大潮流裹挟下去的话,将会很危险。
王杰:民族主义问题是这个片子的关键问题,2008年我在英国跟伊格尔顿讨论过相关问题。西方有一个基本的公式,就是民族主义加极权必然走向纳粹,可以说,中国从现代化开始以来,民族主义就存在着,毛泽东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此我关注这个问题。伊格尔顿说民族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对和错的东西,有好的民族主义,也有不好的民族主义,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很新颖的。我认为我们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去分析,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中来判断它好和不好,总之,对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不能简单化、公式化。
张永禄:民族主义不要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国家每次在遇到重大问题,都是在用民族主义建构民族心灵和社会情怀。
唐功林(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生):我觉得暴力、血腥元素在这部电影里面展示得有点过度,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也太生硬了,镜头语言给我一定的压迫感。
王杰:对,整个现代化过程必然有民族主义,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可以称为人类学笔记,也可以称为民族学笔记。中国人既要走西方现代化的东西,又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是很难的,但很重要。我现在最期待的是中国出现双赢作品,既是类型片,又有很好的艺术性,西方已经有这样的片子的,也得过金狮奖和金棕榈奖。现在,中国的电影还是作坊式的,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产业。不过,就《战狼Ⅱ》而言,成龙的视野就不如吴京好;一部电影的热映,除了它符合这个时期的情感需要,还有它的整个氛围,如果内因、外因正好处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典型。在我看来,侯孝贤他也想这样,他拍了十四年,拍出来的时候适逢台湾大选,虽然台湾大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但没有世界性。而且他的拍摄方式很多中国人不习惯,看不懂,觉得他搞得太先锋了。可以说,侯孝贤他就完全不用类型片的理论,他全部用先锋派的理论。
尹庆红(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战狼Ⅱ》是一部学习好莱坞制作的成功的类型片,从讲故事这个方面来说,它应该是国内功夫片中讲得最好的一个,它一环紧扣一环,观众看得很过瘾。不过,这部电影依旧没有办法在国外获得票房,这肯定就有问题了。我的观点就是在“怎么传递价值观”上出了问题,影片传递的家国同构,大国荣耀的价值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让别人看了不是很舒服,不是很愿意接受,或者说它的情感表现的逻辑还是黄飞鸿那样一个路线,即中国现在也强大了,原来被人家打,现在我强大了,我打人家了,即还没有超越这个情感逻辑。从人类学的角度上看,这是表征跟被表征的问题。另外,影片把非洲进行了某种想象化处理,又是病毒流行,又是反政府军暴动,非洲人不会认可这样的表现,也不能被更广泛的接受,让人看了不舒服。
王杰:电影如果要在中国成为真正的城市文化工业,它一定要有理论,光靠摸索只能偶尔出一个这样的作品,所以,中国电影的路还很长。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电影生产方式的如何结合就是一个理论问题,主旋律作品如果只拍领袖人物,那就容易把自己限制住,比如毛泽东的形象和故事几乎就没有可能纳入到功夫片的生产方式中去,所以,西方电影理论认为类型片一定要用边缘人形象,因为边缘所以才最有活力。总之,中国神话和中国文化的类型化表达,或者说产业化表征是电影《战狼Ⅱ》触及的理论问题,也许这是我们的理论可以开始的地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阶段性成果。
文字整理:周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