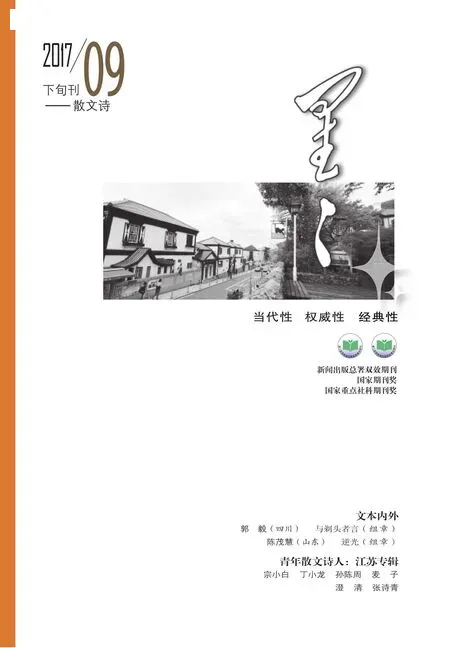与剃头者言(组章)
郭 毅(四川)
文本内外

与剃头者言(组章)
郭 毅(四川)
太阳终于升起
太阳终于升起,我知道,雨雾连绵的冬天已经过去,那些被霾环绕的山谷,一切都是新的。
出彩的鸟翅,横跨的每一匹山、每一条河,让树枝、草丛在春天萌芽。在萌芽里听见悉悉索索的事物,在花谷里打鼓、上升。
流水经过的土地,闪耀着绿卉,与蓝天的白云映出的腰腿和胳膊,引发许多爱情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总会走出封闭的房门,领着各自的爱人,或坐在小河边听鱼群奏出产仔的序曲;或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的鹰追逐着鸟,不留一点悲伤的痕迹……
旁边的狗嗅到叫春的气味,拖着厚厚的皮毛,就要跃出领地,摇着尾巴向异性发出求偶的欢鸣。
而我们如何用力,也只有享受时光,消磨阳光拔出的笑意,拂动鬓角的白发,抬高额头散去眼角的皱纹。
现在,世界终于温暖起来,上帝赐予的每个花园,没有死,只有生在花朵里静静开放。
被灵魂提升的万物,不再那么荒凉,不再在风雨中抖动身体,只有出巢的蜂蝶扇着彩翅,飞过动物寻觅的大地,采着蜜长久地占据着位置。
它们集体咀嚼着香甜的阳光,美妙地舔着嘴唇,与我们消磨的混沌时间,约略是由死向生的一次宽恕和赎罪。
与剃头者言
我不只一次在他的刀锋下缓过神来。在这尘世,他这把修边幅的刀子,今天重诵于卷落的风,又让我整齐于世,有了体面的自我。
颅周无序的发丝,示我以邋遢、虚无,无忌于世上的所有。但我仍空,仍混沌于时间的锯齿间。
我已彻底隐退,魔咒齐鸣的人间,君临的世俗之野,飘起我端公的诵咏。
流落的匠人在街头,不避白眼会召的世间诸物,比起美发店的仙童仙女,实属唏嘘许多。
他的刀子随心所欲,在颅上一一清理,一如号令请走多余之物,纷飞于风中。
一切尚不足以染色的稀发,不再识我。纵然我面目如故,他也在我军旅的路途轻挥着刃,视我无睹。
现在,我安居在川中资阳一角,头顶毡帽,穿过闹市,被人尊为老者。
但作为男人,秃顶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与其颅周绕行的丝须旁骛于世,不如请他让刀锋一一清除。
这样,卓立人前,也方便许多。纵然爱情与我无缘,事业尚不与肉身匹配,但我享有的确是他把我剃成赞歌。
上升的阳光
多么欢畅,神变的天地簇拥其中,一会儿蘸满金芒。
小溪与大河,一件件退隐的阴翳,无须许可,裸身出哗然,挥舞着红练,嬉戏枝头醒悟的鸟。
当光明掏出刀子向黑暗捅上几刀,世界就这么明亮,就撑开华盖摇曳人间的辉煌。
那些经过的爬虫,从地底钻研的虚无,覆在面上,终于温暖了。
它们尚不如低垂的雾,在河畔低矮的身躯,向着金芒飘飞的姿式,如此轻挥的方向。
但也跳动着舞步,蜕变成精灵,迎头赶上了徐来的光。
我曾在不同的山岗,等待万物开放。先知于我的鸟,萌芽在琴声里,告诉一个个春天,用歌唱指引了无穷的远方。
它们一遍遍飞翔,从不把我当成金芒。只在近处、远处扯起琴弦,展开翅膀,让我看到尘世的希望。
它们最高的欢愉,就在神学的天地间,披着袈裟,超度了无以计数的消亡。
我的眼睛
日落之前,我眼里经过的事物移来暮色,一边拽紧坡上徐徐滑降的霞光,一边回头打望尘世缓缓向着星辉渐明的夜空,猜疑那黑暗深处的奇迹。
那一刻,晚归的人低头赶路。我看见他面色凝重,一步步扑进暮色,匆匆忙忙,风声灌满双耳。
他身后的丘陵、远山、沃野、流水……覆满的七情六欲,感知到他的一生奔往的方向:空虚开阔,愈来愈暗,愈加环绕了他的努力和瘦削。
我相信他的世界充满神秘。因为我所见如此,又不去追想,他必将与星辉变得瑰丽无匹。
随后涌来的暮色,也必将在他的周围丈量着银光,与他计算好剩余的路程。
我也将如他,在夜色中紧赶慢赶回到家门,卸下日积月累的重负,轻松地在梦边听久已习惯的鼾声。
那些供我欣赏的诗书,留下来饮食,只不过在我表示赞同的余味里加重了悬念。
我知道我没有哲学,信仰也不够坚定,但我有感觉:时间会掩埋好一切。包括爱、恨……都会在返乡路上,收好脚迹,在睡去的那一刻,睁着眼睛享受到一种难得的宁静。
只是我看透了,而他还在路上携着春天的花朵,并不知深秋的清霜,正一寸一寸浸进他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