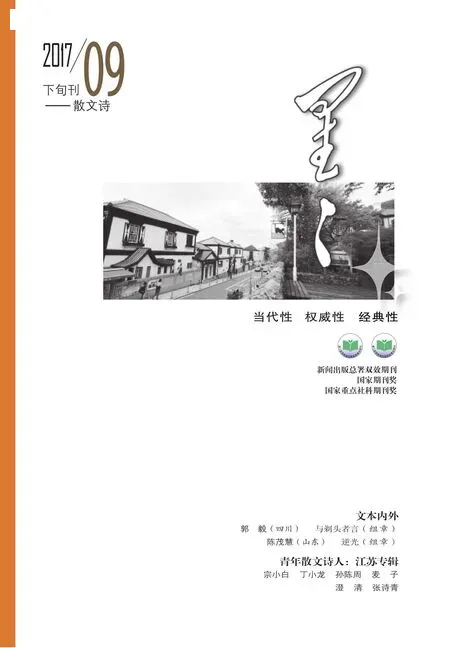秋风吹过禾黍之地(外二章)
张诗青
秋风吹过禾黍之地(外二章)
张诗青
半山腰那片凹凸的田地,长着稀稀疏疏的禾黍。
一条许久未踏的山路,尽管多生了些杂草,但并没有使我感到陌生。
眼下,秋风吹过禾黍之地,岁月依旧。
一群斑鸠和麻雀,时常会飞下来啄食;偶然,也遇到一只觅食的老鼠,但它不是田鼠。
几年前,这里还是我魂牵梦绕的家。
那时庭院很大,除了住人的几间红瓦房,还有做饭的平房,有大门过道,有羊圈,有鸡窝,有狗窝。
唯独没有鸭窝,只因它不怕下雨。
南墙边还有两株葡萄树,等不到秋风来,等不到它变紫,往往就被我摘下来塞进了嘴里。
那种酸甜的味道,略微夹杂着几丝苦涩。
在炎热的夏天,有时院子里会堆满劈柴,那是祖父熬丹参药用的。他用泥巴石块支起一口大铁锅,里面盛着水,水里满是丹参、天麻等草药的根茎。
祖父说熬药也是一门学问。要先用大火煮沸,再用小火慢熬,待到汤药收汁后,捞出药草。再添加白红糖,蜂蜜等佐料。最后,将熬好的药汁用陶罐密封起来,随饮随取。
而今熬药的秘方,随着祖父的离去,也随之失传了。
长着禾黍的贫瘠之地,日渐荒凉。除了在土壤里,尚能见到零散的瓦砾和砖头。
这片土地更换了新的主人。
光阴会在藤架上开花
我相信光阴会在藤架上开花,也会在风中结出果实。
虽然,村外的老井近乎颓废,周围杂草丛生,清晨已听不到一丝喧闹。
但这又有何妨呢?
每天,它依然对着那太阳,那月亮,那大地深处,泉涌不息。
只是聆听的耳朵,离得太过遥远。
这些年,村里的牛少了,羊少了,猪少了,年轻人少了。
相反,荒地多了,老房子多了,空房子多了,老人多了但又急速少了。
不多不少的,是门前的十万大山,青松翠柏,细水长流。
有时,人难免会背井离乡,但植物不会背叛自己。
躯体生于斯死于斯,灵魂生于斯死于斯;斯地是漂泊者永恒的心痛。
我明白,在雪中刨食,坚守冬天的,是麻雀和斑鸠。
而果实是最后的孤独。
酒,不会再唤醒村庄
月光照亮的旷野,没有了紧迫和敌意。
分行的庄稼长势喜人,刺向苍穹的枣枝,才缀满一串又一串的青涩。
野兔们、山鸡们、獾们,甚至黄鼠狼,有资格陷入狂欢。
因为,这片枣园的主人,已不复归来。
是的,他走了。那天带着他的酒。
所有的绳子、套索、夹子,终归角落,却又如释重负。
它们不必为他卖命,但也从此永遁黑暗。
就像解甲归田的士兵,一把钢枪,被一把锄头争宠。
那些残留血腥的体味,会慢慢在雨水中净身,在雪地里得到升化。
直至他的足迹,再也无迹可寻。
旷野解放了。野兔们、山鸡们、獾们,都解放了。
但枣园才开始陷入命运的荒芜。
酒,不会再唤醒村庄,和最后一个猎手。
张诗青,1987年6月生,山东蒙阴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散文诗》《参花》《星河》《知音》《天津诗人》等多种文学期刊,入选《中国散文诗2016》《2016江苏新诗年选》《2016山东诗歌年鉴》《华语诗歌双年展2015—2016》等选本。曾获徐霞客文学奖佳作奖,华语网络诗歌大赛优胜奖等多个奖项。现任《星星》APP选稿编辑,中国诗歌网江苏频道管理员,《指南针》诗歌月报主编。现居江苏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