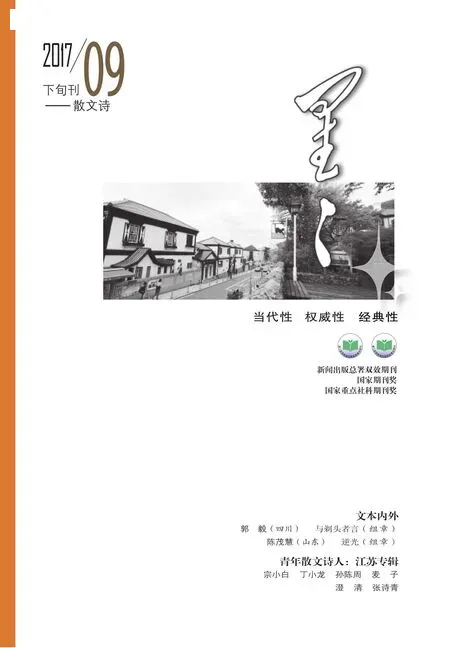山 羊(外三章)
皇 泯(湖南)
黄金时代

山 羊(外三章)
皇 泯(湖南)
将我赶出喧嚣的城市,是一根羊鞭,轻轻地抽打在身上。
将我赶上陡峭的山坡,是一首诗歌,柔柔地抽打在心上。
我是羊,被圈养在城市,许多年也钻不出栅栏,被时间一分一秒地屠宰;我不是羊,但我情愿成为一只羊,自由散漫在山坡上。
这并不是因为诗的浪漫。
如果我能成为一只羊,一只放养的山羊,我也只能吃草。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只羊,也成不了一只放养的山羊,那就让我的诗歌成为西部诗人笔下的草,一岁一枯荣,岁岁都让卑谦的羊,吃我。
有一粒心亮醒在晶露里——栖居九州驿站树屋。
这是我今晚的栖居之地,自然中衍生诗意。
在树上栖一会儿,长成一辈子的树叶。
一片树叶,有一片树叶的生存方式。
也许不需要阳光,阳光太灿烂了,会烤蔫。
也许,不需要雨水,雨水太充沛了,会沤。
在树叶上留下一个脚印,有可能成为一滴露珠。
露珠是一所纯净的房子,没有门槛,没有栅栏。
就像你的清澈眸子,看透一个人的世界。
窗外有虫鸣,拈一粒,都是湿漉漉的声音。
明晨,有一粒心亮醒在晶露里。
扶王山庄的静
无法想象——
从喧嚣沉入宁静,不能自己。
城市在城市之外陌生,山村在山村之内熟悉。
银城,大码头一腰子深的银元,再也无法在过去时的铜锈里闪烁叮当。
丽都,桃花仑鲜艳的玫瑰花,再也不会在进行时的繁华中隐藏芒刺。
一线露珠响入山泉,洗亮了视觉;一粒鸟鸣滴入叶丛,敲亮了听觉。
一首残诗,在咬文嚼字中,步入年轻的韵脚。
一条迎客的狗,吠破了扶王山庄的静。
可以预知——
从宁静陷入喧嚣,不能自拔。
山 歌
一曲土家人的歌,从远古唱到如今。
七十岁,八十岁,虽然,牙齿关不住风,也会演绎永远不掉牙齿的音乐。
音乐,原本在于乐,乐山乐水乐生活。
什么现代音乐,什么流行风,不如拉纤的号子,不如纺织的机声,当然,更想不到瞌睡的鼾声,比所有起伏的五线谱,更美妙。
我的牙齿,也在松弛中,漏风。
我的耳膜,也在蒙尘中,增厚。
土家人的歌,我唱不响亮;土家人的歌,却穿透了我的心扉。
我在七八十岁的歌声中,迈开五六十岁的脚步,回到二三十岁。
土家人的歌,不老;土家人的歌,让我年轻。
我被干涸在浅湖中
洞庭湖的鸟,在弹丸洞穿的时空里,噗哧一声——
停电的视觉一样,坠落……
再也找不到寒冬了,更找不到暖春。
四季分明的江南,仅剩几只怪得没有尾巴的麻雀,在唏嘘着一两条模糊季节的曲线。
站在干涸的浅湖中,看一尾没来得及逃走黑鱼,我知道——
我,被围困了。
无法回到生我养我的羊水;无法吮吸我曾吮吸的奶;无法呼吸我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