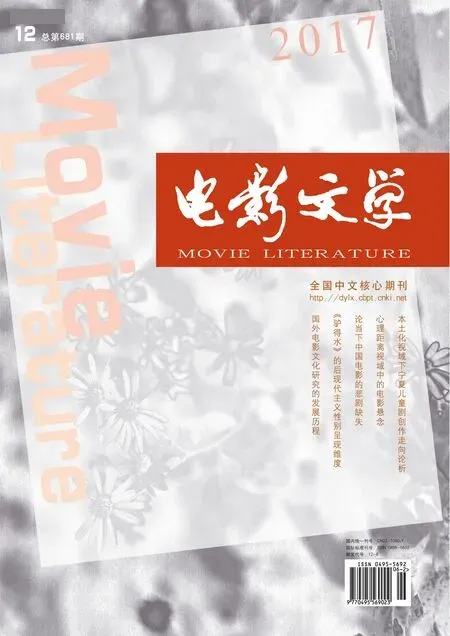《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改编的审美之维
胡 茵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1)
冯小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擅长以平视角度展现普通民众生活的导演,在表现底层人细碎生活时,冯小刚能够传递出特有的审美感知与理解,对于民众微妙的思维或情感,冯小刚善于利用各种影像技术使之外化显现,博得观众会心一笑。甚至其开创的部分以幽默包装,具有荒诞、嘲讽意味的电影已经成为属于一个时代的艺术景观。其新作《我不是潘金莲》(2016)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小说本身就有着接近冯小刚电影的特质,即在幽默、夸张的外衣之下,嘲弄着现实社会。电影在处理“上访”这一敏感题材时,在结合电影艺术特征的基础上综合种种考虑,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使电影在不违背原著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的同时,又明显地彰显着冯小刚的艺术追求,体现出一种属于“冯氏”的审美维度。
一、文本审美之维
就《我不是潘金莲》而言,电影在从小说中蝉蜕而出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审美维度首先是文本审美上的。冯小刚电影被认为“主角都是小人物,讲述寻常百姓的故事,采用冷幽默,对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光彩层面进行暴露和嘲弄,而且时效性很强,当时的新闻热点以及焦点事件都有可能从中找到踪迹”。这一点是与同样看似玩世不恭,实则直指社会阴暗面,因此有巨大艺术震撼力的刘震云原著是类似的。但电影艺术毕竟有自己的种种限制,冯小刚自己也曾表示:“我知道哪些东西是抗不过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坚持的。”电影在叙事文本上,对原著既有所沿袭,又进行了改动。
在结构上,《我不是潘金莲》的小说原著堪称是极具实验性的。小说的正文实际上只有一万字左右,而与之相对的却是占了近九成篇幅的“序”,而李雪莲实际上只是序里面的主人公。从表面上看,李雪莲类似于一条珍珠项链中的绳子,她串联起的“珍珠”才是刘震云所要重点表达的对象。而这些“珍珠”就是一群不同级别、不同面孔,但都因为李雪莲而焦头烂额的官员。真正隐藏在这个出奇庞大的序背后的主人公是拥有朝上谄媚朝下威吓嘴脸的官僚们,而他们背后则有着一种令人深思的官僚社会习气与“朝廷文化”,原本活生生的,能够与李雪莲等升斗小民进行正常交流的人,在这种“朝廷文化”中逐渐被异化了,而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在这种文化中生存着,承受着各自的无奈。可以说,没有序,正文的叙事也是成立的,但是无疑会空洞许多,有了序(实际上序更像是正文,而正文则更像是尾声),正文中的一切就具有更为强烈的讽刺性。
刘震云在小说结构上的大胆创新也就注定了电影会在改编时改动叙事的重心,换言之,电影必须将小说的“序”作为整个故事的主干。整个李雪莲告状——各级官吏如临大敌——李雪莲因为前夫之死而放弃告状试图自杀——在果园主人的劝说之下自杀失败的故事被全部保留了下来,同时,告状本身的荒诞性也被电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我不是潘金莲》与同样表现农村妇女执着“要个说法”的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1992)之间最大的区别,观众普遍会认可秋菊的执拗,而将李雪莲的行为认为是无理取闹。正是因为她诉求的荒唐,那些政府官员都明知案子没判错的情况下,依然深陷在闹剧中无法抽身,即使每个人的动机都是良好的,这才是文本想表达的情、理、法交织在一起最吊诡的地方。
而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不仅基本围绕着序来展开,并且彻底地抛弃了“正文”的内容。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看到刘震云寄寓在史为民这个人物身上的辛辣讽刺。在小说中,史为民被撤职以后开了个餐馆卖肉,有一次他急着从北京回家和老解等人打麻将,但是却买不到票,急中生智的他想到了当年不懈上访的李雪莲,于是他学着李雪莲的样子在车站广场举起一张写有“我要申冤”的纸。很快警察就将他送回了家,他的牌局基本没耽误。当警察训斥他欺骗“党和政府”时,史为民却说党和政府应该感谢麻将,因为正是麻将让本来被无故撤职、心怀怨愤的他排遣了压抑的心情。丢了县长这一官职却因麻将而放弃申冤的史为民和为了要句说法就上访20年的李雪莲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的结局也出现了一悲一喜的荒诞对应。而电影却改为史为民在李雪莲开的小饭店中与李雪莲重遇,两人感慨唏嘘了一番,两人获知彼此都在做生意,都寻找到了另外一条能让自己自在安然的人生之路。相比起原著中,李雪莲对于史为民而言只是一个符号,在电影中,两个人则达成了某种互相体谅和理解,这样一来,观众获得的便是一个更为圆满、平缓和温情的结局。相对于文学阅读而言,电影的观赏更具有集体感和“仪式性”,而以一种完整的,绝大多数人乐于看到的方式为仪式收尾,是符合电影审美特征的。
与之类似的改编还有对专职委员董宪法这个角色的删削。董宪法在小说中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将自己的仕途困顿归咎于自己太有正义感,而不懂官场上的人情往来之道。出于对电影时长(董宪法的结局与改动后的史为民之间有重合之处)的考虑,以及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电影在过审时的压力,这个人物在电影中没有出现。这也就避免了电影之中出现过多的人物,使观众的注意力尽量聚集在主干人物李雪莲身上。
二、形式审美之维
形式也承载着电影的审美诉求,甚至是电影最直观的审美维度。如前所述,在内容上,《我不是潘金莲》一方面延续了原著的大部分内容,但回避了原著中百无禁忌的叙述方式和部分直白讽刺的内容。显然,考虑到电影的强传播性,冯小刚以一种极为谨慎的方式使电影叙事相对于原著少了许多戾气。并且在形式上,冯小刚故意进行了审美创新,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对于《我不是潘金莲》,大量的讨论都围绕着冯小刚在其中运用的诸如画幅、配乐等技术来展开,这些形式审美内容在电影上映初期就不被看好,而在电影与观众见面之后,也是褒贬参半,但无论如何,它们已经成为讨论《我不是潘金莲》审美取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可以说,即使冯小刚主观上的形式实践并不是为了弱化内容的攻击性,支离批评者的目光,那么在客观上,《我不是潘金莲》的形式也丰富了电影的传播话语实践,并且促进了电影的营销宣传。
首先是电影独一无二的画幅变化。就故事的发生地而言,原著中,李雪莲的家乡在河南,然而冯小刚却将其取景地改在了江西婺源。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某种引人陶醉的诗意感,淡化或消声激烈、敏感的官民冲突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为画幅的变动服务的。冯小刚在展现李雪莲家乡这一部分故事时,采用了国内外均极为罕见的圆形画幅,承担叙事作用的圆形占银幕面积不到一半。观众仿佛拿着一个单筒望远镜,看到了一个雨雾笼罩的,排列着古色古香建筑的遥远地方。每一帧镜头都经过了有意的选取,在圆形遮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秀美的工笔山水风景画,头戴斗笠、身披透明塑料布的李雪莲也带有了某种灵动飘逸的“女侠”之感,这是与《秋菊打官司》中着意凸显的陕西地区的干燥、贫困、粗粝截然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圆形的构图也被诟病为对演员表演空间有所限制。为了在小小的圆中尽可能地交代清楚环境,冯小刚几乎没有给李雪莲细致的特写和近景,而其余一些极具表演功力的演员如赵毅等居于画幅的边缘,其面部表情尽管依然体现着人物的特征,但很容易为观众忽略,大量的细节或成为摆设,或被忍痛舍弃。
而当表现李雪莲进入北京开始上访后,画幅又变为立长方形,这是提醒观众环境的重要变化,同时立长方形也带有手机屏幕式的意味。李雪莲的上访以一种手机新闻式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她逐渐从一个家乡的“传说”接近一个市井的“传奇”或笑柄。而由圆入方的切换,还可以理解为,李雪莲已经从一个圆融的人际关系(比如她对王公道好不容易拉扯上的“大表姐”身份)社会进入了一个单纯的人情(如李雪莲找到的赵大头)已经无计可施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中。由于李雪莲来北京时正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在这一段还出现了如《新闻联播》般的有关会议的严肃的报道,这里则表示的是北京这一权力中心,庙堂社会具有某种在“话语”和规则、法度上的威严。
到了最后,李雪莲终于决定放弃告状,在北京开店自力更生时,画幅恢复了正常比例,银幕为画幅所占满。这代表的是李雪莲在心境以及命运上的豁然开朗。
除此之外,电影中暖色调和冷色调的互相切换,配乐有意使用类似戏曲中的鼓声,以表现李雪莲的“击鼓鸣冤”之路,以及她的“窦娥冤”“小白菜”等与戏曲有关的自我形象认同,都是值得玩味的,在此不赘。
三、商业审美之维
尽管《我不是潘金莲》被诟病为有内容服务于形式之嫌,但从整体上说,形式审美上的大胆创新并没有使电影付出失去叙事流畅性和紧凑性的代价,而增加了电影的传播力量。当观众看到画幅的形状从圆变方,再由方变圆时,而方也有不同的矩形,在叙事上,李雪莲与潘金莲之间的区别,则犹如方圆一般一目了然。后来随着这个形象的逐渐丰满,观众又能感受到“方”和“方”之间的区别,李雪莲已经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李雪莲”,她是观众所熟悉的身边芸芸众生中的一位。因此,电影在形式这一审美维度上的表现依然是值得肯定的。电影盈利途径与小说的不同也导致了电影有其基于传播接受模式而特有的商业审美维度。在这一维度中,电影需要在保持基本艺术品质的同时,顾及观众的消费意愿。
首先,电影改变了原著的时间跨度。在原著中,李雪莲不屈不挠地上访了整整20年,可以说上访已经成为她人生的主要内容,她也在上访之中从一个青年人变为一个老者。观众完全可以在小说中感受到李雪莲在知道前夫去世以后生活失去了支柱的绝望感。而在电影中,出于对制作成本(减少年代跨度上服化道的投入)以及对明星效应的考虑,李雪莲的上访事件被缩减为十年,上访是她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时人生的主题,而在一切结束后,依然年轻貌美的李雪莲还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一改动并不影响原著的审美诉求,同时又不违背电影的商业利益。
其次,电影借角色之口对人物行为的动机进行了更多的解释,这有助于观众更好地在两个小时中理解整个荒谬的叙事,乃至理解李雪莲本人。在原著中,刘震云并没有提及“分房子”这一动机,而这成为电影中李雪莲“假离婚”的原因,也是观众一直不认可李雪莲的原因。而在电影中,李雪莲在与史为民重逢后,才说了自己当年假离婚是为了要第二个孩子。这一层谜底的揭开又让观众对她有了更深的同情,整个故事中“官民皆冤”的内核也就被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以自己对黑色幽默的敏感灵活地驾驭着难以简单定义为悲剧或喜剧的题材,把握着大众的娱乐心理。相对于原著,冯小刚在叙事文本、影像形式以及商业传播三个审美维度上进行了改动,在完整讲述原著故事的同时,又让观众感知了每一帧画面下属于冯小刚的审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