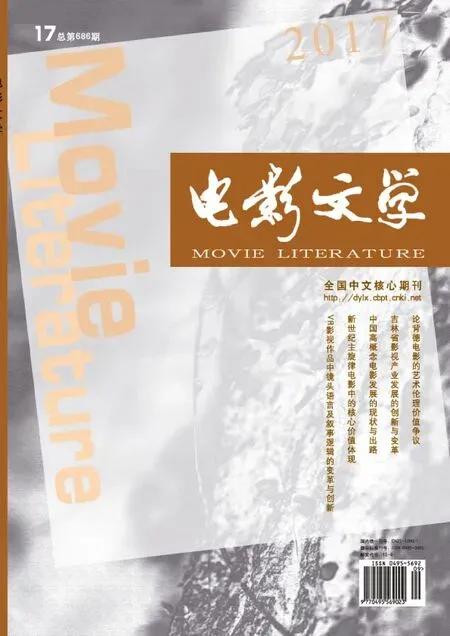《番石榴熟了》:越南本土电影身份记忆
姜 山(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一、越南本土电影的历史语境
作为东南亚地带的泛中国文化地区,越南曾先后被中、法、日、美番邦隶属或殖民统治,历经战争和动荡后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于1976年实现统一解放并对外宣布独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86年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刺激下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在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没有自己独立的电影业,而本土电影也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院线上播映的是清一色的外国引进电影。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电影方才萌芽生长,出现了新闻纪录片、抗战纪录片等类型样式。而直到1959年随着第一部故事片的问世,反映当下时代越南社会的剧情影片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也多是以抗战题材为背景或主调。随着经济改革试水的前后,一批批以现代城市生活为背景、反映现代越南社会生活现实问题的剧情片,渐次显现在越南电影的大众视野,并在新世纪末一度将越南电影(或曰越南民族的电影形象)推至世界电影舞台的一席聚光处。
《番石榴熟了》即是这样一部极具本土特色的电影,通过讲述一个平凡而又不甚普通(童年的意外跌落导致其智力停留在孩童状态)的青年男子阿华及其家族兴衰,勾连起20世纪70年代越南解放前后至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期间的社会历史变迁与人情变故。
二、家庭记忆与国族命运
影片中,男主角阿华因儿时从番石榴树上坠落碰伤头,导致其智力一直停留在孩童状态。于是在父母过世之后,已婚的妹妹阿苏承担起照顾阿华的责任,每天下班回家前来给阿华做饭、收拾屋子;而阿华则以当大学课堂的人体模特为生,独自居住在父母生前的屋子里。当主要人物依次完成登场后,影片以悬念铺陈的方式,通过围绕富人区某僻静庭院里的一棵番石榴树这一线索性事物,构成叙事张力并逐步推进剧情的展开。
打工之余的阿华,总是不厌其烦地站在庭院外面透过围墙的间隙,好奇但并无敌意地观望那棵长势繁茂的石榴树,甚至偶尔还会趁院中无人偷爬进去四处环视。一天,当阿华看见石榴树上结出了硕大的果实再次翻入其中时,不料却被户主的女儿阿兰和佣人发现,于是报警将其拘留。心急如焚的阿苏为了救出哥哥,不惜以博人同情的方式分别向警察和阿兰道出实情:原来那所庭院别墅曾是身为律师的父亲于解放前所建,在尚未无偿交予国家新政府时他们一家人一直在那里居住,而庭院那棵石榴树则是阿华小时候跟父母一起亲手栽种的;虽然被反复强调“那里已不是我们的家”,但智力残缺的阿华其记忆、情感、情结却仿佛偏执地停滞在那段时间不肯前移。
于是不无意外地,时隔不久阿华再次来到庭院,而这次庭院中的阿兰看到阿华后却毫无戒备地、亲切地主动邀请其从院门进来,并带着阿华参观、温故(进屋后的阿华“反客为主”般的熟知屋内结构,阿兰反而身随其后)洋楼里的每一处房间。当记忆犹新的阿华一间间看向久违的空间,昨日的记忆便如同幻影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四口之家的温馨、母亲做手工时的侧影、母亲病逝的沉痛哀伤、暴风雨夜窗口的小鸟以及石榴树上那次意外的坠落。
也正是在“阿华进入老屋故地重游并引发回忆”这一叙事组合段落中,导演通过精细的镜头设计与人物心理蒙太奇剪辑,完成了对阿华与阿兰第二次见面的行为互动与性格刻画。比如,院墙外的阿华与庭院内的阿兰之间相互发出的“窥视”视点对切镜头,随着阿兰的警觉与起身视察,二人间正反打镜头的镜头尺数逐渐缩短,视觉节奏张力尽显;而当鼓足勇气的阿兰透过门洞向外探视阿华时,被左右两边阴影遮幅的画面中那特写放大的、晶莹透亮且充满童稚与渴望的阿华的瞳眸,以及侧逆光照明下纯净无邪的笑容,不仅恰是打动阿兰卸下心防、生发怜悯的关键所在,同时也与片尾被从精神病院救回,却丧失记忆和笑容的阿华的木讷形象,埋设了强烈反差;再如,当二人步入屋内,摄像机跟着阿华熟练地来到二楼,阿兰反而低头跟随其后,此时光线从画面的右后侧窗户射在屋内地板,阿华走至前景光线处停步环视,阿兰则站在阿华右后方的旋梯口门旁看着阿华,一种透视的线条构图营造出一种故人归来却早已物是人非之感。而在接下来叙事的现在与过去时空的四次转换中,导演通过凝视阿华头部(手部)推焦至特写(甚至虚焦)的“局外者”的视点镜头运动完成回忆时空再现的心理蒙太奇转场。比如,第四次回忆激发时的一组对切镜头,将现在与过去的不同时空平行并置剪辑,即现在时的阿华站在二楼露台正面特写面露凝色地向下俯视石榴树上的番石榴,衔接的反打镜头是过去时的小阿华蹲在一楼庭院的石栏后正面特写俏皮好奇地向上仰视着石榴树的果实(同时也是看向二楼露台的视点方向),于是镜头间组成了一种互为视点对视的效果,建构出一种过来人看向后来人、全知者看向未知者的宿命意味;而随着小阿华坠落的回忆蒙太奇再现,触景生情、创痛重现的阿华本能地向后蜷缩、紧闭双眼,同时摄像机随着小阿华坠落的身影快速下摇,以同一运动趋势(摄像机运动、被摄主体运动皆相同)衔接至小阿华倒在白色病床上的俯拍中近景镜头,缠满绷带、昏迷不醒的痛苦表情反映了这次意外给小阿华带来的不可修复的创伤,从而完成过去时空叙事逻辑的转场。而声音方案上,导演则主要通过无人声对话的音响、音乐来完成两个叙事时态的刻画与转换。现在时态中,阿兰所处的富人区庭院内的鸟语花香、僻静舒适反衬出院墙外阿华所生活的贫民闹市嘈杂无序的市井气息;现在时与过去时的衔接处,当阿华步入故居重新站在日思夜想的童年记忆之地时,隐现的编钟敲击音响伴随渐强的电子琴弦乐,生动地营造出阿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激动心情;陷落于童年回忆的四段过去时态中,导演则依次设置了家人团聚温馨祥和的钢琴旋律、伤感的主观音乐伴随喊叫妈妈的哭泣声、风雨雷电夜晚的受惊鸟鸣叫、小阿华从石榴树意外坠落时的喊叫声,分别对应着阿华记忆深处其童年不同阶段塑造其生命印记的重要时刻的固化体验。
但是,当兴奋而意犹未尽的阿华回家后迫不及待地与阿苏分享,却遭到阿苏的呵斥和打断——除了那棵改变哥哥阿华命运的石榴树,“我早已不记得那栋房子长什么样”。这里阿苏对年少回忆敏感而过激的断然拒绝,与其说是因为时间久远而记忆忘却,不如说是其潜意识主动地拒绝和遗弃那段解放后的辛酸过往:丧母、哥哥阿华发生意外、因社会变革而家败、父亲专断地将庭院无偿“献给”国家——或须赘言的是,父辈这一所谓的“献给”行为,在回望的子辈看来,既是一种基于美好期愿却终未实现的幻灭,更是一种生存个体在强大国家机器前的被逼无奈。相较于“因祸得福”、未被时代变革同化裹挟的阿华完整地保留了那段童年(即弗洛伊德所谓创伤的“初始情境”)记忆,犹如风吹叶动的石榴树始终根深蒂固;阿苏早已通过忘却排解的方式进行创伤的自我疗愈,身心沉浸地被柴米油盐的日常经济生活/生存所侵噬吞没,无奈沦为历史潮流中的游砂走石。
历史钩沉的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消弭、世界格局的破冰重组,以美国带动的全球化商业浪潮席卷世界角落,甚至那片激扬高歌政治革命进行曲的红色热土也不可避免地滑入时代涡流。面对经济生存的终极命题,那些美好愿景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放置了对最初理想的狂热追求。
于是,影片中呈现的20世纪80年代的越南,在试水市场经济阶段贫富分化的社会景象:潮湿闷热的东南亚小城里,一边是以嘈杂、拥挤、无序、破旧的街道为表征的贫民区,一边是僻静、宽敞、安全、豪华的别墅区;一边是女模特阿娥不惜干苦力、当裸模为病母和幼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一边是富家女阿兰课外之余在有佣人的别墅庭院里惬意地乘凉、看书、吃水果。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富家女阿兰所居住的这方僻静庭院,曾经是被时代没落的阿华一家所有的。相似的家境却在不同年代遭遇不同的命运戏弄,个体永远只是被历史绑架的人质(贝托鲁奇语)。恰如那随风飘零的父亲手稿,那作为无偿捐给国家,本是父亲生前寄托对社会主义国家未来期盼的毕生心血,如今却在商业经济为先导的新时代一度如废纸般毫无价值体现(讽刺对应的是,阿华给父亲烧的“美元”纸钱,其正是经济全球化、资本意识形态主导现实的符号化象征),连同阿华一家的命运一样成为惨遭国家遗忘、亏欠的历史遗债。于是,一处有趣的情节设置是,法律事务所中排队求助的民众,正是曾经解放前后租屋被无偿收缴的子嗣后代,在经济改革的年代他们争相通过法律途径向国家索取历史遗债,而他们所要寻回的不仅是具象的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屋财产,更是形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政权那终未能兑现的承诺与理想。
三、阶级图景内的放逐与割置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以《青木瓜之味》和《三轮车夫》相继亮相戛纳、威尼斯等A级电影节一跃成名,使越南电影受到世界倾目关注的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其作品因受之于创作者的双重“他者”身份而往往在呈现上夹带有太多的“后殖民”杂质,即以一种超越式的凝视回望满足自身观念预设、只待确认的欲求所指;《番石榴熟了》导演邓一明的本土身份,已先在区别性地使其镜语下的越南图景更加贴近质朴现实的纯粹民风,以一种使命(或曰宿命)般的关注,映射出那繁杂表象下的矛盾内核,即政体改革举步维艰、社会阶层冲突加剧的历史现状,乃至不甚清晰的国族未来。于是,在本片导演邓一明的镜头思考里,无论是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政体革命还是经济改革,都只能是对社会阶级阶层的重新洗牌,而对更加内在性、本质化的民风、人性、精神状态的推进提升却少见裨益,甚至反而因滋生出的自私、冷漠、无情、趋利等人性丑恶,致使原本初始如孩童的纯真、善良、博爱、无私荡涤无存。如果说,阿华待人接物时的纯良(施舍穷人)、憨厚(帮助邻里)、无私(给阿娥钱)、孝顺(祭拜父母)是因其心性随同智力一起停留在了解放前,才得以保有孩子般纯洁无染的心,那么,把阿华当傻子使唤的大妈、故意诬陷阿华的女邻居、强行征用阿华家庭院的政府人员、送阿华进精神院的阿兰父亲等各路群像,则对比鲜明地刻画了在政治经济的动荡时代中产生的一批批从既得利益群体到中低层阶级,因人性异化而显露出的丑恶嘴脸。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被导演镜头建构起的多重“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阿华vs番石榴树、阿华vs老房子、阿兰vs阿华、美院学生vs人体模特、阿华vs阿娥、雕塑家vs阿娥、男老板vs阿娥,即是对裹挟在商业化浪潮中的越南生存现实的最好注解与揭示。比如,如果说阿华对阿娥的“窥看”,是因后者的侧脸画像勾连起了阿华对母亲记忆的柔情思念(阿华童年拾遗的记忆景片之一是母亲身着枣红色旗袍、盘起长发的侧影);那么男老板、雕塑家对阿娥青春少女胴体的“窥视”,则是市场经济规则下赤裸横行的新富阶层(男性主体)对底部阶层(女性客体)的欲望消费与再生产——或须提示但无意在这里展开的一点是,这无疑是资本主义逻辑范畴内阶级图景叙述中性别书写秩序成规的又一次生动镜像再现。
影片结尾,当从精神病院被解救回来的阿华变得面目呆滞,失去了对庭院相关的一切记忆,正如那被阿兰一家搬空遗弃的别墅庭院和那终被阿兰父亲锯倒的番石榴树;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体的改朝换代放逐的是阿华一家及其对越南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美好想象,那么,80年代试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所造就的以富商阿兰一家为表征的新富阶层,则彻底将阿华一家(阿华的纯真人性,阿苏对那个年代的唯一回忆)进行了阉割改造(给阿华打针、锯断石榴树),毁灭了曾经满腔热血理想的一代越南人对社会主义越南的美好愿景与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