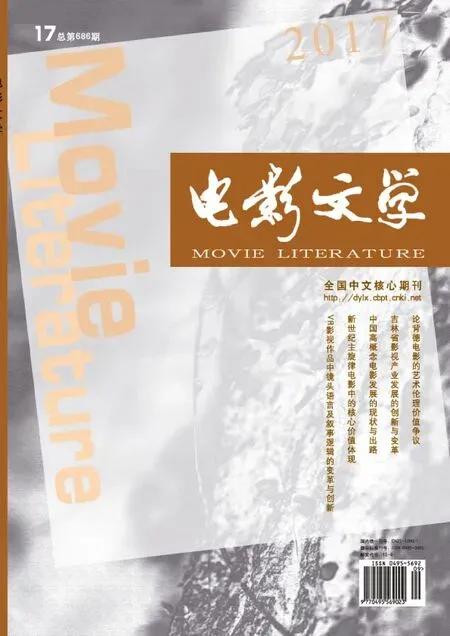论背德电影的艺术伦理价值争议
——当代英美分析艺术哲学的若干学说
侯 力(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背德电影(Immoral Films)是指那类以扭曲的或邪恶的方式表现可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电影艺术作品。由于中外普遍存在的电影审查制度或分级制度,这类电影作品通常不能进入常规电影市场为观众获取或消费,更多的是以地下、线上渠道被非法地获取。尽管如此,它们常以“十大禁片”等名引起话题并留存史册,不同世代的观众仍乐此不疲地获得并观看它们,似乎官方的“禁”恰好激起民间的“热”,这不得不说是文化分层的一种价值撕裂。
伦理道德观上的缺陷及其可能在公民道德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是背德电影被禁的名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艺术哲学界出现了“艺术—伦理”的话题转向,背德电影作为建构理论重要的经验证据被反复讨论。借此争论,艺术与道德的价值关系得到了理论化的重估。本文围绕“背德电影”的价值批评,介绍当代英美分析电影哲学关于电影艺术暨伦理价值的理论争议。
一、《意志的胜利》胜利了吗?
对于艺术的道德考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的哲学很可能推定电影艺术就其整体而言是背德的。因为,电影提供的影像并非真实本身,[1]结合“洞喻”和“仿像与实在隔了两层”等表述,热衷于制造虚像的电影很容易被柏拉图认作与美德隔了两层。当代研究者需要持有异常偏激(甚至是罔顾影史)的态度才能与柏拉图并肩作战,因为,不可能所有电影都是“恶之花”。当人们浏览电影史时,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像《十诫》(1989)、《苏菲的选择》(1982)、《辛德勒名单》(1993)等电影作品对当代人德行理解的促进是不容低估的。但是人们似乎又无法否认,电影史上存在像《索多玛120天》(1976)、《意志的胜利》(1935)等包含严重的、极端的违背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的作品。那么,电影艺术中艺术与伦理的关系究竟怎样?
康德以来,“自律论”几乎在每个世代都形成了相应的艺术思潮。在20世纪中叶,由比厄斯利、西伯利奠基,“审美自律”成为英美分析美学的主流。曾提出“艺术制度论”和“艺术圈”的美国艺术哲学家乔治·迪基,就自认为归入“价值自律论”的传统下。他认为《意志的胜利》(尤其是其剪辑版)是一部拥有杰出美学设计结构的电影,而它在艺术美上的造就与其伦理内容的可厌互不覆盖。[2]这等于说,《意志的胜利》之胜利是它在电影结构的设计上创造并运用了高出同辈的形式技巧。迪基对“审美”的理解是类似西伯利的带有形式静观意味的,他认为对审美性质的理解最好基于西伯利开列的那串审美特征清单。同时,迪基又认为艺术价值是包括了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等的复杂概念,两者均可作为艺术批评的对象,只是不相交。因此,“《意志的胜利》的胜利全在乎它总体的审美品质,而无一关涉其道德缺陷。悲哀的只是,影片确凿的道德缺陷曾为大众拥护”[2]。
比迪基稍早,安德森和迪恩曾以“温和自律论”的理论标签自居,他们将《意志的胜利》和《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等并置,意图显示这些电影的缺憾只体现在道德方面,而且这种道德缺憾不构成审美缺陷。安德森们要比迪基激进些,他们甚至认为,有些作品的“美压倒了道德缺陷”,“可以审美的名义原谅它的道德缺陷”[3],像昆汀·塔伦蒂诺的《落水狗》(1992)和《低俗小说》(1994)就鼓吹或同情杀人、性歧视等背德观念,却在美学结构上配得大称赞。他们以警句的形式说道:“作品道德之鄙并非与其美学的伟大水火不容,有时正是道德冒险、反叛和种种美学敏锐的联合令我们对作品着迷。”[3]总之,自律论者认为审美价值有自身的规律,这是道德的天秤称量不出的,无论善或恶,道德都不对审美结果有影响,甚至有时美学要以背德的方式宣示自身的这种力量。
自律论在英美分析的传统中已占优势数十年了,在制造现代艺术新图景的同时,逐渐偏离了原初的艺术价值问题,并似乎形成了新的体制性歧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看到,自律论不仅对道德论主张的理解过于浮泛,而且缺乏回应背德论的能力。同时,审美自律之下也出现了分化,丹尼尔·雅各布森甚至总结出五种范式,[4]足见其内部原则的分裂。综上,批评的省思还不允许自律论者简单地宣称《意志的胜利》胜利了。
二、道德论:美德轮盘与伦理历险
与卢梭、休谟、托尔斯泰等的传统道德论不同,当代道德论者的分析更加细致、缜密。[5]他们一方面分析了背德内容对构思作品整体的功用,另一方面为鉴别作品背德内容的真实意图提供了策略。
卡罗尔曾说,《意志的胜利》的全版(而非通常看到的剪辑版)是枯燥、冗长的,充斥着沉闷的纳粹讲演,[6]其剪辑版在形式美上的表现则要好很多。即便如此,在卡罗尔看来,形式美并不是审美设计的全部内容,审美设计还包括确保特定艺术风格所应有的反应,例如,喜剧要能逗笑观众,悲剧则须激发观众的同情。如果电影因为表现了可疑的道德观,而导致其设计无法激起想要的那种审美反应,例如,使喜剧让人无法发笑,令悲剧无法激发同情,那么道德的缺陷就造成了审美的失败。[6]借此分析,《意志的胜利》并不是简单的纪录片,影片记录的事件(1934年纳粹党代会)虽不是雷芬斯塔尔策划的,但她运用了高超的镜头语汇与剪辑技巧记录、重述了事件,其美学设计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称颂乃至神化希特勒及其政权。按照西伯利的美学,观众大可欣赏该影片的若干审美特征,影片的大多数时段构图引人入胜,剪辑编织细腻、激动人心。卡罗尔并不否认该片的形式美,甚至还亲笔描写了几个有意味的镜头和剪辑。但是当我们将雷芬斯塔尔的创作意图考虑进来时,西伯利式的静观与沉思就站不住脚了。有道德良知、熟悉纳粹罪行的观众,会警醒希特勒的讲演是谎话连篇的、宣扬仇恨的,影片展现的“领袖”威权是虚假的和欺诈的。尽管有优雅的镜头和剪辑,雷芬斯塔尔设计的意图却无法实现,其原因就在于影片的背德观念。情形对于道德感薄弱或缺乏二战史知识的观众或许有所不同,但是,当假设观众对影片的背德性缺乏觉察时,论者已经将影片的道德价值替换成了中性的。这种假设逃避了原初的问题,所以不构成道德论的反例。
如果卡罗尔的理论只到此为止,那么其与传统道德论无异,但是,卡罗尔的道德论不是规范式的、说教式的。他的理论冷静地接纳电影作品中的背德内容,并以“美德轮盘”理论分析了背德内容对构思电影整体的功用。电影叙事中出现的为数众多的角色,在相互的比较和对比中,形成了系统性、结构性的关系,这种对比关系又突出地体现在道德维度上。[7]卡罗尔认为“美德轮盘”如同思想实验一样,观众会在分析思考中提高伦理道德的判断力。[7]也就是说,背德内容或人物有时能在影片整体设计上起到对比、衬托和冲击的作用,而影片的整体不必为背德观背书。卡罗尔还认为,电影艺术需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它不能像纪律条例那样枯燥,也不应唠叨地说教,因为唠叨说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卑劣。况且,电影的艺术魅力部分地在于叙事的丰富与影音的沉迷,若发挥它之所长编织“美德轮盘”,观众在叙事与影音的聚焦中,自然会判断出值得取的道德态度,刺激对陈旧道德标准的反思。
电影当中从来不缺少背德的人物和情境,但背德部分未必能够代替影片整体表达伦理诉求,为此,道德论开始更加细微地分析、阐释影片中的背德人物与背德片段。同为道德论代表的贝里斯·高特所提出的“伦理历险”和“诱惑策略”就有助于分析背德内容、领会影片真正的道德观。他认为影片可能描绘背德观念在具体情景中对人物的引诱,或想象出某种复杂的伦理情景让人物去历险,这时影片会形成表层与深意两种伦理态度。影片在表层上或许赞同了不当的道德态度,而在深意上影片所发出的却是反意的邀请。[8]191-192高特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48)作为“诱惑策略”的例证,指出它叙述了少女丽萨盲目冲动的浪漫爱情故事,并认为丽萨早年的狂热与幻想是种扭曲的爱情观,电影叙事的悲剧处理不像是意在引诱观众去仿效丽萨,而是暗示地劝诫观众不要重蹈覆辙[8]192-193。高特还分析了小说《破坏者》的背德表述策略,其实,类似题材的少年黑帮犯罪电影也有一些,如《伊甸湖》(2008)。影片中,乖戾少年布莱特对其玩伴实施黑帮式管教,他们挑衅游客夫妇并因冲突将其中的丈夫虐杀,妻子在谋求自保的过程中则杀掉了少年库珀,她逃往小镇后却发现自己陷入复仇的循环中。表层上,影片中接踵而至的谋杀为杀人行为赋予了某种“理由”,但影片却不是在为任何谋杀行为开脱,因为在叙事结尾处观众明白,滋事少年布莱特(混乱的源头)被酗酒父亲长期忽视并粗暴对待,这是其恶劣人格的成因。因此在深意上,影片的叙事意在将少年犯的背德行为与其恶劣的成长环境连起来,意在谴责严重失责的父母。如果观众只因女主角没能彻底“反杀”而愤怒,那么他们似乎领会错了这部影片传达的意思,并且使这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沦为背德电影之一员。
以上不难看出,道德论对电影的背德成分做了深入的辨析,避免了以往常见的简单说教。此外,分析的道德论将研究对象收缩为叙事影片,既体现出在规范性上的软化,也体现出批评靶向精度的提高和内容分析的深化。对于电影伦理批评、新道德论的条分缕析有重要意义。
三、背德论:认知挑战与草莽英雄
审美自律论意图将审美与道德分离开来,将它们的关系论述为平行的、不相交的或类比性的,因此他们认为对背德电影的审美批评不应搅入道德评判;道德论则认为道德在作者意图、叙事策略、观者反应之间起到了意义承接的作用,电影作品中的道德比较、道德历练恰是观者审美的一部分。自律论与道德论的价值之争在背德电影的分析上展开,却激发一个新的理论立场,即背德论。
背德论认为艺术作品,包括电影艺术作品,可以因为表现了背德内容而在美学价值上取得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此观点的英美学者日益增多,并有一些道德论者转而持此观点。背德论较早的阐述者丹尼尔·雅各布森的研究以学理思辨为主,很少分析艺术作品案例,后期在论战中受迫才举了拉金的诗作为例证。但是其他持背德论的批评学者却热衷于以影视作品为例建构自己的理论。基兰就以对影片《人咬狗》(1992)的分析,试图例证他所谓的“认知主义背德论”。基兰认为艺术叙事与现实之间存在审美距离,这个距离让观众在观看背德电影时可以暂时放松内在的道德束缚,去体验那些挑战了人们道德惯性的观念,也因为审美距离的存在,观众并不会被背德观玷污。[9]《人咬狗》以伪纪录片的风格诱惑人们进入了一个连环杀手的生活中窥探,并使观众对他产生好感,尽管该片最后试图确立一个符合道德观的表达,但是基兰认为,该片的艺术价值恰在于它展示了人们多么容易被背德者吸引和引诱。如果把“吸引观众注意力”视为审美体验的充分条件,那么基兰或许是对的。但是这种以“审美距离”为开脱的玩世不恭似乎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审美体验不只是即时的,而注意力的沉迷并不充分地构成电影的审美,它至多是一个必需条件。再者,基兰认为,人们被电影叙事引诱而同情背德者、鼓励观众去尝试其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持有的恶劣道德观,是对观众道德伦理认知的拓展。[9]这种观点实难以让人信服。但是基兰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对的,那就是观众的确常在电影的沉迷中短暂地放弃或忘却其在现实生活中所持有的道德观,背德电影的引诱策略时常这样展开。
伊顿同样觉察到近来那些塑造背德角色的影视作品的成功。她对电视剧《黑道家族》男主角托尼的人物分析表明,影视作品“使观众感受并欲求与其深思熟虑、根深蒂固的观点或原则截然相反的观念或事物”的那种能力,将“因此原因并在此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美学上的成就”[10]。伊顿将她分析的这类人物称为“草莽英雄(Rough Hero)”,是对休谟同名概念的拓展,尽管休谟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伊顿认为,这种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是影视作品的美学成就,因为一方面它克服了观众的想象力抗性;另一方面,作品使观众自我分化、自我对抗,丰富了观众对这类人物的感受。[10]也就是说,草莽英雄身上本质的背德性正是观众倾慕他、同情他的原因,观众最开始抵抗对他的倾慕,同情他使观众自身陷入良善与罪恶的冲突中,这种负面的感受会持续很久并促使观众思考更多,比如习以为常的道德理念是否过于严苛。更进一步地,影视作品在表现这类人物上所取得的可观的成功,已经让“草莽英雄的难题”形成了一种叙事风格或电影类型,许多为观众熟知的黑帮电影、黑色电影、犯罪片等都归属于这个类型之下。伊顿似乎把握到了某种有力的论点,但是当前充盈银幕的“草莽英雄”们在角色人格上是复杂的,他们既有叙事赋予的特别身份(如黑道头目等),却很少是真正穷凶极恶的恶徒,更多的是“铁血柔肠”。而伊顿的分析无法决断,这类人物是因其背德身份而引人倾慕,还是那种民间原生的未经打磨的德行更让人向往。因此,在考虑到“草莽英雄”的人物复杂性时,伊顿的论说很难讲是“富有活力”的。
四、结 语
经过上文的概述与反思不难看出,英美学者争论的背德观与艺术价值的关系、形式美与道德恶、背德电影的社会伦理影响等问题,具有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有些看似背德的电影事实上表征了某种道德认识的转变,其表达的伦理道德观念将有助于澄清某些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见。而有些电影的道德说教不过为其审美匠心的贫乏多添了一道恼人的色彩。但是,道德内容常是电影叙事吸引观众的手段,影片中出现的背德内容或道德冲突并不总是代表其整体立场,更可能是吸引观众注意力、引发观众思考的美学设计,整体上为犯罪和背德欢呼的电影绝少会在艺术美上获得成功。英美学者对于背德电影的论说,丰富了电影伦理批评的理论话语和分析层次,有助于矫正道德说教式的伦理批评和价值虚无的形式分析,更加精准地展现电影艺术与伦理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