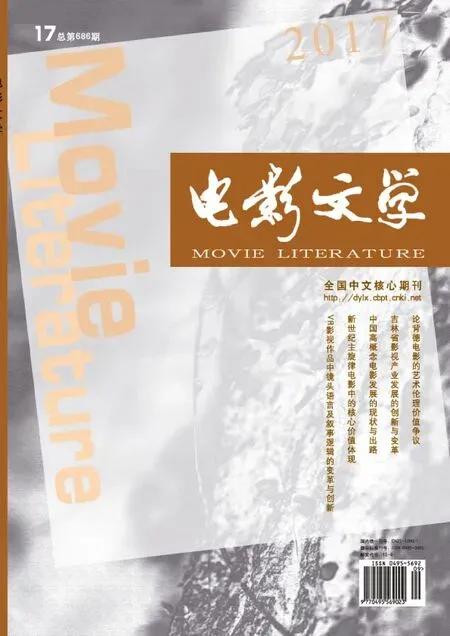侯孝贤的长镜头与“作者电影”探讨
唐晓清 喻子涵
(1.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香港 九龙 999077;2.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长镜头理论的伊始,应当追溯到二战后由安德烈·巴赞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互为表里引领的一波反蒙太奇浪潮。巴赞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中,将其推崇备至的景深镜头的进步意义概括为三点:第一,景深镜头使观众与影像的关系更贴近他们与现实的关系;第二,景深镜头要求观众更积极思考,甚至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场面调度;第三,景深镜头把意义含糊的特点重新引入影像结构之中,使影像构图包含意向的含糊性和解释的不明确性。[1]长镜头理论,其实是对巴赞景深镜头理论的一种不严密的概括,其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对观众的感知过程做出过于严格的限定,从而消解了现实的多义性和自然的流程。
尽管侯孝贤在运用长镜头拍摄手法进行电影创作很长时间以后,都还并不知道巴赞其人及其理论,但他的拍摄理念确实与之遥相呼应。如果说《海上花》时期的侯孝贤刚开始试探着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大胆的实验,那么到了《刺客聂隐娘》时,他已经放得很开,几乎可以不管不顾地坚持己见了。选择独辟蹊径来创造“侯式武侠世界”与还原五代唐朝风貌,对于长镜头的叙事张力及意境建构的能力,侯孝贤是有清楚的考量的。
一、长镜头的叙事张力
侯孝贤的电影大多与他的经历有关。唐代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的《聂隐娘》被选中,始于侯孝贤学生时代的阅读经历。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被聂隐娘吸引的原因,首先便是她的名字:“聂隐娘,聂是三个耳朵,又是隐藏,这个名字首先就很吸引我。我就想着她可能在树上,或者在屋檐上,眼睛闭着,听所有的状况,当感觉明朗了,眼睛一睁开,下来就直接刺杀。”[2]
“在树上”是侯孝贤很迷恋的一种视角,很多场合他都谈到过自己的一段少年经历,便是小时候爬上芒果树偷芒果时体验到的“在树上”的奇妙时空感:“由于非常专注,会感觉到树在摇;因为有风的关系,感觉到风,感觉到蝉声;因为是那么地专注,所以会感觉到那一刻周围是凝结的——凝结是情感的放大,电影里的时间就是这个东西造成的。”[3]25这种类似“四维视角”的俯视提供了一种隐蔽而全知的观看角度,观看者身在万丈红尘而又游离于世俗之外,高维产生的凝滞和孤寂大概便是他提到的那种“明显感觉到时间与空间,感觉到一种寂寞的心情”[4]。
钟阿城提出“刺客的成本”,这一概念深得侯孝贤认可。刺客的成本在于等待、隐藏、观察、寻找时机。聂隐娘在片中名为窈七,“隐娘”二字除了磨镜少年最后若有若无地喊过一声外,更多的是一种表现其特征状态的代号。因此侯孝贤选择就“等待”之重而避“打斗”之轻,用大量聂隐娘的主观镜头来叙述这个刺杀未遂的故事,长镜头便在模拟主观视角上发挥了最大的功效,突出表现为一种沉郁的凝视感。
隐娘奉道姑之命回到家中,与父母匆匆见过后便潜入田府中,此后影片对府中人事的表现大多借隐娘视角。如田元氏一行在园中散步,田季安与臣僚在议事厅中议事,田季安教爱子摔跤,以及经典的田季安与瑚姬坐于榻上温存时,侯孝贤都会采取将摄像机位置稍稍后移的形式,使得整个场景都在取景框内,人物也在此范围内活动,来营造一种人眼的视域。而镜框中的人物,有时也会定定地朝镜头看过来,形成一种“回看”。由此长镜头成功表现了刺客如何“等待”,虽然并非所有场景都明显可辨识,但已经清晰地暗示了这是一种远远观看的效果。
同时影片并没有放弃打戏,只是按照侯孝贤的想法,全片力求的是打戏的写实而非“精彩好看”。人物“不能飞”是一方面,打斗动作也不能过于花哨,剪辑不宜太碎。最独具匠心的是,一贯“不为”的侯孝贤在此做出了难得的“安排”:聂隐娘与精精儿(田元氏)、道姑的交手,与田季安的交手,与节度使府侍卫、黑衣人的交手,其心境与目的都有不同——高手过招,翩若惊鸿;故人相见,且打且试;世俗缠斗,速战速决。其中分寸之微妙,在镜头与剪辑上则体现为意境与节奏感:聂隐娘与田季安交手镜头变化并不频繁,一是因为二者实力悬殊,二是隐娘并非真欲取其性命;师徒交手则只有隐约的两三个镜头,非常近,突出高手过招的点到为止。隐娘与精精儿也是如此。即使打斗场面实在无法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来完成拍摄,侯孝贤仍然尽力延长每个镜头的时间,竭力保持住长镜头的能量感。
二、长镜头的意境建构
为了在《刺客聂隐娘》中还原唐代山水风俗,侯孝贤早在2007年的初期准备阶段就读了月余的《资治通鉴》,“不看那些东西,找不到底色……我把唐朝呈现出来,是透过我的主观、我的理解、对人的理解,然后去寻找,最后把它再次呈现,这个呈现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真实”[3]61-62。自锤炼剧本到开机拍摄,侯孝贤不断打磨自己对唐代生活、唐传奇文本的想象与理解,这也是后来他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所坚持的一系列原则——长镜头、无特效、多远景、用胶片、不吊威亚的底气来源。
影片的外景取景地遍及内蒙古、武当山、神农架大九湖、台湾宜兰等,每到一处,他都坚持不用特效,而是等待自然风光变换到最佳时刻,抓紧时机抢拍下来。舒淇在接受采访时称整个拍摄过程是“等风、等云、等鸟飞去”:飞机飞过,天空留下一道飞机云的痕迹,于是全组停工等待飞机云散去再开机;偶遇一树鸟儿,便想尽办法将其惊飞,为了抓拍的几秒耗上一小时。与其说侯孝贤是在尽力重建已逝的景象,不如说他在撷取从历史的指缝间遗漏下来的点滴,其创作技巧应当总结为,先在心中构建起一个概念,然后再在大千世界中寻找分有。而要将这宏伟抱负付诸实践,自然少不了他的左膀右臂,摄影李屏宾与美工黄文英可谓劳苦功高。
黄文英与侯孝贤从《好男好女》(1995)开始合作,至今已逾20年,她的加入直接影响了侯氏美学风格的升华。侯孝贤心目中的唐朝应如是:节奏舒缓,景致辽阔,鼓声若响,胡汉交融,庙堂富丽华美,江湖宁静温馨……于是影片中有大量场景,从色调、布景、构图等方面借鉴了唐画秾丽的工笔画风。如田元氏在庭院中散步,其后随行着一众举伞盖执宫扇的侍女,一路行来,见院中有动响(因隐娘与府中侍卫打斗),遥遥地定住了,往镜头方向一看,整个画面深得唐人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神韵;又如节度使府夜宴,田季安与宠妾瑚姬跳胡旋舞,素来郁郁的田季安此时才得以纵情开怀,在座臣僚也各怀心事,画面意境与五代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相似,甚至叙述手法上也略有相同,只不过顾闳中使用了连环画卷的形式记叙了韩府夜宴的经过,而侯孝贤使用的是一个个镜头罢了。
工笔之外,写意也有大量篇幅。片中外景的部分,大部分镜头是按照远景来处理,如磨镜少年清晨出门去寻隐娘,隐娘回到道姑身边辞别并说明不杀田季安的原因,隐娘与磨镜少年及采药老者一行离开唐土等,灵感源于筹备拍摄之初李屏宾为侯孝贤找来的大量傅抱石山水画。“这些画里有很多人物,但画面却很苍茫,人物只是灰蒙蒙山里的几个小点,特别大气。”[5]帧帧如画,镜头摇移只是为了配合观众赏画的视线移动,如此长镜头的使用便是水到渠成。后来的拍摄中,李屏宾也确实用长镜头复现了黄文英搭建起来的唐画意境,大僚与小儿、女眷游园的固定镜头,纸人夜袭瑚姬、隐娘辞别道姑的摇镜,隐娘与磨镜少年一前一后的远景,微微晃动的镜头与明烛篝火产生的自然光,交错之间悠扬唐韵扑屏而来。较之美工与摄像,文言台词对于影片的意境建构效果则差得太远了。
三、“作者电影”的传播力探讨
《刺客聂隐娘》属于侯孝贤更具挑战性的武侠题材。唯其美学理念太过冷寂,创作风格一味写实,曲高则易和寡。有人将观众的不接受归结于长镜头导致影片节奏太慢、留白过多造成情节不完整,实际上影片中完全静止的镜头并不多,剪辑较侯氏其他电影来说节奏已经快了很多,剧本也提前放出以补白电影。“电影作者”型导演的作品在传播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创作者的“编码”能否被受众有效地“解码”,较之商业片导演对观众口味及思维模式的熟稔,侯孝贤向来是“背对观众,开始创作”,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了解他的风格与追求,很容易找不到影片正确的切入点。《刺客聂隐娘》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何况观众的期待还是一个“再续前缘”式的爱情故事。
同样,侯孝贤电影作为蜚声国际的东方电影代表之一,其成功常常被误解为一种“东方的胜利”[6]。钟阿城写到1989年去洛杉矶观侯孝贤《悲情城市》放映,“礼服们散去得有道理,片中那样庞杂的血缘关系,简直是考美国人心算。意大利人对家族关系的理解真是一流的,《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奖有道理”[7]。语气虽戏谑,却也点明了关键的一点: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好莱坞文化影响下的西方评委与观众,对于东方电影的理解其实是较为浅层的。李安的《卧虎藏龙》(2000)深得国际赏识,与其学贯中西同时深谙好莱坞套路关系极大:他知道如何将东方文化用符合西方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同时懂得选择。东西方文化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于价值观念,这也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2011)几乎包含了所有好莱坞元素,最后仍然难获国际认可的原因。
《刺客聂隐娘》中不是没有西方元素,甚至多得令人咋舌。剧本创作初期在充实“聂隐娘”这一人物的内涵时,侯孝贤就表示希望将聂隐娘塑造成大卫·芬奇的电影《龙纹身的女孩》(2009)中的“沙兰德”那样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说话不看人,对喜爱之物偏执;同时她还具有另一原型,即《谍影重重》(2002)的主角杰森·伯恩,失忆之后一直在寻回自己的身份定位,甚至《刺客聂隐娘》一片也是暗暗在向《谍影重重》系列致敬。然而侯孝贤的功力便在于,即使《刺客聂隐娘》的故事内核是西方式的主体性确立母题,他也能够施展化归大法,将之融入浓郁的东方情调之中,不露痕迹亦毫不违和。
侯孝贤执导生涯曾多次冲击戛纳奖项,直至《刺客聂隐娘》才得如愿。戛纳予其最佳导演,影片却无所斩获,一直到亚洲电影大奖才包揽下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在内的八项大奖,可见侯孝贤在戛纳的胜利,是一种姿态与信念的胜利。
——从《刺客聂隐娘》看侯孝贤的“归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