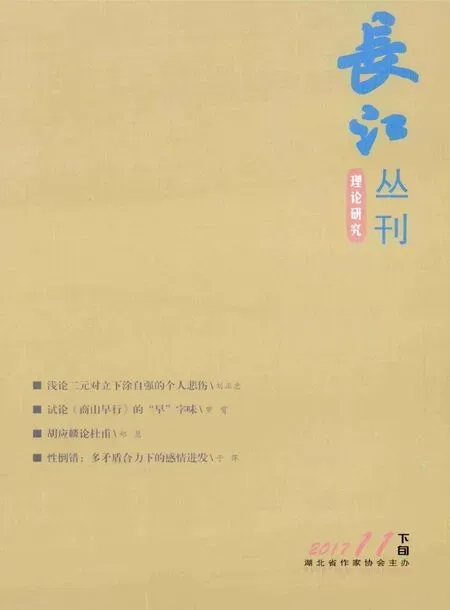“比较”以致“贯通”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比较研究
高一品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搜集、审定、整理史料,进而将各家学说梳理为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至此,即为“述学”,在此基础上,依时代顺序研究各家之间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此为“明变”,进而探究此种传授、交互、变迁的原因,即“求因”。最终以各家学说的影响效果判别其价值,即“评判”。
而本文论述主要围绕胡适在整理史料过程中“贯通”功夫所需要的以西方哲学思想作为材料对中国哲学史进行理解的方法。胡适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如果不注重对史料的校勘与考据而只注重义理的阐发和思想整体脉络的贯通则会流于空疏,流于主观臆测的臆说。而如果只注重训诂考据等,例如清代乾嘉学派,而不注重贯通的功夫,则会流于支离,缺乏对思想体系的完整性认识。可见,贯通功夫的重要作用。而此种贯通的实现则要通过超越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本身而选取、借鉴其他材料及方法进行比较才能获得关于其研究内容本身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认识。我们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内容与西方哲学的参考资料,使二者之间相互印证、相互发明才能理清研究内容的条理系统。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研究方法论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多使用西方哲学概念类比中国哲学的范畴。例如,在对老子的分析中,其以西方哲学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类比老子的“天道”,以斯宾塞的政治学说说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念;在对孔子的分析中,以苏格拉底的“概念说”类比孔子的“正名”思想以说明此正名主义是中国名学的始祖,以康德“感觉无思想是瞎的,思想无感觉是空的”一句类比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证孔子理论中学与思相互依存的关系,并补充说明,二者比较之下也存在差异,不同于康德作为直接经验的感觉,孔子的“学”是指读书,通过传授而获得的间接经验。此外,胡适在论述《论语》中关于道德的问题时,将道德分为内容与外表,而注重内容的道德又分为康德的“道德律令”与宋儒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在对墨子的分析中,胡适将墨家的“巨子”类比为欧洲中古的“教王”,以说明天志尚同的宗旨是在政治组织之上设立一个统一的“天”。在墨家的“辩”中,胡适以西方逻辑学中的“主词”说明“实”,以“表词”说明“名”,而名与实的结合即为“命题”。在说明以上基本概念后,胡适又以维恩图表示种属关系说明作为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基础的“类”的概念。在演绎法中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作为比较对象,“凡‘人’皆有死,孔子是一个‘人’,故孔子必有死。”[1]在《经上》中,“物之所以然”是“故”,凡正确的故都可以作为法,若不能发生同类的效果则只说明不是正确的“故”。可见,名学的演绎法是根据“同法的必定同类”的原则进行,将已知之故作为前提。因而,《墨辩》中的演绎法不同于亚里斯多德三段式的演绎法,其以“人”为孔子的类名,是介于“名”与“实”之间的,等同于西方逻辑学中的“中词”,其认为大前提中的意思已经包含在小前提之中,大前提的作用只是说明小前提的“人”,是介于“孔子”与“有死的”两词之间的“中词”,所以已经小前提已经可以满足要求,无需三段论的架构。通过与其他文明中的传统逻辑学的对比,胡适认为,相较于墨家名学,印度因明学改古代的五分法为三支,只剩余演绎的方法而丧失了归纳的精神,而欧洲中古的哲学缺乏创造性,只是扩充古希腊逻辑的形式,使其逐渐脱离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因此,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墨家名学兼重演绎与推理,有其自身的重要特性。
可见,胡适多以西方哲学的概念类比中国哲学思想,既使得中国哲学思想更易于理解,使得中国哲学史更具体系性,更为贯通,也使得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特色得以彰显。
实际上,此种借鉴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作为材料与中国哲学思想进行比较以彰显中国哲学思想特色的方法可归结为“以西释中”,而胡适此种开新纪元、开新风气的方法被后世所传承。
二、《新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论
劳思光同样赞同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诠释中国哲学思想史。劳思光认为,胡适在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主要注重史料的考证辨别,“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2]实际上,胡适多以西方哲学作为内容、材料以述说中国哲学史,而相较于胡适,劳思光多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述中国哲学的材料,将西方哲学的方法作为工具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其以欧洲近代发明的显微镜可观察非洲古代已产生的细菌并以此解释疾病发生的真相说明西方哲学的解析方法与逻辑论证可打破时空的界限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在论证运用西方哲学解析中国哲学史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劳思光强调,不能认为在逻辑解析方法下所发掘的思想只能出现在逻辑解析方法产生之后,显微镜发明以前细菌已存在,“思想上的显微镜”出现以前,思维规律一样存在。
因此,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以西方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等解析中国哲学史,发掘其中已存的义理,使其体系内部相贯通。例如,在论证仁、义、理三者的关系时,劳思光以逻辑数学说明在理论程序上,礼以义为其实质,义以仁为其基础,在实践程序上,理与义相连,不能分别实践。在理论程序上,“求严格之意志”、“思考之严格性”,“演算中之严格论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观念,即仁、义、礼三个概念相区分。而实践程序上,思考必依据符号而进行,“思考之严格性”需要通过“演算中之严格论果”得以显现,因而二者不可相分离,即义与礼不可分离。
此外,劳思光以形式逻辑论证孔子的“君君臣臣”并不能说明其拥护封建制度。其认为,君君臣臣只具有形式的意义,未论及“君”与“臣”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权分”的理念,如同逻辑学家说明“A是A”、“B是B”时,只表明A与B自身的同一性,而未涉及A与B的具体内容。因而,君君臣臣只是说明“权分”本身必须遵守,并未划分具体内容,不能说明其中是否存在专治,也不能说明其体现了不同阶级的存在。孔子以“君”、“臣”等词只是为构成其陈述形式,只是指不同的职分,说明不同职分应各尽其职,认为其拥护封建专治社会实为对孔子的误解。
可见,劳思光以西方哲学的逻辑解析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理清其中的义理的涵义,使其体系内部相贯通。但其认识到,思维规律的运行与人们能自觉其存在是不同的,因而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内容或以西方哲学的概念类比中国哲学的范畴都应存在一定的界限,不能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进行过度解读,将古人“现代化”。
三、“以西释中”方法论的界限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解读中国哲学史成为一种主流。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该会议讨论的核心是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参加会议的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学科上横贯中、西、马,其中包括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洪谦、郑昕、周辅成、张岱年、任继愈、汪子嵩、艾思奇、侯外庐、关锋等。实际上,此次会议展现了一种“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3]。此种哲学史研究方法会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哲学史研究只是阐述唯物主义如何战胜唯心主义的过程。其忽略了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忽视了历史上唯心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其认识论的根基,忽略了社会历史观的维度。并且当时此种风气导致了一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进行过度解读。例如,《周易》的作者已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到“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等辩证法的规律以及“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指人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包括人类为从自然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斗争,也包括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为夺取经济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同时还包括社会实践。而早在《周易》时期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是无法达到这一高度的。可见,盲目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将许多现代的思想安排在古人名下,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因此,“以西释中”的方法论需要一定的界限,才能保证古代思想内容的客观性而不流于解读者的主观臆想。
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既要学习胡适、劳思光等引进西方思想与方法解读中国传统思想,发掘其中义理,使得中国哲学史自身相贯通,也要为此种解读方法划界,将思想置于其自身所产生的时代进行理解,遵循哲学史进程中严格的历史性,最终建立一套理论的设准,统摄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特显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理论特色,表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使得“哲学在中国”发展为“中国的哲学”。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9.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
[3]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