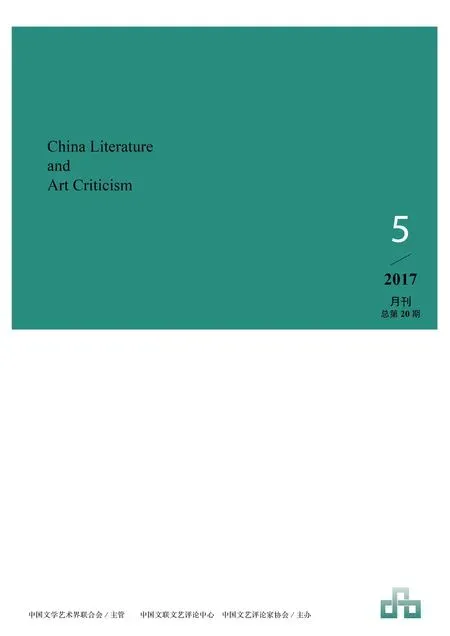不要误读戏曲文学的“地域性”
周津菁
不要误读戏曲文学的“地域性”
周津菁
编者按:真理越辩越明。发扬文艺评论的批评精神,改善文艺评论的生态,提升文艺评论的说服力,有赖于围绕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开展讨论与争鸣。从本期开始,本刊开设“学术争鸣”栏目,欢迎广大文艺评论家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本文对目前文艺理论界正在热议的“地域戏剧题材”问题作了回应,以隆学义川剧文学创作为例,讨论了戏曲文学创作与“地域性”题材之间的复杂关系。戏曲文学作品呈现效果的关键并不在于“本地域”或“彼地域”的“二元选择”,而在于特定题材对地方戏曲艺术形式的具体适应性。
隆学义 川剧 戏曲文学 地域性
在为国家艺术基金做三年总结之际,评论家傅谨提到:“从题材角度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剧团和艺术家在题材选择上愈益趋于地方化和狭隘化,似乎不选择表现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或当代英模就无法向当地政府交代,严重制约了艺术的发展空间。”。学者李红艳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她于2016年10月,在《中国文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戏剧创作地域题材应降温》的文章。两位评论家都谈到:在地方文化功利论、政绩观的影响下,舞台艺术作品在选材上日益狭隘,这严重影响了原创者艺术哲思的高度和广度,制约了戏剧艺术水平的提升。这是针对目前艺术界广泛存在的“地域题材热”现象提出的中肯之语。但是,我们在反对“地域题材”的褊狭性和功利性的时候,还应当警惕另一种声音,就是用“二元对立”的态度看待“地域题材”的问题,即走向问题的另一端,认为但凡是“地域题材”的,就都不好,就都要反对。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我认为,戏剧作品艺术水平和思想境界的高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地域”指向。首先,主创者看待题材的角度,编、导、演的水平,艺术院团的存量积淀,都会影响作品的呈现水准。而回到“地域”问题上,“地域”的,是族群的,也是世界的,世界是由一个一个人类片区组合而成,此“地域”与彼“地域”,小“地域”与大“地域”并无好坏之分。莎士比亚戏剧是英国“地域”的,日本能剧是东瀛“地域”的,布莱希特是德国“地域”的,没有“地域”文化就没有世界文化。而作品的好与坏,与它的用材并无直接联系。世界戏剧没有“通用”的题材,但有“通用”的价值:有的人用了“地域”题材,却没有做出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有的人没有用“地域”题材,却用本土艺术的形式,做出了戏剧的生命力,能拨动全人类的思想和弦,让作品具有了超越文化的魅力;还有人用了“地域”的题材,结合得天独厚的“地域”艺术形式,奉献出了能为世界文化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化营养。戏剧的好坏,在于它挖掘主题的深度,点染人物的亮度和展示情感的力度,题材只是材料,做大餐的手艺才是关键。谈到戏曲,我们似乎还应当关注地方戏曲剧种的艺术特性问题,外来的题材虽好,却不一定适合本土戏曲剧种——用本地的方言、音乐和人物形态去表达。
剧作家隆学义先生的几个作品对于讨论“地域”题材问题颇有启发。隆学义先生于2015年2月去世,他毕生创作了十余个川剧剧本,主要有《金子》《鸣凤》《白露为霜》《东坡先生》《草民宋世杰》《貂蝉之死》等。他根据曹禺原著《原野》改编创作的川剧《金子》,入选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并荣获了包括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中国戏曲学会奖在内的各类大奖34项。隆学义先生硕果累累,在现代川剧剧作家中具有代表性,而他的创作经历和成就表明,戏曲文学题材的“地域”性是一个复杂的,与多种舞台因素纵横交错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放弃”或者“死守”,就能获得最佳的舞台作品。
隆学义先生是一个改编大家,他的作品有改编自巴蜀“地域”文化之外的《金子》《白露为霜》等,也有改编自本土文学作品的《鸣凤》和以川渝“地域”人物为原型创作的《布衣张澜》等。这些本土和非本土的文化内容,无一不通过川剧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表达。隆学义毕生都在尝试写作不同“地域”题材,为了适应这些“地域”文化迥然的题材,隆学义先生进行了戏曲文学形式的创新和试验,有的戏,获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而有的戏却不一定获得了理想的呈现。
一、本土戏演本“地域”题材的得与失
从操作层面来看,川剧对表达本土风情民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川剧是四川地方音乐、舞蹈、四川语言、百姓形态动作的凝练结合体,当要表达的戏剧内容和艺术形式同源同脉时,艺术家的表达便会顺风顺水。
川剧《鸣凤》改编自四川籍作家巴金小说《家》。这出戏主要讲述鸣凤追求自由爱情而不得,被封建主义毁灭的故事。鸣凤在巴金的《家》中只是一个“戏份”极少的小人物,她的生命如同萤火虫的光亮倏忽闪烁,最终消弭在阴沉的黑暗中。隆学义的川剧《鸣凤》拮取了萤火虫的意象,奠定了这出戏的唯美基调,并将此意象由歌、舞、说白等戏曲形式加以表现。创作立意点的奇特,使这出戏并不将“铺叙故事”作为叙事重点,而将笔力用于人物情感变化与跌宕的关节点上,该剧分为五场:“情绽”“爱鸣”“惊变”“敲窗”“投湖”。每一场戏的设计,都是为了生动淋漓地呈现一位少女——心灵的成长与挣扎。这出戏中,每个人物各具风格,却在舞台呈现中都很讨喜:老太爷、陈姨太、冯乐山、李驼背、王妈……这些民国四川的老式人物,经过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很自然地贴合进川剧之中。被理论界津津乐道的,是隆学义以李驼背之口吐露的苍凉悲情又戏谑的说白:“恋爱是一种病,用结婚来医;结婚是一种病,用离婚来医;离婚是一种病,用死亡来医。”在以现代抒情诗式的唱词描绘纯洁少女形象的同时,隆学义在人物的唱词中灌注了大量四川民间俗语,并用积极修辞的方法,将说白和唱词浇筑得朗朗上口,富有古典韵律和现代诗学的交融美感。例如:“虫虫飞,虫虫飞,/虫虫虫虫飞。/哪里来?/何处归?/一闪一亮一熄,/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虫虫虫虫飞。”“一个捏金童,/一个捏玉女。/玉女身上有金童,/金童身上有玉女。”
从《鸣凤》开始,隆学义就开始尝试他的“散文化”戏剧风格。采用“散文化”的戏曲文学结构,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散文化”从总体上追求生活的本真性,不重视对“冲突”和“矛盾”的营造,而常以生活场景的展示为脉络,展示人物的性情。这种戏曲文学的构造方式,继承了传统戏曲文学线性、写意的美学特色,重抒情,而淡化戏曲的叙事功能。例如,在戏曲《东坡先生》中,隆学义直接以“雪”“风”“月”“涛”“情”“云”“迷”作为每一场的名称,这种注重“诗性”而轻于“结构”和“冲突”的戏曲文学结构方式,不太适合当下观众的接受习惯。这一点,隆学义先生也是明白的,于是他努力以四川本土文化入戏,讲四川的“言子儿”,展示四川的“民俗”,谈论四川的“热点”,以具有亲和力的地方形式内容,激发观众的热情。在这时,这些来自本土的“地域”的题材就能为他提供更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使他的川剧有看点,有特色。而在演员塑造人物时,也因为他们更加熟悉本土文化而倍显生动。川剧《鸣凤》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到川剧《布衣张澜》时,问题便不那么好办了。
川剧《布衣张澜》分为引子“布衣忧患”、第一场“布衣犟项”、第二场“布衣清泉”、第三场“布衣苦舟”、第四场“布衣情深”五个部分。隆学义先生摘取了张澜几个人生片断,以民生为重心,以布衣为象征,贯穿始终,力图展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表里如一、方正做人的高洁风范以及和百姓水乳交融的布衣精神。“布衣”是贯穿各场的主题意象,这使得该剧具有高度的象征主义特色。隆学义先生也遇到了“地域”“大”题材的诸多限制:由于是写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剧作家必须更加尊重政治、历史的真实,在追求“失实求是”的戏剧原则时,充满创造力的“臆想”和“编造”便需要更多地让位于“史实”的表达需要。为了规避“历史问题”,躲避“敏感话题”,隆学义先生设计了张澜的几个生活小故事,但如此看来,此剧充其量只能算作情景剧——缺乏大的戏剧构架。隆学义先生和此剧作曲家任礼康一起想了很多办法,以本土的文化特色,来调和结构上的不足。首先,以“布衣”的文学意象来牵引和贯穿全剧脉络,从而解决戏剧结构的“松散”。任礼康以“布衣”的文学意象作为基点,设计音乐框架,用主题曲变奏的方式,为全剧寻找舞台艺术支撑点,达到聚气的目的。这些用于变奏、发挥和呈现的音乐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四川本土的艺术存量。比如,本剧的末尾,有一段张澜夫人刘慧征的抒情唱段。曲作者使用了【香罗带】曲牌,增其抒情性。在张澜与刘慧征的对唱中,曲作者加入了清音行腔方法“哈哈腔”,增加音乐张力,表达强烈情绪。又如,主题曲在该剧中并不是一支反复出现的单一曲子,而是一个音乐结构体系,它在全剧不同段落反复呈现时,根据戏剧情景穿插和融入了本土化的音乐元素:川北号子、西充号子、川江号子、石工号子、嘉陵江号子,这使得整个音乐作品馥郁着浓重的乡土气息,这是对张澜奔波一生,却始终不忘淳朴本质的最好象征和表达,音乐裹挟着鲜活、清新而乡土化的文学意象。《布衣张澜》就是李红艳老师在《戏剧创作地域题材应降温》中谈到的典型的“地域”题材。隆学义老师在运用这个题材的时候,显然是有着难处的——舞台剧讲“名人”多有忌讳,“求是”和“事实”殊难兼顾,于是隆学义先生终而放弃了以严谨的叙事结构“重现”历史名人故事的想法,继续践行他戏曲文学的“散文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好在这是一个本土题材的作品,丰饶的地方语言和音乐文化才能顺畅地溶入川剧艺术整体,帮上“聚气”的大忙。
二、本土戏演非本“地域”题材的是与非
闻名遐迩的川剧《金子》原本是一个“外来文化”艰难适应本土剧种的“反面教材”。《金子》的成功无疑是被“逼”出来的。川剧《金子》始改编创作于1997年,初演时保存了曹禺原话剧剧名《原野》。这个从东北文化移植而来的故事,一开始便患上了川剧的不适应症。主要有以下几点不适应:一是话剧《原野》风格雄强,曹禺描绘和渲染的,是一种与大自然与动物天性相呼应的“野性”和“生命力”。这种“东北”风格与擅长表现神仙美眷,讨论人伦关系的“西南”川剧有出入。二是曹禺笔下的花金子,是一个掺杂着野性和性欲的女人,川剧的旦角在她的面前显得过于“柔软”,因此川剧《原野》的第一次呈现对曹禺原著的表达就不准确。总结起来说,曹禺的《原野》与川剧之间的第一个距离是文化上的——东北文化的苍茫雄强与西南文化的质巧柔软;第二个距离则是戏剧风格上的,曹禺话剧试图描绘的是野性和生命力,而川剧则长于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譬如“婆媳妯娌”之间的伦常关系。这两个“距离”实际上都可以统一在地域文化的“差距”上,因为戏剧可以看作地域文化的集中表达。既然川剧无法复制话剧《原野》的主题和人物,那么索性暂且抛开话剧,按照川剧和巴渝地方文化的规律,创造一个川剧金子。1998年,隆学义先生和导演胡明克一起,进入川剧《原野》的第二稿修改打磨。他们决定以主要人物的调整,来牵动整出戏的改进计划。调整主要人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启用能唱擅演的沈铁梅担纲饰演第一主角,这就意味着沈铁梅所扮演的金子即将取代仇虎,成为整出戏的核心。第二件事由第一件事情引起:创造一个重庆“俏媳妇”金子形象。这出川剧的名字由《原野》变为了《金子》。比起东北少妇,隆学义先生更加熟悉的是重庆媳妇儿,因此他笔下的金子具有重庆女人的特点“娇”“俏”“真”“直”“善”,在确立了人物的地方文化性格之后,隆学义着手改编情节桥段。而事实上,他发现传统川剧已经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身法和程式,去帮助他呈现一个“娇”“俏”的重庆女人,这也正应了“艺术源于生活”一语。而隐藏在传统川剧旦角“俏丽”之下的,是一个个悲哀的灵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哪一个不是深居闺阁,备受束缚的女性形象,而川剧赋予了她们内敛、隐忍、幽怨的品格,即或是刚烈,也是在隐忍、凄丽的外套下表现,比如说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按照川剧表演的规律,一个美的金子,应该首先是丈夫的妻子、婆婆的儿媳妇、族弟的嫂嫂……她在表现她的独特个性之前,首先应该表现得温婉、隐忍、善良、规矩。她不能与自然天性对话,而只能与家庭关系对话;她不能讲欲望,而只能讲纯洁的感情——这是一个被传统戏曲样式所设计的,被伦理“极端束缚”的金子形象。此外,金子在舞台上又必须是美的,不能是野蛮的,应该是程式的、节制的,而不应该是轻狂的。善良风情的金子被卷入复仇的风潮之后,会有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选择善良到底。女性本是世间真、善、美的代表,金子在作为第一主角之后,她的戏剧动机只会有一个:阻止虎子的复仇行为——她想跟虎子远走,去到黄金铺路的地方,了却仇虎心头的夺妻之恨;她想留住大星、焦母还有小黑子的性命,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仇虎一心陷入复仇深渊而无法自拔。到这里,川剧《金子》的主题已经离话剧《原野》有距离了:《原野》讲述的是农民复仇的故事,戏剧主要冲突在仇虎与焦阎王寡妻焦母之间直接展开;而《金子》的矛盾中心在于“金子想要阻止仇虎复仇而不能”。阻止复仇,即倡导以宽容去化解仇恨。宽容——这便是《金子》创新的戏剧主题。
如今川剧《金子》声名远播,其原因并不是因为隆学义先生重复了曹禺,而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颇具重庆地域文化色彩的“金子”,并因为“金子”人物形象的成功,带动了整个剧作主题的升华。虽然《金子》算得上是一个外来题材在本地成功的典范,却告诉我们一个铁的事实:利用丰饶的地方文化资源,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仍旧是地方戏曲剧种获得良好演出效果的可行办法。我们可以将本土以外的人物做出本土文化特色,就更能把本“地域”土生的人物形象呈现好,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本“地域”还是他“地域”,而在于对人物的挖掘力度。
川剧《白露为霜》是隆学义先生改编曹禺话剧《日出》而创作。故事讲道:沉浮在浊世中的陈白露,目睹少女小东西的悲惨遭遇,而救助不得;面对方达生苦苦劝告,却不能自拔于浮华虚伪的洋场。最终她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生命,就像白露为霜一样,融化在日出之后,回到泥土之中。该剧以“芦苇花飞白,白露结清霜。清霜如女郎,女郎绿水旁。日出清霜化,清心泥土藏。”这首小诗贯穿始终,极富象征意味,确定了该剧的“诗话”特征。《白露为霜》对曹禺经典的重塑,具有现实意义。陈白露身上被打上了当下都市女性的性格痕迹和命运困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人皆渴慕幸福,而支撑幸福的到底应该是“物质”,还是“精神”和“自由的理想”?曹禺《日出》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十里洋场。隆学义先生为了让这个戏更具有川剧性和地方性,在剧中加入了重庆大码头的民间环境、用四川清音《小放风筝》来表现少女时代的陈白露,甚至用四川民间曲艺音乐“莲花落”来表现老妓女“夜来香”和茶房“隔夜茶”。然而,无论如何改编和润色,总也不能改变曹禺原剧的“洋场”特色,川剧擅长表现市井和小人物,但对表现声色犬马的洋场,却不十分在行。本土的文化内容虽然丰富,即使适时加入,有时也稍嫌生硬。
隆学义先生的几个川剧剧目让我们看到:无论运用什么题材,创作的目的都是深挖主题,塑造人物。本“地域”的题材和非本“地域”的题材都有可能做出好戏,也有可能差强人意。因此,面对戏曲文学创作,我们不能将目光过多纠结在“地域”问题上,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特定题材对地方戏曲剧种的适应性问题上。例如《原野》的金子虽然来自东北,但这个故事发生在农村,展开在婆媳关系中,这个“伦理关系”的引子是可供川剧发挥的;又例如巴金小说《家》中的鸣凤,川剧的花旦、闺门旦和奴旦可为她的戏曲舞台呈现提供现成的程式和身法。说到底,能不能做出优秀的戏曲,题材只是多种舞台创作因素中的一种,而题材这种因素,又不仅仅只具有“地域”性这一个属性。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再谈一谈我对傅谨先生所提出“地域性题材降温”问题的理解:首先,这个观点是傅先生对当下整个戏剧生态作出的评论,戏剧的种类繁多,如话剧在艺术形式上受“地域性”文化的影响就比戏曲小得多。话剧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更具有共通性,因此话剧的确应该站在更宽泛的文化视野中进行选材。其次,傅先生是站在“地方政府推动戏剧文化”这一操作层面上来讲的,其语意重点其实是“提醒地方政府,并杜绝他们的功利主义”。作为戏曲从业者,我们要理解这一观点,却不要“非此即彼”地误读。中国戏曲应当开拓眼界,根据自己剧种的特点,大胆尝试新的适合自己的题材,以激发新表现形式的探索。这一切都建立在解除“浮夸”与“跟风”的坚实艺术实践之上。
*本文为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川剧艺术创新发展视阈下的隆学义川剧创作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YBYS147)成果之一。
周津菁: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