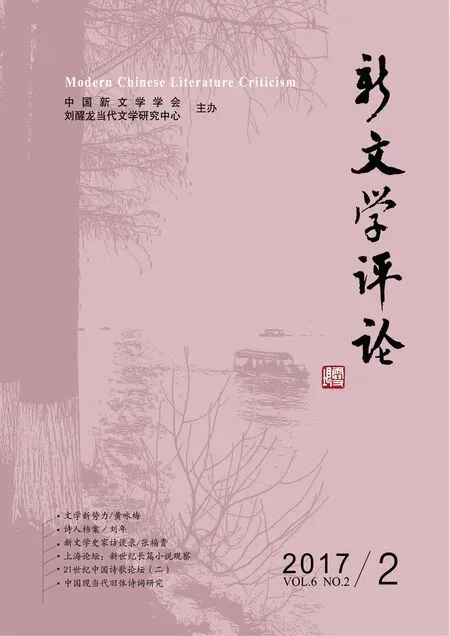大地的慈悲,赤子的性灵
———有感于刘年和他的诗
◆ 蔡 丽
大地的慈悲,赤子的性灵———有感于刘年和他的诗
◆ 蔡 丽
即使如我这样性情偏于老实散淡的人,读刘年的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仍不经意间就生出亲近感。刘年的诗,一部分是少年之诗,青春意气,义胆忠诚;一部分是中年之诗,荒山寒水,寂寞而苍茫。从其少年之诗,可以看出他的热烈性情,从其中年之诗,可以熏染他的阔大胸襟。一个诗人的一部诗集,记载了他真挚淳朴的性情,也记载了他立身于人世,耿耿于自我修养的精神之旅。刘年的诗,沁心,温暖。而当掩卷沉思,不禁自问,刘年之做人和做诗,实在是逆潮流而行的。以人格修炼的韵致和境界来修炼诗,刘年人越走越空阔,诗越写越简淡,这对于一个偏于逞才使气,偏于思想深沉,偏于技艺的复杂生涩的诗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一、 理想人格的高瞻与低就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刘年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人。做过水泥厂的机械维修工,辞职后做过各种小生意。一个现实生活离诗歌的场域很远的人,他最后以诗歌为生——做诗歌编辑,写诗,应该说,没有非不得如此的强大动力,一个人是很难放弃安稳的生活和看得见的有利前途的,而刘年确是在不惑之年,抛下妻子儿女,选择北漂。诗歌对刘年,意味着什么?谈及写诗的动机,刘年说:“因为一部《红楼梦》,我迷上了汉字,因为这部书,我开始写诗歌。因为写诗,我内心里,有了痛处,有了软处,有了底线,因此,一些手段便不敢用,也不想用。”这段自白很值得注意。首先,刘年说《红楼梦》是“影响了我足足一生”的书。我想,对正在不惑之年的刘年而言,这“影响足足一生”应该主要是指《红楼梦》对其人生转变和新的道路选择的影响。《红楼梦》恐怕启示了他红尘一切归于虚空的彻悟,促动了他“换一种活法”的现实行为。而诗歌的本质,正是以语言之乌托邦承载着生命在世俗之上的充实善美,它深深地打动了刘年,促使他从一个生意人、一个官场客转变成为一个衣食无着的诗人。同时,刘年对诗歌的体认具有高度的道德意味,他把诗歌当作做人的依持,诗成了捍卫人格尊严和净化灵魂的圣殿。
而当诗歌以灵魂净化的力量存在,成了人格尊严和道德底线的守护地时,诗歌于供奉它的心灵高大而神圣,在今天的生活语境里,它实在已经高到近乎痴人说梦,令人难以维持。因此,它需要有扎根于大地的基础支撑,贴近作为肉身的,弥漫着世俗烟火气的那个人。而刘年,他写诗的另一个动机,十分明确,多次提及:“新诗,本质就是自由。生命的本质,也是自由。”获得生命的自由舒张,这恐怕是他为诗最本质的动机。写诗,在相当程度上,是从非我的人生道路上撤退下来,回归本我,做回他自己:“从小就很听老师的话,想做个好人,多为他人着想,多作牺牲。于是,我半生都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口舌上。35岁,当决心为自己的内心而活的时候,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35岁,刘年告别过去,吟诗上路,重启人生。
二、 赤子之心
生活在蝇营狗苟中,每天为现实生计名利奔波,个体日渐成为庸众之一,刘年怎么会刹住了他的脚步,撇开众人,立地而彷徨?《永顺城》诗里,刘年写道:
几十年来,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买卖,一个人劝酒,一个人摇头,一个人看戏
一个人冷笑,一个人叹息,一个人挤公交,一个人排队挂号
一个人在人潮人海中找人
《永顺城》是一首悲伤的诗,“一个人在人潮人海中找人”把人活着的孤独和分裂提炼得生动又准确。对诗人来说,这“一个人”的意识已然鲜明而尖锐,“一个人”的存在孤独表明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凸显,一个“内”的“我”在众人中毫不被容纳,显得孤单兀立。刘年写出了肉身之个体精神与现实的高度分裂,精神的,内心之个体找不到对应的现实个体。湘西的永顺,年青的刘年讨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人潮人海中一边顺流而行,一边茫然四顾的情形。在某一个时刻,他意识到要找到那个丢失的自我就必须离弃这置身其中的庞大的人潮。那个顺从于人潮的“我”终于蜕去,显露出真心之真我。刘年,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
生活中,人最复杂多样,诗人中有才子,有士人,有思想者。有真诚面世的,也有矫揉造作的。我所理解的赤子之心,是指具有真挚、健康而美善的人格的人,且往往源自本性出于天然。首先,这个人本质上是平凡朴实的,从他身上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一种最基本的质朴、善良而谦逊的品德。其次,真诚,是他立身处世的基本立场,且他的真诚从家庭、从本性的背景中自然流溢,因此,唯有真诚才是他的自在,真诚地面对世界,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个人,构成了他生活的愉悦,是他人生惬意和舒坦的保证。再次,这个人的心智往往是非常强大的。在他或率由本性,或在真诚而开敞地裸露于世界的过程中,他的健全强大的心智不断地阻挡和化解外部的种种伤害,又不断地坚强他的天真和淳朴。最后,对周遭世界而言,这个人是一个光源。他的存在,往往给人以热情,温暖和希望。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性灵和人格,往往滋润别人很久,甚至一生。
无论是从日常交往还是从刘年诗歌的整体阅读,我们都能够感知,刘年是一个真诚率性的人,一个有着泥土的芬芳和天空的疏阔的人。即便成为北京城的一个诗人,评论家也说他是一个“厚道”的人。刘年的诗歌,本质上讲,是赤子之诗。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理想追求是其诗歌的核心。从他简朴淡雅的小诗,我们认识到一个赤子的形象和其日常生活的面貌。这是一个普通、善良而平凡的人,来自湘西,人因为时光而改变,心灵向着世界敞开。早年的诗歌是少年情怀,醉心于大地与亲人的情感,有浓情蜜意,更有意气不平,更是任侠仗义,豪气萧萧。进入中年后是一个善良明白人的人生写照,对自己持守甚严,有君子之训诫默念于心,对世界满怀慈悲。琐碎,常念叨些身边平淡事。思念家乡的妻子,老觉得对不起逝去的父亲,亏欠了家乡的儿子。偶尔忘情的时候会敞胸露怀。喜欢背包上路,注目于群山和皑皑白雪,心中一片阔大的宁静。然而也孤独,也有累得爬不动的时候。有很多想要,希望这世界美好,人获得充实。也有很多不要,拒绝对丑和恶低头弯腰。他的诗歌所写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诚挚普通而又有高远向往的一个人。他所念叨的是这世界上这每日平凡的生活中,一个普通善良人时时念叨的。他心灵的那点光辉,实在是从诚挚,坦率,自然的人格品质中发长出来。而他的诗歌给人温暖,给人鼓舞,也正在于这淳朴善良人对生活的热爱和珍视,从而能够在微不足道的日常点滴生活书写中,见出生命那最温暖的星光与韵致:
儿子抱着篮球进来,说饿了
妻子抱怨他没有换拖鞋
在这间小出租屋里,她制定了很多法律
阳光刚好落在砧板上
我像个手艺精湛的金匠,锻打着细细的金条
那一刻,真想宽恕这个世界
——《土豆丝》
人生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常常不如意的人生中,人从哪里获得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念?《土豆丝》一诗,注目于生活的“小”,它让我们在生活喧嚣浮华的快速道上突然定住并恍然醒悟,那最可珍贵的生活的黄金,原在于时间的光影里那些小如尘埃的细节,正是这些被忽略的,被踩在脚底下的微不足道的细节构成了整个生活的基础,支撑着整个冠冕堂皇的大生活。于人,于时代生活,这首诗都是意味深长。这样的小诗,刘年写过不少。刘年正是以一个轻柔自然的,充满温情爱意的方式,狠狠地敲了敲我们的时代人生价值观和生活观。
三、 大地与星空
刘年走在这一条裸露本我,张扬美善人格的道路,源自于他对另外一条浮华功利的人生道路的弃绝。从普世追逐的显耀人生道路转入孤单困顿的自性人生道路是一个堪称超凡入圣的过程,心灵自然经受种种挣扎、伤悲、寂寞、压抑的熬煎,有对过往人生的深刻反省,有回归本途的欣喜畅意,有心灵向着高处和远处的亲近。作为表现自我的诗歌,也就如一罐中药般百味俱陈,此谓诗之苍茫。药以苦去病,更由苦生香,刘年固执地认为诗歌是“疗治人间的药”,我想,他这一味诗药的苦,定然是退却的过往人生之种种遗留,也即诗歌苍茫的底蕴,而他这一味诗药之香,定然是从那蝉蜕般的新人生中发散出来的人情趣味和人格力量,也即苍茫的本性。细思之,除了前面谈过的赤子之心外,还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对美与善的欣悦敏感,如:“风中的群山,你的乳房,我的人生 都在摹仿水的形状。”“摘猕猴桃的时候 挑小的,丑的,有伤的 好的,留给过冬的猴子和山楂鸟。”其二,对人世的明悟有得,如:“天上没有不散的云啊,地上没有不老的人 我轻轻地唱 那么多的风,把天空吹得又轻又薄”——这是关于时光与生命;“懂了吗?喇嘛歌颂过的就是诗人诅咒过的人间 懂了吗,那些诗歌串起来,挂在风中,就是经幡。”——这是关于凡间与圣所,“可以,在他肩上睡去 醒来 有时,是清晨;有时,是中午 这一次,是中年”——这是关于父亲与儿子。其三,以大地和星空为托寄。刘年喜欢“落日、荒原和雪”,喜欢背着背包走向远处,喜欢一个人在河边吹奏陶笛。他对那更具原生生命气息的村庄和集镇情有独钟,在其间,他能够找到天、地、人本有的一份共在,这共在可以是欣悦的,也可以是掺杂了痛苦和无奈的。而唯其自然天命不可违的本性,刘年对这既温暖又冷涩的生命发长出厚实的爱与怜:“一天看不到一个人,背雪水时女人一定要唱歌 歌声里有青稞和牛羊,所以歌声里没有忧伤 一天看不到一朵云,背牛粪时女人一定要唱歌 人间没有了歌声,就像没有了寺庙一样荒凉。”而刘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放下自己,以大地的广厚,星空的浩渺为生命的依托,将渺微的生命融入宇宙天地之间,心随万物流,仁与山川在:“桐叶,托着阳光,像微微颤抖的手掌 杨叶,像微微颤抖的心脏 舍不得啊,这辽阔的人世,这风里的阳光 你的微笑,加重了我的悲伤。”刘年一部分写行旅的诗,写着走着,走着写着,人越来越渺远孤单,心思越来越沈静空廓,诗便如那遥远的天地与人的风景,微茫之中仅余一色:“走了十里,没见到一个人 又走十里,依然没见到一个人又走十里,还是没有见到人 一声呼喊,是天空和鹰都懂的语言。”
四、 在世与出世
刘年厚道,然性情里有鲜明的烈性,烈酒狂歌,肝胆义气,更有任侠豪迈、抱打不平的一面。因而诗歌里不乏少年之意气,扯起嗓子嘶吼,音是又高又重,然浓墨重彩中总有一股挥不去的浅薄。尔后,诗人的心胸渐为山川之广阔,脾气渐浸生灵之悲慈,性情里的烈渐化入温柔敦厚,诗歌也由窄狭走向深广,由单纯走向丰富。再后,人走得远了,身心俱空,万物流畅不滞,一切都在纵浪大化中,诗也就随人一起飘摇成仙,为“余晖脉脉水悠悠”,难以牵连出属于凡人的和筋带血的苦痛。在世与出世,是人之两极,要论人的复杂丰富矛盾纠结,是在世与出世的中间状态。要论诗歌的丰富亲近耐咀嚼,也是这包孕了在世与出世之中间过渡状态,生命的力与韵俱全的诗歌。如下一首:
为什么悲伤如此巨大?为什么欢愉如此短暂?
为什么,我如此眷恋生命?
我应该如何向你描述我的远方?
佝偻在土地上的人,天边的北斗七星,是永远拉不直的问号
——《悲歌》
这是一首让人在阅读的时候,目光的潮润和鼻子的酸涩在无意识之间,就顺着诗句的行进暗暗涌流的诗。此诗之好在于,立足于渺小肉身的生命疼痛,把个体生命的追问从大地的厚阔向上展伸至宇宙天空的渺远,以最平朴的文字传达生命的苍茫。还在于,此诗从追问出发考辨生命的渺小与博大,沉重与高远,颇有屈原《天问》的生命诉求和人格品性,格调甚高,而又能做到诗歌力与韵的一体呈现。刘年把他的诗集命名为《为何生命苍凉如水》,我刚读完的时候,重心在苍凉二字,觉得它对于具备年轻意气和充溢的理想主义的刘年来说,有点偏“重”了。后来再连起来作为一个反问琢磨,就觉得甚为适合。我体会这生命的苍凉之感,应该是在北京服务于诗歌的刚入中年的刘年刚踏入的、正是诸般滋味蒸腾挥发的人生境界——这是一个还有着青春激扬的生命逐渐转入高远静穆的人生时锐敏与敦厚共现、单纯与疏阔流荡交接时的人生感。一个人心胸的博大始终包含着他对种种尖锐、挣扎、撕裂、伤害、质疑等心灵疼痛的自我消化,仿若蚌孕珍珠般对异化物的含蕴,而诗歌的丰富耐咀嚼,就在于呈现生命之于火的燃烧力的挣扎向着酒的醇厚水的韵致揉进的过程。只有力的张扬,诗歌多于浮燥少于沉阔,只有生命韵致与滋味的自得,诗歌多于虚阔少于劲涩。刘年的生命感怀,恰恰既有尖锐的疼痛兀立,又有向高远空渺的融化。一首诗里,他行走的人生之路——由非我自觉到返回自我,再由这自我自觉地迈向寂寞孤单的养圣之路,这其中的人生之味,都得到了表达。
古典诗歌里,诗歌向更丰富复杂,境界更壮大的人生的承载,往往需要字数和格律的配合,五言四句演变为七言八句,内因正在于此。而在刘年的诗歌里,我也注意到,他大多数的诗歌是抒情短章,小巧精致,诗蕴也较为单纯,少部分长篇章,往往叙事与抒情结合,既有主观表现,也有客观描摹,其内蕴往往较为复杂,其境界也较为丰富阔大。这其中不一定都是好诗,有一些做得不够平衡,比如本是少年意气的,他话说得多了,劲使得过了,就有空架子之感。如《酒歌》、《遥远的竹林》,而另有一些大主题,由于刘年本性善良,热爱美好,不擅于往人性黑暗处思考,同时人生的经验还有待累积,理想主义的执着还有待冷漠现实的补充,他就把大而沉的主题写“轻”了。如关于父亲之死,在诗集里有好几首,但都没有写好。应该说,小诗,抒情短章,养人进而养诗,刘年已经经营得流畅自如,而在比较长的篇章里,刘年还需增长功力,调试火候。这其中除了失衡的,当然也有做得完美的,如《废墟》。
好诗没有办法评,最好是自己读去。我只想从刘年诗歌的整体发展角度来谈谈此诗的格调。刘年是从修养自身来修养诗歌的,自我抒情写意是他的出发点,他的诗歌总包孕一个“他自己”,他的诗歌,又充溢着对人世对生活的思悟,能够冷静通透地看清这人世间,能够清醒地超脱这人世间,以诗写人世,既是现实的平静直面,又有超脱后的容纳和悲悯,诗具有对现实广阔深厚的思想的质地。最后,他又收回到自身超越凡俗的心胸与人格的韬养上,以“托体同山阿”的生命归往,感念这天地间的命运消长转逝,而将一切盛衰兴亡、生死明灭纳于一颗心的涨伏。最后,他又是一个非常厚道质朴的人,心胸激荡如此历史与人世、生灵之兴亡存废的波涛,他不会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不是他的姿态,他既不是一个教主,也不当一名神仙,他是万千生灵中的一个,是命运的奴仆。面对这浩荡庞大而灰暗的生命,他,匍匐在地,凝望苍穹,满含眼泪。所以,这首诗,呈现的是一个敏感于生命从而敬畏生命,来自众生从而悲悯众生,参悟命运却恭敬于命运的人之诗。
五、 古与今
刘年的诗歌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在读刘年诗歌的时候,我多次想到陶渊明和王维。元遗山说陶渊明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渊明的诗歌之美,首在性情的真挚和人格的高贵,舍弃俗世功利,向自然真醇的性灵回归。我们从刘年身上,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任真”的性情的。黄山谷说陶渊明“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作诗的功夫恰在诗外。在刘年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不求诗而求人的作诗思路,体会到他诗歌的自然适性的特征。就理想人格的追求方面,刘年又有王维那种自觉地独善其身的行为,对山川自然具有高度的人格化追求。可以说,刘年的身上具有从庄子开始就建立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归往,以天地生灵的自然法修炼人的生命境界。然刘年与陶渊明和王维都不同的是,陶渊明关键在于任真,释放自己的真性情;王维关键在于有得,表达自己对天地宇宙阴阳契合的妙悟;刘年的走向恰在于一种仁慈,认识到宇宙天地大命运的不可违而敬畏天地,自觉到自身蝼蚁般的生命而平等于宇宙天地的一切蝼蚁生命,从而将自己供奉于诗这一以语言来完成的生命永恒屹立的神面前。在这方面,我想起写《陶庵梦忆》的张岱,尤其是刘年的同乡,写《边城》的沈从文。
张岱在《陶庵梦忆》的自序里,感叹人生之种种变幻,一心之痴念固执,感情是何等复杂,态度是何等谦卑。一册人生梦记,是为“持向佛前,一一忏悔”。沈从文写人、人生,避开社会道德和功利的尺度,只从对生命的思悟、欣赏、品味入手,发掘民间的、卑贱的人生本质背后,人对一切美好高贵人性的本能追求。因此我们读《边城》,无法去评判哪一个人错了,只能深深地感念人事的参差和命运的悲哀,《边城》留下的,是一支命运哀歌的悠长余韵。沈从文文学的出发地正是湘西。半个世纪后的湘西诗人刘年仿佛是从沈从文的散文和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他身上那种对水的亲近,对天命的敏感归顺,对生命的平等敬畏,确与同乡前辈有共通之处。

云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