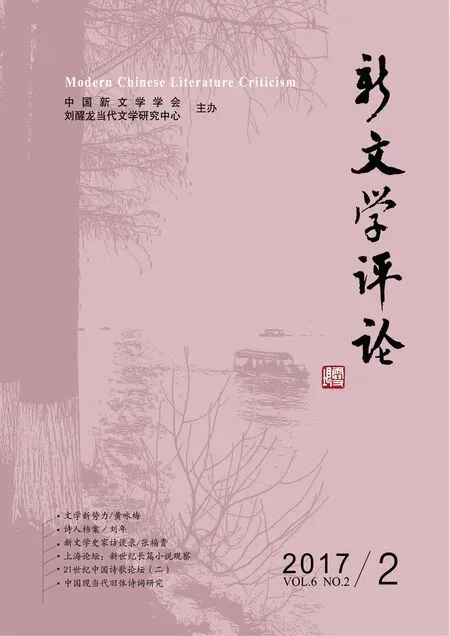状态与情绪
——黄咏梅论
◆ 刘大先
状态与情绪——黄咏梅论
◆ 刘大先
我不愿意用“70后”或者“女性”这样的代际或性别话语来谈论黄咏梅,虽然她无疑可以置诸这些说法当中。但前者夸大了某个偶然性的十年在长时段历史中的位置,往往有一种对于时间的诞妄而不自知,并且很容易在一种群体性的描述性命名中遮蔽内部具体个体之间的千差万别;后者更是因为其无所用心而导致望文生义,将现象与词语当作问题与意义本身,而忘却它们背后的意涵和所指。抽离出这些外在的先验身份设定,我们可以在她的文本中看到关于中国当代城乡变迁中从经济形态到人际关系、从幽微的精神活动到细密的情绪波动的转型,这些与她自身作为一个作家从梧州到桂林、从广州到杭州不断迁徙的生命履迹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辙,成为“流动的现代性”的一个表征。黄咏梅的写作超越了个人化的女性私密体验,却保留细腻的观察、体验和想象,并且将之冷静地呈现为疏离的状态,从而更为冷静地融合了外在的客观情形与内在的心灵波动。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她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代感,用一种似乎轻盈飘忽而实际上滞重黏稠的文字展示出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碎片、缺失、遗憾与温情。而她独特的地方也许在于,明确自觉到当精神救赎无能为力的时候,作家所应该审慎地保持的谨小慎微和谦卑,却也并没有逃避到怀旧与欲望的恣肆当中,这可能反倒能够成为在心灵板结层面撬动出一丝裂缝的杠杆——意识到生活的不完满,也不妨碍继续去热爱它,如果在世无所作为,那拯救就从敞亮它开始。
过程与碎片
较之专注于个体情感、家庭龃龉、私人欲望与现实纠结的女性作家,黄咏梅作品的题材很杂,从事各种职业的底层与非底层、流动与非流动、农民工与小资白领,甚至老年人的性心理(《蜻蜓点水》)都有。这些人物大多可以归纳为离散者,或者漂泊在路上,或者离散于精神的家园,或者在谋生的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在情感道路上豕突狼奔。她以旁观者的视角,平静地讲述离散者在变动中的人生无常与有常,就仿佛在日常生活之流中裁取一截洄水或旋涡之处,没有一个缘起性的开头,也很难说有一个终结性的结尾。这样的小说拒绝戏剧化的起承转合,更多的是呈现出过程化的状态。过程保持了变动不居和流动不已,但同时也是一段段、一块块无法拾掇的片断和碎片。这些人与事情的碎渣处于过程之中,因而具有了生命的绵延性质,它们是生活本身的状态。
“人和光阴都一样是流动的”,在情节类似张爱玲的《封锁》的短篇小说《特定时期的爱情》中,黄咏梅一语道破天机,而之所以不同于张爱玲,也正在于如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定时期”。这个“特定时期”外部世界变化剧烈,连带着牵动了人的内心在剧烈中似乎都变得麻木,它们充满种种可能性,也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解之谜。《勾肩搭背》中两个游走在广州的异乡人短暂的相遇、合作,生意利益上的互助中产生暧昧的情愫,终归要在功利现实中无疾而终。这个小说让人想起导演符新华的独立电影《客村街》,推销员和洗头妹在浮世喧嚣中的邂逅和失散,有意味的是,黄咏梅和符新华都让这种失散消退了浪漫主义色彩,而转化为非虚构式的冷静甚至冷漠描摹,这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氛围与状态的把握:卑微者的命运无法被虚饰,而他们粗糙干涸的内心承受不起细腻与脆弱的柔情。
没有结局的状态显示了生活的无逻辑和非理性,就像《鲍鱼师傅》中那个优秀的保洁工,他晦暗不明的往事和前途未卜的将来在无始无终之中,所能够把握的只是当下。尽管中间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插曲,比如和雇主之间的微薄的友谊,同事之间惨淡的交情,然而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沉重的生活本身已经让这样的人物不堪重负,仅仅是活着就几乎耗尽体力、疲惫不堪。虽然鲍鱼师傅似乎永远干劲十足,并且偶尔发现了音乐对自己的放空和治愈功能,但显然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诗意基调经不起锋利现实的轻轻一击。《金石》里采矿工难以言说的往事,侵入当下的生活,既普通又荒诞,既令人同情又充满黑色幽默,作者将它们展示出来,无由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黄咏梅像绝大多数当代作家一样,已经不再试图或者没有信心建构某种蓝图式的目标与方案,而只能尽力让这种复杂绞绕、泥足黏滞的状态摹画出来。这里面透露出当代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症候:经历过曾经的宏大意识形态解体之后,应然的世界已经隐匿遁形,个人在颇为尴尬的夹缝状态中,左冲右突,也摆脱不了时代语境的桎梏,当一切都在转型与摸索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只是本能地向前奔走。
时代确实变了,“在农村里走人情这种事情,一旦被挪到大城市里,就成了走关系了”(《档案》),在广州风生水起的李振声连在乡村里的生身父母都不再相认。这个“拔根”的行为显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割裂,不仅在肉体与空间上,也在心理与精神上。城市完全有着另外一套行事规则和道德规范,它原先在八十年代,也就是黄咏梅和她笔下的青春期人物那里,曾经是一个被想象美化了的远方。《契爷》中偏僻小城中的少女夏凌云给笔友写信,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情节。那是一种八十年代晚期氛围,在旁观叙事者“我”的眼中:“我们这里的人,从一出生看到的浔江水,笔直地朝太阳落下的地方流去,只在系龙洲边稍作休息,便毫无疑虑地释然流走。水总是闭着眼睛的,而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身边悠然自得随天而去,所以,他们也特别感到安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浔江都不急,你犯得着急吗?即使总是有外来的人,带来很多关于下游的故事,跟他们无关的,他们也只是听着,听归听,也落不下地的,留不下根的,这些故事,等于在水上写字,在水上绘画,在水上雕刻,再天花乱坠,再形象生动,也终于无影无迹。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却在慢慢遗忘这条江水。不仅因为它变得窄小了,变得了无声息了,变得浑然不觉了,还因为它不在人们身边了。它被隆起的一条大公路隔绝了,人们现在一走出街,首先就看到这条长龙一般卧着的国道。”圆融自足的状态被打破,新的生活方式像国道一样悄然而至,城南旧事一样的小镇旧事都付诸东流,“我”也丢开往事和小城,不回头地往前奔去。小说的结尾写道:“车一开,我的兴奋感就随着这蜿蜒的公路,一直崎崎岖岖的。我坐的位置在最前排,我的眼睛一直朝前看,我对前边所要经过和到达的地方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我压根就没想到要往后看,更没想到如果在汽车的后视镜上瞄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母亲在镜子里,提着一袋夏凌云的糯米糍粑,追着我们这趟车跑。”从不往后看,一直向前奔,是我们时代的基本意象。值得注意的是,向前奔本身也如同“我”的青春期冲动一样,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旨归,而是听凭本能冲动的驱使,一头扎向未知。
《瓜子》里的少年“我”可以视作“我”到了城市后的化身,身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处境之中:既不愿回到故乡,又难以融入都市。出身管山的“我”老爸在小区当保安,为了“我”能真正进入广州的生活而委曲求全。但实际上,这些进城的山民们与广州是隔离的,不仅“我”在学校里被安排在远离同学的“孤岛位”,当门卫的老爸和老爸的上司,那个似乎已经在城市获得立命基础的孟鳖也同样不过是一个个的孤岛。小说中写道:“孟鳖和我老爸,两人赌气地,齐齐站在东门口。眼看着,小区里进出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那些人跟平常一样,手里拎着菜,肩上背着包,他们迈着一天工作之后的疲劳步伐,跨进了东门。他们哪里有工夫去察觉这个跟自己擦肩而过的保安脸上,升起了跟往日不一般的笑容;他们更不会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多年来如一日地对他们迎进迎出的保安的内心,此刻,是如何在翻腾着汹涌的波涛。”城乡之间的互不理解固然其来有自,而处于底层的门卫之间的彼此压迫和仇视却是乡土伦理崩溃、共同体瓦解的产物。对比一篇写乡村题材的《何似在人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廖远昆是松村“最后一个抹澡人”,即对死者进行最后清洁处理临终关怀的人。小说中写到两个被抹澡的对象:耀宗老人在“文革”时候逼死了远昆的父亲,是他的仇人;寡妇小青则是他的爱人。仇与爱最终都在廖远昆的抹澡中得以消弭,乡土文化与伦理体系也在自足中得以完满。最后廖远昆失足跌入河中淹死,自然的水流替他抹了最清洁的一次澡,可以视为这个传统的最后挽歌。无论浔江边的小镇、管山和松村,都是乡土社会的镜像,它们在必然的城市化进程中分崩离析,共同体中的个人离散在流动的过程与异于原乡的空间之中。因为固有的观念遭受冲击后弥合性的新意识形态尚未成型,人们再次成为碎片化的个体,这也是多种层次彼此隔膜疏离的根本原因。在缝合阶级、认同差异的方法没有找到之前,黄咏梅笔下的人们也只能盲动般地出走。就像“我”在老爸受不了孟鳖的侮辱捅了他一刀后,要被送回管山。“我”在中途下了车,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中茫然地寻找广州的方向。
丧失与逃逸
身处变化过程与碎片状态中,人的自然情感倾向于怀旧与缅怀,黄咏梅倒是很少有此种沉溺,或者说她将其转化为体恤和对于情绪的呈示。《少爷威威》清晰地展现了两代人情感结构的变化:谭蜜斯抛夫弃子去香港讨生活,回广州看儿子魏侠,语重心长地教育他:“‘细侠,凡事要懂得争取,忍让和善良,都是没前途的,知道不?’魏侠领教了谭蜜斯向酒店的三次争取,觉得谭蜜斯还真像是个精明的职场女白领,他进一步想到,这么些年,她一个人在香港,赚钱当小资,享受花花世界,可不就是靠的这副精明和神勇?”如此一个勇往直前攫取利益的人,也还知道“情义无价”。但魏侠的小女朋友菜菜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除了物质索求,简直称得上没心没肺——无情无义都算不上,因为情义不在她的价值系统里,因而也不会产生道德反思和愧疚心理,所以她在魏侠进派出所之后一走了之,连个解释都没有。“老掉了牙的少爷,似乎就坐在黑黢黢的窗户里,浑然不觉得,时光已不再,这满眼看去的花花世界,已经没了少爷的份儿啦。” 魏侠这个准花花公子东山少爷已经成了东山大叔,美好的时光“十分钟就结束了”。有意思的是,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惆怅,也许并不是薄情而是疲倦,只是在物质与欲望对情义全面胜利的时候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并尽可能去适应这种新的局面。
《开发区》里的女人连那点惆怅都已经荡然无存,乐此不疲于“九分钟约会”式的功利算计:“所谓的‘九分钟约会’并不是给男人和女人们规定见面交流的时间,其实仅仅是一杯咖啡消费的时间。九分钟,你桌面的咖啡就算一口都没动,都要被服务员收回去,在咖啡被收回去的同时,你的约会时间已经用完了。如果你要继续坐在这里,要继续寻找你的姻缘,那么,对不起,请继续交钱续咖啡,一杯咖啡二十块。不用说,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流水作业,而这种男人和女人因为同一个目的坐在一桌的约会,等同于一桌流水席。”在这种复制了机械大生产模式的情感流水席上,谈不上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质素。女人所有的精力乃至人生目标就用在了寻找男人以及男人所表征的物质生活品质上,这个封闭的自我完全没有向更开阔社会空间打开的自觉。她的所有激情都残留专注于生物般的欲望满足之中:“很熟练地拈着一只蟹钳,捅进一截瘦瘦的蟹腿上,跟做手工似的,一点一点地把那里边的肉掏了出来,那么认真地,卖力地,寻找着一些甜头。”
激情的消逝是我们时代情感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利己主义的冰水漫淹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留给人们的是一地鸡毛的鸡零狗碎。如果我们时代有激情,也只存在于未被世俗磨折摧损的纯真和一意孤行的偏执狂那里。《表弟》这个小说表面上看去可以解读为媒体的扩张与平庸之恶造成的后果,内底里其实是激情的孤注一掷。表弟拒绝现实,沉迷于网络,自造了一个“江湖”,让贫瘠的青春在虚拟空间中灿烂绽放。当现实挤压了虚拟世界之后,他所做的是让最后的激情在现实中绽放,这种决绝有种悬崖撒手的天真与纯洁。与表弟保留了类似纯真的是在负一层管理泊车却不断追寻“天问”的阿甘(《负一层》)。阿甘身处的环境是人人都被抽象化为某个机械符号的环境,不同的符号化身结撰起一个庞大复杂却有条不紊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公正严明、等级森严,富于秩序感。小说中有一句话,“记住了这辆车,阿甘就记住了总经理了”,也就是说总经理与阿甘都是这个系统里的某个节点,它们几乎不发生身体与精神的交集,只是靠系统自身的逻辑结构联结在社会网络的不同梯级网点。身处“负一层”的阿甘迟钝温和,如同天真的璞玉,“自圆其说是阿甘这些年培养起来的本事”,她通过幻想和崇拜偶像塑造出自成一体的信仰与精神系统,这在工具理性的网络中是一个异端式的存在,注定了她的悲剧。当她从负一层爬到最顶层,一跃而下,完成的是与表弟一样的飞翔和拒绝。
另一类的激情也注定发生变异,那就是心怀美好理念而终究在现实中发现了它的伧俗败落的小姨(《小姨》)。小姨并没有因为理想主义的衰败和失落而改弦易辙——“人生观跟人的牙齿何其相似!乳牙更换掉,新牙按秩序刚排列好,牙根还没站稳的时候,对付那几只歪斜、出格的牙齿,我的矫牙钢箍就像紧箍咒般起作用,但要对付一副已经咀嚼了几十年、牙根已经深扎牙床大地的牙齿,任何方式的矫正都是徒劳,除非连根拔起。同样,要想把小姨稳如磐石的人生观连根拔起,除非小姨的脑子被洗得一干二净!可这世界上谁发明过洗脑器。”——反倒走向更加极端。在抗议毒工厂的行动中,她将衣服撸起举手向天,半裸着身体,如同师哥从前送给她的那幅《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女人一样。如同曹霞敏锐的分析所说:“小姨为之发疯的,是在她以之为精神凭借突破了俗世的多重困扰之后,一直追求向往的美好境界最终被‘美好’以及自我想象的‘历史深度’本身证实为虚妄。于是,她的‘决裂’就不单单指向俗世伦理,而是对坚持多年的精神自我和历史守护的全盘否弃。‘发疯’这一结果表明她将极端孤独地切断与俗世的种种尘缘,不怀希冀地与之做一个了结。如此不含功利的自我消灭显示了一个纯粹精神体从希望到幻灭的全过程。作者毫不留情地将小姨置于一个四处‘隔绝’的俗世,不给她留一点现实生活的希望,径直将她的精神推到彻底撕裂的地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放大作者自己的疑惑与悲戚:面对俗世对‘我’的覆灭,对历史实存的掩埋,如小姨般的坚持,到底有无意义?”这个追问是有力的,因为“意义”在我们时代被搁置了,那些追求意义的反倒成了神经病。这不是个体人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社会语境带来的普遍后果。
如果想在这样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安稳生存,可能只有和光同尘,同流合污。就如《达人》里的丘处机,这个丘处机和阿甘一样,是生活在幻觉中的。印刷工人丘处机在繁重枯燥的工作中让自己轻松逃脱的方式是读武侠小说。“因为有这些书看,丘处机觉得当印刷工人很有趣,那些机床的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传奇故事呢,一张白纸,进去了,再出来,纸上就有了人物,就有了七情六欲,就有了悲欢离合。有了这些,丘处机真的连车间大门都不想出。”这个时候,“肉身的丘处机与魂魄的丘处机早就脱开了十万八千里!”他过于弱小,无法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中悠游辗转,转而逃逸到心造的幻象里去。但这种逃避显然是无力的,他无法像个大侠那样为上访的农民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甚至在自己残疾后送外卖的工作也朝不保夕。只有当他搞定了交警队长,才能苟延残喘,“孩子们从后边看去,丘处机和他的‘长春子’号像在模仿电影里那个披着披风的超人,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地面飞起来”——这个时候,他才成为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达人。
旧时代的达人无处可逃,《八段锦》中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在体制式的群众药店的排挤下难以为继。“自从医疗改革之后,病人都被赶到医保指定医院看病,这些人,既信赖傅医生的医术,又依赖医院的福利,他们到医院走关系,‘偷’出医院的空白处方单,只要将傅医生开的处方写在这些处方单上,然后再返回医院找相熟的医生签个字,就得以刷卡消费了。那些医院的医生倒也不担心会出问题,任他们信任傅医生,而中药横竖是吃不死人的。属于零风险操作,医生们轻松赚得人头费,至于医院嘛,也乐得个客似云来,互惠互利,暗自默契。”流氓的欺压尚可以被打走,但制度性的规则却无可违抗,傅少杰最后不知所终,凭空消失,加深了逃无可逃的命运感。黄咏梅在不经意间抓住了我们时代丧失与逃逸的真相,但她和她笔下的人物同样对新历史的展开无计可施。
日常生活的焦虑
如同表弟、阿甘、小姨所显示的,丧失感往往与忧郁和躁狂联系在一起,而回避与逃逸则导向冷漠和无聊。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性体验,其根底里则折射出作家的隐在焦虑,它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小姨在广场裸露出干瘪乳房的瞬间,叙事人“我”在震惊中既同情又恐惧。与古典时代的悲剧那种置身事外的陶冶净化的怜悯与恐惧不同的是,此处的同情与恐惧分明连带着自我代入的切身感受。在小姨身上,“我”无法理解的怪异之物,某一天也可能吞噬“我”,它构成了一种当代命运般的巨大存在。《暖死亡》这个原欲寓言同样有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恐惑(uncanny),似乎有种神秘力量在作祟,而导致了林求安的不思进取和暴食症。当事人也想改变现状,却总是被这股力量所左右,面对自己的沉沦无能为力,这种温暖地死去令人不寒而栗。它可能不仅仅是生理和肉体意义上的死,而是整体性精神的死亡。当没有目标,陷入本能欲望之中时,“求安”而实不能安。《对折》里都市夫妻的麻木与隔膜,《单双》中赌徒的莫名绝望,都可以视作精神上不安所带来的焦虑症候。
有关焦虑的现代病、都市病的书写在现代主义以来的小说诗歌中不绝如缕,黄咏梅承接了这些遗产,并注入了当代中国生活的切肤体验。如果仅仅是书写这样的主题也谈不上新意,因为类似的观念在当代小说中也并不少见。我认为,黄咏梅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她切实地营造出来一种当代病的情绪和感觉,写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焦虑。这种情绪与感觉很难用理性明确的语言归纳与总结,而显示为模糊、含混的面相。她的笔下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小白领,尽管原因和动机有所差别,却几乎都无一不受制于这种惘惘的威胁。这种日常生活的焦虑是可以与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焦虑和革命年代的焦虑并提的,与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的不满或者革命规训中欲望的被压抑不同,日常生活的焦虑恰恰来自放逐了意识形态崇高之后欲望横流之后的虚无感。这在当下中国尤为明显,因为曾经的远大目标遭遇了历史实践挫折,新的认同和观念统合暂时没有完成整合,日常生活本身在满足生物本能和世俗功利之外无法提供精神的慰藉,而人却又有着超越性的追求。其间的断裂使得焦虑成为一种时代必然的病症。
如果说草根底层更多是为生存而焦头烂额,遍布在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来自于精神的空虚和认同的虚无。《关键词》里因为傍富翁获得巨额财产的女子,在穷极无聊的蠢动中寻找生活现实中的通缉犯,而她在这个过程中成了自己心理的通缉犯。《隐身登录》里的癫痫女病人,上网寻找刺激,无欲无爱,只有无聊,并不是真的生理需求,而是精神上的缺失。如何缓解焦虑,乃至斩绝焦虑的产生来路,在黄咏梅那里是无解的话题。她的小说是从认识入手的,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具象来展示社会细胞中的裂变。她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即一旦具有实感的生活冲破了心造的幻影,无聊的病人进入到现实的空间,则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文艺女青年杨念真》中的普鲁斯特杨可以说是当代小资的典型画像。她的人格就像她用于qq签名的自我标榜——“亭亭玉立,笑傲人世,善待自己,顺心自然”,全部都是一些抽象的、理念化的存在。生活在她那里是由卡尔维诺、三岛由纪夫、塔罗牌构成的,直接经验狭隘,靠间接经验建立生活以及与世界的联系。与具有过于丰盛的内心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在现实中的苍白无力。普鲁斯特杨们无法具备深沉的精神,小说中泡腾片爱情的说法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状态:“感情生活处于一片真空的人,独处久了,旧情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普鲁斯特杨和小门都死死抓住不放。而在她们相互倾诉的时候,旧情又变成了一颗味道酸涩的泡腾片。各自面前放一杯无味的冰水,一粒旧情扔进去,水花还没来得及溅出,就蒸腾翻滚起来,颜色、味道迅速溶解,熟门熟路,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受煎熬般的声音。”她们的行为模式也是这种方便的、随意的、“不彻底的”,现实世界轻轻触碰的力量,就可能激发出她巨大的变革。小说最后写到因为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普鲁斯特杨忽然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可笑:那些在文本中的毁灭之美在真正的灾难面前“统统都是些矫揉造作的屁话啊,什么凄美的情怀,什么永恒的美,都是些麻醉人的药剂而已”。当她作为志愿者踏在灾区的废墟上遇到经历了灾难的女孩时,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启示:“她将一些什么东西埋在了这废墟底下,那东西穿越泥土,穿越岩层,穿越地壳,穿越熔浆,最终沸腾燃烧了起来。”张悦然的小说《家》有着类似的情节,城市小资在大历史面前幡然觉醒,投入具有实感的生活之中。这似乎预示着作为我们时代文化主流的小资阶层变革的可能性,然而正是这种轻易就能被改变,也说明了他们的轻浮和浅薄。事实上,外部世界的刺激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自省与改变,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还是需要主体内部的自我觉醒。
戏剧化的自觉是如此罕见——实际上那种普鲁斯特杨式的转变是非现实的,充满了顿悟式的肤浅与夸张,更多的普鲁斯特杨们是在无意的阴差阳错中平稳过度。《粉丝》可能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黄咏梅将粉丝这种当代现象极端化了,王梦迷恋近乎成痴,却在与职业粉丝的交往中最终放弃了痴迷。但反讽的表象背后未尝不是一种由于现实(结婚这一在文艺粉丝那里看来世俗的举动)而带来的成长与变化。黄咏梅表现出一种温婉的调和,那些如同黏稠暗黑的沥青一样的生活,让人裹步难行,却是一种人们不可能竦身一摇、飞升跃出的基本环境。在这里,务实和有效的态度,可能反倒是立基于此,进而清算旧账,认清自我和自我的生活,破除现实所带来的幻相。
《旧账》中在广州做销士(sales)的“我”和搭档阿年为了销售额贝仙(percent),一起公关,屡有斩获,业绩不菲。但和父亲的关系始终无法弥补,原因是当年母亲为了赚钱支持他出门打工,攒钱的时候被鞭炮炸死。颇悲凉的是,这样的悲剧故事居然被他和阿年用来当作调动客户情绪的段子。小说不仅仅是讲述父与子之间的代际冲突与和解,而且是关乎城市与乡村之间权力关系的嬗变、乡土记忆与时代生活之间的纠结,指向了乡土沦陷、亲情分裂、资本横行、贫富分化的尖锐现实。父亲与乡亲们来到广州上访,打出“抗议政府征地建高尔夫球场,还我土地”的横幅,就是一个显豁的隐喻。但这种以卵击石的举动甚至连目标都找不到,“我”之所以答应帮忙,是为了清理亏欠父亲(乡村)的旧账。“旧账”的意指同时也包含了城市开发对于乡土的伤害,甚至更远一点可以追溯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农民与农村的剥夺。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具有转型社会中特定的双重性,既在城市中生活,适应了它所规定的一系列明制度与潜规则;同时又与乡土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脉联系和情感联系。
小说中有一段闲笔,写到“我”的心理活动:“我老爸典型的世代农民,要说手上有点权力,顶多也就是在每个节气对土地发号施令。‘雨水时节抢晴播,惊蛰春雷万物长,芒种忙下二季秧……’这些顺口的指令,几乎不用回忆,就能从我的嘴里跑出来。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关注这些节气啦。在我办公桌的台历上,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客户约见指令,十多年来,每年每月每周每日,我全由这些指令安排。偶尔有哪天,日历上空出了些位置,看看,哦,再过两天就是大暑了。‘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不假思索地顺出了这句,就像我女儿背那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据说我们家的田现在还坚持在种,忙的时候,老爸一个人搞不过来,就雇些江西工来做,每日一天六十块。 我经常心疼地对弟弟说,叫老爸别那么累啦,耕个一亩三分的,够自己吃就行了,别累坏了身体。实际上,我们几个给他寄回去的钱,足够他在农村吃用了。老爸对我弟弟说,田地越不耕就越瘦,久了不耕,就连根毛也长不出来了,以后,你们回家了,都喝西北风啊?我老爸始终觉得,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家,像他一样,每天依仗着老祖宗留下的田地,数着一个个节气干活,过日子。有时候,我走在广州的路上,人满为患,也会想念农村,想想,我那农村里的老爸,一个人,对着那么一大块空阔的土地,发号施令,种的稻子、菜心、番薯、花生等等,全都是他的兵,像他那样过日子,其实也不赖。”乡土记忆已然如同血脉埋藏在“我”的潜意识中,可以脱口而出,并且都市的喧嚣与繁忙会让忆念中的农村变得宁静美妙、温馨安稳。城市与乡村之间剪不断的关联除了人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之外,主要还体现于城市现代性的暧昧与混杂——似乎依然是个熟人社会,现代性的表征契约规则并没有完整建立起来。乡民抗议的问题无法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得到解决,只是在我的帮助下敷衍着,悬置在那里。小说无法给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也没有走向戏剧化的高潮。黄咏梅的反高潮是作家的无力,但她让当下状态出场,本身就成为一种叙述的力量。她的叙述像一个刷子,将覆盖在社会、生活与精神表面的浮灰掸去,呈现出深层的褶皱、纹理和沟回。写作行为本身就是缓解与释放焦虑的一种努力,也为在现实中治愈焦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