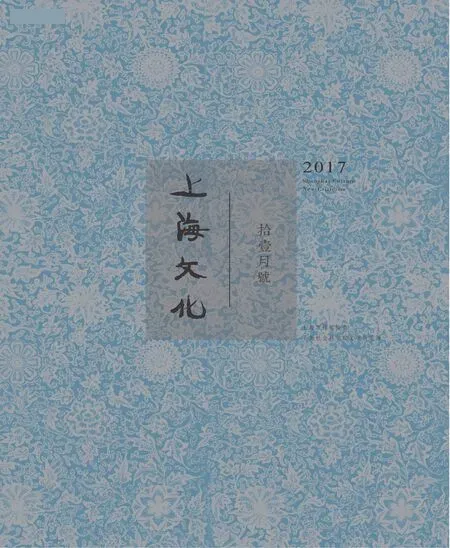失去的东西读王定国及其他
吴雅凌
失去的东西读王定国及其他
吴雅凌
献给静茹
柏林德意志剧院(Deutsches Theater of Berlin)在台北艺术节上演《等待戈多》。
好一场苦夏的等待。长达一百三十五分钟的对话。一开始,厄斯特拉戈(“戈戈”)对弗拉狄米尔(“狄狄”)说,帮帮我。他在戏里忙着脱了靴子又穿上。他连面对靴子也是虚弱的。但没人能帮他。那双挤脚的靴子让戈戈无时无刻不感觉疼痛。他一度想丢掉它,在月亮升起的坡上。也许有人能捡到它而它刚巧是合脚的。那么,对靴子对那人连同对戈戈,那都会是好事。但不会有别人捡到它了。那双带来痛苦的靴子永在戈戈丢掉的老地方等待他。帮帮我。还来不及等到放羊的孩子上来宣布戈多先生今天来不了但明天会来。帮帮我。一开始虚弱中的这句话让我早早乱了分寸。
当天夜里,我做了个梦。依稀是某个古寺园中的石墩旁,又或是荒原的一棵树下。梦中重逢的两个人好比脱靴子的戈戈和读圣经的狄狄。总是一个更虚弱些,另一个更孤独些。戈戈不停在问,狄狄二十年前为什么失约,仿佛忘尽了二十年人世沧桑,单记得那人失约了。狄狄无言以对,良久只能说,这一生他除了戈戈没有爱过别人。
天没亮就醒来。原来梦中人竟是电影《一一》的主人公NJ和初恋情人阿瑞。
有幸赶上今夏台北的另一盛事。时隔十七年,杨德昌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台湾首映。
*
戈戈:(冷冷地)有时候我心里想,咱们是不是还是分手比较好。
狄狄:你走不远的。
基隆的友人送我两本王定国的新书,让我去台南的路上有书作伴。
说是新书,小说集《戴美乐小姐的婚礼》实于2016年9月问世。至于《探路》,“小说家三十年来第一本散文抒情书”(封面语),则是今年2月的出版物,内中收录了作者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间为 《中国时报》“三少四壮”专栏每周一撰写的五十篇散文。作者自称写专栏是“走上天真又冒险的歧途”——“散文比小说难,难在使我不自由,如果小说是看他人,散文就是找自己。找自己何其难?挖太深像自恋,挖太浅怕失真……”(探路,“离场”,页251)。赶专栏的整整一年同时写《戴美乐小姐的婚礼》。散文与小说,俨然如另一种形貌的戈戈和狄狄在等待戈多的路上。
……说来让人掬一把泪,都是为了写小说。这一年来的小说是这么进行的:先把专栏散文写到足够撑场一个月,紧接着赶紧喘口气、换腔调,犹如重新刷牙漱口兼又练丹田,这样的慎重其事,无非就是为了接续写到一半的小说残篇。小说一直使我念念不忘,毕竟因为只有它让我感到自由,允许我大量说话,远离俗世又能关怀他人,且又可以尽情拥抱我所牵挂的人(探路,“离场”,页253)。
王定国,1955年生,彰化鹿港人,十七岁写作成名,中年转战商界成知名企业家,封笔二十五年,2013年重返文坛。按他本人的说法,“刚开始只想安顿情绪,试着找回十七岁的文学心灵,没想到落笔之后,每个句子瞬间成形,整段文字娓娓道来”(探路,“两个人的写作”,页214)。就这样每天夜里写作直至晨光慢慢涌进书房。五年里一连出五部书,部部精彩异常。
读他的文字,仿佛可以真切地看到他的模样。“不多话,总是沉默地一旁观察着什么,眼神很坚定”(热冷,页268)。用字之精到,让人惊艳。难得的是对待世事人情的温柔和克制,真真如2013年复出之作的标题,是那么热,又是那么冷。在与印刻出版社总编初安民的对谈中,他说“不为自己写作,也不为众人,只为小说里的人写作,替他们发声,甚至仿佛替他们死”(热冷,页265)。所谓文学,想来就该有这样一种公正的善意呵!
《探路》第四部分“归来”,既是接应前三部分如“出航”、“停泊”和“对峙”等行路阶段,也暗合“回归文坛”之意,其中多篇谈及重新写作的辗转与日常,《两个人的写作》、《黄昏写作》、《最想见的人》、《离场》,那么坦然又克制地,一遍遍安顿“文学和商业同时在身上穿梭”的自己。文学与商业,相看两厌的两种身份在他身上难分难舍,俨然如另一种形貌的戈戈和狄狄在等待戈多的路上。
二十多年封笔岁月,等待的“戈多”无他,“最想见的人”无他,是那个文学的自己。
有时我渴望见到你,彷徨的时刻,你会替我写字,专注而优雅,且又那么安静,像一只船停泊在深夜的岸边。……你暗中遥控我的形体,使我不骄奢也不躁进,不虚荣造作或沦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商贾……
但有时候,我却又非常疑惑为什么一定要见你。你曾经叫我善良,却也使我软弱,我在分秒竞争的商场中不够狠,只能像个温柔却不起眼的老手(探路,“最想见的人”,页219—223)。
曾经他是台中房地产业的广告企划红人,由他拟出的文案是楼盘大卖的保证,早在1988年以前就喊出一字一万台币的行情,且规定商家一字不得改动。后来他讲述当年的“嚣张气焰”:“文学里面是没有报酬率的”——如今回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敲出多年以前停顿下来的最爱,我大概是在向文学赎罪吧,或者说我是借着文学重新找回那个可爱的孤单的我”(热冷,页265)。
二十多年封笔岁月,他也自称是在钓鱼。孤独的猎者,苦行僧般走向荒野,最常面临钓无可钓的安静时刻,随着流淌的绿光找到安静的自己(探路,“手感”,页202-204)。
这样,似乎进一步明白他说的为小说里的人写作。小说里的人,何尝不也是自己呢?那二十五年失去文学的日子,终于以另一种形貌出现。
*
狄狄:嗯,他是……他是个相识。
戈戈:哪呀!我们简直不认得他。
狄狄:不错……我们跟他不熟……可不管怎样……
戈戈:就我来说吧,我就是见了他也认不出他。
《最想见的人》既呼应散文中的作者自况,也是新小说集的第一篇标题。有纪发疯地爱家中收养的孤女思佳,从十五岁爱到三十五岁。发疯的有纪在房内两墙之间来回冲撞,撞得头破血流不肯停下,后来被送去疗养院。“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一天不找她,每天写信寄到自己的家,但她早已不在,信寄了就退,退了又寄”(婚礼,页53),好比戈戈的靴子脱了又穿,穿上再脱。就在他“不敢再有任何的期待”(婚礼,页22)时,她忽然出现在令人迷惑的满街灯火中。他紧追不舍眼前陌生的卖春女郎,想认出那个穿白上衣配小黑裙像只白蝴蝶般的女孩。
同样是等待的主题,在《戴美乐小姐的婚礼》中显得面目模糊。这是合乎情理的。戈戈和狄狄也说不清戈多究竟是谁是否存在。
主人公是个中年男人,生意失败,妻子外遇,说不尽的潦倒:“失去的东西更美。我们本来都好好的,她是温婉的家妇,结婚多年后仍然是大甲溪沿岸最美的女人。我用我最丰盛的爱来爱她”(婚礼,页112)。妻离子散之际,他做起拉皮条的生意,专为富商牵线搭桥介绍小姐。人生在坏与更坏之间徘徊时,有个戴美乐小姐走进来了。“从她进门到现在不到半小时,我还迷惑在五里雾中”(婚礼,页81)。她不像是来应征小姐,“人长得算是普通漂亮,气质也只是含苞待放而已,可是那张脸就是看起来无辜,好像没做错事却被推了进来”(婚礼,页81)。何况她坚持用本名而不另起艺名,好比波卓(Pozzo)一度被误认作戈多(Godot)。名字引发的困惑总是藏着让人心酸的玄机。
戴美乐小姐就这样闯入他的人生,成了他的麻烦。第一夜下海哭个不停把客人气跑。三番两次放鸽子没做成什么生意。为了她被黑社会老大剁掉一根小指,为了她得罪某个政要立委连带一应的旧客,为了她终于把生意解散歇了业。与此同时,戴美乐小姐的样子渐渐清晰起来。她收养一群流浪狗,一个人住在野溪边。看到她不施粉黛的邋遢样,“很难想象当初我怎么会拱她出来迷倒众生”(婚礼,页124),“简直就像个单薄不起眼的粗胚,刚从天堂坠落下来,身上漂亮的羽翼全都掉光了”(婚礼,页149)。他渐渐看清她的真实模样,夜里穿过野地走进溪边那个铁皮屋她简陋的落脚处,听她静静述说本是政要立委的弃女身世。“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些我所失去的,原来美乐竟然早就失去了”(婚礼,页175)。
爱情就这样来临了。尽管从一开始他对她有莫名好感,特别是声音好听,很像四十年前母亲哄他入睡的声音(婚礼,页83),但在受困的人生中他本是无所谓等待的呵!就算等到重症昏迷的妻子醒来,还有情感的外遇需要克服。就算拉皮条生意兴隆,还有心里隐隐的不安难以安抚——“当我把她交到一个馋鬼手中,那种罪恶感以及我的痛心,简直就像失去了所有又重新失去一次那样”(婚礼,页177)。他遇见她本是龟公与女神的交情,本像戈戈和狄狄那样见了戈多也认不出戈多的呵!戴美乐小姐偏偏寄来一张卡。她送走所有的狗,溪边剩下她一人,“换你来收容我吧”(婚礼,页176)。爱情来临的时候,他和发疯的有纪一样,在家里“来回撞墙般走在急乱的方寸之间”(婚礼,页178)。
王定国的小说写着满满的爱与悲伤的故事。按他自己的话说,“表面上虽然写爱情,着眼点其实为了掀开现代人的苦闷荒原,这是在我个人而言除了爱情形式之外我无法做得更好的”(热冷,页264)。失去的东西以另一种形貌出现。等待,于是又被命名为爱。
我本该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不是王定国的小说与贝克特的戏剧那么巧有某种偶然的相契,而是在文学里正如在日常世故里,看不见的戈多无处不在。
*
这样的小说要表现什么?
失去的东西会以另一种形貌出现(探路,“最想见的人”,页221—222)。
台湾译本以“果陀”译Godot,以“阿福”译Lucky,均系妙译。评论家们一再提起,Godot乃是派生自God的生造词。贝克特本人却说:“我不知道谁是戈多;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我也不知道等他的那两个人是否相信他存在”(Lettre à Michel Polac,1952)。
阿福是戈戈和狄狄遇见的路人波卓的奴仆。通常他脖子拴着长长的绳索,两手满满的箱子、折凳、野餐篮、大衣等大小行李,拿起这个就掉了那个。在柏林德意志剧团的演绎下,看不见连接主仆二人的绳索,也没有大小行李,阿福一直在整理一匹太大的布,大到足以覆盖整个舞台表面。那匹布衾一片华丽鲜妍的桃红颜色,与整出戏的灰调子形成对比。阿福的工作注定是徒劳的。他一点点地折好收起那匹布,却一次次被拖曳在地的布绊倒,刚整理好的部分重新散落一地。他再爬起,又再被绊倒。再爬起。又再被绊倒。用不着波卓拉紧另一头绳索,挥起鞭子嘴里百般辱骂。全场人的眼与心全交托给了阿福那不断循环往复的动作,无望然而庄重,伴随他爬起和绊倒之间的节奏一同呼吸和战栗。
我带着王定国的两本书南下。一路不及读。满街满巷的凤凰木开罢的时节,台南不再有火烧连天的景致,但那蓝天白云让我看不够,仿佛在别处看不到似的。等到重新北上基隆,我才打开书停不下来,直至《书房》的那一页——
书房里的故事,听来是有些沙哑的啊,却一声声都是来自苦涩岁月的喉咙。文学莫不就是这样跋涉过来的,它总有一个寂寞的发声管道,那种孤独的精灵要是万众取一选中你,那就别想逃脱,活该你就是文学的代言人,注定要在别人体会不到的深意中漂泊……(探路,“书房”,页228)
这段文字让我一时触景生情想起阿福和他那匹桃红的布衾,想起所有那些日常与虚构的西绪福斯式的努力。来台湾多少回,头一回没有吹到太平洋的风。记忆中在宜兰看日出,从罗东乘坐区间车到花莲,再换自强号到高雄,一路沿着东岸行进,穿梭在山海之间。才打个盹的功夫,身边的人看一眼海水说,到西岸了。我平生第一次见识太平洋的风时,它相当强悍不由分说,让人在瞬间里无法呼吸不能动弹,让人如同遇见诗人读诗一见钟情。记忆中另一个黎明,我枯坐在几乎无人的基隆内港,天边微微染成绯色,远近的海水渐呈很淡的蓝。有个捡垃圾的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只纸折的洛克马。我对他笑。他用那一种让我恍如回到儿时的乡音,有一搭没一搭,说起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普渡。
在杨德昌的电影里,NJ与阿瑞中年重逢,又一次不告而别,回家对妻子坦白,似乎等来了曾经错失过的机会,却发现已经没有重来一次的必要。
一和一叠加,成了二,俨然是贝克特笔下的戈戈和狄狄。他们在寂寥不堪的日子里互相指责彼此折磨。狄狄觉得孤独就把戈戈喊醒。戈戈抱怨狄狄,做了噩梦不能告诉他还能告诉谁去?我羡慕在等待戈多的树下三次互相紧紧拥抱的戈戈和狄狄,至少他们如戴美乐小姐所说的“愿意一起死”(婚礼,页174)。
因为这羡慕,我学着心存感激。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