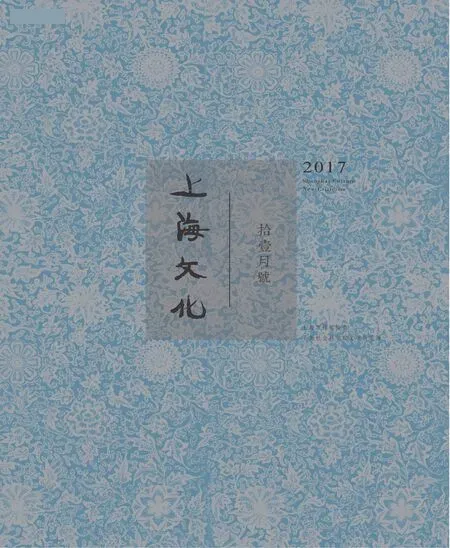猪尾焦虑与屠苏之死
吕永林
猪尾焦虑与屠苏之死
吕永林
周晓枫 《离歌》
零
弗洛伊德有一个十分幽奥的理论假设,早在他1892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就已显露端倪,然而直到1920年代,该假设才被正式码放在世人面前,但也从此在老弗洛伊德的著述中盘桓不去,它便是著名的“死亡本能”假说,即假设生命体内存在着一种让生命向着无生命状态复归的力量或冲动,这一力量或冲动既能越出所谓“快乐原则”的疆界,更能突破所谓“现实原则”的禁令,其终极目的,乃是让生命恢复无机物式的“平静”。对于这一“谜一般”的理论假设,笔者倾向于认同拉康的说法和做法,即将“死亡本能”假说视作弗洛伊德最具天才的发现之一,同时,又将其中的生物学意味悬置起来,而凸显其思想开启功能。譬如:老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其核心是生命的无机化冲动,而笔者可以藉此追究的一件大事,便是人的精神的无机化冲动。
一
人常常会“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也常常会三心两意,戏花如蝶。人既可能死心塌地地跟现实同床共枕,也可能一辈子念念不忘欲与梦想成欢。有的人呵护信仰,有的人撕碎一切。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在一瞬间、一时间乃至其一生所呈现的反思休歇和思想凝固,此种情形,笔者称之为人的精神的无机化。
人的精神无机化是人的另一种“死亡”,也是人的“销魂”之道,其中以欲求欢乐者居多,但也不限于此,诗人们说,“黯然”亦可,“远游”亦可。由是观之,则人世间到处都是“死者”,睁眼可见“亡魂”。
二
在各种“亡魂”中,笔者欣赏这样一些,他们或是命令自己“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的限制’”,或是让自己陷入一种“最耗精力、而又几乎无望的造反”——即“反对自己的狭隘和惰性”的斗争中,尽管他们有的最终逃向了病,有的则迅速沉入肉体的死亡,但在我眼中,他们一直是人类心灵史上的英雄。
现实生活中,笔者所见、所知极多的“亡魂”,是像周晓枫所作《离歌》中的屠苏这样,他们既不能克服自己和时代的丑恶,也不能克服自己和时代的颓废。在今天,对此类“死者”进行各种精神考古,实在大有必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为数众多,而且是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你我自己。
三
2015年1期的《十月》杂志卷首有言:“本期始,将开设‘思想者说’的新栏目,旨在召唤文学与当代思想对话的能力,记录当代人的思想境遇与情感结构。”2017年5月,周晓枫《离歌》发表,刊于《十月》“思想者说”一栏。在笔者看来,“思想者说”比非虚构或散文更准确、更具体地说明了《离歌》的文本样貌,《离歌》一文的紧要之处,便是文中之我对屠苏这位“双重”的死者进行了一次单方面的精神考古,笔者也正是将《离歌》作为一篇思想随笔来阅读的,而先不去管它是非虚构还是虚构,是散文还是小说。
四
人的一生,其实是一条由数个乃至无数“亡魂”流转、接续而成的河流。早在六到十八个月大的“镜子阶段”,人就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亡魂”流转事件,自此以后,我们混沌的心灵就从无所固执的无政府状态中越出,转而献祭于对某种“理想自我”和世界统一性的狂想与追逐。
《离歌》中,现在之“我”通过阅读小夜的博客而“追踪”到,十七岁时的屠苏曾将“未来的理想”定位为:“要做官!”(《离歌·四十》)“我”因此被“尖锐地刺痛”,其实大可不必。在无数人的无意识深处,所谓官,便如同低级别的国王,或者国王的某种替代,因此在将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统一起来方面,他拥有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可能,如若放在史诗时代,他应该就是史诗中的主人公。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之内的我和屠苏其实是一样的,而在文本之外,我们和屠苏也常常是一样的。我们都曾有过甚或至今仍藏有类似的梦想,不能在人群中建国,我们就在沙上、纸上、屏幕上建立自己的王国。“我”和屠苏的“文学梦”,其根底也基本在此,包括“我”在文中追怀的1980年代及其理想主义,其根底也基本在此。
就其欲望满足的情形而言,屠苏最接近此种销魂的时刻,大概是他高考一飞冲天的时刻——农家贫苦子弟,以地区状元身份考取北京大学,受万人仰慕,在那一瞬间,屠苏完全可以将自己想象成有关创造历史的史诗的主人公。
后来的屠苏,一直想要“重建”这一“原初的满足情境”,或者说重抵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美妙的“死亡”境地。然而在他厕身其间的现实语境中——被文中之我命名为“体制绞肉机”(《离歌·四十》),那种高考式的“简洁的公正”(《离歌·三一》)不见了,在“严酷的真实”面前,屠苏显然缺乏真刀真枪创造历史的巨大能量,辗转反侧之间,他选择倒向对道德和伦理的撕毁,于是由此而来的数次“重建”,也就倒向了丑,倒向恶。
五
精神的转折与更迭已然发生,究其本质,乃又一次“亡魂”的飘移,并且前后内里相通—— 一个人坚持理想和倒向现实之间,往往只有一墙之隔,而贯通于墙下的,是他不由自主地想要销魂的欲望,或者说是他在精神上想要摆平自己,进而“静止”下来(“无机化”、“死亡”)的欲望。不过,对于这个叫作屠苏的“亡魂”来说,无论是坚持理想还是倒向现实,里面都不存在尼采或卡夫卡所谓的自己反对自己的“造反”行动,因此尽管同为“亡魂”,此“亡魂”却非彼“亡魂”的同道。
屠苏倒向现实后的苦恼在于,在某些分外幽暗的具体处境中,比如在“体制绞肉机”中,丑恶也需要资本,比如关系,比如金钱,比如一个人既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的钻营与投机本领,等等,这些屠苏基本没有,因此,在其个人的“机关时代”,屠苏成了一个长期的失败者。
“在鼓城中学一动不动站了几分钟,我恍然明白屠苏的处境。他从最苦的农村来到鼓城,从血肉相搏的鼓城中学考上北大,再从北大到机关工作,层层晋级……背后是家乡人的羡慕和惊叹,对他们来说,这是美妙而狂喜的成功;然而对于不断置身新环境的屠苏来说,是他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重新放到最底端的位置、最惨痛的角色里。从鸡头变凤尾,从零开始,在崭新的底层从头再来。每一寸向上的光荣,都是由更低一些、更深一些的黑暗换来的。如同屠爸爸乐于示人的合影,看似辉煌,可屠苏永远占据可有可无的边角。屠苏向陡峭而凛冽的高处,攀援。没有援手,只有黑暗和内心里,呼啸的风声”(《离歌·三一》)。
六
有一个问题:屠苏赴京后所处的位置,是“凤尾”吗?
自古以来,人们对凤凰的想象数不胜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一诗,更将国外的不死鸟(Phoenix)传说融汇进来,从而使浴火重生的凤凰成为新世界或理想的共同体的象征。抽象而论,在一个理想的共同体之内,或者说在一种朝向正义、良善、美好的社会总体性之内,每一位共同体成员都该有其不可替代也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都该享有其应享的财富和自由,受到应受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个人都应该作为全社会的中心(平等化),就仿佛亿万条溪流“相造乎道”,反过来说,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成为全社会的中心(反等级化),即不应该成为那少数的国王或主人,换而言之,共同体的所有史诗,其主人公只应是无数个人的联合体,即共同体本身,同时,每个个人又能感同身受,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中的一员……如此,那么一个常年居于凤尾的人,内心会是怎样?
七
屠苏所在的共同体显然不是我们想象的凤凰式。“毕业屠苏留在北京。不算如意。文笔出色的屠苏本来分配给某位领导当秘书,没想到,最终被才华略输但更有背景的同学代替。为了留京,慌不择路的屠苏流落到工厂,在蒸汽、齿轮和噪声中写材料、写报告、写领导讲话稿”(《离歌·十四》)。即便一飞冲天时刻的少年屠苏曾经有过对凤凰式共同体的想象与期待,可当他真正从校园下山时,社会给他的这一刀,已足以葬送其所有的想象。更何况之后又是:“作为薪资微薄的小公务员,在北京的汪洋中,他只是近于无限的分母之中微小的一个。北京是个黑洞,有多少明亮的起飞,就有更多的陷落和葬送;每个成功者的励志故事背后,是一万个失败者的悲剧结局被掩埋”(《离歌·十四》)。
屠苏心中,很可能,他会觉得自己只是个猪尾。
八
文中之我分析说:“屠苏私下非常羡慕得势者,又不甘心,他们明明技不如己。可屠苏不愿亲力亲为,他的提起和放下都不够彻底。就像他为自己的不得意寻找外在借口一样,屠苏寻找外在的援助——这种祈求,就像虚弱者祈求神明。一浪一浪地被推动,丧失定力的屠苏像被迫离开的海星,吃力挪动自己看似钙化的触角,寻找新的礁岩。位置还是不够好,他祈盼洋流把自己带到更为理想的位置。与明慧的婚姻不够好,喜欢的文学太冷门,落脚的单位太清贫,屈就的职位太低微……一介书生的屠苏,没想到书本之外的世界复杂得难以圆融应对”(《离歌·三九》)。
这一灰暗进程中,屠苏的焦虑感必然会越来越重。但他的焦虑,绝非什么“凤尾焦虑”,而是“猪尾焦虑”,且此焦虑本身,已然显露出这个人可能躲向病甚至躲向死的征兆。到最后,除非是他杀,否则我们可以断定,是脑神经物质或别的身体物质的造反,将屠苏带入最为彻底的销魂和无机化状态。人在其根底上的不自主与不自由性质,可见一斑。
九
所谓“凤尾焦虑”中的“凤”,其实已经离我们所想象的理想共同体相去甚远,但既然称“凤”,至少应该有其较为可观的社会公正性,也应该有其较为可观的社会保障和补偿体系,及其精神氛围,所谓世道人心,尚善存焉。如此,则“凤尾焦虑”当属于一种程度较轻的焦虑,其中一个关键,有此焦虑之人心中会有个“服”字,用在屠苏身上,他心中存有的当是“技不如人”之感,而非“他们明明技不如己”之感。当然,一个中年人能不能“正常一点”地拥有一套可供栖居的房子,也很关键,在“凤”式共同体中,岂能出现如下情况:
“环顾亡友的家,我暗暗感慨。屠苏年近半百,来北京三十年头,和同龄人相比,居住条件欠佳。单位的周转房,合住,屠苏的使用权只限于两室之一。好在另外那屋主人住到岳父岳母家,屠苏这才享有基础的隐私。家里布置堪称简陋,像年轻北漂住的过渡房。桌椅是在夜市大排档常见的,桌子是可折叠的简易桌子,椅子是圆小、无靠背和扶手的简易塑料椅——我小心坐下去,姿态谨慎,怕坐翻摔在地上”(《离歌·八》)。
而在“猪”式共同体中,屠苏生前的焦虑必重。心里不服,且苦,再加上恼,加上恨。在此种共同体内,巨大的社会分化和人心分化无疑会不断催生各种“中心”对众多心灵的魅惑与专制——宏观的,微观的,权力的,财富的,消费的,娱乐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向往中心,必定会成为无数人的迷梦,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乃至亲人的灵魂和血肉献祭于斯,也必定会成为一种流行的疯狂或社会神经症,且代代相传。当然一开始,大约人人都不会想象或承认自己只是祭品,大家至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或家人能“翻身”。屠家一家,一度就被嵌入了这样一种命运。
与此相反,在“凤”式共同体内,应该会有许许多多迷人且能留人的“地方”、角落和边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从《离歌》中我们可以隐约见出,这样的“地方”、角落和边缘在屠苏所属的共同体中不多:
“鼓城在宣传语中是座历史文化名胜,但到处,都是极力掩盖却依然裸露出来的贫穷,从物质到精神都在没落”(《离歌·三十》)。
十
屠苏在北京人中的位置,就如同他的房子在北京城的位置:
“屠苏家的位置,恰在贫富夹层里:一边是富丽堂皇的新建筑,一边是散发排泄余臭的危旧房。自律且自傲的屠苏,多么怕沦入后者之境,中年已无多少余勇和体能的屠苏,即使只是背负小夜的包袱跃向前者,最终还是从裂隙之间掉了下去”(《离歌·二七》)。
可哀的是,屠苏的北大基因,似乎在任何层面都不曾耸立于“体制绞肉机”对面,成为这位北大毕业生的有力支援,大学及其化育力量对阵社会收编时的惨败,不言而喻。并且,“屠苏同一宿舍的兄弟,竟然先后走了四个”(《离歌·十三》)。无论他们各自的情况具体如何,这都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现象,除非,这只是一个莫大的巧合。
十一
小夜的出现,在刹那间肯定曾给屠苏带来了一线非比寻常的光亮。小夜是屠苏“有生以来第一个暗恋的姑娘”,“是他中学老师的女儿,她写诗,因此卓然不群”,但是这段暗恋“徒劳无功”,后来,“两人失散江湖”(《离歌·四》)。可以说,屠苏记忆中的小夜离他记忆中的那一“原初的满足情境”极近,因此,选择跟小夜在一起,应该包含了屠苏进行自我治疗和自我拯救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很快,小夜这道光便熄灭了,现在的、真实的小夜不是精神上的革命者,因此不可能召唤屠苏去做“精神界之战士”,进而从这样一条“亡魂”之路拯救他,或者说创造他。小夜如今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服从者,对于屠苏,她所能给予最多的,是一种其真实性尚待考证的“仰望”,以及无需考证的“怂恿”。
文中之“我”认为此时的屠苏,“维系内心平衡和成就感的,只剩一个女人的歌唱。他是坐在小夜神坛上的男人。除此之外,他找不到一把舒适的座位。”然而,“这是一把杂技团的座椅,被一根危险的长竹竿抬升到高处。每把高高在上的椅子,下面都有支撑的基础,有人靠权力,有人靠财富,有人靠艳遇,有人靠亲情……支撑屠苏的,是小夜的仰望和倚仗”(《离歌·三二》)。
可是很显然,小夜并不足以使屠苏摆脱焦虑,屠苏需要另寻安魂之道。“年近半百”的屠苏选择在职读博,且读的是“教育学博士”(《离歌·十八》),“企望重走金榜题名之路,这也是唯一的血路,尽管渺茫,至少尚有窄窄的缝隙……”(《离歌·三一》)而屠苏之死,就在读博期间。
屠苏究竟因何而死?也许是他自己绝望,放弃,也许是他的身体造反,强行替他做出选择,以此结束焦虑,结束苦恼。总而言之,“屠苏退到死亡的极夜里”(《离歌·四五》)。
十二
经由《离歌》,我们试图考古一条名为屠苏的“亡魂”之河。
笔者认为,除了《离歌》文末提到的“屠苏酒”,屠苏二字,还可解为杀苏——苏字为姓,抑或是名;杀为自杀,众人杀,我杀。所谓自杀,要么是屠苏自我厌弃,要么是屠苏厌弃世界,要么是他要跟二者同时撇个干净——由于在之前许久,屠苏就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无机化了的“亡魂”,因此自杀,本质上仍归于“亡魂”的流动。所谓众人杀,是指社会、家人、同事、小夜、世道等等都跟屠苏之死脱不了干系,无论大家曾对他施以什么——期待,催逼,还是压迫。所谓我杀,则指文中之我对屠苏的告别与清剿:“我所怀念的那个人,早已不是屠苏”(《离歌·四六》)。
十三
老实说,文中之我对屠苏的告别有些太过急切,尽管我也在不时地审视自己,比如坦承自己的“还击”“像在被污染的河里,一条鱼指责另一条鱼”。“这是我们的相似、我们的残忍”(《离歌·四六》)。但是“我们”之间更大的相似,在于别处。
十七岁的屠苏和四十七岁的屠苏一样,所有人同十七岁的屠苏和四十七岁的屠苏一样,本质上都是“死者”,都是“亡魂”。我们生命中最光辉的时刻,大概是我们用那朝向善的精神无机化去克服那朝向恶的精神无机化的时刻,多么希望,它们也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而我们生命中最阴暗的时刻,大概我们是用那朝向恶的精神无机化去埋葬那朝向善的精神无机化的时刻。在这样的意义上,十七岁的屠苏和四十七岁的屠苏之间只有咫尺之遥,我们同十七岁的屠苏和四十七岁的屠苏之间也只有咫尺之遥。因此,屠苏并未远去,也很难清剿,屠苏就在我们身边,屠苏就在我们身上。
当然无论如何,屠苏已无法开口说话,而他在《离歌》中说的话语和留下的文字,还显得有些稀薄。因此,如果《离歌》是非虚构之作,这便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可能的弥补,是作家去做更多的调查和访谈,比如去访谈屠苏更多的同事,访谈屠苏各个时期的同学和老师,等等。由此想到,卡波特创作《冷血》时的种种努力,着实令人佩服。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小微化青年形象谱系研究”(项目号: 2015BWY006)阶段性成果。
❶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❷雅诺施记录:《卡夫卡口述》,赵登荣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❸可参见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第89-96页。亦可参见李新雨所译拉康:《镜子阶段作为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出来的“我”的功能之构成者》,载于“豆瓣”网页:https://www.douban.com/note/507902381/。
❹弗洛伊德语。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高申春译,中华书局,2013年,第472页。
❺只取其比喻意,非对猪这种动物本身的不敬。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