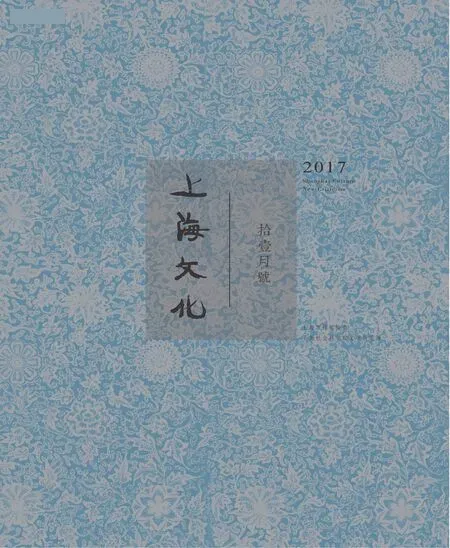远方除了遥远三个短篇中的空间、都市、与“边地”想象
康 凌
远方除了遥远三个短篇中的空间、都市、与“边地”想象
康 凌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场大雪?
金理在鹿鸣书店组织过一场读书会,请了郑小驴带着他的短篇《可悲的第一人称》到复旦,与中文系学生交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驴,也是第一次仔细读他的作品。作品本身并不复杂,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北京经历了情感与生活的失败后,跑到中越边境上一个叫做“拉丁”的地方稍作停留,继而进入原始丛林,试图通过种植、贩卖药材来“干出点名堂”,但最终由于持续的严寒与大雪冻坏了药材而功败垂成。
在读书会上我说,这部作品写得非常“悬”,一不小心就会被回收到某种流行的成功学叙事中去。具体来讲,小说的情节本身建立在一种中心-边缘、城市-边地的结构性关系中,而对于这一关系的当代文化想象,则在很大程度上由两种常见的成功学叙事所支配,一是我们所熟悉的“进城”故事,即主人公通过自身的拚搏努力,扎下脚跟,成为新北上广人,另一种则是近来日渐增多的“逃离”故事,以逃离北上广,回乡创业为典型,其主角既可以是大学毕业生(名校尤佳!),又可以是进城务工者(所谓“凤还巢”)。这两种叙事虽然貌似对立,但却分享着同样的关于成功、关于意义的定义——亦支撑着同样的“半张脸的神话”(王晓明,2000)。在这个意义上,后者无非是前者的一个绿色减配版,它们是李陀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在不同经济区域的变种(李陀,2012)。
正是在与后一种成功学叙事的比照中,《可悲的第一人称》显示出某种危险:同样是都市失意,同样是流逐边陲,同样是试图重新“创业”以进入都市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体系,并视其为“成功”(“我曾离成功那么近”),那么,《可悲的第一人称》与前述“逃离北上广”的成功学叙事之间,是否只隔着一场偶然的大雪?这场大雪所覆盖与揭示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似乎只能用一场大雪,来结束这个故事?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小驴强调,“我”的失败绝非仅仅因为一场大雪,即便没有它,“我”也会在之后药材的运输、销售中遇到一系列问题(包括没有“关系”,没有渠道等),因此,“我”的失败是结构性的、必然的,“我”将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城市。换句话说,这场大雪更应被理解成一种失败之必然性的宿命般的展演。
一方面,我非常认同小驴对于这种必然性的敏感,也正是这种敏感,赋予了这篇小说以内在的张力。另一方面,顺着小驴的文本与回答,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去讨论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不论成功或是失败,“我”重回都市的冲动从何而来?在这一离开与返归的空间迁徙过程中,“拉丁”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它与大雪另一端的“北京”构成何种关系?
读书会很快结束,但更多的问题却渐渐浮现。在我看来,“北京-拉丁”,或者更普遍地说,“都市-边地”在文本中的对峙与互动,构成了一个极佳的样本,使我们得以考察一种以都市为中心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想象及其“空间的生产”。带着这些想法,我阅读了一些近期发表的、同样涉及空间想象的短篇小说,并试图整理出一些基本的问题与分析框架。本文正是这一阅读的产物,其中,我的分析将依旧以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主,并旁及甫跃辉的《朝着雪山去》和苗炜的《星期天早上的远足》。阅力所限,我无法为当代文学中的空间想象勾勒一个完整的谱系,仅希望以这一讨论,展现其中的一个侧面: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体制不仅生产出了“都市-边地”及其等级化的空间关系,更将这一关系嵌入都市主体的再生产之中,成为他们经验与想象自身的创伤、意义以及个人空间的内在部分,亦成为当代空间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何处是拉丁?
让我们从《可悲的第一人称》的第一段开始:
车子到了拉丁,前面就没路了。老康告诉我,越过那片丛林,河的对岸就是越南。那是我头回看到榕树,巨大的树冠遮盖了大半个天空,像片树林一样。四周寂静得让人发慌,仿佛时光遗忘之处。
也就是说,故事始于一个没有“路”的地方,一个“时光遗忘之处”,始于空间的终结。假如“车子”可以被视为现代文明不断拓殖的移动疆界,那么拉丁则身处其外。它是一处空无,它没有自身的生活、历史、或文化。当然,路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故事要继续,就必须从无中生出有,必须进入、占有、改造这一(无)空间。而这一改造过程,既是叙事的时间内容,又构成了其部分的形式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从“我”进入它的那一刻开始,拉丁有了自己的历史:它既是主人公的活动领域,又是叙事者的书写对象,拉丁由此不再是“寂静”的,它既进入了人类实践,又进入了语言与再现——“空间的再现”于焉起始。
然而,拉丁的“无历史”性绝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事实”的客观再现,(假如这种再现是可能的话),毋宁说,拉丁的“空无”是先定的、预设的。在同一个段落中,叙事者接着说道:
在北京很多个失眠的夜晚,坐在黑暗中,好几次我都幻想过会有这么一个场景:站在葳蕤的原始丛林前,周围空旷无人,四面八方都是我的回音。我泪流满面。不知怎么,想哭的冲动最近越来越频繁。而这种感觉离拉丁越近,冲动就越强烈。
换句话说,早在叙事者到达拉丁、进入拉丁之前,这一空间就已然是“空旷无人”的了。拉丁的无历史性先于拉丁本身出现,或者毋宁说,正是对于这一无历史性的需求,造就、询唤出了拉丁这一空间。叙事本身的第一人称视角也不断提示我们,对于拉丁的描述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特定主体位置、主体视角与主体需求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拉丁可以被视为一个身处北京的都市主体之“幻想”的物化形式。“我”的拉丁之旅,亦由此成为这一幻想的对象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拉丁的进入、占有与改造,恰是一个都市主体在一个想象空间中的自我展开:更确切地说,一个在都市中失意、失败、失眠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失败同时也是空间的失败,我在后文中将进一步展开这一问题——试图通过建构拉丁这一想象的空间,来展开自身在都市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望与意志:拉丁原来在北京。
而拉萨则在上海。在《朝着雪山去》中,“我”的同学关良因为嫌上海生活“没意思”而决定徒步去拉萨朝圣,并以此为理由,向同学们伸手借钱。不论是半信半疑还是慷慨解囊,“我”的同学们最终凑足了经费供关良上路。在这里,拉萨这一空间同样被再现为“意义”的物化形式、而关良则作为“拉萨”的具身化(embodied)再现而出现在“我”与同学们的公共话语中,这一双重再现过程早在关良上路以前已经完成。与拉丁一样,拉萨的意义并不源于其自身的历史,而在于上海都市主体的生活与想象中。
也就是说,在文本展开之初,“拉丁”与“拉萨”早已被设定为空洞的符码,有待“北京”与“上海”为其赋值,并由此获得其特定的意义,承载特定的功能。而这些意义与功能的来源,则是作为叙事主体的生活世界的都市空间。由此我们得以进一步提问,都市空间的生活经验,如何生产、规定着都市主体对边地空间的想象方式?而这一边地想象,又如何重新嵌入到都市主体的生活世界中,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边地与都市,分别与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制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鲁宾逊的边地冒险
在进入这些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空间本身的物质性与历史性。
在《空间作为一个关键词》(Space as a Keyword)一文中,大卫·哈维注意到,随着近年来的文化与后现代转向,空间日渐被作为某种想象与符号而加以讨论,空间的物质性反而被遮蔽起来。这一遮蔽中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哈维强调,因为围绕空间而展开的真正的政治斗争与反抗,必然最终要落实到“物质的”、真实的、经验的公共空间中(D. Harvey,2006)。哈维的这一提示所表明的是,不论是想象的拉丁还是想象的拉萨,当它们被“布置”在“中越边境”、“西藏”这些具体的地理位置上,它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些“边地”作为一处事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所携带的物质性与历史性。而对这些物质性与历史性的翦除,恰是资本主义空间规制的暴力性的表现。
之前我已经分析了《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叙事者,如何在一开始就通过将拉丁描述为一个“时光遗忘之处”而取消了拉丁自身的历史性——这一描述所暗示的是,在都市主体进入之前,拉丁无法拥有自身的历史与故事。类似的,在《星期天早上的远足》中,当叙事者第一次来到云南的云想客栈时,迅速“发现”了一片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太阳不高不低地挂着,晨雾散去,这是群山环抱下的一片坡地,田地枯黄,几头牛呆立在田间,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有几处玛尼堆,红黑相间的藏式房屋稀疏地构成一个村落,每家的院子都有高高的木架,晒着青稞。炊烟升起,犬声相闻,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哗啦啦地蜿蜒着。”而正是在这一世外桃源般的空间中,叙事者得以展开他与女主角的重逢故事——以“风景的发现”为前提,云南边地的藏族村庄,再一次被征用为都市主体展演自身欲望与想象的舞台。
这一改写与征用绝不限于对“自然风光”的描摹,《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叙事者在拉丁逛了一圈之后如此描述这个地方:
拉丁小得像个拳头,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三五十步就搞定了。我几乎没看不到什么青壮年,几个牙齿掉光瘪着嘴巴的老人眼神里充满了好奇,纷纷瞥向我。他们一定嗅到了我身上带来的陌生人气息。
唯一的小卖铺在拐角处,我去买了盒烟。老板是个老女人,吸着旱烟,她用拉丁方言问我哪里过来的。我回答说从北京,她的嘴巴半天也没合拢。天很快黑了,白天的光在拉丁全面退却,稀稀落落的几个窗口开始亮起了灯。我听见山上的黑鸦叫唤得一声比一声凄厉,就在旁边高大的梓树上,像是不欢迎我这位不速之客。……
叙事者总结道,在拉丁,虽然他“不想成为一个另类”,但依旧“吸引着他们的好奇心。”在这里,“陌生人”、“不速之客”、“另类”等自我描述,无不指向一种清晰的主体-他者之间的二元划分。而这种二元对立的双方无疑不是平等的,如果说“我”已然“像个有修养的文明人”,那么深处拉丁的那些“过早衰老的女人”、“浑身脏兮兮的小孩”、“牙齿掉光瘪着嘴巴的老人”,则共同构成了一道他者的奇观。对于读者而言,在这一叙事中真正的“另类”无疑不是叙事者,而是在叙事者的凝视中所浮现的这些异样的、不同于“文明人”的拉丁居民。叙事者的视线在拉丁穿行而过,并将其空间重组、改写,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除了老康以外,要么成为原始、落后的前现代奇观,要么便是故事结尾处那些沉默、匿名、等待着“我”的召唤的“劳动力”。然而,不论作为奇观还是作为劳动力,边地居民都已成为失去自身意志与历史的纯粹对象,成为叙事者“我”用以组织、再现自身主体经验的工具与客体。
对边地居民的这种征用,是与对边地的土地的占据与开发并行的,两者共同构成了都市主体对边地空间的拓殖历史。在进入原始森林后,“我”迅速发现自己“成了这片原始丛林中真正的主人”,“决定这些动植物的生死”。有趣的是,“我”在原始丛林的自然景观中,既没有以人猿泰山的方式“融入”其中,又没有如陶渊明般与之“相看”。作为“主人”的“我”对这片土地的统治方式,遵循着典型的资本主义殖民开发的逻辑:“我”与村政府签订了合约,租下一块肥沃的土地,投入二十万的原始资本,买来种子与化肥,雇佣了二三十个劳动力,依据自己在农学院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开始种植药材。根据“我”的计划,随着药材价格的上涨,“我”的这笔投资将能换回“一两百万”,之后“我”将回到北京,而届时,“整个世界都不在话下”。
从雇佣劳动、科学技术的投入、土地开发、商品生产与销售到资本增值,“我”的计划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以对都市空间的重新占有为目标。吊诡的是,“我”虽然是作为都市生活的弃儿而流逐边地,但“我”在边地的所作所为,却严格依照着支配了都市生活的资本主义逻辑而展开,在某种意义上,“我”几乎可以被视为都市资本主义的一位信使、一位传教士,将资本的逻辑复制到拉丁,对这里的土地进行殖民:拉丁成为一个微型的北京,而“我”则将成为这里的资本大鳄。
在这一奇妙的空间互换术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失败者成为资本逻辑的空间拓殖的中介物,“我”的拉丁之旅,由此成为鲁宾逊的孤岛冒险的当代中国版本。(老康是星期五吗?)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鲁宾逊的账本、他对劳动时间的计算与划分、他的商品生产方式、他与财富的关系等等,在在透露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以此,他在荒岛上完整复制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生产方式。顺着马克思的思路,萨义德将《鲁宾逊漂流记》放在了大英帝国的资产阶级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他看来,鲁宾逊的荒岛冒险使他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和拥有这片土地”。在鲁宾逊的实践背后,是“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与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与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事相联系”(E. Said, 1995)。
与之类似,作为“森林之王”的叙事者“我”,亦可以被视为都市资本主义在边地空间的拓殖先锋。在“我”的眼中,本地居民成为他者,而土地则成为生产资料。后殖民主义者大可以于此展开各种批判论述,但在我看来,我们或许尚不应急于将叙述者作为某种“殖民者”而打发掉,一方面,“我”固然本身已然成为资本扩张的一个中介工具、一个客体,但另一方面,“我”的身上似乎还凝结着都市与边地间更为复杂的空间关系,以及在这种空间关系中展开的主体创伤及其疗愈。
离开的路与回归的路:剥削与疗愈的辩证法
在刚到拉丁时,“我”曾“拔掉手机电池,把手机卡扔进了火塘,将手机送给了老康”,这一姿态使“我”感觉自己“抛弃了全世界”。然而,姿态似乎仅仅是姿态,“我”之后在拉丁的全部实践,几乎都可以被视为重回那个“世界”的努力——不仅“我”本人希望带着种植药材所得的“一两百万”回到北京,更重要的是,“我”在原始丛林中的土地开发,正在将这一边地空间纳入一个以药材为中心的全国乃至国际的生产、销售网络。“我”/拉丁与北京之间的隔断与重连(及其失败),构成了小说推进的一个基本线索。而正是这一“重连”的过程,值得更进一步的分析。在讨论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事业时,萨义德指出,这些项目“在系统地追求从土地上获利,同时使之与国外的统治连为一个整体”。它们将“把宗主国卵翼下的全部空间加以统治、分类并使之普遍商业化。将帝国主义说成是‘天然的’肥沃与贫瘠、可利用的海道、固定划分开的地域、土地、气候和人的结果。这样,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就完成了。它是‘依照领土作出的劳力分工,从而产生的国家空间的划分’”(E. Said,1995)。同样,“我”在拉丁的土地开发与药材销售计划,亦会将这一片原始丛林与以都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网络“连为一个整体”,成为其中的商品生产空间之一,成为资本增值进程中的一个部件。在这个意义上,对边地空间的去历史化,仅仅是为了在之后重新占有它,将它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历史中去。
事实上,资本的影子从始至终都闪现在都市与边地的空间占有过程之中。《可悲的第一人称》里,“我”需要二十万的原始投资才能种植药材;《星期天早上的远足》里,季阳为了离开北京环游世界,不仅卖了房子,还向好友贝贝借了十多万;《朝着雪山去》的大半情节都是围绕着关良行前的筹款而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穿越空间的“远行”本身就是一项投资行为,或者说,它总是将边地与都市置入某种债务/债权关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它的收益是什么?它如何被“投资人”们所理解?
在《朝着雪山去》里,关良的行前筹款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除了叙事者“我”对他有所怀疑,大部分同学几乎是主动地将钱送给了关良。他们几乎都与关良一样,认为眼前的都市生活“没意思”,却又与关良不同,因着种种生活的现实压力乃至创伤(情感、学业、工作、个人出身等等),而无法“想打游戏就打游戏想去西藏就去西藏”。于是,他们的投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意义的“外包”方式,要求关良及其旅行提供足以匹配其投资价值的意义感。在这里,“意义”成为商品,而都市主体则成为纯粹的、空洞的消费者,关良时不时的汇报,则无非是一种分期偿付。与此同时,“边地”的使命亦早已被事先派定:当都市生活的压力使其不再可能提供意义,“边地”空间便成为了意义的生产地,也正因此,它成为了都市主体的空间想象的内在组成部分,成为都市创伤的疗愈之所——关良的同学们因为他的远行而兴奋莫名(《朝着雪山去》),“我”与季阳在云南边陲再续前缘(《星期天早上的远足》),在北京两次陪女友堕胎的“我”在拉丁使小乌受孕(《可悲的第一人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药材”这一意象呈露出其双重意义: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药材”是边地所提供的一种商品,具有资本增值的功效;而在符号/象征层面上,“药材”则同时具有治愈都市创伤的“疗效”,成为都市主体意义感的供应商。都市对边地的“投资”,在这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其双重收益。
有趣的是,都市创伤本身也往往与空间的争夺息息相关,更准确地说,对边地空间的占有,常常是对被剥夺的都市空间的一种补偿与置换。在《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并行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是“我”的拉丁之旅,二是“我”对北京生活的回忆,尤其是“我”与李蕾的恋爱悲剧。然而,两人情感生活中的幸福与挫折,几乎都为同一个主题所充斥:在北京买房。当两人“加在一起的存款接近二十万”(又是二十万)而可以负担得起一个“小房子的首付”时,他们“浑身都洋溢着幸福感”,而恰在此时,北京的房价开始疯长,“好不容易我们精疲力尽无限接近首付的时候,房价一脚油门,一夜之间又变得遥不可及起来。那段时间,我已经不敢再去看房产中介,深深的挫败感如山一般压了过来”。也正是因此,两人不得不打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她在最不该来的时候来了”。由于租住在“不足五平方米的隔断间里”,两人的日常生活时刻被隔壁情侣的各种令人尴尬的声响所影响,这也成为两人争执不断的主题。李蕾对“我”的最深的伤害,便是那句“跟着你,反正这辈子甭想买房子,你就一辈子租房住的命!”这句话不仅刺伤了“我”,更使“我”真正“难过了起来”,因为“我”彻底意识到,“我给不了她什么。甚至是租间像样的单间,都要精打细算半天”。由于持续的拮据,两人不得不第二次堕胎,最终李蕾离开了北京“这座讨厌的城市”。
在某种意义上,两人的爱情悲剧与创伤源于在一场都市空间争夺战中的失败。房产价格的疯长是都市资本主义的掠夺式投机行为的典型表现(D. Harvey, 2012),在这一过程中,都市个体的挫败、异化与创伤既源自于、又表现为对个体生存空间的压迫与剥夺——那些无法在都市中获得空间的人,只能被驱逐边地。
然而,这一被迫出走却在符号与叙事层面上被展示为一场自我救赎与自我疗愈——边地空间似乎早早地为都市失败者准备好了救赎的可能,准备好了生活的意义与重新出发的资源,乃至将都市生活的被剥夺与被损害翻转成了一出激动人心的王者归来的大戏,或者至少是一次惠而不费的重寻生活意义之旅。换句话说,正是在空间的层面上,我们得以窥见资本主义文化统治中的剥削与疗愈的辩证法。“二十万”虽然无法在北京支付首付,却足以让“我”在拉丁获得一块土地。对“边地”空间的想象的占有,成为对失去的都市空间的某种补偿与置换、对都市失败者的疗愈——他们不仅将获得空间,更将获得生活的意义。资本主义文化以这一温情脉脉的承诺,掩盖了对都市与边地的双重剥削,关于“远方”的想象成为一份不在场证明,既遮蔽、赦免了“此处”的剥削,也延宕、阻碍了对这一剥削的抗争。萨义德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读出了本地空间与海外殖民地空间之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想象上复杂的联动关系(E.Said, 1995),而《可悲的第一人称》等文本,则为都市与边地空间之间同样的互相依存提供了样本。资本主义一方面以地产投机掠夺了都市空间,另一方面又为它的受害者们提供了边地这一想象的疗愈空间,在那里,一个人似乎可以完成所有他在原有的都市环境中所无法完成的梦想。或者反过来说,恰是边地这一疗愈空间的存在,成为某种预备已久的创伤缝合术,使得对都市空间的剥夺进行得更为肆无忌惮。与此同时,如我之前所分析的,在这一疗愈过程中,流徙边地的都市主体自身又被作为一种中介与工具,对边地空间进行拓殖与资本主义改造。也就是说,作为失败者的都市主体,非但没有试图反抗资本主义的空间掠夺,反抗资本主义对“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D.Harvey, 2012)的剥削,反而被精巧地转化为其空间拓殖计划的一部分,向边地扩张。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小驴的文本以一场大雪阻断了这一进程,并暴露出这一疗愈方案不过是一场幻梦。这场大雪之所以显得突兀,恰恰因为它不属于、且不服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疗愈的辩证法。这场大雪将药材冻烂在地里,既无法成为商品,又无法治愈主体。然而,只要都市中的资本主义剥削与空间掠夺继续进行,便依旧会有更多的“我”、更多的“拉丁”出现——《星期天早上的远足》里男女主人公重逢的云想客栈,不就是一个“忽然有一天目以心为形役,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白领跑去云南开的吗?
资本主义空间拓殖以都市为起点,不断占领、改造着都市与边地的空间与居民,其微妙而强硬的逻辑,无法为边地的一场大雪所撼动——它的真正对手,依旧是一种都市的、集体的、政治性的空间抗争。正如边地的“意义感”是一种结构性的产物,都市的“无意义”同样有着有迹可寻的、伴随着暴力与剥夺的历史。然而,在都市中失去的,依旧将在都市中寻回。在《朝着雪山去》的末尾,关良终于徒步来到拉萨,当他“呼噜呼噜地”解决了两碗拉面后,“毅然决然地朝对面的网吧走去”。面对老同学在电话里的询问,他的回答依旧是三个字:“没意思。”然而,之后他又要往何处去呢?网络的虚拟空间,是“边地”之外的新的疗愈地之所吗?故事结尾暗示关良回到了上海,那么他在上海的故事,将如何书写?
同样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里的“我”,因为小乌的怀孕,也将再度回到北京,再度面对都市资本主义的空间压迫,在那里,他将如何展开新的故事,展开新的空间争夺?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除了本文开头提供了两种成功学叙事及其反例外,是否有其他的资源,以供他们——我们——展开一种新的空间想象?然而无论如何,当他们再次回到都市时都已清楚地了解,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