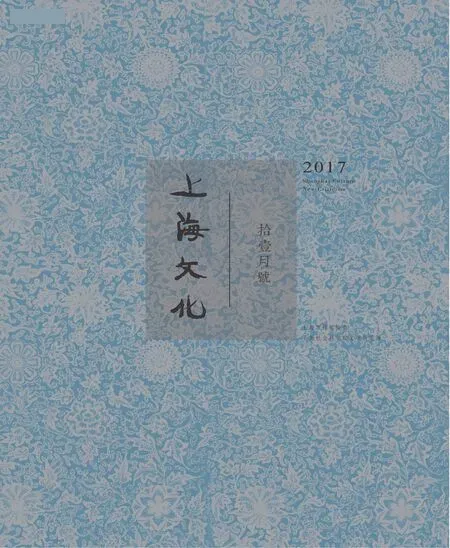我的父亲狄金森:论诗学影响①
安妮·芬奇
梅圣莹 齐 悦 译
我的父亲狄金森:论诗学影响
安妮·芬奇
梅圣莹 齐 悦 译
起初,我不想与她有过多牵连。她就像是一个我过于熟悉而且感到羞愧的亲戚。我觉得尴尬。我发现她忸怩作态,在学校时读过她的诗句,往好了说,软绵绵,往坏了说,倒胃口:“我爱看它舔过一里又一里”(Fr383 I like to see it lap the Miles-),“我要戴上小饰品—”(Fr32 I’ll put a trinket on-),更别提那无所不在的“一只鸟儿,从小径走来 —”(Fr359 A Bird,came down the Walk-)。我尤其烦这句。“他不知道我看见了”(“He did not know I saw”)这不太可能,而且用“fellow”这个词蛮横地指称那只可怜的小虫——他“吃了那家伙,生吃”(“ate the fellow,raw”)——有一种奇怪的、故作轻松的语调,让我紧张。而且,她似乎总是以“Emily”的名字出场诉说,那么这个叫做“Emily”的孩子究竟是谁?如果她是一个儿童诗人,那么她真是一个奇异的儿童诗人。她不像是在写给我,而是——忸怩作态地——写给一群广义的,假想出来的孩子,某些想像中的听众或读者。
然而她的力量,她的独立,她的害怕和她受伤的绝望,她的强烈抽象和漫不经心,都一一经受审视。我当时读到的那些狄金森的诗是压力之下的被扭曲的选择,对于这种压力,我当时没有任何概念。在我父母——一个哲学教授和一个诗歌艺术家——的影响下,我带着欣喜和好奇在家里接触过众多诗人,不过,我第一次读到狄金森却出于学校的安排。我从来不记得我父亲曾大声朗诵过她的诗歌,或者凭记忆背上几句,虽然克兰(Crane)、艾略特(Eliot)和叶芝(Yeats)的诗句,时不时从他口中流溢。在他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排排的布莱克(Blake)、但丁(Dante)、弥尔顿(Milton)、艾略特(Eliot)、史蒂文斯(Stevens)、庞德(Pound)、瓦雷里(Valery)和惠特曼(Whitman),但没有给狄金森留下一席之地。还有我的母亲,她欣赏赫伯特(Herbert)、欧佩(Oppen)、缪尔(Muir)、博根(Bogan)和默雷(Millay)等诗人,对狄金森却一直不曾留意,直到后来。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我愈发明确地想要成为一名诗人,我的父亲一定是开始欣赏起她的诗歌了,因为他开始同我愈发频繁地谈论起狄金森。事实上,他开始不断地向我絮叨:“不要担心读者。看看狄金森。她生前不曾出版。你只管写。如果你的诗歌是好的,它们会找到自己的读者。”我开始了解到,狄金森,虽然生前没有发表作品,却通过信件在有识之士的某些圈子里培养了一群读者。可这对于我父亲来说似乎没什么区别。他保证我的作品不需要我刻意努力也能找到读者,这话使我想起一个大权在握的文学出版人几年之后说的话。当时我问他女作家的作品在他出版社所占的比重,他说“有啊,我们正要出版几个女诗人的作品——比如说”——他说到了一本书,其作者已经去世约有大半个世纪了。“但她去世了,”我指出。“是的,”他说,“让人振奋的是女诗人确实得到了广泛认可,即使有时这有待时日。”
我确信我父亲是想用一个伟大女诗人能够获得的成就启发我。但是我所看到的形象却是一个谦恭的女作家,她把自己称作“无名之辈”(I am Nobody [Fr260]),拒绝了唾手可得的出版机遇。她唯一被承认的形象就是一个害羞且安静的孩子,我当初读她的诗,觉得它们的确孩子气十足。总而言之,对于一名年轻女性正要面对一个今非昔比、充满竞争、无比刺激却仍然以男性为中心的诗坛,艾米莉以她土灰色的脸,不食人间烟火的、病态的诗,似乎不是一个健康的榜样,尽管教科书努力把她描绘得一副无忧无虑、不惹麻烦的样子。几乎是无可避免地,我愈发讨厌她。随着我的成长,那些粗俗的玩笑也被顺耳地接受下来:艾米莉只是需要优质的性爱生活。她过多地活在脑子里和灵魂里(我那时没读过露丝·欧文·琼斯[Ruth Owen Jones]2002年的文章,若读过兴许会大大改变我的看法)。大众神话中的狄金森形象本来可以一笑了之,按照这个神话,狄金森是个听话的小女人,干瘪的老姑娘,她留在家里只因她父亲只吃她烤的面包,她曾设法与男性体制相安无事,但直到死后才做到,他们终于可以把她作为一个标杆,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充满激情的,雄心勃勃的女人圈禁在我们的地盘。
结果表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我十二岁时,另一股线索彻底铰了进来,影响了我对狄金森的理解。我发现了一种私密而难以启齿的对狄金森的爱。发生在我青春期的一个事件让我无比震惊地进入了女人的世界,此事的后果可能至少二十年后我才得以慢慢理解,我遭受过一名家庭成员的性侵犯。一些学者认为狄金森和她的同时代以及在她之前和之后的女孩子都曾遭受过同样的事件。我摆脱了这段经历,对此一笑置之,就像我的生活在各个方面从未被改变过一样,但在之后的二十年中它却缠绕着我,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典型的应激反应:被禁锢的成长,感觉自己被封冻在时间里,我使劲地蹬水而周边的世界却抛下我径自前行。在某处,我还是十二岁,尽管二十几年来我并不理解这是什么缘故。
温蒂·佩瑞曼(Wendy K. Perriman),在她《受伤的鹿儿跳得最高》(A Wounded Deer Leaps Highest)一书中发现,在三十三种被心理学家鉴定为乱伦受害者的人格特征中,狄金森表现出了其中的二十八种。回望过去,我发现这些特征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接受治疗前的自我中也大多清晰可见。但如果要我将它们概括为一种特征,那便是一种诡异的“死于生”(death-in-life)的意识,它紧紧抓住我不放,狄金森似乎也有同感,正是这一点吸引我最终进入她的诗歌。
她捕捉这种感受的第一首诗是“我为美而死—还未等(Fr448)”,这首诗大概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读到的,我真的被它吸引了。这十二个诗行强行拧进了我十二岁的意识,围着我的思绪和我的身份意识打转。这里有个诗人,她懂得一个人怎样活着并说着话,甚至很年轻,同时却又死了不动,嘴唇上盖着苔藓,眼睛再也看不见书页。以起首短语“I died”开始,诗歌的词语扩展又收缩,如同奇异的能量丝,向外颤动着扩散,当我夜晚躺在床上,它们包围着我,穿过我,继续扩散,进入无限的外太空。接着它们开始膨胀,如同那些缠绕在我父母门廊柱子上的紫藤的恶魔化身。
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
Adjusted in the Tomb
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
In an adjoining Room
我为美而死——还未等
在坟墓里安身
另一个,为真而死,躺入
一个比邻的小屋
诗歌以女性声音开场,那是我熟悉的女性诗歌那种轻盈的民谣的诗节,或者那是我所知道的一个女人写出来的,就像狄金森的其他诗歌一样。但是接着,怪异的事情发生了。首先,隔壁房间的那一个(the“One”)原来是男人。就这首诗歌的语境来说,这是一个奇怪而且有点不合礼节的搭配,这种死后的亲密。紧接着在一个空洞的,令人不自在的瞬间,那个人似乎表明他认为诗人也是一名男性:
He questioned softly quot;Why I failedquot;?
quot;For Beautyquot;,I replied—
quot;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 —We Bretheren, arequot;, He said—
他轻声问道:“因何至此”?
“为了美,”我回答—
“而我—为了真—它们是一体—”
“我们是兄弟,”他说道—
这位逝去的兄弟清楚地听见了诗人从墙壁那边的坟墓发出的低语——并且在他听来,那似乎并不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而是“兄弟”(“Bretheren”)的一员。不过(我在七年级时寻思),可能她仍是一位女性,只是逝者将她称作男性;或许在前两个诗节中暗含着一种愉快的平衡,一种平等的差别。可是,到了最后的诗节,通过一个明喻的反转,狄金森表明,诗人也认为自己是一名男性,或者等同于男性:
And so, as Kinsmen, met a Night—
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
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
And covered up—our names—
于是,像同族相见在夜里—
我们交谈隔着墙壁—
直到青苔爬上了我们的嘴唇—
也遮盖了—我们的名姓—
(王柏华 译)
面对最后这两个意象,我总有一种战栗之感,一部分战栗来自欣赏,欣赏她对死亡的勇敢想象,不过更多的是厌恶的战栗。这两人是兄弟的假设——无论是由于19世纪普遍的阳性化语用传统,即男人意谓着人类,或者是出于某些更为诡秘怪癖的原因——掩盖了一个谎言,就好像这谎言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这谎言会伤人——至少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女性诗歌声音,不是书写爱情或者纠缠不清的关系,而是勇敢地经受死亡,再从另一端爬出来,书写它。“我为美而死”给我送来了这一种女性形象,但它也顺势将其带走了,它明确表明,她或者她的人物角色获得这个强大地位是通过成为一个兄弟来完成的,成为一个男人的同姓宗族,这个男人即使已经死去躺在坟墓里仍散发着不劳而获的男性特权的光辉,由此,他才能将这个简单的词语“兄弟”(“Bretheren”)授予这个女诗人。这种性别困惑在我的意识中溃烂,从根部与我对狄金森的诗学力量的初始感悟交织在一起,因为就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其他女诗人可供选择。
在1987年的文章“我的母亲狄金森”(“My Mother Dickinson”)中,我追溯了狄金森的谱系,发现她是一度兴盛的感伤主义“女诗人”运动中的唯一幸存者,这批感伤主义女诗人基本上取用民谣的传统诗体,书写自然和亲密的个人经验。我在文中写到对她的感激,感谢她将众多诗人如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弗朗西丝·奥斯古德(Frances Osgood)和丽迪雅·西格妮(Lydia Sigourney)的传统带入了诗歌主流。但其中有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对狄金森的幸存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没有它,她绝不会成功)似乎是她的男性层面,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的角色呈现,这与她所在的“感伤主义”传统构成对立。在众多女诗人中唯有狄金森得以幸存并活跃于20和21世纪,不仅靠她过人的天赋,还因为她是一个混合型诗人,是一块合金,由男性诗学传统之钢与女性之铜熔铸而成,而其他女诗人不是。狄金森分享了露易丝·博根(Louise Bogan)在其《美国诗歌成就》(Achievement in American Poetry)中所概括的女性的“感受路线”,同时也参与了男性的“真理路线”。
所以,这里有某种根本上的含混,对我这样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躲闪,这位女诗人之所以伟大与这个基础有关,而她是我当时以及随后若干年里所知道的唯一伟大的女诗人。这种性别杂糅在男性诗人中并非闻所未闻;但是在女性诗人群体中,诸如权力与共谋的因素会使情况复杂化。我那时不知道狄金森的诗中仅有一小部分是以男性口吻写的——即使我当时知道了,由于这首诗是令她闻名一时的核心代表作,以及这是我在学校期间读到的,在我作为一个女孩和诗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它跟我十二岁的成长经历紧紧缠绕在一起。我也曾为美而死,为一个年轻女孩的脆弱之美——并且当我犹疑着醒来,打量着我的墓穴的内景,我能找到的唯一亲人——能说出我冰冻的意识的唯一诗人——便是狄金森,她把我拽进一种兄弟关系中,她的一个兄弟已经在那里了:“来吧,”她说:“成为一个男人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奇怪的是,狄金森就这样对我的诗歌发挥了最亲密的男性影响力,其密切程度超过了所有男性诗人,不论是叶芝(Yeats)或霍普金斯(Hopkins),邓恩(Donne)或赫伯特(Herbert)抑或是斯宾塞(Spenser),甚至史蒂文斯(Stevens),克兰(Crane),奥登(Auden),休斯(Hughes),惠特曼(Whitman)。上述诗人都或多或少对我产生过影响,然而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像狄金森那样独一无二且无可争议。经由狄金森和她奇怪且无性别的角色,我开始与我的男性缪斯建立一种迟疑的,半抵抗式的关系。当我挣扎着去建立自己的诗歌身份时,狄金森成为一座通向男性中心主义的诗学传统,通向那“真理路线”的桥梁,对我来说,这就好比是给了我一个礼物,一份遗产,一扇门。她向我展现了一个女人就诗歌而言可以大胆地称自己是一个男人,并且在那个死后的中性世界里,女人的诗可以跟男人的诗同等尊贵:她的诗歌像是一座小小的无性属的墓碑,一个石碑形状的圣像,不可磨灭地镌刻在纸页上,如此深刻和永恒;苔藓可以覆盖它们,但它们可以像男人们的墓碑一样永垂不朽,世人无从分辨这一座还是那一座,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既然它们的名字已被遮掩。
由于在19世纪西方历史与文学中被默认的和所谓中性的位置事实上是男性,不必明言,性别问题仅与女性有关。狄金森既然拥有强大的男性的一面,她实际上就去除了自己的性别所指。她从分配给女性诗歌的小角落中抽身而出。如果说狄金森诗歌中那种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强劲坚韧,那些幸存者的品质,起初让我感到反感,不愿去接近的话,那么正是这些相同的品质最终滋养了我并启发了我的创作。在我十二岁发现狄金森之前好几年,我已经阅读并喜爱过一大批男诗人的作品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雪莱(Shelley),卡罗尔(Lewis Carroll),利尔(Edward Lear),林赛(Vachel Lindsay)——紧接着,丁尼生(Tennyson),赫伯特(Herbert),罗宾逊(E.A. Robinson),霍普金斯(Hopkins),叶芝(Yeats),罗特克(Roethke),劳伦斯(D. H.Lawrence)和克兰(Crane)——然而我认为只有狄金森让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成为我心目中的“男性”诗人,我也可以从一个独立的视角去书写严肃的话题,而不需要顾忌任何人,就像默雷(Millay)在她的爱情诗中所做的那样。
有些影响就好像传统观念中的母亲——他们无论怎样始终都在那里。叶芝于我正是如此,其他人则问题重重。它们挑战你,使你感到不适。它们将你扔至半空中。狄金森就是如此。她让我振奋过,之后好几年又将我打入谷底,然后她再次激发了我,把我朝另外一个方向扔出去。当时我二十多岁,坐在一个研究生诗歌写作工作坊,把课堂抛在一边,以便沉浸在她的诗作 “巨痛之后,有一种徒具形式的感觉—”(Fr372 After great pain, a formal feeling comes-)。突然间一种错位感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是因为在工作坊的语境中阅读熟悉的诗歌,我感觉当我阅读这些诗歌时就像我在书写它们一样。不管原因是什么,我坐在那里,阳光在我膝头的书页上投下了长方形的阴影,越来越近,一瞬间我似乎觉得自己完全进入了艾米莉的大脑。我感受到她的韵律、词语在我的指端呼吸,她的敬畏和痛苦在我的心脏里跳动。我感觉到我对她的理解,作为一个女人——甚至,作为一个同辈中人,带着她的全部沮丧,她的惧怕,她的无权无势,以及她的勇气。和以前一样,狄金森似乎与我同在,感受到了我作为女诗人的痛苦——并且最终给我送来礼物。再一次,她成为我的姐妹,我的父亲。有了理解之后,想要表达的欲望随即而来,去阐明我所感知到的狄金森。我感受到狄金森与传统诗体韵律的挣扎,她像另一个人,另一个诗人,开始与我对话,我写《格律的幽灵》(The Ghost of Meter)这本书的灵感就诞生于那个时刻。
当我开始觉察到狄金森在诗体韵律上的主体性,我也同时觉察到她的雄心,跟我自己的各自独立,不会消亡。从这样的一种联系中,产生出了一种各自独立的意识,我从未从其他女人身上感受过这一点:从默雷(Millay)和蒂斯黛尔(Teasdale)到希尔达·杜丽特尔(H.D.)和毕肖普(Bishop)那里,我只是感觉到钦佩与欣赏,甚至热爱,或者参杂着批判;我跃跃欲试想去挑战她们,想写她们那样的诗,甚至想超越她们——但绝不是那种反抗,向某个能应战、不断应战,但不会被驱逐出去,永远不会走开的人反抗,那个永远与我各自独立却又与我在一起的人,那个因此而给了我一种语言的人。这就好像我认识到狄金森的强大和她的权力与我年轻的热情如此相配,于是我开始尊重她的独立空间——就算是反抗她,也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文学母亲对于我的根本意义所在——或许不是——此刻这正是我如何看待一个父亲的态度。
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地认识了狄金森,不仅作为一个同辈中人也作为一个他者,我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反抗她或者说至少改变她,我想,正是这个过程有助于我来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在我度蜜月之际有一种冲动让我开始动笔写下这首诗”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当时我脑子里并没有想到狄金森,但现在回头来读,从诗中似乎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它的“父母诗”(parent poem),借用我本科时的老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的这个词语,我的”威斯敏斯特”的“父母诗”就是”我为美而死”。 “威斯敏斯特”收录在我的第一部作品《前夕》(Eve)中,描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躺在一起,没有墙壁将他们分隔,显然他们不是兄弟而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威斯敏斯特
在这些过道和专注的长凳中间,
当夕阳把丝绸降下,透过栏杆状
回忆的光,传来你的低声召唤
发自石床,回声悠悠的玫瑰
绣上大理石身躯,你恳求道,
“这不是我的脸;把这麻坑石拿走。”
其他士兵仍握着僵硬的矛
无尽的视线望向屋顶。但我
曾目睹你崩塌的生活。你需要去死。
我阅读残忍的雕刻,在低矮的
山鲁佐德纪念碑上——如此设计
以拉丁语带领读者穿越——
永远逼近,等待着,引出渐枯的眼泪
给铅与石投下光环。尘埃写下巨大
冰冷的书页,推向,以沉默的黑色与金色,
你大理石床单的倒塌。单臂,你躺
在你丈夫身边,你日渐消瘦的手指分开
铺在你碎裂的乳头上,等待着石头
和时间去掩埋它们。石头会下跪。
这里,淤泥心的国王们和沙石身的公爵们,
在教堂,黑暗在你掌心,
死亡的时间已终结。这里了无生命;
我的夜晚正在抛弃有你躺着的夜晚,
那里她和他在一条过道上走向他。
尽管这首诗前三分之二部分是写给妻子的雕像(我现在甚至觉得,或许是写给我母亲的),在完成这首诗历经的年月中我决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在我的诗中,我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女性,不像狄金森的说话人,满足于在一种无语的石头的不朽状态中被永远地混淆为一个男性,甚至为此感到荣幸;第二,以此口吻,我诗歌中的说话人,尽管仍处于一种活着的死亡状态(那时我还未开始疗伤),她公然宣告她自己的夜是不同的,不同于那些男性士兵和异性伴侣主导的父权制的夜晚,他们都为那个大写的“他”服务(在书写《格律的幽灵》(The Ghost of Meter)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了韵律的意义,我当时没有采用抑扬格五音步,因为我尚未自觉地意识到这种传统格律的意义;现在,从某个角度来说这首诗歌也可以被解读成一首关于被传统格律禁锢的作品。)
当然最重要的是,“威斯敏斯特”这首诗的末行以大写的S暗示了女性主体,映射了当时正在我体内生长的女性中心主义精神。也许正是这种精神的涌现使我得以跟狄金森分开,得以反抗她,不是以对我的母亲们和母亲诗人们所怀有的无限尊敬,而是以我面对父亲的孩子所采取的挑战姿态。我经常怀疑对男性上帝的普遍信仰与男人所反对的自由以及彼此分离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上帝父亲永远都会爱和接受男人,男性会被理所当然地合法化,无论他们是怎么看待其他男人,也无论他们如何对待彼此。或许,我曾经思考过,在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女神或女性上帝形象,这直接地或间接地导致了在我看来许多女人在其生命中的母性匮乏,更使得许多女人,包括在竞争中,不愿意去考验或削弱与其他女人的纽带。
如果不是由于这种女神中心主义的观点(在写上述诗歌的同时我发现了它),我不知道我还能否发现、探索甚至逃离狄金森。我再一次在我和她的两首诗中发现了联系,两首诗都着重描写了一个微小事物由小变大的现象:狄金森的“我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当我死时”(“I heard a Fly buzz -when I died -”)和一首收录在我早期诗集《前夕》 (Eve)中的 “在紫罗兰里面”(“Inside the Violet.”)。就像“我为美而死”和“威斯敏斯特”一样,这两首诗都描写了一种诡异的凝固的动作。但在“我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当我死时”和”在紫罗兰里面”这两首诗的最后一节中,视角是完全内化的,不是聚焦于墓碑和尸体的意象,而是聚焦于外部世界的离奇转化,即脆弱的意识从自身分离然后附身在微小的事物上,就像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形预兆。
I heard a Fly buzz-when I died-
The Stillness in the Room
Was like the Stillness in the Air-
Between the Heaves of Storm-
The Eyes around-had wrung them dry-
And Breaths were gathering firm
For that last Onset-when the King
Be witnessed-in the Room-
I willed my Keepsakes-Signed away
What portion of me be
Assignable-and then it was
There interposed a Fly-
With Blue-uncertain-stumbling Buzz-
Between the light-and me-
And then the Windows failed-and then
I could not see to see-
我听到一只苍蝇嗡嗡—我死的时候—
房间里沉寂无声
就像大气一片沉寂
等待风暴再次来袭—
四周的眼睛—已将它们拧干—
气息已稳稳地凝聚
为那最后的一击—国王
被见证—就在这房间里
我馈赠了最后的纪念品—签字
赠送了我的那一部分
能转赠的一切—就在此时
插进来一只苍蝇—
以蓝色—颤悠悠—磕磕碰碰的嗡嗡—
在亮光—与我之间—
然后窗户消散—然后
我看不见看—
(王柏华 译)
“在紫罗兰里面”
长长的树篱旁我父母的车道上,
沙砾日日等待他们的轮胎将它
碾开,在树篱旁那窄窄的一条
土地里,保存着土壤的肥厚秘密,
不让移动的太阳得知,我认识
一株紫罗兰。它一直长在那里,
在巨大而灿烂的树叶的阴影里
耷拉着它多节的肩膀,皱巴巴的头
垂向地面。
一天我蹲下
发现它的眼睛比以前近了许多,
我朝它里面望去。我的眼睛遗失在
我之所见,那荡着回声的原始深处,
虽然我的双手还停留在车道世界
它的搏动在我周围放缓,如喧声的太阳
将所有的砾石粉碎成阴影
并朝土地击打。紫罗兰的内部逼近;
它的心向我窥视,抓住我就像
抓住一株紫罗兰。当它黄色强壮的
喉咙转向我,打开就像打开一扇门,
内部的光自一轮沉默的太阳喷涌而出,
淹没了我的脸并塞满了我的眼睛,直到
我不再向紫罗兰里面看。
在两首诗中,说话人都被微小事物不知不觉地吸引,看似无害的微小事物却突然向她扑来并主导了她的意识,她的感官甚至她的自我感知。说话人凝视着紫罗兰的心,就像狄金森诗里的说话人聚焦于自己庄严的死亡场景,忽然间发生了反转,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行为的主体了。在“我听到一只苍蝇嗡嗡—”中,临终之景被荒凉的杂乱无章感取代了,而“在紫罗兰里面”中,主体转换的意义被进一步扩展:一种自然视角的萨满教式的觉醒,紫罗兰成为了真正的主体,诗歌的感知者。这两首诗都重述了拒绝被拘囿于界限之内的经历,当然界限感的缺失正是乱伦受害者的一个主要症状。在两首诗中都同样发生了对主体的侵犯;如果说狄金森的笔调或许带着某些狡黠和虚无主义的幽默,那么“在紫罗兰里面”,转换更无痕迹,而且多了一些对界限感缺失的精神上的积极辩解的可能性。它似乎是一个根本上的转变,不仅受女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也受到20世纪末的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以及佛学影响下的精神融合,这一切使得”在紫罗兰里面”中的视角转换有了更充分的实现。
这种反抗式的关系在我第一首明确献给狄金森的诗歌中更加明显;这种挑战虽然微妙,却的确存在:
悼念
“你会找到它 — 当你尝试死亡”
——艾米莉·狄金森
从我不能过的所有生命中,
我选定了一个
让它阴魂不散地缠着我直到让出边界
把我单独留下。
一个生命将会通过我的声音消散
让我变得像一块石头,
飘零的树叶可以沉落
于石头之上,而不是将它淹没。
这种经过细心平衡的关系所呈现的亲密感既是相互抗衡的也是彼此依赖的;这首诗的风格起初太接近狄金森,出版方坚持让我修改到不那么狄金森为止。“选定”(“elected”)是狄金森最偏爱的一个词语,我还是追随了她的脚步,采用了这个词;但,无论选定或不选定(elected or not),这首诗宣告,她已不再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了,我的诗歌想象力已经强大了,足以将她的影响力移出边界。经由我的声音,她消失了——这既是因为我有我的声音了,也是因为它在我的声音之内——我摆脱了独立了,通过反抗她而变得强大,坚定如磐石,再也不会被飘落的树叶掩埋。
我其实知道我在保持自我尊严和身份的同时与狄金森建立起一种有意识的亲近关系,这是任何男性诗人都无法相比的,对其他女性诗人我也从未采取过对狄金森的那种反抗和逃离的态度,尽管我即将翻译萨福(Sappho)而且希望在文学影响上继续历险。能够形容这种亲密又分离,尊重又反抗的关系的最佳词汇便是“父亲”。几十年来我一直对俄狄浦斯情结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质疑,如今我开始反思,或许有某种类似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构成了我与狄金森关系的一部分动力。也许哈罗德·布鲁姆,我读本科期间的老师,对“影响的焦虑”的观点归根结底是正确的,虽然作为一名女性我当时觉得我被他的理论拒之门外了;也许与我们的先驱诗人作斗争(假设我们在经历文化羞耻和失忆症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找到他们)确实会使人坚强,就算是女性诗人。
如果是这样,那么此种模式在我身上则表现出一种反讽的变形。在女性层面上,我对狄金森产生了受伤的亲密感,并且学会了如何去认可和尊敬她的伤痛中的分离。有些悖反的是,艾米莉·狄金森之所以成为我文学上的父亲也许是因为她曾遭受过家庭成员的侵犯,有可能是她的亲生父亲,像佩瑞曼(Perriman)推测的那样,或者是另有其人,如果此事确实发生过的话,此人滥用了父权社会给予的特权,也就是父亲们的特权。但也许这不比其他任何文学影响更悖反,一个个体的声音和出场继承了一种文学传统同时又摧毁了它,这神秘的过程使得我们书写的每一个文字都背负着一种生与死的较量。
富兰克林(R. W. Franklin)编《艾米丽·狄金森诗集》(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三卷本。Cambridge, MA:Harvard UP,1998。引用时根据诗歌编号(缩写为Fr)。
哈罗德·布鲁姆(Bloom, Harold) 《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Oxford,Eng.: Oxford UP, 1997
露易丝·博根(Bogan, Louise) 《美国诗歌成就》(Achievement in American Poetry),New York, NY: Gateway Editions, 1962.
安妮·芬奇(Finch, Annie) 《前夕》(Eve),Brownsville, OR: Story Line P, 1997.
阿博·安(Ann Arbor) 《格律的幽灵:美国诗歌中的文化与韵律》(The Ghost of Meter:Culture and Prosody in American Verse), U of Michigan P, 1993.
《我的母亲狄金森》(My Mother Dickinson),《诗歌的身体:关于女人、形式及诗学自身的散文》(The Body of Poetry: Essays on Women, Form, and the Poetic Self),阿博·安(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3.
露丝·欧文·琼斯(Jones, Ruth Owen)《“邻居—朋友—和新郎”——威廉·史密斯·克拉克,爱米莉·狄金森笔下的主人》(“Neighbor-and friend-and Bridegroom-”:William Smith Clark as Emily Dickinson’s Master Figure),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11.2 (2002): 48-85.
温蒂·K· 佩瑞曼(Perriman, Wendy K),《受伤的鹿儿跳的最高:乱伦对艾米丽·狄金森生活及诗歌的影响》(The Wounded Deer Leaps Highest: The Effects of Incest on the Life and Poetry of Emily Dickinson),Cambridge, Eng.: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6.
❶安妮·芬奇(Annie Finch),诗人、作家,荣获多项文学奖,已出版18部著作,代表作为《苏格兰的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cotland)、《前夕》(Eve)和《日历》(Calendars),最新作品为2013年出版的《密咒:新诗旧作集》(Spells: New and Selected Poems)。同时她对非虚构类散文作品、戏剧、歌剧剧本(opera libertti)传记及诗歌翻译等领域也有所涉及,曾出版《诗歌的身体:论女人、形式及诗性自我》(The Body of Poetry: Essays on Woman, Form and the Poetic Self)等评论性散文集。此文”My Father Dickinson:On poetic Influence”原发表于《狄金森学刊》(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2008年,总第18辑第2卷。由梅圣滢和齐悦合作翻译,经复旦大学文学翻译工作坊“奇境译坊”学术组讨论,吸取了部分同学的修改意见,最后由王柏华老师逐句细心修改、加注并审校。特此致谢。——译者注
❷狄金森生前留下了三封写给“主人”的充满激情和痛苦的书信,学界简称“Master letter”,此外,狄金森至少有七首诗作献给“主人”。此人很可能是她心目中的爱人,他究竟是谁,一直没有定论,经常被提到的两个主人人选是《春田共和报》的主编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费城牧师沃兹沃斯(Rev.Charles Wadsworth),但谁也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露丝·欧文·琼斯(Ruth Owen Jones)的文章《“邻居—朋友—和新郎”——威廉·史密斯·克拉克,爱米莉·狄金森笔下的主人》(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ume 11, Number 2, 2002)提出,狄金森的“主人”是她的邻居、阿默斯特学院的植物学老师威廉·史密斯·克拉克,他与诗人的父亲爱德华·狄金森一起建立了阿默斯特农学院。克拉克拥有阿默斯特当地最专业的花房,充满自来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琼斯认为,狄金森对植物异乎寻常的热情似乎与她对克拉克的恋情有关。另外,狄金森生平、书信和诗歌中的若干细节都与克拉克有着千丝万缕的隐秘关联。不过,《狄金森的激情》和《狄金森花园》的作者朱迪思·法尔(Judith Farr)认为,虽然琼斯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她的基本观点和若干论据或许是站不住脚的,另外,法尔指出,另一位“主人”人选鲍尔斯对园艺的兴趣也十分浓厚。——译者注
❸本文收入论文集《格律的幽灵:美国诗歌中的文化与韵律》,见参考文献;后更名为《母亲狄金森:如何创造诗学传统》(“Mother Dickinson,How to Create a Poetic Tradition”,收入专著《诗歌的身体:女性、形式及诗学自身》(The body of poetry: essays on women, form, and the poetic self,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53-58)——译者注
❹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1831-1885)生于阿默斯特,儿时就与狄金森相识,后离开阿默斯特。1866年起,经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大西洋月刊》撰稿人,狄金森选定的“导师”)介绍,海伦了解到狄金森的诗歌创作,并一直积极鼓励她发表诗作。1870年代起,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学者们发现,在狄金森生前,只有海伦充分认识到她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海伦后成为专职作家,发表小说《罗蒙纳》(Ramona,1883-1884)等,被同代人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当代女作家。——译者注
❺弗朗西丝·萨根·奥斯古德(Frances Sargent Osgood。1811-1850),19世纪40年代中期最受崇敬的女诗人之一,属狄金森的前辈诗人。其作品以爱情诗居多,也因与作家爱伦·坡诗歌往来而出名。——译者注
❻丽迪雅·西格妮(Lydia Sigourney,1791-1865),19世纪上半期女诗人。其作品的主要主题包括死亡、责任及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译者注
❼露易丝·博根(Louise Bogan,1897-1970),美国国会图书馆第四位桂冠诗人(1945),多年任《纽约客》杂志诗歌编辑。在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有一批诗人坚持抒情传统和技法,被称作“反动一代”(Reactionary Generation),或“小诗人”(Minor Poets),博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译者注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