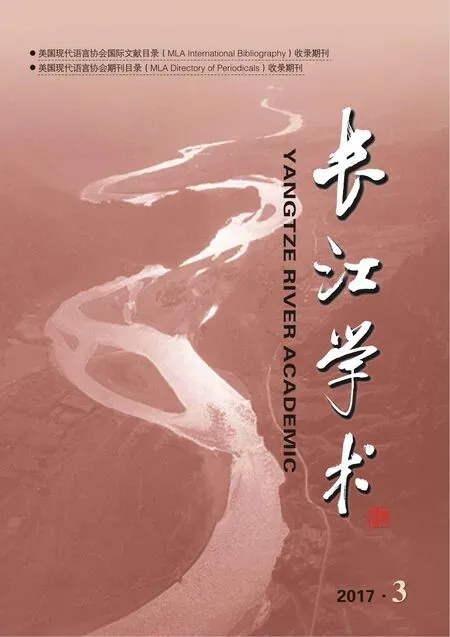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雷马克热”
——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考察
彭林祥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雷马克热”——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考察
彭林祥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1929年至1931年间,中国文坛出现了“雷马克热”:先是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抢译,稍后又迅速引进并上演《西线无战事》的同名话剧和电影,紧接着又出现抢译《西线归来》的大战以及《雷马克评传》,以及在此三波热潮期间雷马克作品经历了肯定、批判、否定等评价,呈现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复杂多元的文学趋向彼此颉顽互竞的“时代镜像”。“雷马克热”的出现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也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及时输送了艺术资源。
雷马克热 《西线无战事》《西线归来》 反战文学
1927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作一战结束以来他一直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他仅用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但手稿却在抽屉里搁置了半年。最先在德国的《福斯报》上连载,随后做了一些修改,于1929年1月31日由柱廊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出版。连载期间,《福斯报》的销数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小说初版五万册。即告售罄,并迅速在多国引起了轰动。到1929年7月,德、美、英、法四国销数如下:德国,70万册;英国,15万册;美国,17万册;法国,18.5万册。此外荷兰、瑞典、丹麦、挪威、匈牙利、西班牙、捷克、波兰、意大利等国俱有译文。1929年6月开始,远在东方的中国文坛也卷入对雷马克及其小说的译介,迅速在中国文坛出现“雷马克热”。德国文学在中国文坛影响,甚至“维特热”和“歌德热”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而“雷马克热”却鲜为人知。笔者据期间的书刊广告(影剧广告)、评论文章以及新闻报道等从四个方面力图再现这场文化界持续三年多的热点事件。
一、《西线无战事》的抢译及评介
30年代的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西线无战事》在欧美诸国轰动并热销,迅速影响到了上海文化界,上海的西文书店也渐次出现了德译本、英译本,而通晓英、德文的读者,如林疑今和马彦祥,二君自会捷足先登。而《西线无战事》小说本身深具吸引力,并在欧美诸国半年时间内销数甚巨,自然也让中国出版界看到了中译本的市场前景。所以,林疑今和马彦祥读到英译本后决心翻译此书。
林疑今曾回忆《西线无战事》的翻译过程:“有一天,从《申报》上看到雷马克《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的评论介绍,设法买到一部英译本来看,一下子就给紧张故事吸引住了,就大胆尝试翻译。……凭着一股冲劲,日夜赶译,深夜人疲倦时,就用冷水洗脸冲头提精神,工作其实非常粗糙。”林疑今说的应该是1929年6月1日《申报·艺术界》刊登的署名曼如的书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文中对该书有极高的评价:“《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可以算是巴比塞的《火线下》以后最伟大的战事小说……这部小说表现了步兵的灵魂,而且文字直率朴美,如史诗。作者用这样的文字,毫无浅薄地感伤地,暴露了战争的深巨的恐怖和牺牲,以及难以相信的狂暴和愚蠢,同时又写出了那些背着来福枪和行囊的人的淡漠的态度和幽默的趣味,所以全书非常地有力而且动人。”应该说正是这样的激赏,诱使林疑今去购读英译本,从而有了翻译的想法。尽管已无法考知林疑今开始翻译的具体时间,但应该不会早于1929年6月中旬。而马彦祥动手翻译该书的时间几乎与林疑今同时。马彦祥写于1929年10月28日的《〈西线无战事〉序言》中说:“以两个人三个月的时间才将这本书译完……洪深先生就德文原本校对了一遍,又几乎费了一个月。”据此推算,马译本开始翻译的时间估计也在6月下旬。尽管林、马二人开始翻译小说的时间几乎相同,但进展却有快慢。林译本在9月下旬已经完成,立即送交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为了便于促销,译者还请其五叔林语堂为该书写了序(序言完成时间为1929年9月27日),10月下旬,林疑今的译本《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初版问世,11月上旬再版。马彦祥的翻译进展则慢得多,加之翻译完后,他的老师洪深又依据德文原本校对,直到10月底才完成译稿。
林疑今、马彦祥二人翻译《西线无战事》一事很快都为对方所知,双方展开了一场抢译活动。眼看林译本出版在望,为了争夺读者,马彦祥抢先在《北新》第3卷第17期(1929年9月16日)刊出了图书预约广告,其中有如下信息发布:“全书约二十万言,三百余页,精印一厚册,定价大洋一元五角,预约六折,每册大洋九角,准于双十节左右出书,预约自即日起至双十节止,期满即按定价发售。外埠预约寄费加一。预约处:上海四马路光华书局北新书局。”紧接着《申报》(1929年9月25日、26、10月6日)连续多次刊出了该书的预约广告。实际上刊出预约广告时,书远未完成(马彦祥为译本写的《序言》的时间为10月28日)。而林译本直至出版前夕的10月20日才在《申报》首次刊出了宣传广告,10月26日再次刊出广告,宣告《西线无战事》的问世。两周以后,11月9日《申报》又刊出了再版广告,可见林译本销路颇不错。而马彦祥终于赶在1929年11下旬出版了名为《西线无战事》的译本(为了符合预告的时间,在译本的版权页上印着1929年10月发行)。此译本初版3000册,书前有马彦祥的《序言》和《本书作者小传》(译自英译本),书后有洪深的《后序》。尽管马译本问世时间晚于林译本约一个月,但在译本的质量上,洪深不但修改过马彦祥的翻译,还拿德文原本校正,翻译上的精益求精,使得马译本质量颇高,初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到1932年11月上海现代书局出至第9版(《西线无战事》以平等书店名义印行过三版后,版权以1200元转让给现代书局,书局接续其版次继续再版)。而林译本,出版后的销路也颇不错。曾主持水沫书店编务的施蛰存对此书的出版过程有回忆:“我们把林疑今的译稿接受下来,做好付排的加工手续……我们的书在11月上旬出版,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大广告。(施的回忆不确,水沫书店的广告载《申报》1929年10月20日,笔者注)……以后,在五个月内,再版了四次,大约卖了一万二千册,在一九三〇年的中国出版界,外国文学的译本,能在五个月内销售一万多册,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这本书,恐怕是水沫书店最旺销的出版物,由这本书带销的书,也有三五千册。”
译本争先出版,同时介绍雷马克以及《西线无战事》的文章也纷纷见刊。自1926年6月至当年年底,就有十余篇介绍或评论文章(见后面的具体论述)问世。如《新文艺》创刊号(1929年9月15日)刊出了《一部震动全世界的小说:西方前线上平静无事》;《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期(1929年10月10日)上刊有《德国最近出版的两部欧战小说》;《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1929年10月)上又有《关于〈西部前线平静无事〉》;《语丝》第5卷第34期(1929年11月4日)也刊载了赵景深的书评《〈西方前线平静无事〉》。此外,《申报》《民国日报》《青春月刊》《真美善》《出版月刊》等报刊及时刊载了该小说的介绍或评论。可以说,自1929年6月的大半年时间里,《西线无战事》译本接连出版,以及该小说及其译本广为评介,成为了中国出版界和文学评论界的热点话题。
二、《西线无战事》话剧、电影的上演
如果说《西线无战事》的评论和译本的接连问世成为“雷马克热”的第一波,那么《西线无战事》话剧及电影在中国的陆续上演就是“雷马克热”的第二波。
《西线无战事》在世界文坛影响甚巨,小说本身在写作也有剧本的特点。正如雷马克本人所说:“也许因为我想当剧作家而没有成功,……我的所有作品写得都象是剧本。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所以,话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小说问世不久就介入了这部作品。但相对电影拍摄的时间而言,改编成话剧上演无疑会快得多。所以,《西线无战事》的话剧最先与观众见面,最先把《西线无战事》搬上戏剧舞台的是日本戏剧界(英、美诸国也有小说改编的话剧上演,但晚于日本)。由于中国文坛对日本戏剧界排演《西线无战事》多有报道,借此我们也大略知道日本排演该剧的情况。“在日本,也由秦丰吉译成日文,而且有人编成剧本,抢着在舞台上排演,大家万人空巷争先恐后去鉴赏了。”日本戏剧界最早上演该剧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1929年11月底。1930年3月出版的《出版月刊》第2、3期合刊中对日本的演剧情况有更详细的报道:“在日本,这部书也已被改编为戏剧,由新筑地剧团连续于十一月末在帝国剧场及本乡座表演,两星期内吸收了二万的看客。最近又在新桥演舞场重演,依然是天天满座。此剧的舞台监督为高田保氏,舞台装饰者为吉田谦吉氏,俱为日本戏剧界闻人。”
正是《西线无战事》对当时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战争的悲惨一定可以打动年年受兵火劫害的任何人。帝国主义的杀人可以惊醒正酣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的中国民众。”与日本戏剧界联系颇多的上海左翼戏剧团体艺术剧社也把目光瞄准了《西线无战事》,该团成员陶晶孙迅速翻译了日本作家村山知义改写的剧本《西线无战事》。为了尽快排演,剧本在数天内译出,江南书店在十天内就印刷出版了。由于江南书店印刷此剧本主要用于排演,加之江南书店很快就被查封,陶晶孙改译的《西线无战事》剧本未见公开出版。剧本内容上与原著有较大的变化,“在整个意识方面,却大有出入了。……它尽够可以给观众体验一些自身的——不,是现社会的切身大问题;和暴露些布尔乔亚所操纵着的,战争提线戏了”。
经过一两个月的紧张排练,上海艺术剧社在1929年3月第二次公演中演出了《西线无战事》。由于《大众文艺》《出版月刊》等报刊都有该社公演的报道,从中大致可以了解该剧的公演情况。公演的具体时间为3月21日至23日,连续三天。票价有八角、六角两种。地点为北四川路横滨桥日本人经营的上海演艺馆,“这是个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小剧场,还得按日本剧场规矩‘席地而坐’,但它拥有上海唯一的旋转式舞台。这种转台可以较快地装置好比较复杂的场景,及时转出”演出剧目共两个,一个是《阿珍》(五幕话剧),另一个是《西线无战事》(三幕11场)。夏衍担任舞台监督,并首次创造性地用红绿灯指挥的办法来指挥演出。《西线无战事》由沈西苓担任导演,许幸之任舞台装置,主要演员有刘保罗、唐晴初、李声韵、陈波儿、石凌鹤、王莹等,参演演员五十余人。“开幕前先放映了一段欧战电影,并配有文字说明,舞台灯光的渐明、渐暗也是首次使用,音响效果也做得很好。”由于上海艺术剧社所演剧目比较“左倾”,演出内容“含着充分的宣传意味,做政治的工具”,触怒了当局,于1930年4月28日被查封,话剧《西线无战事》未能继续上演。
正当话剧《西线无战事》在中国上演之际,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正在争分夺秒地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将其搬上了荧幕。电影编剧为马克斯威尔·安德森,导演为路易斯·密而斯顿。影片以普通士兵保尔的视角,运用写实的格和细节描写,成功地表现了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该影片于1930年5月17日在美国上映,一经上映就吸引了大量观众。中国电影界也不甘落后,在影片未映之前就曾予以介绍。如1930年5月12日创刊的《电影月刊》就刊有《〈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之演出》,配剧照4张。《电影月刊》第2期又刊有《〈西线无战事〉摄影场游览记》,并配有剧照8张。1930年9月中旬初,中国电影界成功引进了这部影片,并迅速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影院放映。《申报》从9月19日至10月4日半个月时间几乎天天有《西线无战事》的电影宣传广告。电影在上海反响热烈,《申报》在1930年9月22日有《西线无战事开映盛况》的报道:“9月21日在本埠南京大戏院开映,于上午九时许,其全日戏券已经售罄,为海上大影戏院从来未有之盛况。”凌梅写的影评《雷马克与〈西线无战事〉》中也曾有记录:“最近在上海的南京大戏院公演着它的影片了,每天卖座极盛,连演了四天,还是拥挤不上,在中国,这种情形实在可说是难能可贵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这部《西线无战事》是怎样地震荡着中国人的心啊。”甚至远在苏州的一些中学生还曾专门坐火车去上海看这部电影。周曙天在《从〈西线无战事〉说到武力抗日》中也曾叙及南京放映该片的情景:“这部影片又运到中国了,而且又流行到首都的南京,现在正在世界和南京的两大戏院中开映。前日夜间,我一时也‘不知亡国恨’了,跟着人家一股气儿跑到世界大戏院,从万头钻簇之中挤进去,抢得一个座位坐下来,将全片看完。”
可见,《西线无战事》的话剧和电影在中国接连上演,让雷马克其人其文从出版界蔓延到戏剧界、电影界,使“雷马克热”持续升温。
三、续作《西线归来》的抢译及传记的问世
《西线无战事》出版以来,引起了世界文坛大轰动,而雷马克其人其文并未受到欧美诸国的礼遇。德国国内的一些人大肆攻击这部小说,污蔑雷马克是犹太人,认为他在战争中看到的只有恐怖和污垢,小说继而被政府当局禁止发行,雷马克在银行的存款也被政府扣留,小说的版税也被收取重税。美国芝加哥政府禁止英译本的发行,英国曼彻斯特的教育会也提议加以禁止,奥地利的军营图书馆禁止收藏《西线无战事》;在法国虽然未遭禁止,但发卖却不自由,日本的剧本几乎被政府禁止排演;等等。小说问世后待遇不公,因而虽有美国联合通讯社竭力催促,雷马克起先并不打算续著,但一些读者特别是士兵的来信让他感动,后来他改变了想法,开始写第二部作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西线归来》。1930年12月13日开始,首先在美国《柯里尔》周刊上连载。《西线无战事》的姊妹篇《西线归来》的发表可谓盛举空前,共有十六国的十八家报纸或杂志同时连载。连载结束之后,各国又迅速地开始出版各种语言的译本,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在1931年也迅速掀起了“雷马克热”的第三波。
实际上,早在《西线归来》动笔之前,中国文坛对于雷马克的续著已有零星介绍。1930年7月,杨昌溪发表了《雷马克的续著及生活》一文,对雷马克的续著就有如下预告:“最近他开始写第二部作品,目的并不是要想获得令名,因为他决定要帮助普通人,在柏林接到的许多兵士们给他的信使他得着一点安慰,他不得不把兵士们在战后的生活写出,替那些与他同在炮火下残留的灵魂道出心中的苦闷。”本年年底,杨昌溪又在《雷马克的新著》中对即将问世的小说有进一步的介绍:“此书系描写德国青年军人战后的生活,主旨也与《西线无战事》相同,刻已定名为《同伴》(Kamerad),俟在联合通信(指美国联合通讯社,笔者按)有关系之世界各国新闻纸刊登后,再出单行本。”
这些预告和介绍早已吊足了中国读者的胃口。《西线归来》在美国《柯里尔》连载结束后,鉴于《西线无战事》的成功经验,中国出版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翻译者自然也不乏其人。于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抢译《西线归来》大战在1931年的上海出版界上演。小说连载在1931年2月才告结束,而在3月16日的《文艺新闻》上刊载的《呜呼“后来者”迎合市场的投机》中曾记录下当时已经预告的七种中译本,分别为:杨若思、王弢合译,名《战后》(光华书局);开华书局拟出,名《退路》;杨昌溪、林疑今合译,名《西线归来》(神州国光社);沈端先译,名《战后》(南强书局);张资平校译,名《归来》(平等书店);某留日学生译,名《后方》(南京《中央日报》);译名《西线有战事》(拟刊登《马来亚》半月刊)。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众多译者争先翻译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可能只有雷马克的《西线归来》享此殊荣。预告有七种,最后问世的有四种,具体如下:1.《退路》(上册),冯次行、袁文彰译,开华书局1931年3月初版,列为“新时代文艺丛书”之一,书前有张资平序。2.《西线归来》,林疑今、杨昌溪合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4月初版。据英译本转译,书末有林疑今的后记。3.《战后》,沈叔之译,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8月出版,据日译文转译,书末有译者后记。4.《战后》,王海波、杨若思译:光华书局1931年10月初版,据德文原著,并参照英、日译文译出,书前有贺扬灵序《写在〈战后〉前面》,及译者的《关于雷马克》,书末附《译后的话》。尽管只出版了四种,但是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接连推出四种不同的中文译本,这足见雷马克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力。
与抢译《西线归来》同时,报刊上这部小说的介绍和评价文章也不断问世。如有杨昌溪的《雷马克新作获得佳评》和《〈西线无战事〉与〈战归〉》。除了对其小说的介绍、评论外,对于雷马克其人的有关情况的报道或介绍也连篇累牍,十分热闹。如有《雷马克失了自由》(《文艺新闻》第4号,1931年4月6日)、《雷马克与战争文学》(《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1期,1931年4月10日)、《雷马克眼中的法兰西》(《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1期,1931年4月10日)、《雷马克说:死者的遗言是不再有战争?》(《文艺新闻》第9号,1931年5月11日)、《雷马克的第三部创作》(《青年界》第1卷4期,1931年6月10日)、《雷马克与克雷马》(《现代文学评论》第2卷1、2期合刊,1931年8月10日)、《雷马克晤谈记》(《现代文学评论》第2卷1、2期合刊,1931年8月10日),等等。
在“雷马克热”三年多的时间里,杨昌溪全程参与并为造成中国文坛的“雷马克热”(据现今能查阅到的刊物统计,在此期间,他发表或翻译关于雷马克的文章就达20余篇,还与林疑今合译了雷马克的《西线归来》)做出了突出贡献。除此之外,他还根据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报纸、杂志有关雷马克及其作品的介绍评论,结合国内的《申报》《真美善》《现代小说》《大众文艺》等报刊有关雷马克的报道,于1931年3月完成了6万余字的《雷马克评传》(上海现代书局于1931年7月初版)。全书除《序》《引言》和《后序》外,包括“欧战前后的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之创造”“《西线归来》之本事”等十章。由于作者对中国文坛的“雷马克热”颇为熟稔,在评传中也详细介绍了《西线无战事》《西线归来》在中国文坛的反响等情况。在笔者看来,它不仅是一本评传,更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雷马克热”一次及时的梳理与总结。
四、雷马克作品评论的众声喧哗
由于雷马克的小说涉及战争主题,使得中国文坛在谈论雷马克的小说(包括改编的戏剧和电影)时对“战争”“战争文学”“反战(非战)文学”等都发表了看法,这也是“雷马克热”中重要组成部分。但在30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内阶级矛盾剧烈,批评者审美、政治(阶级)立场迥然不同,这场讨论因而众说纷纭。需要言之,“雷马克热”期间,中国文坛对雷马克的作品有肯定,也有批判甚至否定,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梁实秋在《〈西线无战事〉》的书评中首先就指出了小说的缺点,认为全书没有一个连贯的有组织的布局,显得结构松散。但对于小说的优点他也不吝赞美之词,认为作者描写的手段确是极能动人,写枪林弹雨中兵士的恐惧、放荡、戏谑、友谊,都很深刻,他写伤病的痛苦,慈母的悲哀,都能打动读者的至情。所以,在他看来,尽管小说中并没公开提倡和平,直接诅咒战争,但作者能保持客观描写的态度,所以这本书胜过肤浅的“非战文学”。
马彦祥的观点颇类于梁实秋,他在《〈西线无战事〉序言》中说:“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态度是何等的诚恳。他并不像其他作者借着书中人物来发表‘怎样愿意后人记好了这次的教训,不再让战争发生’之类的爱国主义者的论调,他只将他冷静的观察所得,加以选择后,一件一件的事实用他最忠实而最简洁的笔,细细地叙出来,丝毫不掩饰,丝毫不夸张,而且在真理之外丝毫不偏爱地。但是在每一页纸上都浸透着战争的恐怖,充满着一般曾经参与过战争的人们的大声疾呼。”朱端钧在《〈西线无战事〉后序》中则以文学的道德目的来评价小说的价值,他认为雷马克尽管未明确地鼓吹非战,甚至没有取嬉笑怒骂嘲弄挖苦的态度描写战争,但是读了他的战争小说却可让人有“放下屠刀”的想法。与梁、马、朱三人的论调相近的还有林语堂,他在《〈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序》中认为,雷马克的书能轰动一时就是他能把战争的真相及兵士的感想活跃地赤裸裸地描写出来,比如用枪尾刀戳人须戳在腹部,不在脑部等都是动人的地方。他认为雷马克所写下的却是人类史上真真实实的一页史实。
杨昌溪在《雷马克与战争文学中》中探讨了一战所引发的法国、英、德、匈等国的非战与讴歌两派的战争文学,随着一战的结束,非战文学成为战争文学的主流。在他看来,在非战文学中,巴比塞的《火线下》显然高于雷马克的作品,雷马克的仅仅停留在暴露战争的事实和罪恶,而巴比塞“在一切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中算是第一部由事实的昭示指示人们一条永久的光明之路……在战争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上加以捣灭”。与杨观点类似的还有张文实的书评《〈西线无战事〉》,他也认为巴比塞在《火线下》中对于战争的认识是正确的,而雷马克对于战争的解释是浅薄的,“它只是一部暴露战争的作品,对于战争的中心问题,是没有把握的”。但也有论者把雷马克视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生活的体验,阶级的意识,热情的激荡,和文学的天才,这一切使他在20世纪文学舞台上,无产派写实主义运动中透露了头角。他写了一部小说,在动人的题名下,激动了时代的轮子,骚乱了历史的篇幅!”
华蒂则把雷马克的战争小说放在战争文学的发展史上给予新的评价,在他看来,一般的战争文学作品,往往容易流于过分主观化。虽说是取材于战争,但为了过分主观化的缘故,以致不是限于浮薄的夸张,就是流于亏弱的感伤。倘若过于抑制主观,则又往往成为虚伪的报告和简单的记录。而雷马克的作品“没有主观的教训,没有浅薄的感伤,没有难以置信的夸张,没有矫揉造作的记录,没有狭窄的偏见,没有私心的袒护。所有的一切只是最忠实的笔调把整个的战场的一切,展露在大众之前”。所以,他认为雷马克“在战争文学上开辟新的园地,创造了新的苗秧,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作品之时代意义和历史的评价是不容争辩的实际”。稍后,他又在《关于雷马克及其新作》中探讨了雷马克作品风行世界文坛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他描写的忠实和魄力的高强。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当不能不顾到一个更主要的,更富意义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这就是他代替现时代万千的大众,喊出了迫切的,强烈的心底苦闷和渴求”。
与上述批评者大体持肯定态度相反,也有批评者从阶级意识上分析雷马克的作品的不足。如《大众文艺》上刊载的《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西线无战事〉》中就认为雷马克的意识“不过是一个德国知识阶级被驱到战场的一个事实,自然说不到无产阶级的意识,给读者的整个感觉还只是一些模糊的苦闷,和在乎根底可以有反战狂情可以产生的材料,却还没有给读者们一个准确的解答”。祝秀侠在《战争·非战文学与西线无战事》中认为《西线无战事》“仅是一部‘暴露’战争的作品,对于战争的中心问题则还没有把握到。在作者意识方面,自然还是小有产者的意识,虽然作者用了许多自己的经验和历史放在里面,但毕竟也和其他泛泛地描写战争的小说一样”,“只是一本描写战争比较深刻,比较细腻的作品而已。意识方面还是不充实的”。甚至有批评者从民族或阶级的立场意识到雷马克作品包蕴的非战思想对目前中国的现实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副作用。赵铭彝就认为“《西线无战事》的非战思想,我们还不能不有些怀疑。……但如果是为‘正义’或是为我们的阶级底出路而发生战争,是不是也应该反对?……像这个漫无目的的非战思想,不是我们所应取的态度!”姚蓬子甚至认为《西线无战事》和《退路》宣扬的是一种麻醉性的非战论,必须揭穿这两部作品的假面具,“正如密砒一样,在甜味之中含有毒质的”。周曙天在《从〈西线无战事〉说到武力抗日》中则联系到中国此时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西线无战事》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的流行会削弱国民武力御侮的决心。
总之,在我看来,雷马克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坛所遭受到的肯定、批判、否定等,实际上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复杂多元的文学趋向彼此颉顽互竞的“时代镜像”。
五、结语
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坛对一位年仅30余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进行轮番抢译,并改编其小说为话剧上演,引进改编的电影等,这场“雷马克热”持续时间达三年多之久,这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并不多见。雷马克能如此隆重地被介绍到中国,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军阀互相混战,农村破产,城市经济发展也颇受掣肘,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尽管国民党在1928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围剿却越发激烈,普通民众对长期的战争越发反感,雷马克小说的反战主题契合了30年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既有持续的内战,又有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以及广大民众的心理需求。此外,“雷马克热”的形成既与世界各国舆论界和中国文学界的大肆宣传以及出版界出于经济利益的推波助澜有关,也与洪深、马彦祥、林疑今、杨昌溪等一大批翻译者、批评家的极力推动密不可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件”以后,日本对中国侵略加剧,中国人民被迫陷入保家卫国的战争。正如李今所说:“反思与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非正义的反战文学,显然与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抗日的现实需要不再合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反战文学自然在中国社会没有了市场,文坛对雷马克其人其文的关注急剧降温,尽管其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不断再版,甚至还不断出现新译本和零星文章,但对雷马克其人其文的关注已经很难达到昔日胜景。二三十年代之交文坛出现的“雷马克热”以及对战争文学的讨论为中国战争小说及时输送了艺术资源,从而催生了新文学史上一大批战争小说。如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庐隐的《火焰》、葛琴的《总退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张天翼的《二十一个》《仇恨》,周文的《雪地》《山坡上》,黑炎的《战线》,孙席珍的《战争三部曲》(包括《战场上》《战争中》和《战后》)等等。这些小说既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也对战争极尽嘲讽揶揄。直接或间接与“雷马克热”有关。
责任编辑:陈建军
Remarque Craze i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30s: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Advertisements Centered Peng Linxiang
Peng Linx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Guangxi,China)
From 1929 to 1931,“Remarque Craze”appeared i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Firstly,Competing for translation on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Secondly,the rapid int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of drama and film.Thirdly,Competing for translation of Return from the Western Front and Remarque Biography.During the three stages,Remarque’s works obtained affirmation,criticism negative evaluation,showing“era image”of the 30s when Chinese literary trendswere competing with oneanother.“RemarqueCraze”and i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hasmany other factors.Anyway,introduction of his works supplies Chinese literature of modern war with new resources.
“Remarque Craze”;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Return from the Western Front;Anti-war Literature
彭林祥(1978—),男,四川广安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生产、传播及接受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广告史论”(15BZW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