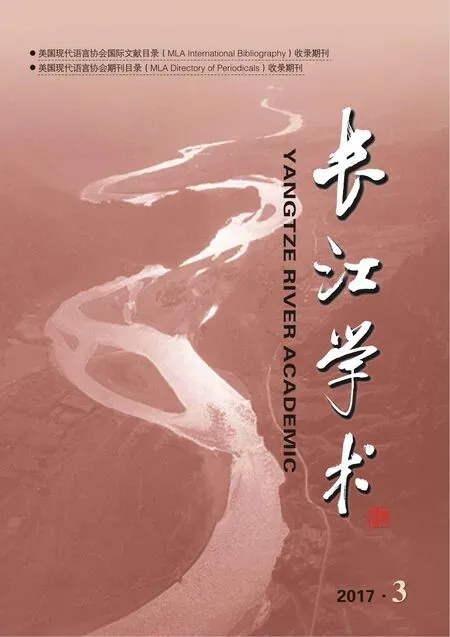经典的噤声效应
——谭恩美小说中的作者身份和文字书写
〔美〕丽萨M·S·杜尼克著 姚红艳译
(1.乔治王子社区学院,美国 马里兰州;2.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经典的噤声效应——谭恩美小说中的作者身份和文字书写
〔美〕丽萨M·S·杜尼克著 姚红艳译
(1.乔治王子社区学院,美国 马里兰州;2.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女性族裔作家的作品被收录于教学大纲很大程度是由于其有别于“传统”美国文学宏大的叙事方式。但是对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口语叙事模式及其作者差异性的过度强调,从某种意义上将之置于经典之外。对谭恩美作品的批评研究大多忽略了其文本当中书面文本以及中国母亲读写能力的重要性。《接骨师之女》这部小说对女性书写的文学特质的强烈关注表明,在书写和笔头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写作能力代表着比口述叙事更为重要、甚至更为有效的传承文化记忆和代际文化身份的方式。通过分析书面文本的重要性,本研究将展示谭恩美在作品中如何呈现书写能力和写作方式,以期揭示批评上存在的问题,即仅通过对口语传统的理解就确定其属于非西方叙事模式。对《接骨师之女》中作者身份的误读反映了在形成和应对文学经典时所必需的收录与排斥机制,以及在认识作品价值方面起到限制作用的噤声功能。
文学经典 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 口述叙事 笔头写作
在过去二十年里,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的小说《女勇士》,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MarmonSilko)的《仪式》(又译《典仪》或《仪典》)以及一批美国非洲裔女性作家的作品相对频繁地出现在大学课程大纲里。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被收录很大程度是由于其有别于“传统”美国文学宏大叙事方式。大学教师和文学批评家们都试图强调传统的口语叙事模式、特别是诸多族裔女性作品中出现的口述故事模式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同等重要。虽然对这些作家的关注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于文学的定义和理解,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作者差异性的过度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将之置于经典的传统概念之外或对立面之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局限性的结果是对于符合美国族裔写作模式的作品肯定其价值,而那些不符合这些模式的作家就被排除到我们的批评视野之外。这样,一些作家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重要作家,而另一些则被降格为流行作家
在美国亚裔女性文学的王国里,我们可以通过对谭恩美的作品的探讨,看到这一排斥效应。对谭的作品的批评集中在口述故事的对话性如何制造或联通双文化、双语言的移民母亲与她们第二代美国化的女儿之间的鸿沟。特别是自从汤亭亭的《女勇士》强调中国传统的“口述故事”是美国华裔女性叙事方式的主要特质以后,对这一口语传统的关注就成为对美国华裔女作家批评的核心。但是,就谭恩美作品而言,对口述故事重要性的批评关注限制了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对于谭恩美前三部小说《喜福会》(1989),《灶神之妻》(1991)和《百种神秘感觉》(1995)的研究,已经准确地确定了她的作品中的冲突范式,即中国母亲的口语叙事(即口述故事)与美国女儿对这种叙述方式最初抵制、最后接受之间的矛盾。对谭恩美作品的批评研究大多忽略了其文本当中有别于其他作家如汤亭亭的方面——书面文本以及中国母亲读写能力的重要性
通过《接骨师之女》(2001)这部小说来重新评估其作品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甚至修复这一批评上的缺陷。这篇小说对女性书写文学特质的强烈关注使我们意识到,在书写和笔头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写作能力代表着比口述叙事更为重要、甚至更为有效的传承文化记忆和代际文化身份的方式。此外,《接骨师之女》并非一部脱离谭恩美以前主题的全新作品,但是它代表了在她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的、关于身份和语言的、更成熟的处理方式
在谭恩美所有小说中,口述故事在说中文的母亲和说英语的女儿之间以及在操不同中国方言的个人之间产生了多层次的误解。作为一种语言策略,口述故事在谭恩美小说当中常常未能清楚地将说话者的信息传达给听众。一些评论家在分析谭恩美作品时,试图将口述故事的使用复杂化,但是他们未能看到读写能力和书面叙述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朱迪斯·凯撒(Judith Caesar)提出虽然谭恩美多话语的口语叙事值得注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说话者。遵循通常着重强调口语形态的论述程式,凯撒明确地提出,通过呈现中国移民口音明显、支离破碎的口语,谭恩美给他们的声音赋予了价值,正如美国非裔作家给予了黑人社区口语以价值一样
在“谭恩美和汤亭亭文本中的中国叙事符号”一文中,袁媛(Yuan Yuan)最能认识到谭恩美小说中口述故事的局限性:她论述道,口述故事体现了一种明显的缺失。在谭恩美的所有小说中,她笔下的人物强调她们在二战以后移民美国的经历侵蚀了她们的文化记忆。在她的作品当中,在中国出生的母亲试图将这些文化记忆以故事的形式告诉给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以使记忆永存,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对女儿们来说,这些故事仅仅依赖于母亲的记忆,并不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文本。因此母亲们对自己的故事不断修正,对出生于美国的女儿们通常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指涉对象被抹杀或丢失了。正如袁媛(Yuan Yuan)所论述的那样,“简言之,中国距离现在的记忆相去甚远,已然丢失,无法重获,只能通过遗忘而非记取的叙述方式加以呈现”
口述故事或整个口语交流所造成的问题,在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精美说自己不能理解母亲二战期间在桂林度过的那段日子。精美说她一直以为那个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童话”因为“故事的结局一直是不同的”。她母亲不断改动故事的结局以至于无法为精美提供一个可供识别和认同的故事。直到素云最后一次讲完故事时,精美才明白母亲到底试图告诉她什么。当精美惊诧地意识到这些故事一直都是真的,并向母亲询问故事里的婴孩后来的命运时,素云“想都不想就干干脆脆地说:‘你爸爸不是我的第一个丈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只有当母亲给故事一个可以认知的结尾,并将它置于一个她可辨识的叙事结构之下时,精美才开始明白故事的深意。
对素云的故事的误读和误解在谭恩美的小说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交流上的失败一部分是由于错误的翻译。翻译,正如李肯凡(Ken-fanLee)所指出的,“指的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而且还包括文化和心理上的互动”
这些由不同的叙事模式所导致的矛盾远非彻底失败,而是通过谭恩美对母亲们说教的刻画得到了某种缓解。在谭恩美的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中,翁温妮的叙述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这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即母亲必须教育女儿如何倾听,如何理解她的故事。在文本当中,温妮把那些“过于复杂”的过往和秘密告诉给了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但是她只能用并不娴熟的英语来讲述。温妮说她要告诉女儿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发生,为何不可能有别的可能”。在接下来的叙述当中,温妮用口述故事的形式讲述她自己的历史,但是在讲述过程中,她必须帮助女儿理解她支离破碎的英语和那些无法翻译的部分。当故事记录下温妮从孤苦童年到受虐之妻的人生时,叙述有意识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它所使用的语言上。
虽然温妮对女儿说的是英语,但是她必须教女儿那些当说出来的时候
(斜体为原文所示)没有对应翻译的中文。当温妮急需从她的嫁妆帐户里拿到钱的时候,她给表妹花生发了一封电报:“快,我们就要逃难了!”她继续解释资金的必要性,但是却被听故事的女儿提出的问题打断:什么是逃难。温妮没办法根据这个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于是她试着通过解释这个词的重要性来回答女儿提出的问题。她说:逃难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噢,美国话里中我还想不出有哪个词与这两个字的意思一样。汉语中,各种各样麻烦事都由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不,refugee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已“逃难”了,现在还活着。要是你幸免于难,你绝不愿再谈起你逃难的事。
这段文字展示了谭恩美为她的中国母亲所设计的声音:用生动的意象来平衡简洁的措辞以展现叙事。同时它还表明谭恩美笔下的母女在交流的过程中常见的困惑和误解。但是当她解释并进一步拓深“逃难”这个概念以后,她就可以在她余下的叙述当中使用这个词,以取代不那么确切的英文翻译。后来,当她告诉女儿恐惧如何能改变一个人时,她说“你只有到了逃难时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在你身上存在着”。虽然叙述当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是女儿开始能够从母亲的教导中理解它的重要性。因此,在谭恩美小说中,口述故事不能被看作是完全的失败,也不应该被忽略。但是不通过思考,口述故事是无法为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正常运作的。
在谭恩美小说当中,思考通过笔头文本这一媒介得以实现。例如,在《喜福会》中,中国方言的差异就异常明显:龚林达无法和未来的丈夫龚丁交流,因为他说的是广东方言。虽然他们同在一个班上学习英语,但是即便是这种交流模式也不能完全奏效,因为他们只会说“老师的英语”,即一些关于阿猫阿狗的简单陈述句。在英语课上,两人必须写中国汉字进行交流。林达将写字条看作他们关系的重要交流工具。她告诉读者说,“至少我们有一张纸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虽然林达和龚丁不能听懂彼此的中国方言,但是他们能读懂纸上写的中国字。虽然两人不能交谈,但是中国文字的普遍性使得他们能够跨越口语交际的界限清楚地交流。
书面文本的使用在林达和龚丁的关系中再次出现:他们用书面文本使恋爱过程更加顺利。安梅告诉林达,在电影里,大家在班上传字条,“然后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计划,给龚丁“传了一张字条”。因为他们在甜饼工场上班,可以控制运气纸条,女人们决定将讯息放到一个饼里来安排求婚。早前,林达和安梅都觉得这些运气条很有力量,又有点傻气,但是为她们自己所用之后,运气条变成了一个书写交流的重要形式。找遍了很多美式祝福,她们最后决定用“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这一句,这样既可以跨越翻译的界限,又显得很得体。因为女方求婚举动打破了中国传统,所以林达在不同于自己的传统和语言中,用福饼来“请”龚丁娶她。写下来的英语必须翻译出来(因为龚丁不认识spouse这个词),但是文本的实体性使龚丁得到了信息,并在口语的即时性之外译出。文本的使用,或在这个例子中英语文本的使用,使林达能够在口述故事无效的时候利用无声的文本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即便对方也说中文。
林达对喜饼的运用证明了谈话者之间的一些微小但是重要的冲突和误解必须通过文字书写或书面文字来缓解。和林达一样,《灶神之妻》中的温妮也非常了解写作和作者身份的重要性。温妮通过为花店写条幅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创造意义的能力。正如珠儿告诉读者的,每束插花里都有的红色条幅并不包含典型的祝福语。相反,“她的贺词都用烫金汉字写,写出她对生死的看法、对幸运和希望的渴望”。这些灵感迸发的条幅上写着充满创意的语言:“祝新饭店财源茂盛”,“为你第一个宝宝创造一流的生活”。这些代表的不仅仅是创造力的迸发。对温妮来说,这些条幅的创作才是她生意兴隆的原因,也是她个人身份的表达。
温妮不断强调自己和母亲的读写能力的重要性。温妮告诉读者,小时候有一次她跟着母亲去市场,因为不识字,所以她不知道妈妈买的报纸是什么。因为不识字,她错失了最终将改变她命运的重要信息。但是,在她叙述的结尾,由于她有能力写信给未来的丈夫,才让她在共产党掌权之前逃离了中国。在传统社会,人们认为“女孩的眼睛只用来做针线活,万万不能用来读书”。温妮的母亲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掌握两种语言,这意义非凡。温妮能用中英文写作的能力表明她对口语叙事的运用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非受到某种局限的结果。温妮可以在两种语言以及两种表达形式之间进行选择,表明口述故事只是有选择地出现在某种情境中,而非中国女性表达真实自我的唯一选择。相反,文化水平——即读写能力,标志着谭恩美笔下的母亲形象是强有力的。
虽然谭恩美通过自己的写作为中国移民母亲发声,但是在她许多作品中出现的书面书写赋予了中国人以及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书写自我的自主性,而评论家们由于过度强调口述故事的重要性,而并未意识到这一主体性。谭恩美有意塑造了她笔下的中国母亲话语的复杂性。在《母语》一文中,她强调了自己有意识地想要给那些“破碎的”和非标准英语赋予价值和意义。她告诉读者她书写的是种种不同的英语变体,从小到大都在使用的英语变体。最重要的是,她说她“想捕捉语言能力测验所不能揭示的:她的意图,她的激情,她的形象,她说话的节奏和她思想的本质”。谭恩美试图捕捉任何语言能力测试都不能呈现的东西:她笔下中国母亲基本的读写能力。此外,她还捕捉到了她们的文学写作能力。谭恩美对非母语者审美力的强调,着重体现了她们的叙事方式中潜在的艺术。谭恩美并没有像某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着力表现对话语的重获,而是通过描绘中国妇女对书面文本的使用,展现了有别于专注口语叙事批评所呈现的、被边缘化的妇女的形象。
在《接骨师之女》中,谭恩美将注意力更加集中于文字书写使交流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上。斯蒂芬·索利斯(Stephen Souris)在他对《喜福会》的评论文章中论述到,文本中的中国母亲对着虚空说话,“母女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接骨师之女》通过对墨水物质性的认识,集中展示书面文本的永恒性和写作最基本的重要性。墨水的物理性质与书写过程以及文本与永恒性之间的关联在全文中均有所体现。茹灵的老师和文中的父亲形象潘先生认识到,文字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能不消弭于时光之中被轻易地抹杀,通过这一认识强调了书写文本的永恒性。他相信书写文本能成为古器,因此他强调书写“真实目的”的重要性,他提醒茹灵说“你一旦将墨落到纸上,你再也无法让它换回原形。”
宝姨也曾明确地将书写的动作与文本的质量联系起来。她教导女儿茹灵说,当你用现代瓶装墨的时候,
写出来的尽是脑海里面最表层的东西。最表层可没什么好东西,就像池塘水面上漂浮的,就只有枯枝败叶,孑孓虫。可是倘或你提笔之前,先在砚台上磨墨,这个准备步骤会帮你荡涤心志。你一边磨,一边扪心自问:我志在何处?胸中有什么样的情怀?
通过让人们注意为写作准备砚台所需的工作,宝姨强调了写作的实质性过程。她相信使用砚台这一更具实质性的写作过程,迫使作者了解她真正的意图,而不是当下一时的情感。通过这一思想的不断重复,小说强调了写作意图的重要性,并表明对小说人物来说,重要的写作类型并非不假思索地记录下即时的想法,而是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保存和交流精心挑选的思想信息。
因此,《接骨师之女》中的写作和文本呈现出力量和重要性,因为它们是经过作者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创造出来的,而非随意为之。宝姨教导茹灵说,写字的时候“要想想自己的目的”,茹灵意识到当宝姨写字的时候,“气沉丹田,然后运到手臂,传到笔端,将力道用到笔划上。”因此,每一笔都代表着书写者的精神和个性,纸张上的文字也蕴含着比其形态所代表的、更深刻的含义;它们代表着作者的目的和个性。纸张上的字迹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字本身,还体现了作者的生命和性格。茹灵的自传写得一丝不苟,讲述的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故事。完美的竖排格式、毫发不爽的手稿让露丝认识到文稿显然是精心处理过的,进而意识到文稿的重要性。虽然露丝看不懂手稿上的中国字,但是由其呈现方式,而能了解到重要性。
露丝明白其中的深意,因她年幼时在沙盘上写字以及写日记的经历使她对写作油然而生敬意。当写下宝姨的“讯息”给妈妈发号施令,年幼的露丝意识到,她“从没发觉,文字竟有这么巨大的力量”,她假装自己写下的是宝姨的鬼魂告诉她的话,利用文字来控制母亲。虽然全是她自己的话,她的“鬼写作”却有力量让母亲搬家,并扰乱母亲的日常生活。露丝在日记中写下对母亲的憎恨时,她同样利用了文字的力量,因为她知道母亲肯定会看她的日记,而且她也知道这些文字会对母亲产生特定的影响。她在日记里写下那些话,她十分清楚自己的动机,并意识到,
这么写很冒险。这纯粹是恶意的。可是罪恶感却让她更加逞强。她接着写出更加恶毒可怕的话来,尽管她后来把这些话涂掉了,可是已经太晚了……‘你动不动就喊着要自杀,那为什么从来就只说不做呢?我倒希望你快点动手。死掉算了,快去吧,去吧,去吧,自己了断吧!宝姨让你去死,我也一样!
露丝第二天发现母亲从窗户坠楼时,她对文字力量的恐惧使得她相信自己杀死了母亲。她开始相信文字及其书写具有潜在的力量因而非常重要。这一想法影响了她的一生。
成年露丝吐露她童年时期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战胜了她想写下自己文字的愿望。她知道如果她写简·奥斯汀风格的小说,“她可以在小说中重新塑造全新的生活,改头换面,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但是通过重新书写,抹去生活中她不喜欢的东西的想法让她感到害怕。通过写小说假想出另外一种生活,这一想法给她带来的恐惧使她不能自主进行小说创作,而只能将她的文字书写局限于作为一名鬼写手,为他人写作。即使作为成年人,她也相信“随心所欲地写作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痴心妄想”。她害怕将母亲剔除在她虚构的生活之外会让她真的从现实消失。这一恐惧使露丝无法通过原创写作获取自主感。露丝作为鬼写手的工作使得她能够改写他人的文字,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她的恐惧也强调了文中其他人物也认识到了文字书写的力量。当帮他人写作时,她不用投入属于个人的东西,这让露丝感到“安全”。
通过母亲发掘自传,露丝最终意识到了原创性写作的重要性。正如宝姨用她的自传挽救了茹灵一样,茹灵也由其自传对露丝的影响解救了露丝。在小说结尾,露丝将继承宝姨建立的传统,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些中国妇女运用文字书写的自传彰显并建立了她们个人身份的持久概念。小说通过茹灵写给露丝的自传向读者揭示了宝姨的身份,尽管茹灵从来没有将这个秘密告诉过女儿。因此,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中自传书写的层层剥茧,强调了作者身份与自我表述之间的确切关联以及笔头叙述优于口头叙述的重要性。
这些自传的书写特质不仅表明了每位女性的身份感,而且还强调了笔头叙述具有优于口头叙述的力量与稳定性。对茹灵来说,写作具有文化与祖先传承的双重重要性。藉由重述母亲的自传,她表现出了对文字书写的力量和重要性的尊重。但是,文字书写于茹灵而言还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力——也就是自己口述那些记忆的能力——在衰退。她开始讲述的第一句话是:“这些事情我不应该忘记”。她自传的开场白表明,通过文字书写她能够在自己的记忆逝去之后仍然能够保留过去。茹灵的讲述如一件古物获得了实质的永久性,而这正是口述故事的不断改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不具备的。虽然她的口语表达(和谭恩美笔下的其他母亲一样)常常会造成女儿的误解以及与女儿关系的疏离,但是她的笔头叙述使得露丝最终能理解她的故事。
与谭恩美前三部作品中“喜福会”的母亲、温妮和李旷(Kwan Li)的口语叙述不同,茹灵的笔头叙事使得露丝准备好有意识地理解并内化故事的文化意义。茹灵的故事是书写下来的,所以超越了母女交流的即时性,而保留了翻译的可能性;文本的实体性使得茹灵还能挖掘并解读自己的记忆,纵使失忆而无法向女儿口传自己的往事。笔头文本迥异于口语叙述,可供日后翻译和思考——这是露丝能够理解文本的唯一方式——而口头叙述即时而为,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理解。露丝不懂中文表现了无法读写的另一种具体表现,从而凸显了需要特定的知识来为母女间进行翻译的必要性;而这一需求与谭恩美作品中的其他女儿形象的需求相对应。笔头文本的永恒性和实体性使露丝能够将手稿交给那些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人翻译。
翻译是由唐先生完成的。他能够帮助茹灵在她的文本中再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懂得中文和英文两个语言体系。唐先生利用一张茹灵年轻时候的照片,并发挥自己所有的感受力来翻译茹灵的手稿。他告诉露丝说“如果能看到她的形象,对我的翻译可能会有所帮助,更好地传达她用中文表述的含义”。唐先生告诉露丝他需要两个月才能译完全文,并说“我不想一字一句按字面意思翻译出来了事,我想尽量措辞自然些,又要保证把令堂的意思准确传达出来,毕竟这是你们的家史,要传给子孙后代知道的,所以不好有错误”。他说他不想仅仅逐字逐句翻译茹灵的文稿,这表明他并没有局限于严格的语言翻译,而是融入了对文本的思考
显然,不管是在口头上还是在笔头上,谭恩美都让中国移民母亲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有了合法的声音。谭恩美在作品中对女性作者身份的表达以及对文字书写的力量和重要性的强调,标志着她采用的是比口述故事甚至口头叙事更加宽泛的审美传统;她采用的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在《接骨师之女》的结尾,露丝通过主动投入写作的方式认同了自己的华裔身份,这一形象强调了谭恩美作品中文学传统的重要性。“露丝下笔写作的时候,想起了这些。故事写给她的外婆,她自己,还有那个即将成为自己母亲的小女孩”。通过另一位美国女儿,即谭恩美本人的作品,这种女性书写——即女性书写女性,女性书写自我——成为宝姨、茹灵以及最后露丝的笔头自传中不断强化和重复的主题。
如前所述,《接骨师之女》并不背离谭恩美之前的风格,而是突显其作品中招致忽略的特点。对这一特点的误解导致了对谭恩美作品的分析流于简单化。例如,茹灵的叙述缺少其他叙事的口头标记,实际是一种笔头文本。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也许将《喜福会》解读为实验性的口述故事,并将文本中的话语当成实际的话语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每个声音实际上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文本的可能性。在《喜福会》中关于母亲的那些章节,我们没有看到在谭恩美其他作品中可以找到的、人们所听到中国移民说话时的风格性话语。和温妮或李旷不同,母亲的话语似乎并不是直接说给美国女儿听的,而是制造了一些女儿无法阅读的文本。在这些文本的某些部分,每位母亲的话语变成了叙述话语,而每位女性成了自传的实际作者。虽然实际上是谭恩美写的这些自传,但是叙述话语显示出良好的写作修养:风格独特,语言考究。将自我书写到纸张上的重要性在《接骨师之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在谭恩美其他小说中口语表达失效,文本出现,应用新的方法来阐释中国移民妇女的文字书写。
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不仅口述故事,而且还用写作来声张身份。她们对文字的理解力、文字书写的永恒性给她们带来的力量以及她们对文本书写的积极参与,表明谭恩美笔下的母亲并非只是讲述故事那么简单。汤亭亭的《女勇士》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华裔美国文学的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并被收录到大学教科书内,但是将同一批评标准运用到谭恩美(也许还有其他美国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中,局限并曲解了对其作品的讨论。评论界对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母亲的读写能力缺乏认知,导致研究和分析建立在(人物)边缘化而消解的臆想之上。不少评论家以为,母亲支离破碎的英语是将特定的中国文化身份和记忆传承给女儿的唯一方式。这些研究在开启对谭恩美作品的讨论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忽略了谭恩美作品中华裔美国移民妇女所表现出的复杂性。谭恩美的小说表明中国母亲并非没有能力与美国女儿进行交流,而是这些交流互动在艺术上非常复杂。谭创造了一个有别于汤的文学传统。她笔下的母亲不会仅仅依赖口语表达,而是能够藉由写作能力而不是其局限性,在口头表达和笔头表达之间、发声和沉默之间自由穿梭。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文本当中对作者身份的误读其实有可能是对谭恩美本人作家身份误读的一个隐喻。实际上,相较汤亭亭的作品而言,对谭恩美的作品贬多褒少,表明了经典形成和经典批评所产生的效应。罗伯特·戴尔·帕克(Robert Dale Parker)在“物质的选择”(“Material Choices”)一文中论述到,批评经典的论述通常是以代表的概念为基础的,而正是由于对代表这一概念的依赖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代表的概念假定“存在一个稳定而连贯的实体作为代表”,而且“‘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对等的、或一对一的关系。所指(如身份)是独立于或处于整个指称过程(如一部小说)之下的。因此,承认口头叙事,如口述故事的批评倾向采用了某种身份政治——通过代表经典作品中的某种声音,我们代表了一种建构性的身份(当然这是一种美好而高尚的尝试)
距离利奥塔(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The PostmodernCondition)中引入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已经过去了25年,大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已经得到拓宽,包含了女性作品以及有色女性作品,但是对谭恩美作品的批评表明,对这些作品的收录都是以大量噤声为代价的,这些声音对“身份代表”这一经典批评的基础提出挑战。对口语叙事或其他“非传统叙事策略”几近崇拜的关注,同样会束缚那些试图开拓或摒弃经典批评的尝试。忽略谭恩美所有作品中的主题而广为关注口语叙事,揭示了批评实践对文本接受和最终认可所起的引导作用。正如约翰·加里洛里(John Guillory)所论证的,经典——由出现在教学大纲上的作品组成——是用来教化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我们应该明白,很多人用它来代表族裔话语或少数团体话语,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固步自封的。
责任编辑:张箭飞
The Silencing Effect of Canonicity:Authorship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Amy Tan’s Novels
〔US〕Lisa M·S·DunickTrans.Yao Hongyan
(1.A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Prince George’s Community College,Maryland,U.S.A.2.A Ph.D candidate of English Department,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The inclusion ofethnic women writers’worksin university syllabiis a function oftheirdifferencefromthe grand narratives of“traditional”American literature.B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ir oral forms of narration found in many of these ethnic women’s texts and these authors’difference contributes to their being outside of a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canon.Criticism of Tan’s texts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written texts and the literacy of Chinese mothers.In her novel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the intense focus on the literary quality of women’s writing shows that literacy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nd written texts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and often more effective means of transmitting cultural memori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across generational lines than talk-story.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written texts,this study will demonstrate the ways that Tan’s works present literacy and writing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riticalproblems with identifying non-Western narratives only through an understanding of oral traditions.The misreading of authorship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mirrors the mechanism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necessary in both forming and reacting to the literary canon and the silencing function that imposes limit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recognizing literary value.
Literary Canon;Amy Tan;The Bonesetter’s Daughter;Oral Narrative;Writing
丽萨M·S·杜尼克(Lisa M·S·Dunick),作家、编辑,现任美国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社区学院英文系教授。This article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MELUS(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31.2,2006.(本文原载于《美国多族裔文学》总第31期,2006年第2期,第3—20页。)本文的翻译和发表得到作者杜尼克教授的翻译授权和MELUS《美国多族裔》主编盖里·托滕教授(Garry Totten)的版权授权,在此一并致谢。
姚红艳(1975—),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