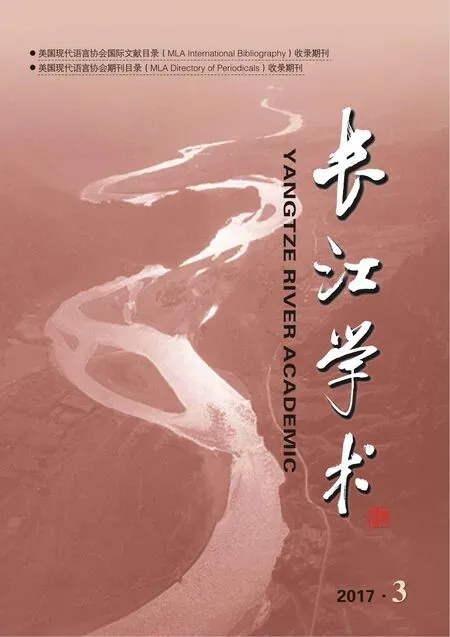三个世纪的男性气质:《异乡人》中“王者”杰米·弗雷泽的奇案研究
〔澳〕詹妮弗·菲利普斯著 吴濛译 朱宾忠审译
(1.卧龙岗大学;2.3.武汉大学 英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三个世纪的男性气质:《异乡人》中“王者”杰米·弗雷泽的奇案研究
〔澳〕詹妮弗·菲利普斯著 吴濛译 朱宾忠审译
(1.卧龙岗大学;2.3.武汉大学 英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2)
《异乡人》系列的男主人公杰米·弗雷泽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八世纪大男子主义的典型代表,但由于与来自二十世纪的妻子克莱尔的结合,其形象变得丰富立体,成为了一个符合二十一世纪口味的男性英雄。三个时代合力塑造并丰富了杰米·弗雷泽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概念,而是复杂的流动的过程,通过形式上的分裂和转换,同时维护和颠覆了男主人公所在时代的性别期望。
杰米·弗雷泽 男性气质 三个世纪
引 言
1991年,戴安娜·加瓦尔东出版了《异乡人》系列的第一部小说,她的读者(主要是女性)发现自己与叙述者暨女主人公克莱尔同时爱上了男主人公杰米·弗雷泽。后文中我们发现杰米曾经是一名战士,一名苏格兰高地勇士,更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但当克莱尔第一次遇见杰米时,他却是以弱者的面貌出现的。杰米与读者首次见面时,蹲在一个角落里,抓着脱臼的肩膀,痛苦地翻来滚去(《异乡人》第3章)。事实上,克莱尔见到杰米的仅仅数小时内,不仅医治了他在与英国士兵的两次不同小规模战斗中所负的战伤,还将因肩部中枪而失血过多的杰米从昏迷中救醒。对于一位即将在系列小说中担任核心男主人公的人物而言,杰米总是容易受伤,又依赖某位女性的治疗——尽管这位女性可观的知识技能得益于其来自二十世纪的背景——无疑削弱了作品对勇士男性气质的传统建构。
从杰米出场那一刻起,作者便以迥异于传统的手段对他进行塑造,这预示了在《异乡人》系列的许多后续事件中,杰米表面上的英雄主义和大男子主义行为会遭到削弱。尽管该系列的首部小说《异乡人》自始至终是从克莱尔的视角叙述的,但是大部分叙述的焦点却在杰米身上。杰米是克莱尔穿越时空之后遇见的,他们成了朋友,很快又不得不成了婚——这段婚姻由于克莱尔在1945年的时空中已为人妻而变得错综复杂。尽管克莱尔是小说的叙述者和代理读者,但杰米·弗雷泽提供了更为复杂而有趣的研究视角。他既是一名苏格兰高地勇士,也是一位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学者;他是个童男子,但不是和尚(这是他在新婚之夜告诉妻子的);他是众人的领袖却服从宗族的领导;他是个领主却无家可归;他是位英雄,但后来却被邪恶的黑杰克·兰德尔粗暴地伤害。众多矛盾之处不仅让杰米这个人物令人着迷,也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本该是传统英雄式(或“超雄性”)大男子主义的化身,是像蓝博、终结者和野蛮人柯南那样毫无争议地展现出高度男性化气质的典型人物。
对杰米男性气质的描写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人物身上负载着三个世纪的历史和文化。表面上,杰米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他的男性气质与他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杰米首次亮相时,是苏格兰高地纯粹由男性组成的突袭队队员之一,后来我们发现他还是领主的侄子和可能的继承人,最后发现他本人也是一个领主,只不过已经无家可归。我们遇见1743年的杰米·弗雷泽时,他正处在詹姆斯二世党人即将起事的历史阶段。因此,他也置身于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事失败的苏格兰式想象和神话之中。
与来自二十世纪的克莱尔结婚,让杰米的处境进一步复杂化。克莱尔有着二战以后女性的知识和见解,她拒绝当作杰米的“财产”,也不愿像典型的十八世纪的妻子那样温顺谦恭,言听计从。在男性话语中,女性的见识会被视作威胁,引发“危机”,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克莱尔的见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杰米男性力量的表现。在《异乡人》系列中,杰米不得不承认克莱尔在他们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后来,他们在一起协作时比分开时更有效率。
这种具备双重世纪色彩的男性气质由于小说的初创背景而进一步复杂化。不仅加瓦尔东在塑造杰米·弗雷泽的过程中受到了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第二波的结束和第三波的兴起——而且最初的读者群和小说的总体接受情况也受到了这些文化里程碑的影响。2014年,《异乡人》改编的电视剧在Starz电视网首映,对于电视剧观众而言,杰米·弗雷泽(由山姆·修汉饰演)身上显而易见的男性气质又进一步受到了二十一世纪电视观众立场的影响。杰米身上有关性别和性别角色变动不拘的表达不仅为当代大众文化所接受,也符合其预期。
这一章不仅探讨了杰米·弗雷泽是如何丰富大男子主义原型的,而且将透过三个世纪对男性概念、表达和期望的不同镜像,进一步研究它们是如何影响杰米性格的具体表现和我们对他的看法的。要分析杰米的男性化行为,以及在阅读、观赏《异乡人》系列小说和剧集中多重历史架构的影响,必须重点关注男性气质研究的几个关键方面,主要包括,男性气质作为概念的流动性和男性气质话语“危机”的内在缺陷。
多重而复杂的男性化表现
与文学、电影和文化执着于男性化表现不同——这些表现被视为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男性气质”的反映——一些理论家,尤其以布罗德和考夫曼以及康奈尔为代表,提出一个概念,认为男性气质是可以进行不同排列组合的。探究性别本质需要这样的灵活方式,如洛伯所言,这是“从社会生活中不断地被创造和再创造的,也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实质和规则”。因此,如果性别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如果男性气质是因时而变并且因文化而异的,那么就不存在某种单一而理想化的男性气质形式。
随着男性气质流动性概念的出现,学术著作中有关男性气质的分析也发生了变化。布伦顿· J·马林认为,“男性和女性气质的预设,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和历史决定的”。马林提出,“某个历史时期被视为男性气质的东西到了另一个历史时期,可能被视为禁忌,反之亦然。这种文化上的变化表明,男性气质是一个依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变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同的面貌”。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分析是与阅读《异乡人》系列小说、观看《异乡人》系列剧集时起作用的各个历史时间相联系的,并不涉及男性气质这个广义概念。正如马林所言,“[有关男性气质的]基本设想对于正处在某个文化时刻的人们产生着切实的影响”。
为了尝试理解父权制男性气质的建构,R·W·康奈尔承袭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做法,提出了“大男子主义”的概念。康纳尔的概念并非暗指个人经验意义上的男性气质;而指构成男性化行为标准概念的复杂特征的名称。康奈尔将大男子主义定义为:
性别实践的构成,体现了目前公认的有关父权制合法性问题的答案,这种父权制保证了(或用于保证)男性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
康奈尔没有将男性霸权视作对行为的定义,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体系。建立这个体系,是为了解释以男性为主导的体制(如父权制)所进行的文化操控。这不仅解释了父权制,还试图将父权制合法化(父权制将那些明显处在男性霸权规范之外的群体定位为边缘化群体)。康奈尔避免列举男性霸权群体的行为特征,因为:
严格奉行男性霸权的男性数量可能很少。但是大多数男性能从男性霸权中获益,因为他们从父权制红利中得到好处,这种好处通常来自女性的整体从属地位。
康奈尔认为父权和大男子主义密不可分,声称“男人对父权制的兴趣凝聚在大男子主义之中。这在政体上是被制度化的;在异性恋男性的生活中是被暴力、威胁和嘲笑强加于身的”。虽然看起来文化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维护父权,康奈尔指出,这种权力是会受到挑战的,“不同群体的男性,追求大男子主义的不同目标,彼此发生冲突是很常见的”。因此,尽管所有男性都对父权拥有共同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同类结构中并不充当某种统一的力量”,因此大男子主义及其服务的父权制可以通过重新评估而瓦解。
尽管康奈尔避免定义男性霸权行为;其他批评家却提供了这样的定义。麦克因斯引用伊恩·克莱布有关男性气质的调查,其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男性气质的特质[…]似乎是不变的,与男性相关联,表现为养家糊口者、供养者、劳动者,是人类物种中积极主动、与外界打交道的那一半:男人是强壮的、积极的、理性的、独立的、任务导向型的、不易受伤的和成功的(奥尼尔1982)。列举这样的特质,无关乎其基于的是态度调查或理论推导,也无关乎辨识的是文化刻板印象、性别角色或男性身份——一个男人的自我感觉。
迈克尔·基梅尔(2006)声称,这个列表竖起了预期行为的男性霸权模式,也指向了受排斥群体中被边缘化的“他者”。
从表面上看,杰米·弗雷泽的特点似乎完全符合男性霸权模式。他为了保护克莱尔不落入杰克·兰德尔的魔掌,娶她为妻并宣称,“你拥有我的名字,我的家人,我的家族,如果必要的话,我将用血肉之躯保护你。只要我活着,那个男人就不会再碰你一个指头”(《异乡人》第15章)后来,杰米从兰德尔手中救回克莱尔时告诉她,“为了找到你,我会不惜杀掉十几个人”(《异乡人》第21章)。
然而,由于《异乡人》系列的苏格兰背景,当涉及到分析小说描写的人物和环境时,男性霸权模式并不完全相符。罗莎琳德·卡尔结合十八世纪的苏格兰背景,反思了康纳尔大男子主义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她指出,康奈尔依赖的是一个二分系统,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男性气质都从属于男性霸权形式,这并不能反映苏格兰和英国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像卡尔一样,马修·麦科马克也不认可男性霸权模型的实用性,因为在英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男性化形式能占据主导地位。
抛开得在英国背景下考虑大男子主义的问题不谈,对于杰米·弗雷泽这个人物而言,大男子主义并非完全不适用,因为他本身也拥有跨国背景。虽然人物和背景设置在苏格兰,作者加瓦尔东却是美国人(事实上,在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前,她从未去过苏格兰),电视制作人罗恩·D·摩尔也一样。因此,我不会完全拒绝这一概念,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思考杰米·弗雷泽这个人物所代表的男性气质是如何比他表现出来的男性霸权主义复杂得多的。正如我们在通读系列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杰米的男性气质常常被复杂化——特别是考虑到观众在观看《异乡人》改编剧集时,有四个历史时期在同时运转。这么一来,我将展示在文本内外的每个时间架构中,性别角色和期望的变化是如何通过杰米·弗雷泽这个人物的方方面面被反射和折射的。与理想化男性霸权模式的描述相比,他构造了某种更加流畅、更加复杂的男性行为。这种流动性,如康奈尔所言,是男性话语“危机”中分析男性行为“分裂”和“转换”的解毒剂,从而避免了他所担心的情况,即这种“危机”心态会“激起恢复男性行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尝试”。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杰米·弗雷泽的男性化表现中有许多明显的“分裂”和“转换”。但这种复杂的男性气质不会妨碍他作为一个男性罗曼史领袖的英雄地位或定位,即使要面对伤害、失败和缺陷。
十八世纪:历史背景
《异乡人》的主要叙事背景设置在18世纪40年代的苏格兰高地,杰米·弗雷泽的男性气质也因而定位于此时此地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学环境中。171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事失败的历史背景,以及1745年的再度起事对杰米男性气质的影响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克莱尔穿过石头群,回到的是1743年——正是悲情的卡洛登战役发生的三年以前。即将爆发的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事在《异乡人》系列小说第一部中仅占少量篇幅,但对第二部小说《琥珀蜻蜓》中的事件却至关重要。第二部小说于2016年改编成了《异乡人》电视剧第二季。
在《异乡人》第一部小说文本中,选取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事作为背景的目的之一,是在高地突袭者及酋长道格尔和他的哥哥,即麦肯齐家族的领主科勒姆之间,建立一种紧张关系。科勒姆作为男人和领袖的能力受到了身体残疾的影响,他无法从佃户手上收取租金,而这是大多数高地领主的责任。相反,他派弟弟道格尔上路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克莱尔跟着道格尔和他的人马一起,打破了他们的同性群体分组。她很快意识到,虽然道格尔白天以领主的名义收租,但晚上在酒馆,他打的却是漂亮王子(即詹姆斯二世)的名号,从居住在他家族土地上的贫苦佃农手中抽取更多的租金。道格尔这么做,并没有让哥哥知道或得到他的同意。
道格尔把杰米的伤疤当作英国人残暴行径的视觉象征,不仅仅营造了紧张氛围,也削弱了杰米的性格力量以及他在叙事中的英雄地位。夜复一夜,杰米懒懒地坐着,任凭叔叔道格尔当着一屋子陌生人的面,从背后扯掉他的衬衫,他的脸“像石头一样”(《异乡人》第11章)。克莱尔质问杰米,既然道格尔的行为让他很不舒服——无论是个人感受还是政治层面——他为什么还会予以默许,杰米告诉克莱尔,他对叔叔的孝顺比自己的舒适更重要——至少短期内如此。
将小说设置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事的前几年,不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也充分利用了苏格兰文化想象中的历史现实和神话般的国家象征。正如艾布拉姆斯在评论电影中的历史人物如威廉·华莱士时所言,历史真实性“是从属于神话和象征的,也是强调这些神话和象征中的男性人物的”。除了提及梅尔·吉布森在电影《勇敢的心》(1995)中对华莱士的刻画,艾布拉姆斯还指出,在帮助塑造苏格兰国家神话的过程中,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形象是多么“经久不衰”。同样,邓肯·皮特里也注意到苏格兰电影中频繁使用“十八世纪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传奇、比喻和象征”。这些比喻在加瓦尔东的小说作品和摩尔的改编剧集中都显而易见。
在这种背景下,杰米·弗雷泽成为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经久不衰的悲情形象的又一个化身。然而,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詹姆斯二世党人不同,比如沃尔特·司各特小说的同名主人公威弗利(1814)和罗伯·罗伊(1817),杰米·弗雷泽不是詹姆斯二世党人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当杰米的身体(带着英国人造成的可怕伤口)被叔叔道格尔以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事业之名裸露出来,他的不情愿是非常明显的。后来,杰米在流亡巴黎期间,假意与“漂亮王子”成为朋友,同时与克莱尔一起密谋阻止查尔斯回到苏格兰。但杰米很快惊讶地发现,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查尔斯传播的一份詹姆斯二世党人支持者列表中。查尔斯并没有事先向杰米及其族人确认他们是否愿意重回战场,助他夺回王位宝座。
尽管下文描述了杰米在战场上英勇的领导和胜利——包括詹姆斯二世党人几场重要战役的胜利,如历史上著名的普雷斯顿潘战役(《秋之鼓》第36章)和福尔柯克·穆尔战役(《秋之鼓》第43章),但杰米是“意外”进入詹姆斯二世党人军队的这一点还是削弱了他作为一个战争英雄的地位。此外,杰米作为一个“不情愿的”詹姆斯二世党人的身份,也使他在起事失败中的角色不能算作个人失败,倒不如说是他刚好被卷入了这一系列不幸事件之中。这样,杰米的英雄行为(包括卡洛登战役)才能够深入詹姆斯二世党人怀旧心理和神话情结的文化核心,而不被起事失败的历史现实削弱。
从表面上看这段历史,可能会认为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事业的苏格兰高地勇士毫无疑问是富有男性气质的,而且这与苏格兰尚武的男性气质相一致,但有证据表明,这不一定是当时对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看法——特别是在卡洛登战役之后。相反,在詹姆斯二世党人的诗歌和歌曲中,詹姆斯二世党人被描绘成一个女人,思念着消失的爱人(这里指的是查尔斯)。在这样的阅读中,如马丁所认为的那样,这个女人变成了一个“有关苏格兰的隐喻,这个国家由于缺乏新生力量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朱丽叶·希尔兹称,将詹姆斯二世党人比作女性的隐喻化描写,启发了辉格党讽刺作家对詹姆斯二世党人追随者们女性特质的强调。这种女性化的讽刺由于漂亮王子查尔斯乔装成女性离开苏格兰的传言而进一步发酵。对辉格党讽刺作家而言,查尔斯选择逃亡,正是他在男性军事领域惨遭失败的转喻。
辉格党人并不是唯一对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事业做出女性化解读的群体。皮特里在分析电影对苏格兰的描绘时称,“尽管詹姆斯二世党人传奇对男性的强调多过女性,但仍可以被编码成女性行为,只不过在大场面上让身着华丽苏格兰短裙的男性英雄们出场”。詹姆斯二世党人浪漫传奇和电影虽然描写了暴力、战争和男性群体,但其格外吸引女性的趋势,在《异乡人》的读者和观众群体中显而易见。尽管作者戴安娜·加瓦尔东将其称为“历史小说”,她也注意到其中的文体变形元素,包括:
历史、战争、医学、性、暴力、灵性、荣誉、背叛、复仇、希望和绝望、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的建设和破坏、时间旅行、道德的模棱两可、剑、草药、马、赌博(以牌、骰子和生活来赌)、勇敢的航行、身体和灵魂的旅行。
然而,除去这种体裁拼贴,这些小说常常被明确地定性为浪漫传奇,其市场受众也几乎都是女性。此外,2014年《异乡人》系列剧集开播时,大部分发表的新闻和评论都将其称为“女性版《权力的游戏》”(详见韦斯特;戈德堡;贝克及其他;瓦尔马
最初的詹姆斯二世党人被女性化,而不是出现一个超雄性的替代品来对抗这种女性化——如康奈尔所言,这本应是个常见的反应——此时,如希尔兹声称,一些苏格兰作家(包括沃尔特·司各特、詹姆斯·鲍斯威尔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将这些典型的“女性化”特质与诸如“英雄的勇气、崇高的自我牺牲、忠诚的奉献和慷慨的同情”这些男性化军事气质进行了融合。结果产生了“多愁善感但重新男性化的苏格兰身份”。于希尔兹而言,这个结果差不多既关乎起义失败之后重塑苏格兰男性身份,也关乎塑造统一的英国男性身份:
十八世纪中期的伤感小说探索了女性气质的积极内涵,将英国身份与女性化的但不是柔弱无能的男性气质联系起来;国家故事反过来又强调了苏格兰高地人的感性和对家庭生活的挚爱,从而完成了融入一个统一的英国的进程。
勇士与学者的统一,情感与实用的统一,女性(但不是女性化的)与男性的统一,让我们在杰米·弗雷泽身上明显看到了男性气质的复杂,在其他人身上也是如此,这反映了其所处的十八世纪的文化现实。
十八世纪:国家背景
如努斯鲍姆所言,在十八世纪,“男性气质越来越成为衡量真正国家身份的流行指数”。因此,拥有理想化男性气质的杰米·弗雷泽,还可以被视为整个苏格兰的提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可以被看成英国人克莱尔和苏格兰人杰米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对她的昵称——“撒克逊人”——是盖尔语中嘲笑苏格兰高地外来英国人的叫法。
克莱尔第一次听到这个叫法是在1945年,当时她和第一任丈夫弗兰克一起去因弗内斯游玩(《异乡人》第1章),这个词反映出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失败的200多年以后,苏格兰高地的人们对英国人的不信任依然根深蒂固。通过时空旅行回到 1743年后,这个词也被用作怀疑的符号,特别是当道格尔·麦肯齐的高地突袭者在与英国士兵交战中发现克莱尔时,尤为如此(《异乡人》第3章)。但即使从杰米第一次用这个词称呼她开始,也只是一句玩笑话,问她是不是没指望他比她这个“小不点撒克逊姑娘”更勇敢。从那时起,这个词在杰米的用法中象征着友谊和爱,后来甚至是至死不渝的忠诚。
正是从表现他们关系的语言中,杰米和克莱尔展现出: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不信任和怀疑在渐渐愈合。他们的关系在小说第一部(电视剧第一季)中得以进展,这种关系所隐喻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进展。当杰米为了保护克莱尔而走向战场时,他也如卡尔所言,是在保护这个国家(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是在保护两个国家的联盟):
将女性视为国家的象征,使男性的英雄梦想在守护家庭的一家之主角色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样一来,男性在军事领域保卫祖国的责任,就被看成是他们守护家庭的男性责任的自然延伸。
尽管小说对杰米和克莱尔的结合做出了正面的描写,但是《异乡人》中隐喻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正如马丁所言,对这些国家层面的问题,可以做出具有性别色彩的阅读。
尽管苏格兰让从未拥有足够男性气质的英格兰更加男性化,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威胁——这种威胁不是苏格兰融入英国身份就可以消除的。的确,苏格兰神话般的原始男性气质不可能消失,这正是为什么与苏格兰式的野性联盟在意识形态上如此令人着迷。
克莱尔和杰米的关系展现出苏格兰和英格兰联盟的可能,但这个联盟的复杂程度在英国上尉黑杰克·兰德尔对杰米·弗雷泽的虐待中表现得一览无遗。
对《异乡人》改编剧集的批评中,有一条是其对强暴(或威胁强暴)的频繁描绘。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强暴针对的是女性角色(主要是克莱尔),但迄今为止,第一季中最具画面感和影响力的强暴场景却是英军龙骑兵上尉兰德尔对杰米·弗雷泽的强暴。尽管兰德尔也曾企图强暴克莱尔和杰米的姐姐珍妮,但当他把性虐的魔爪伸向杰米时,他显得最为残忍。让系列小说和剧集中的男主人公,一个看起来是理想化大男子主义化身的人物,成为如此残暴性侵的受害者,不同于之前影视作品中出现过的任何场景。此外,电视剧对于强暴事件的视觉渲染,让人们明显感受到十八世纪英格兰对苏格兰的侵犯。
因此,黑杰克·兰德尔具备了双重功能——他对杰米的强暴不仅是苏格兰惨遭英格兰凌辱掠夺的转喻,而且为当时英国和英格兰的男性气质提供了更加复杂化的概念。罗莎琳德·卡尔表示,“高贵优雅的英国绅士是爱国男儿的城市精英典范”。但十八世纪英国男性气质的性别表现并非那么简单。如凯伦·哈维所言,男性“礼貌”应该与战争暴力放在一起解读。因此,作为龙骑兵上尉的兰德尔,因其肩负的爱国义务,本应比杰米更加高贵优雅,因为杰米身上那种苏格兰高地式的军人气息,显然是很粗鲁的。然而在兰德尔对杰米、克莱尔和杰米姐姐珍妮的虐待中,他的野蛮暴露无遗。
二十世纪的女人在十八世纪的男性社会:克莱尔·弗雷泽
我们已经看到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是如何让杰米·弗雷泽的男性气质表现更加复杂的。然而,由于《异乡人》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女性神秘穿越时空的故事,所以二十世纪这个背景对杰米·弗雷泽的性格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两个二十世纪的人物被用于突出、对比和复杂化杰米·弗雷泽身上十八世纪男性气质的表现:克莱尔和弗兰克。
小说开篇时,曾是战地护士的克莱尔·弗雷泽(娘家姓博尚)不仅正在努力适应二战之后的平民生活,还在近乎绝望地尝试恢复与丈夫弗兰克的联系。和战时迈入工作领域的许多女性所走过的路一样,克莱尔很快发现自己将要努力适应回到战前“传统”的女性行为模式。于克莱尔而言,这意味着重拾家庭主妇的角色,支持弗兰克作为牛津大学历史讲师的新事业。
在这种背景下,有趣的是,她并没有走上预期的道路,而是被命运带到过去,在那里继续扮演原先的战地护士角色,尽管是在200多年以前的战争年代,也没有什么途径可以接触现代医学。《异乡人》中对性别行为预期的另一个颠覆在于,读者会认为,和1945年相比,回到十八世纪会大大限制克莱尔的女性力量。然而,杰米作为高地勇士的角色让克莱尔比1945年的身份更能发挥她的天赋和训练。杰米承认有她在身边,他会更强大,也成为了她医术的直接见证者(和受益者)。在这一点上,杰米功不可没。
然而,杰米和克莱尔的婚姻并不总在反映性别角色和行为的进步。在从黑杰克·兰德尔手中救出克莱尔后,两人之间第一次争执,因为克莱尔觉得杰米表现得好像她被抓走反倒是她的错一样。杰米沮丧地回应,因为克莱尔不仅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而且还造成糟糕的后果:
这是你的错!如果今天早上你照我说的那样留在原地,这根本不会发生!但是没有,你不听我的,我不过是你的丈夫,为什么要听我的呢?你打心眼儿里只肯按自己想的去做,接下来我看到的就是,我发现你平躺在地上,裙子被撩了起来,这块土地上最糟糕的人渣在你双腿之间,差点就在我眼前要了你!(《异乡人》第21章)
克莱尔的反应也表现了她的不满,因为杰米对她行为的期望显然受到了十八世纪性别规范的影响,这种规范让二十世纪的女人克莱尔很不高兴。照克莱尔的说法,她指责杰米认为“女人只适合按照吩咐做事,服从命令,交叠双手温顺地坐着,等待丈夫回家告诉她们去做什么!”,妻子是丈夫的“财产”,对杰米来说,妻子不过是“有冲动时插入那活儿的东西”(《异乡人》第21章)。
在克莱尔和杰米的争吵中,相比对性别行为看法不一致,这一次争吵的收场更具争议:因为克莱尔拒绝服从杰米的“命令”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的说法),杰米实施了体罚。这次遭遇是如此暴力,以至于克莱尔后来将其描述为“这一辈子第一次差点挨了打”(《异乡人》第21章)。杰米觉得自己完全在理,这么做不仅惩罚了她的错误,也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她的弟兄有了交待,而且她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财产”,这么做完全合乎逻辑。在杰米看来,他不仅有权体罚她,而且如他所言,“要是我想打断你的胳膊,或者除了面包和水什么也不给你吃,或者把你锁在壁橱里好几天——你也别以为你没逼我那么做——我完全可以那么做”(《异乡人》第21章)。
这一场景,尽管准确地再现了十八世纪婚姻的规范,但对《异乡人》的粉丝来说却颇有争议,早在这一集播出前,演员们就因为这一场景遭到了很多质疑(尤尔根森)。不单单是读者们无法赞同杰米对于婚姻权利的观点。作为二十世纪的女人,克莱尔不仅不同意,还激烈地反抗了杰米对她的所作所为,她不仅打得杰米鼻子出血,抓伤了他的脸颊,还在他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切都强化了读者对杰米的愤怒,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对待克莱尔(《异乡人》第21章)。当改编剧集中这一幕场景的对象是当代观众时,他们更加被激怒了,也许是因为拍摄的方式不合适,包括,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奇怪的欢快音乐”(乌帕德亚雅)让这一幕更像是为了滑稽幽默,而不是表现小说中描述的创伤。事实上,正如一位评论家在试映现场所体验的那样,这一幕甚至让有些观众大笑起来(威尔金森)。这种欢快的拍摄手法让观众体会到杰米正在经历的快感,而不是小说中描写的克莱尔的恐惧,在那一刻她感到“深深的背叛,被我依靠的那个朋友、保护者和爱人所背叛”(《异乡人》第21章)。
克莱尔拒绝屈从于十八世纪的性别规范,如果这一点威胁到了杰米·弗雷泽,那么不仅他对婚姻的看法、他控制(和惩罚)妻子身体的权利不会发生改变,而且,正如“危机”话语所假设的那样,他将进一步巩固业已根深蒂固的信念。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杰米意识到克莱尔不会屈从,他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也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女性应该服从的观念。正如杰米在对话中所指出的(原小说中并没有这段对话,电视剧为了二十一世纪的观众而添加),“妻子服从丈夫。妻子不服从时,丈夫要约束妻子。现在看来,那是在过去,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的做法。但也许对你和我来说,得换一种方式了”(1.09“清算”)。然后杰米发誓再也不会因为“叛逆或愤怒”而动她一根手指,这誓言所发的场景是克莱尔把匕首按在他胸前,威胁说如果他再敢打她,就把他的心挖出来当早餐吃(《异乡人》第22章)。在这部小说的剩余章节,以及其他七部小说中,杰米再也没有打过克莱尔。
二十世纪男性气质的幽灵:弗兰克·兰德尔
就像英格兰人克莱尔可以被看成整个英格兰的转喻一样,她的第一任丈夫弗兰克·兰德尔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以及二战之后的英格兰男性气质。不过,克莱尔的穿越使她的二十世纪背景与杰米生活的十八世纪形成了正面交锋,但与克莱尔不同,弗兰克这个人物与杰米从未谋面;他们分别留在各自的时空之中,其间相隔202个年头。这样,弗兰克的男性气质如幽灵般影响着克莱尔和杰米的关系,她常常想起自己依然深爱的第一任丈夫,这种回忆渗透着她的叙述。因此,从她穿越时空到达1743年那一刻起,弗兰克就不在了,他被困在了1945年。
由于叙事中的在场/缺席,弗兰克这个人物与杰米形成了隐性对比和显性对比。当读者在《异乡人》开篇见到弗兰克时,加瓦尔东突出地表现了他性格的某些方面。这些性格特征与读者将在杰米身上发现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隐性的对比。弗兰克战时供职于军情六处,战后他很快接受了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的任职。尽管克莱尔和弗兰克依然相爱,作者还是暗示了和谐表象之下的婚姻压力。在战争持续的数年间,他们多数时候处在分居状态,更加剧了这种压力。另一个有关他俩婚姻压力的暗示出现得很早,当时克莱尔提醒弗兰克,尽管他们已经结婚八年,却还没怀上孩子(《异乡人》第1章)。克莱尔提出收养孩子的想法,遭弗兰克拒绝。他说:“我只想要我们的孩子[…]。我担心一个收养的孩子,一个和我们没有真正血缘关系的孩子,会像个入侵者一样,让我很讨厌”(《异乡人》第2章)。
弗兰克和杰米之间的对比,会让人想用二分法的框架,让每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他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故事的叙述焦点在杰米身上,与杰米共度的时间也更多,读者会倾向于更欣赏杰米的男性气质,而不是弗兰克的。这种二元对立还可以上升到国家意义层面,正如詹姆斯·R·凯勒在分析电影《赤胆豪情》和《勇敢的心》时所发现的,这些电影作品在苏格兰高地人和“英国花花公子”之间呈现了某种并置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异乡人》中的男性化表现要远远复杂得多。虽然弗兰克和杰米的男性化表现有一定差异,他们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克莱尔爱着这两个男人,说明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点。
弗兰克供职于军情六处,他把其他男人送上战场,自己留在相对安全的伦敦总部,而杰米在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中奔赴前线战斗(后来又上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这样的隐性对比在阅读中不难发现。但杰米还是一位领袖,手下人战死沙场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负担。同样,表层阅读会在弗兰克的学术追求和杰米的行动主义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二分。但这样的阅读没有看到这两个男人在男性化表现中的细微差别。书生气的弗兰克并不是没有暴虐而野蛮的一面。克莱尔返回,坦承她在十八世纪度过三年光阴,弗兰克难以置信,他的反应是抄起一个花瓶砸碎在地板上(《秋之鼓》第5章)。同样,虽然将杰米看作英勇男性气质的化身会更简单,但他确实受过良好教育,在法国念过大学(《异乡人》第16章)。杰米在语言上也很有天赋(《秋之鼓》第8章),与国王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进餐时,他的言谈举止妥帖得当,完美地融入了巴黎上流社会(秋之鼓》第9章)。
在父亲角色中,杰米和弗兰克的共同点也大于不同点。虽然弗兰克清清楚楚地告诉克莱尔,他很反感去养育一个不是自己“骨血”的孩子,但造化弄人,他不得不这么做。克莱尔从十八世纪返回时,已经怀上了杰米的孩子。她很确定弗兰克会和她离婚,就把真相告诉了他,说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尽管是在200年前),腹中骨血是那个男人的。然而弗兰克却不愿和克莱尔离婚(《远行者》第3章),后来布丽安娜就出生了。尽管他早先声称会讨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克莱尔却描述了他是如何在一周之内“全心全意地”爱这个孩子的(《远行者》第3章)。尽管杰米和弗兰克在生育能力上有所不同——弗兰克没有生育能力——他们在收养非亲生孩子这一点上却很相似。杰米从巴黎妓院救出了九岁的克劳德尔(还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叫费格斯),这个孩子打从生下来就住在妓院里(《秋之鼓》第12章)。
克莱尔的两个丈夫杰米·弗雷泽和弗兰克·兰德尔形成了隐形对比,这说明对于他们身上不同的男性气质,应该做出复杂的解读,而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解读。他们也表明,尽管杰米·弗雷泽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但二十世纪男性气质的精魂肯定渗透进了对他的人物刻画中,这是由于,或许是由于戴安娜·加瓦尔东个人的小说写作背景。
二十一世纪女性的性意识
正如我们所见,克莱尔来自二十世纪,这让她不同于其他将背景设置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小说中的女性,她不仅影响了杰米对女性和性别角色的看法,也影响了他对性与性爱的参与。加瓦尔东对杰米和克莱尔之间性关系的描写,不能被置于当代时间架构之外,尤其考虑到如希尔兹所言的情况,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苏格兰作家如沃尔特·司各特、詹姆斯·霍格和约翰·高尔特创作的小说中,将女性的性感描绘成对社会的威胁。希尔兹认为,“尽管女性的感性可能使她们适合驯养、开化那些拥有原始冲动的人,但情感泛滥的倾向会让她们自己显得原始而冲动”。
无可否认,克莱尔的性感唤起了杰米的激情,在《异乡人》系列的两季电视剧中,这对夫妇的性爱场景比比皆是——但这并不一定如十八世纪的作家们警告的那样,必然说明了杰米的原始和冲动。首先,杰米在新婚之夜是处子之身,这在十八世纪的文化和文学中是意料之中的,但对于二十一世纪改编电视剧的观众而言,杰米在新婚之夜向克莱尔承认这一点,可以视为性别角色的成功逆转。
除了颠覆新婚之夜新娘破处的“传统”情节以外,《异乡人》电视剧首播时,许多评论还聚焦于对克莱尔性能量的描写。在第一集的两个不同场景中,都是克莱尔主动挑逗丈夫弗兰克发生关系的。克莱尔的性能量在与杰米的新婚之夜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第一次裸体站在她面前时,她命令他脱掉衣服,但自己却穿着衣服。她徘徊着,缓缓地绕着他的身体走动,当客观外在的性吸引力明显崭露以后,克莱尔内在的主观能动性也毫无疑问地表现出来,她快乐而兴奋,期待两个人共同享受性的欢愉。之后,在另一处性别角色的逆转中,克莱尔不仅扮演了经验丰富的情人,她还引导他去享受性的快感。那一刻,克莱尔置身于画面之外,而镜头对准了杰米狂喜的面庞。
对克莱尔性能量以及对她启蒙杰米享受性快感的描写,在影视作品的性描写中是很罕见的。更常见的是征服女性身体的镜头,能让剧中人和观影者都得到性快感。莉莉·鲁夫伯鲁曾就《权力的游戏》中“男性凝视”的运用写过一篇长文
结 论
正如我们所见,《异乡人》系列的读者同时与三个时代发生了联系,而且可以看到这三个时代是如何影响杰米·弗雷泽的男性气质的。《异乡人》改编电视剧的观众又接触了第四个时间维度,即创造和消费这一系列的二十一世纪。通过细读文本可以明显发现,杰米·弗雷泽的男性气质同时维护和颠覆了他所在时代的性别期望。正如康奈尔所言,与专注于构建现代男性气质时面临的“危机”相比,考虑男性气质形式的分裂和转换是更富有成效的。通过塑造一个自身男性气质深受不同时代影响的主人公,小说家戴安娜·加瓦尔东和电视制作人罗纳德·D·摩尔已然创造了这样一个体现分裂和转换的人物。不过在《异乡人》的世界里,杰米仍然是引人注目令人满意的人物。在他流动而复杂的形成过程中,十八世纪的杰米·弗雷泽,由于与二十世纪的妻子克莱尔相结合而变得更加丰富,从而成为了契合二十一世纪趣味的男性英雄。
责任编辑:张箭飞
Three Centuries of Masculinity:the Curious Case of Outlander’s“King of Men”Jamie Fraser
〔Australia〕Dr Jennifer PhillipsTrans.Wu Meng.Proofread.Zhu Binzhong
(1.University of Wollongong;2.3.English Depart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Jamie Fraser,the hero in the Outlander series,seems at first sight to be the hegemonic masculine archety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ut later is found to be enhanced by his partnership with Claire,his twentieth-century wife,and finally becomes a masculine hero fi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three centuries make a joint effort in shaping Jamie’s masculinity,which is not a static,unitary concept,but a fluid,complex formation.Through disruptions to and transformations of masculine forms,JamieFraser’smasculinity simultaneouslyupholds andsubvertsthe expectations of the time period of which he is a part.
Jamie Fraser;Masculinity;Three Centuries
詹妮弗·菲利普斯(Jennifer Phillips),女,文学博士,目前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人文、法律和艺术学院工作,主要从事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朱宾忠(1963—),男,湖北竹溪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吴濛(1989—),女,安徽六安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