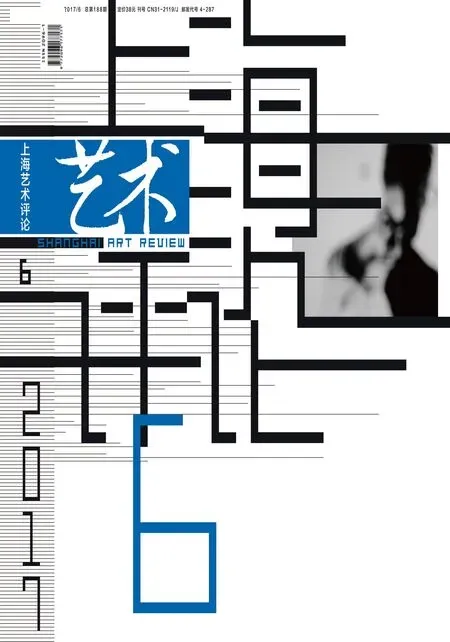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芳华》:磨蚀在时代变迁中的芬芳年华
龚金平
对“文革”的控诉、批判、留恋、感伤,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的一个重要母题。创作者从最初在回望“文革”时进行激越的抨击、沉痛的反思,到理性的沉潜、人性丑恶的揭示,最后又对“文革”产生莫名的怀念,甚至将“文革”美化成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抚惜感叹。这就不难理解,对于严歌苓和冯小刚来说,“文革”的伤痛因隔着遥远的岁月风尘已然模糊,但经过主观的过滤,那些澎湃的时刻仍然熠熠生辉,值得描摹、铭记,并在描摹与铭记中揭开那些当时被遮掩或忽略的黑暗与丑陋。说实话,要对一段“历史”既深情投入又保持一种冷静的剖析、疏离的烛照,这在情感的尺度和思考的维度上很难把握分寸。影片《芳华》(2017)在这个方面的得失都极为明显。
在影片《芳华》中,导演冯小刚用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表现20世纪70年代部队文工团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特定的时代风云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压抑、塑造、扭曲,对于人物命运的关键性影响与改写。总体而言,《芳华》有关“青春记忆”的那一段是色彩饱和、光线充足、运动流畅、情绪充沛的。尤其在那个排练厅,那些正值“芳华”的女舞蹈演员,展现她们柔美的身姿,青春洋溢的笑容和挺拔修颀的身体。尤其当她们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时,伴随着动人的音符,影片为我们奏响了一曲青春交响曲。
如果说排练厅以及舞台上的表演属于“艺术世界”,影片在这个世界里努力展现艺术之美,青春之美。而宿舍等地则属于“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各种不怀好意的捉弄、嘲笑、侮辱,各种暗暗的心机、算计都如影随形。但是,影片的本意并非表现人性的这些阴暗、嫉妒、自私,甚至残忍,而是想凸显个体在集体本位的秩序中的压抑、无力和挣扎。因为,部队、文工团作为一个权威意义上的“团体”,它具有神圣性,更具有“集体性”。正是在这种“集体性”的保障下,个体才会觉得安全、温暖。但是,当个体冒犯或者忤逆了“集体”时,“集体”的惩罚也是不动声色但又雷霆万钧的。刘峰下放到伐木连,何小萍被流放到野战医院“锻炼”,都是“集体”以组织的名义对“不合规范个体”的处罚。
当然,在时代性的更迭与嬗变中,“集体”的权威正在一点点受到质疑、挑战甚至挑衅。尤其在一个功利化的年代里,在个人利益至上的背景里,“集体权威”与“集体利益”显得那样虚弱不堪。这时,个体得不到“集体”的保护,只得依靠权力、金钱来获得安全感,如果这样都没有,就只能依赖稀少而珍贵的情感以获得内心的温暖。所以,文工团解散之后,这些曾经被组织宠爱的个体被抛向社会,只能各显身手,各安其命:郝淑雯与陈灿凭借父母的权势很快在社会上拥有巨量的金钱与较高的地位;林丁丁凭借家族的帮助,远赴海外安享富太太生活;萧穗子因为有写作的才华,也拥有了安稳的生活;而曾经的“学雷锋标兵”刘峰,成了一位残疾退伍军人,一无所长,生活也几乎一败涂地;曾经被家庭嫌弃的何小萍,在精神失常之后,虽然得到了治愈,但仍算是弱势群体,只能与刘峰相互依偎,彼此慰藉……
因此,《芳华》像是一部怀旧之作,用一个部队文工团的命运沉浮来裹挟几位团员的人生起伏,甚至折射中国最为跌宕起伏的几十年风云变幻。这类题材的魅力就在于人物命运和时代变迁的交织、映照、互文式隐喻。观众能在人物的命运书写中看到人物本身的性格、品性的决定性作用,更能看到时代性洪流如何使个体身不由己地走向自己并不期望或未曾预料的轨迹。以此作为参照的话,《芳华》其实是有点单薄的,在情绪比重和情节节奏的处理上并不如人意。
如果说影片是为了展现一幅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的浩荡画卷,那么,影片应该在节奏上注意张弛有度,精心选择情绪的着力点,保证各个段落有适当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小高潮,并在冲突的累积中将观众带入更为震撼性的结局,从而在情绪的奔涌中令观众感动、深思,获得情感上的净化或者精神上的洗礼。但是,《芳华》在前半段花了太多笔墨表现文工团的排练、何小萍在文工团所受到的排挤与歧视、文工团里复杂的情感关系。这些内容当然是这个文工团最重要的历史印迹,也是表现人物之间关系和人物心理波折的重要载体,但是,在这些略带拖沓的叙述和略显平淡的剧情中,这一部分的情绪感染力其实非常薄弱。
本来,自从何小萍进入文工团,她才是理想的叙述视点的担当者。因为,影片可以通过她的眼睛来观察这个对她而言充满庄严魅力的世界,并最终悲哀地发现这个世界背后的种种不堪,从而以何小萍的心理嬗变勾勒那个“革命时代”的粗粝面目。但是,影片却让老年萧穗子的回忆来串联全部情节。萧穗子作为一个旁观者,固然可以保持一种叙述的冷静、客观,甚至因置身事外的安全距离而变得清醒、犀利,但其实也必然带来对他人内心的隔膜与困惑。当年老的萧穗子用解释、评论性的话语来说明林丁丁、何小萍的内心世界时,观众的心情很难说是感激还是反感。因为,这间接说明影片没有能力通过各种艺术方式来呈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波澜,演员也无法通过微表情的处理、细节的凸显来透露内心的微妙起伏。尤其是对于那些至关重要的情感逻辑,影片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细节与场景,才能让观众觉得人物的选择无可厚非,甚至理所当然。例如,刘峰为什么会爱上林丁丁?萧穗子为什么会爱上陈灿?林丁丁为什么会如此滥情?影片几乎无法提供水到渠成的情感逻辑,观众也就只能在突兀与错愕中暗自失望了。
由于影片在前面的部分铺陈了一个很大的情感摊子,不仅造成这些情感的描写粗疏而草率,而且造成影片主题上的偏移与错位。在这些情感关系中,观众也许可以原谅情感逻辑的简约化处理,但难以容忍这些情感关系对于时代的表达如此无力。在影片所涉及的20世纪70年代,理应有那个年代的择偶标准和爱情价值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爱情的心理学和社会参考维度都有重大改变。影片理应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爱情关系变化来折射爱情价值观的变化,而爱情价值观变化又正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注脚。如此,影片中复杂的爱情纠葛才会有超越情感本身的社会意义。本来,郝淑雯得知陈灿是高干子弟之后,立刻芳心暗许,这勉强可以算是时代人心的一次侧写;还有林丁丁,从单纯地爱慕有才华、有颜值的陈灿,到喜欢风光潇洒的摄影干事,时代风尚一变,立刻又毫不犹豫地投入华侨的怀抱,这本来是一条非常有潜力的线索,但影片描写得过于隐晦和单薄,失去了叙事意义和情感力量。更重要的是,影片对于两位主要人物刘峰和何小萍的情感关系处理得突兀又表面,几乎脱离时代的影响而成为“纯粹情感”的高调宣言。
当影片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表现20世纪70年代的文工团成员的生活,却又在这些命运书写中未能提炼出像样的社会命题和人生感悟,随后的几十年用几个场景就交代了刘峰和何小萍的人生际遇,就更显得粗疏了。如此一来,影片就真的只停留在为几个当事人编写回忆录的初级层面。甚至,这份回忆录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刻骨铭心,但对于观众来说却可能感觉漠然。
此外,影片的叙事重心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萧穗子在影片开始就强调这个故事是关于刘峰与何小萍的。既然如此,影片就应该更多地将叙述焦点放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关注他们内心的憧憬、矛盾、两难、犹豫、勇敢。但是,影片不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何小萍同宿舍的几个人身上,又未能在这几个人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戏剧冲突(那些女孩子之间的欺负实在上不了台面),同时还留下几条断断续续的情感线索,实在有些凌乱。尤其对于刘峰,这个被各种细节和动作证明了的“学雷锋标兵”,却突然强行拥抱林丁丁,实在让人始料未及。本来,让刘峰突破外界施加的刻板标签,展现一个圆形人物的立体性与复杂性,这可以成为影片的一大重要突破。但这种突破的前提是让观众对人物有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了解,而非想当然地让人物突然告白就证明这不是一个只想着做好事的“活雷锋”。
影片可谓成也文工团,败也文工团。“败”之处在于未能通过文工团及团员的命运轨迹来表达更为宏大和具有穿透力的时代命题,“成”的地方在于通过细腻的描写为观众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艺术形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些有历史质感和生活气息的画面中,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感受那个特殊群体各自的苦痛与悲欢。因此,《芳华》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让20世纪70年代部队文工团的生活以近乎纤毫毕现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但影片对人物命运感染力的营造,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捕捉与表达有笔力不逮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