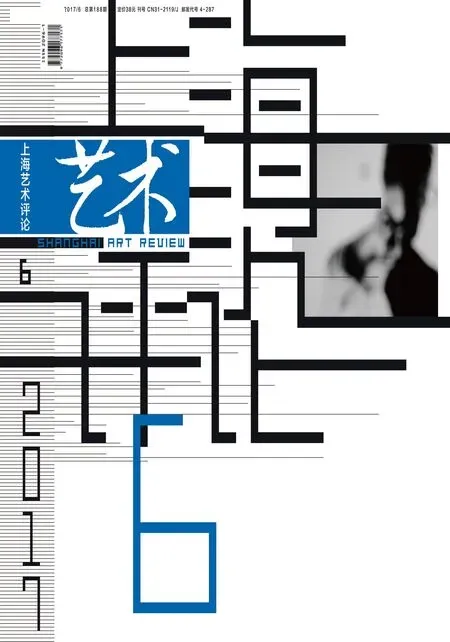一种漫步艺术
卢茨·科普尼克 石甜(译)
一
在《拱廊计划》里,本雅明精彩描述了用皮带牵着乌龟漫步的习惯,这是19世纪中期的一种减速方法,专心观看城市景观,也接受别人的凝视。牵一只乌龟散步,抵消工业速度和交通的力量;不是根据城市交通系统的抽象快节奏,而是根据人体的缓慢节奏,穿梭并标记了这座现代城市。
本雅明对城市漫游的关注,反映了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一直对城市漫步感兴趣,想把都市街道的热闹变成充满想象力的游戏场,在工业现代化越来越多的理性和节奏中,重新获得迷路的艺术,创造性的迷失。本雅明回顾了查尔斯·波德莱尔等19世纪漫游者们以及他们的期望,从城市拥挤人群的大步流星中,提取审美体验的强烈时刻。波德莱尔赞同漫步艺术是一种工具,改造自己的身体,远离了现代时间的冲击。
漫步当然不是现代美学的独家发明或者发现。它给现代主义艺术家提供掌握工业化空间的某些决胜战术。弗里德里希·尼采发现,独自漫步可以找到巨大的娱乐快感,把脚步的节奏转化为诗性和辩证思想的强大引擎。伊曼努尔·康德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哥尼斯堡大街上严肃散步,为了锻炼身体,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的严格要求。让-雅克·卢梭尽可能找机会去散步,强调思考和散步的内在关联。
如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等现代主义者,强调都市漫步者可以从工业社会的分裂空间中汇集零碎的印象;对卢梭而言,散步的缓慢艺术赋予行走个体一种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感,一种感知一致性。散步把笛卡尔学派哲学认为是分开的两者整合成一个单一动态的统一:精神与物质。我走、故我思、故我在;卢梭这样说,揭示了笛卡尔前工业化时代和本雅明工业时代漫步乐趣的巨大差异。对于卢梭(尼采和康德)而言,散步触发和激发思考。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则相反,散步的行为不再有助于思考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演的是没有认同、也非存在的时刻,反抗坚定认同、目的论、工具理性的现代要求——我走,故不再是我。
对卢梭而言,散步激发他的思想和自我概念,因为它把行走者从“唤起我回忆起自己处境的一切”中解放出来。正如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所写,卢梭的漫步提供了调整异化感的一种有效手段。散步,意味着通过超出限制的缓慢身体运动,扩展心灵和身体。每当我们散步时,我们总处于给出某种有意义判断的持续过程,虽然极不稳定,但在“不断路过”的印象中有一种“在这里”的感觉。去散步,要有游离结构,但又不脱离物质基础、移动和身体衡量。把移动的身体转变成知觉的一个活力媒介,把自己暴露于某种形式的自我异化、不确定中,希望加强经验,恢复在视觉和其他感官传递中被遗忘的。
对这三位诗意的哲学家而言,慢下来,是暂停现代二元论、线性、目的论、目标为导向的时间和透视、结构的、抽象的空间。在所有流动和变化中,把感知的身体放在一个不稳定的认知领域,让漫步主体探索她感官系统的局限,感知这个世界由开放的潜力和基本不可预测关系所组成。在这些漫游者的变换视野中,空间不再被认为是固定和均匀的,没有时间、叙述和记忆。漫游者只不过是想慢下来,与周围空间相遇,作为颤栗、惊讶和狂喜的一种潜在资源——审美体验的资源,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探索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一方面,在关于漫步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之间;另一方面,漫步在21世纪审美实践的重要性。本文的重点是加拿大艺术家珍妮特·卡迪夫(Janet Cardiff)的作品,在她的作品中,漫游所扮演的角色。卡迪夫的作品尽力混杂不同时间表达和历史,要求我们重新思考。
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珍妮特·卡迪夫进行声音的实验,让她成为当下最有趣的艺术家之一,从视觉的主流关系中寻求释放审美和虚拟。卡迪夫最为人熟知的是她的“声音漫步”(audio walk):带有本地地理信息的立体声录音,一段段故事元素和音乐片段,现场声音和不同音效混合到一个音轨;无形的艺术品意味着用耳机来听,跟着卡迪夫记录时的步调走过如纽约、明斯特和伦敦等城市,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丹麦的路易斯安那博物馆等博物馆。她的其他一些作品,将当代艺术中听觉的地位推向新的实验前沿,让我们体验声音作为一层膜,让我们的脚步慢下来,连接(分离)身体和环境、表现和知觉、运动和影响、虚拟和实际。特别是她在2001年的装置艺术《四十赞美诗》,卡迪夫把四十个扬声器围成一个圈,每个扬声器有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的16世纪宗教剧《寄希望于他人》(Spem in alium)的一段声音。
“你好,你能听见我吗?”我们一开始听到卡迪夫的声音,她在路易斯安那博物馆漫步,用声音向听众致意,把“我”作为她作品的唯一接收者。“我想让你陪我走过花园。让我们到外边去。”我们听到脚步声,听起来像走过一段硬木地板。我们听到一扇门在我们面前打开的吱吱声。在几秒钟内,卡迪夫平静、亲密的声音已经设法使我们想要把自己的身体动作、感知与包围我们的耳朵的立体声结合。我们一开始进入声音漫步的世界,顺利又有效,两个元素是关键的。第一个与卡迪夫的声音有关,温和、色情又节制,这个听着空洞的声音似乎直接致意我们,好像在我们的耳边或者周围,仿佛使我们有一些亲密、信任和开放的精彩形式;就像我们曾经或从来没有听过除了这个声音以外的声音。
被拽入卡迪夫的世界时,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关注身体移动本身的力量。“我们走下楼梯,”在路易斯安那漫步一开始,卡迪夫继续说,“试着按我的脚步声来行走,这样我们可以呆在一起……你听到海浪吗?……这里很美丽。“这是她感觉、记忆、和期待的过程,这是让自己听觉上沉浸到她所看到的、听到的、记得的、梦想、愿望和想象中,无需关闭我们自己感官感觉——我们自己的感知、记忆、梦想和愿望,自己的存在感。

珍妮特·卡迪夫,《四十节赞美诗》,2001
1990年的上半年,当卡迪夫开始尝试创建声音漫步的想法,她琢磨了最近一些作品,将漫步实践带进艺术媒介中。卡迪夫把不同声音、声音效果和叙事时间进行分层,让听众体验根本不同步的多样性,囊括了不同当下和过去、时间向量与轨迹的支离破碎。卡迪夫的声音反对任何线性时间、顺序和年代。
珍妮特·卡迪夫的声音漫步是一个例子,让我们身体感觉到自己的听觉。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立体记录技术复杂化甚至取代普通的分离方式,往前看,而且鼓励听众/观众/漫步者直接引导自己“感觉”身旁事物,从而置身于各种环境和时间视野。当我们听直升机飞过头顶,我们相应调整我们的身体姿势和动作,我们不得不融入到那些拉贝尔认为的声音基本二元性,即地点特殊性及其对空间固定性的相对挑战。在卡迪夫的作品中,存在,就是允许漫游者触及自己身体形象的不确定性(inconclusiveness)和流动。把我们同时置身于各种实际和虚拟世界中,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与我们的触觉身体,去感知和遨游空间的急剧收缩、扩张和增长。卡迪夫作品中的“存在”,是揭示自己一直“不存在”。
在卡迪夫的作品里,空间永远不是单一的。聆听和漫步不只是使空间时间化,而且触及了我们整个感觉中枢,从而体验什么是空间的时间性和多元性。它成为接受异构、不稳定和我们感知的空间与身体感知的空间的交织本质。她的声音触摸我们的内心,但这种感受是无形,而不是可见;它出现于看不见之中,而不是来自移动和时间图像的影像呈现。卡迪夫采用行走的媒介及其慢速美学,为了探索空间的迷失,释放空间的无法表达性——空间拒绝被转变成静态的、文本、图像或其他任何表征形式。我们现在要转向行走的慢速与无法表达(unmappable)之间的关系。
三
没有什么比描述“时间、生命和人类意识像一条河”一样更陈词滥调了,缓慢但不可避免地流向终点。它表明变化的某种自动性,因此可以预测进展或从初始到终结的过程。事情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但变化本身是可预计的。
卡迪夫在采访中清楚地表达:“音轨中,当我回忆起一些有趣的事情,我立即与听众分享。对我来说,它们永远是过去;但对听众来说,它们是当下的一部分。我感兴趣的是,时间以这种方式推移,过去和现在之间纠缠不清,回忆它,把它带进现实。”卡迪夫的重点是,我们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漩涡、涡流、倒置和不同速度。每个当下怎样同时囊括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的期望,看上去几乎不可能从一些外部角度来表达当下。
卡迪夫2000年的漫步作品《一条巨大的缓慢河流》(A Large Slow River),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盖尔洛赫花园的奥克维尔画廊展出。漫步从画廊里开始,卡迪夫的声音似乎描述一个破坏和混乱的场景,然后我们跟着卡迪夫到门口,在画廊的花园散步。她描述这些风景:植物、花卉、湖边、海浪撞击海岸。她经常说起破碎的记忆、梦境和反思,时大时小的亲密。音轨中出现第二个声音,是乔治·布雷斯·米勒的声音,有巨大的压迫感和神秘感,把我们注意力吸引到一些电影的过去战时黑暗岁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声音似乎在平行宇宙中。但是在其他的时刻,他们彼此对话。各种声音效果增加了神秘感,我们穿越各种过去和现在,我们见证了回忆和当下如何形成一个混合想象,像海浪冲刷岸边一样不固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听到,手风琴演奏者、歌剧演唱者们、孩子们的声音、海妖、动物、枪声,以及不可避免的直升机声,一些声音与卡迪夫的声音相联系,一些与米勒的叙事世界相联系,一些明显跨越两者边界,互相结合成对漫游者来说高度混乱的声音体验。漫游到最后,主人公搜索了一些无名人士的录,录音带从当下过去,面对一个未知未来说话。米勒的声音(在录音带里)在漫游的最后一刻出现:“爱因斯坦说,时间如河。它不会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速度”。

珍妮特·卡迪夫《回忆之地》2006 “声音漫步”(audio walk)
跟随卡迪夫的脚步走过盖尔洛赫花园时,时间的确有不同速度,这是卡迪夫的惊人能力,让漫游者获得速度不可比拟的动态,我认为这是她的慢速美学作品核心。在这个特定的漫步中,卡迪夫又一次激起接近感,表达当下空间中,异质时间的未分解共存:“我在休伦湖的海滩,”卡迪夫沉思,提起一系列情感回忆的场景。“我的脚趾踩进泥泞中,深深感觉到它们的消失,就像每个波浪冲刷它们一样,从父亲打湿的肩膀跳进水里。现在我在另一个海滩,现在是晚上,海浪的声音通过窗户玻璃传进来。“记忆进入了卡迪夫的分裂叙述,视觉水平上很少有这种体验。它出现,被传到正在聆听的漫游者那里,作为触觉或触觉场景:脚趾接触泥土、她父亲的肩膀感觉湿润,声波穿透玻璃的力量,与睡眠者的耳朵进行身体接触。
卡迪夫沉浸在时间的多重河流中,卡迪夫听众的漫步,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不稳定的,经历了被罗杰·卡约(Roger Caillois)称之为精神衰弱(psychasthenia),即一种深刻的人格解体感,由我们暂时无法可靠地将我们的身体放置在空间中造成。卡迪夫的漫游者不只是听到脑海中的其他声音,他们也开始吸收别人的感觉,或其他空间和时间的物质体验穿在自己身上。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无法定位和确定具体主体所在的地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那里的。在卡迪夫的声音漫步中,不同记忆和破碎故事的触觉共存。
在现代美学实践中,速度体验往往导致暴力爆炸或身体边界的递减硬化,卡迪夫关于缓慢行走的作品成为媒介,有趣地探索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展,而不用担心现实中解体或投降。卡迪夫混合了虚拟和实际,鼓励我们体验我们自己移动的身体在各种空间和时间中的重量。在卡迪夫看来,慢下来,意味着恢复我们的能力,并期望成为以及变成他者,与时间的不同河流接触,我们所看到的被复杂化。慢下来,让我们再度迷失:体验每个现状都有记忆的虚拟和潜在未来。
四
唐·伊德认为,当音乐冲洗、冲刷着听众,我们遇到知觉场域的某种可能性,“焦点关注‘延伸’到声音边界作为当下。这种‘延伸’和‘开放’再次充满空间-时间。但空间性也是‘厚重’,我无法找到其界限。虽然我可能‘沉浸’在声音‘氛围’中,但找不到空间边界。视线的空间意义是模糊的”。在这样的经验中,世界变成声音,我们作为听众被完全融入进它的无边无垠整体中。我们只是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影响和共鸣的媒介, 在我们周围似乎没有任何界限。
珍妮特·卡迪夫在2001年首次录制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唱诗班作品《四十节赞美诗》(Forty Part Motet),后来在不同地方展出。在卡迪夫的《四十节赞美诗》中,在意愿和非意愿、主观和客观、感觉和审美、有限和无限之间,漫步行为有意打开了边界。
之前提到过,《四十节赞美诗》来自《寄希望于他人》,由英国作曲家托马斯·塔利斯于1570年创作的一个宗教剧,八组五个声部的唱诗班。《寄希望于他人》是一个大实验,是早期现代音乐文化将重点从连续色调的旋律关系,转换到相互作用声音和谐互动的例子,事实上它是如此激进的一个实验,过去和现在的听众都忍不住觉得,抵达他们的耳朵的声音常常被厚厚的地毯蒙住了。每个声音都不断移动:它们有时唱歌,有时沉默;它们有时加入其他的声音,有时追求自己独特的旋律音高;有时部分唱诗班的一部分成员似乎回应其他成员的演唱,有时似乎每个成员都愉快地忽略彼此。
自2000年代初以来,卡迪夫对塔利斯基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唱诗班乐曲的改编版本,安装在教堂、博物馆和其他展览场所,合唱团成员的每个声音被分别记录,然后分别通过四十个扬声器播放,固定在一个巨大的圆圈,每个扬声器指向中心。《四十节赞美诗》不要求听众在前排和静态位置坐下,而是让我们自己沉浸到塔利斯的赞美诗中,通过在整个安置的扩展雕塑领域内积极移动我们的身体:走近单个扬声器和声音,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整个唱诗班的某些片段。听众不是仅作为一个声音表演的被动接收器,而是通过他或她的走路活动,将其带入生活,开始不断和出乎意料地创造、再创造塔利斯复调声音之间雕塑般的关系。
关于新媒体美学的研究,经常被认为与二元论相似:做与不做、实际和虚拟、精神和物质、这里和那里、现在和然后、战略行动和无意识融入、触觉和象征意义等并置。卡迪夫的《四十节赞美诗》让我们想象一个不同、一个更复杂的、但毫无疑问也不太完善的概念,关于审美快感的主、客体关系,进行和“完成”的二元论,实际和虚拟、行动和感知。这种奇怪的二元性,是卡迪夫慢速美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在卡迪夫作品中,我们都是声音。有时,声音穿过我们。
在卡迪夫的作品中,把移动身体作为审美体验的最基础媒介,《四十节赞美诗》把声音和再生产、触觉和无形、实际和虚拟,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动态统一。卡迪夫的目标是鼓励我们使用所有的感觉器官,产生审美的时间-空间,它是一个开放的共存,各种声音和关系、过去和现在、这里和那里都同时存在。
五
在我们这个不断迁移、高流动、加速电子连接的时代,提倡漫步的慢速艺术可能被视为既体面又合适的:有益调解把身心重新安置在特殊地点,而不是全球空间的抽象和快速分隔(fast-spaced)。
在卡迪夫的作品中,一方面,她让土地-城市风光充满了萦绕的记忆、不确定的故事、叙事、有远见的期望和正在进行的移动。漫步,留下的既不是空间,也不是地点。卡迪夫的慢速美学强调的是,用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话说,地点只不过是“零碎的、内卷的历史,不允许别人翻看的过去,积累的时间可以展开,但却像故事一样被保留,保留在一个神秘状态,包裹在身体疼痛或快感中的象征”。
另一方面,卡迪夫对身体移动和声音的多向性(multidirectionality)的独特结合,导致主客体之间、有意和无意之间界限的深层审美解体。在卡迪夫的作品中,漫步,意味着放弃对控制的现代文明式傲慢,并学会承认我们既不是感觉的自决靠山,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
在卡迪夫的作品中,慢下来,让我们放下我们通常的意图、动力和路线,放弃我们渴望掌握和控制,为了被意想不到的遇见所吸引和再体现。她的慢速美学打开另一个/些空间:想象的意料之外的状态——虚拟的和有潜力的,记忆的和未知的——帮助构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