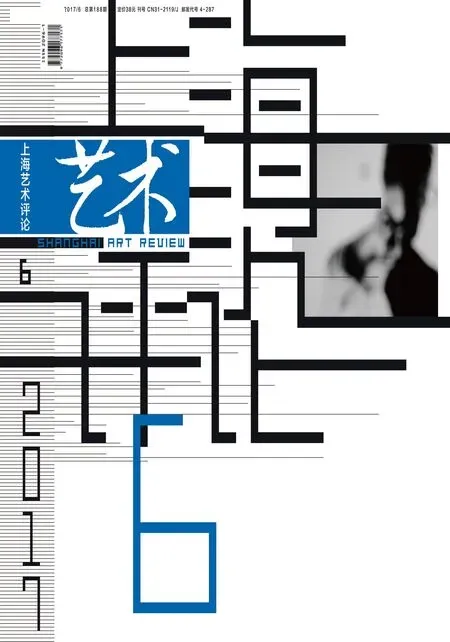寻找乌托邦:“神”的故事—关于电影《皮绳上的魂》的讨论
王 杰 周晓燕等
王杰(浙江大学特聘教授):2017年8月上映的电影《皮绳上的魂》(以下简称《皮绳》)改编自西藏作家扎西达娃的两部短篇小说,扎西达娃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所以,我们的讨论绕不开小说原著,尤其是《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电影涉及很多问题,包括乡愁,乌托邦等,扎西达娃在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中直接提到了莫尔的乌托邦,叙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与藏族地区文明发展的复杂关系。
徐玉明(浙江大学博士后):关于电影的内容,它借用藏传佛教的象征,来讲述一个也许与藏传佛教无关的故事。这里喇嘛并不代表藏传佛教,而是代表塔贝自身的“命运”。这部电影总体框架是对现代性的思考,不过从终极的宗教意义上来说,小说的宗教感和神圣感达到了一个高度,而电影没有。
彭斯羽(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我不太理解对于这一段旅程,塔贝设定的目标是什么。电影的最终是作者与活佛对话,活佛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来统摄。”可见电影的目标是在于导演自己想法的表达,而不是塑造塔贝这个人物。如果这样来看,那这个电影真正的主角是作者。
王杰:是的,无论是电影和小说原著都与宗教有关,借宗教神话来讨论现代人的人生意义。电影真正的主角是作者,小说中关于这点说得比较明确,而电影却不是很明显,因为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小说中,作者与他自己写的人物之间有明显的交集,而电影却以另一种形式来展现,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创作。“天珠”在小说原著里是没有的,我认为天珠的设定是受好莱坞大片影响,有了这个线索物的好处在于方便叙事,好像有了这个天珠,就有了使命,主人公就要去完成这个神秘的使命。同时,也从叙事学的角度,给了我们分析的角度。小说作者的设计比较符合“多重语境”下的艺术表现,比如当时的语境,小说发表于1984年7月29日,作者想呈现出多语境性和多时空性。按道理讲在山上应该没有电视机,听不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声音,而写作的地方则很有可能是在城里,城里是有电视机的,所以,《皮绳》的时空设置其实和《路边野餐》有些相似,甚至有可能更复杂。因为,《路边野餐》只是回到了九年前的时光,去寻找曾经的恋人和曾经的生活,而《皮绳》不仅在寻找自己的,还在寻找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原著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的问题意识和思考的框架还是很大的。西藏这个地方,其实用马克思的思考方法来探讨是最直接的,这是现代化与原始文化相遇的地方,因为有些地区还是很蒙昧的,比如塔贝,这个人物拒绝一切现代文明。
丁旭(浙江大学博士生):我不太同意塔贝拒绝一切文明的说法,因为小说中他去甲村的时候学习了如何开拖拉机,甚至他的死亡也是因为学拖拉机而导致的。可以说他对于现代科技是带有某种好奇心的。
王杰:是的,小说中塔贝死于拖拉机车祸本身就是一种很明显的与现代科技不调和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多语境的叠合。我们可以用两点来分析,一是关于这个时代,它从小说到电影提出了什么问题?小说和电影的表达有什么不同。原作的情节很简单,如果用原作的情节拍电影,会很难拍。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这个电影拍得并不好,看完这部小说,我记住了扎西达娃这个人,电影《皮绳》看了之后,很失望,但失望不要紧,小说还在,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周晓燕(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皮绳》拍成电影后,获2016年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我先看小说后看电影,无形中会有对比,我认为小说比电影更艺术。小说中有个扎妥寺,寺中第23位活佛和23届奥运会之间有意义联系吗?我觉得扎西达娃是理解魔幻现实主义或者说超现实主义的,而《皮绳》的导演并没有很好领会。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曾被收录到1988年出版的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丛书名叫《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面也有莫言的小说,只是莫言代表的是家族式魔幻,扎西达娃代表了藏族文化的魔幻性叙事。可以说,藏族天生就具有魔幻基因。我觉得扎西达娃有可能并没有深度参与编剧,按我对扎西达娃的思想的认识,他是不能接受导演这样拍的,可是影片却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对此,我不太能理解。另外,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是谁的魂系在了皮绳上?
王杰:我想23这个数字应该是巧合,是作者在写的时候顺手让它和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这个大事件关联起来。1984年对你们来讲是纯粹的时间概念,但其实1984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另一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人奇迹般暴富,比如小说中的农民,暴富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冲击很大。我当时读《红高粱》,感觉莫言对此是欢呼的,而扎西达娃的这部小说几乎是打着问号的;莫言的《红高粱》是热情拥抱现代化和市场的,是野性的,这和现代性当中的崇高是一致的,比如《红高粱》中“我爷爷”是去抢人家的老婆,抢人家的酒坊,最后还去打仗。其实,放在现代化这个背景下,两者的小说和电影,如果说他们有高下的话,就是在关于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表达上。对于现代性,我认为扎西达娃不会愚蠢到要回到过去,没人愿意回去,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又向往过去,过去经过一种审美转换在作品中展现,这个过去和现实中的过去不是一个东西。所以我认为扎西达娃的小说还是符合我的“乡愁”理念的。乌托邦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如果它不通过过去,就不会有一个理想化的存在。
连晨炜(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扎西达娃的同名小说写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市场经济逐渐展开,这部小说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主人公要寻找的“皮绳上的魂”就是在传统地方性经验遭遇现代化冲击后试图找寻族群灵魂的一种努力。香巴拉是西藏信仰中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心灵世界,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而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一指称显然需要新的意义来填充。实际上寻找“皮绳上的魂”这一诉求在21世纪的今天更为需要,它在各个地区、领域、群体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是一个需要多数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王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电影《皮绳》的寓意也是很关键的东西,涉及到审美意义的滑动性和具体性,因此,我们就要把其中自然的存在作一些分析,比如神鹿和狗的寓意阐释清楚。鹿在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是意味深长的,比如敦煌壁画和佛经里面经常有鹿,它是神和凡人世界的传递者。
王杰:文学会涉及到大量文化的符号和民族记忆,比如《皮魂》涉及到神话系统、宗教系统和现实怎样去重新组合的问题。它里面就谈到琼的爸爸的身份是个行吟诗人,是唱《格萨尔王》的。《格萨尔》是西藏的民族史诗。这里涉及本雅明说的“讲故事的人”,行吟诗人是神话的代言者。现代化之后,整个世界不存在神话了,但神话可以转化为一种寓言,就是神话的基础没有了之后的故事,比如琼的爸爸,琼有他爸爸的文化基因,我想在这里还有很多弗洛伊德的东西,弗洛伊德的确是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资源。梦幻和现实的关系,在现代艺术生产中已经成为一套话语系统,用精神分析理论,从弗洛伊德到拉康还是好解释的。为什么张杨能拍《皮绳上的魂》,因为这套东西已经完全符号化,按照这个系统就可以操作了。比如这一套东西,从魔幻现实主义到现在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哪个是他者,哪个是自我,哪个是它们中间的传递,再设计一块石头,完全可以照着某种成规来弄,这是不难的,是套路,学电影的人对于这一套东西十分熟悉,但是没有本雅明说的灵韵。本雅明是原型批评的一种类型,他的理论对于当代艺术分析非常重要,在神话这个大的体系不存在的情况下,本雅明有助于我们把握住碎片化时代。电影《冈仁波齐》里有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人都稳稳地在那个体系里,有信念,不犹豫。后来开始进入小说《皮绳》的年代,这个体系就破了,然后到张杨的《皮绳》,这个体系就更碎了。所以,好的讲故事的人,即便是碎片,也能很好地把握住人物。这个题材很好,但是不好拍。从80年代到现在,肯定很多导演看过这部小说,也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但为什么没有人拍,的确很难驾驭。因此,张杨加进去一个为父复仇的故事,这是小说没有的,完全是好莱坞的类型片。
周晓燕:从期待视野角度来看,我们在座的各位倾向看到一部需要观众“有准备”才能看懂的电影,而不是无需任何知识储备,更无需思考就能看懂和听懂的爆米花电影。《皮绳》并没有把现代化列车上的人的魂表现出来,还是定位为商业片比较合适,而这个定位恰好与导演在诸多访谈节目中表达的自己的艺术追求相反。

电影《皮绳上的魂》
王真:其实好的商业片也可以达到很高的审美效果,这个题材可以拍成一个既有比较好的票房,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的电影,也就是说这个题材本身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电影《白鹿原》我看完之后也是大失所望,它也在阐释一些神话的大的体系。神话相当于全息摄影,在神话体系里,即使是一个碎片也可以表达出全部,破碎了之后,只有少数人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性,它能够通过碎片把握住整个全息。大部分人,碎片就是碎片,这个碎片就像一个万花筒,看上去是五彩缤纷的,但是实际上仍然没有把握住整体,这也是当代艺术的特殊性。
王杰:中国的传统艺术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有一个深刻的断裂,一直到文革,都在断裂,中国的语境和西方是不一样的。电影《皮魂》观后的宣传会上,导演张杨讲到,西藏其实很敏感,可以说全世界最敏感的地方之一,但他是得到允许去拍摄的。
彭斯羽:按商业片来分析它,就不把它拔高了。它不能唤起任何宗教感。塔贝的决定始终太突然。如果把这部片子当公路片来看,也感觉不到这一路上主人公的灵魂。作为一部电影,如果能表现一个人为什么走一趟,好好地表达出来就很好了。踏实地讲故事,做成商业片也没什么不好的。
丁旭:小说里面所描写的仪式,包括活佛去世、磕头以及他们在“甲”村的经历等,这些是电影里没有,在小说里指向现代文明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我觉得可以定义为“他者”或者是“少数文化”。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小说的最后,“我”想知道琼离家的日子,于是数了她身上的皮绳的结数,发现结数刚好跟塔贝手腕上的念珠的颗数相吻合,是108个,有一种乌托邦幻象的感觉。
王杰:小说对未来是很茫然的,但电影改编后变得很明确的,他就要找到那个地方,相信找到了那个地方一定有解。我认为,把去世的活佛处理为一个声音的存在,好像一个上帝一样,是很诡异的。电影《皮绳》的幻象感非常突出,导演自己认为用幻象就能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肤浅的地方。最终人宽恕一切就圆满了,符合宗教理念,但是不符合当代人的情感逻辑,或者不符合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所以我认为电影版的《皮绳》始终没有乌托邦,但是小说版是有的,一个理想的,又是不存在的地方,就是塔贝要去找的地方。
徐玉明:对于抽象的宗教,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宗教如何组织其意义世界,可以说这是世界观的层次;第二个是在这个宗教中的人需要做什么,可以说这是伦理学的层次。宗教能带给人意义,并且这个意义是直接指向这个人自身的。那么,如果我们将影片理解为其意义指向塔贝之外的无论是荧屏背后还是影片之中的那位作者,那么这个意义也就并非指向塔贝。可见,塔贝的形象与作为塔贝“命运”象征的喇嘛形象实际上已经外在于电影的意义建构了。因此,并非塔贝代表藏族,而是作者意图代表藏族。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指向。宗教带给社会一个意义性的维度。一个社会可以在某个体系中具有某种意义或者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其意义性通过宗教得到了维系。
王杰:所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宗教性的电影。宗教电影有两种,一种是懂宗教的人,通过看电影得到一种洗礼,有所感受。另外一种,也就是张杨这种,是因为用西藏题材,这个题材必然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对于电影《皮绳》而言,这就是卖点。因为,现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情况,就是整体意义的缺失,西方世界,即便是欧盟都找不到北了,不知道什么是未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打宗教牌是容易赢的。张杨选的这个西藏素材有当代性,可惜他自己没有到那个境界,没有唤起观众的宗教感,这是他的失败。如果只展示西藏佛教的神秘性,那么这种艺术家是很愚蠢的。很多艺术家只是在做文化产品的生产,然后销售,获得了名誉和金钱,成功了,但没有唤起人的宗教感。扎西达娃后来的小说都没有这篇好,他也想要表达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达到像《百年孤独》、《白鹿原》那样的水准是很难的,涉及到更多的符号系统,很难短兵相接,击中要害。电影《皮绳》现在还想把它表达成一个宗教系统,这就更难了,电影加了一些复杂的东西,但反而破坏了原有的宗教感。
张杨之前拍的《爱情麻辣烫》是没有神圣性的,可是爱情还是有神圣性的。如果说文学生产是在往两个方向前进的话,宗教就是在把人类往神性的方向引,那么,《爱情麻辣烫》是在把人往动物的方向引。这是现代化的一个问题,好像越感性,越野性越好,这是有问题的。虽然在特定语境下有合理性,但把它作为神性对待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宗教就是动物性,那动物早就成了神了。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经常用动物来比喻神,而且都是怪物,如电影 《长城》中的饕餮,它不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动物。古人认为,人和神的沟通是通过神兽实现的,所以,电影里增加了神鹿、石头天珠、小孩等,加进来就是为了让故事叙事的复杂性和线索多一点。电影渲染了神秘性,神秘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撑是很可笑的。《哈利波特》有它特有的文化系统支撑,所以它的神秘性可以成立;《指环王》把语境还原到远古时期去,还原到一个神话的世界,而张杨努力想创造一个现实世界,同时又想创造一个神秘世界,这在我看来是荒诞的,荒诞不等于魔幻。
王真:扎西达娃的心中是有神的,而张杨的心中是没有神的。神,若有,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如果没有,就会被他这样庸俗化地图解为神秘。有学者说神就是“他者”,把他者推向无限远,也就是最高、最纯粹,最具有普遍性的他者就是神。

从终极意义和文学角度而言,只有否定的形式能表达出新的希望,比如新天使,它是不完美的,但如果是完美好看的,那么从表达上来看,就是世俗的维纳斯。所以,扎西达娃没有去重建神话世界,而张杨在影片结尾偏要告诉你神是什么。按照尼采的说法,神是要死的,就是美杜莎的目光。那么“神”是什么,神就是乌托邦,一个可能存在的理想的完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