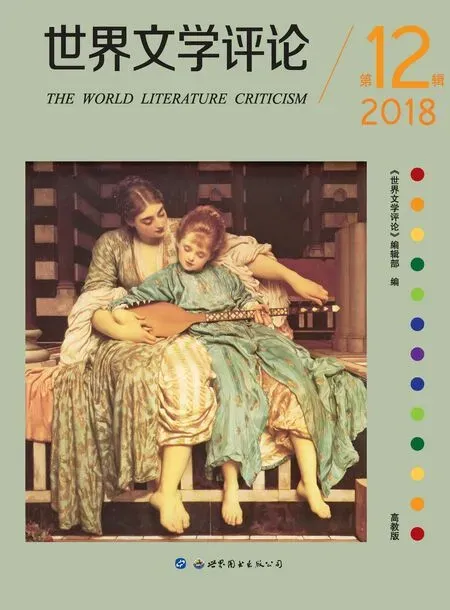富士山汉诗中的神化叙事①
唐千友
一、富士山与富士山汉诗
富士山(FujiSan)位于静冈县与山梨县的交界处,海拔3 776米,是日本最高的山峰。从地理属性上来看,富士山是典型的成层休眠火山,山顶有直径约800米的火山口,在火山口的周边,由于熔岩侵蚀的作用,锯齿状分布有八座山峰,即“富士八峰”。从形状上看,富士山属于标准的单体锥形火山,具有独特的轮廓美。同时,由于山体高耸入云,富士山山顶终年积雪。
富士山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之一,不仅在日本国内,在全球也享有盛誉。它也经常被称作“芙蓉峰”或“富岳”以及“不二的高岭”。富士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为日本众多艺术家提供了无穷的创作题材,是古今文人讴歌的对象。自古以来,这座山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日本汉诗以及日本的传统诗歌“和歌”之中。高野兰亭(1704—1757)《冬日登楼望芙蓉》诗曰:芙蓉突兀压楼台,极目登临酒一杯。万里浮云天外出,三峰积雪日边开。振衣大岳寒光动,依剑中原紫气来。自有名山常不负,千秋辞赋试仙才。诗中的芙蓉即是富士山。
正如《冬日登楼望芙蓉》一样,富士山汉诗是指古代日本人直接运用汉字创作的讴歌、赞美富士山的日本汉诗。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成书于公元751年,这意味着汉诗在日本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唐千友(2012)统计了《日本汉诗新编》等10部国内出版的日本汉诗文集,这些诗集跨越日本汉诗发展的各个阶段,共辑录日本汉诗约3 000首,其中有关富士山的汉诗共计136首,约占总量的5%。这些汉诗有的直接以“富士山”为题,有的则是以“芙蓉”“富岳”等富士山的别名为题,既描写了富士山客观实在的一面又叙述了它人文抽象的一面,考察这些汉诗,我们发现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富士山的不同风貌,其中对富士山的神化叙事可以说是富士山汉诗鲜明的创作特色。
二、富士山汉诗神化叙事的表现
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山岳与宗教神话总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因缘。《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山岳与宗教的因缘起源于人类对山岳的崇拜。当原始先民面对巍峨壮观的山岳以及发源于崇山峻岭中的河流,无法理会山岳高耸入云的磅礴气势、兴云布雨和孕育万物的神秘力量时,自然就产生了朴素的山岳崇拜。我们知道日本起源于农耕社会,日本人民历来就将孕育农耕所不可或缺的水源的山岳视为神居住的地方,同时山岳也是往生的先祖们灵魂居住的他界,因此敬山文化在日本由来已久。
富士山作为日本的第一高峰,自然是山岳崇拜的图腾。赖春风(1753—1825)《折腰山》诗云:亭亭出尘姿,谁复竞高标?折腰如揖我,山色隔江招。这里的“折腰”可谓语出双关,既指攀登如此高的富士山让人折腰,又指富士山的“亭亭出尘姿,谁复竞高标”让人为之折腰,显示了作者对富士山的崇敬之情。资料记录显示,在文化十三年(1816)一年间,登拜富士山的人数就达到了一万数千人之多,而当时的日本总人口约为三千万人左右。这种对富士山的崇拜催生了日本的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富士山的神秘性就表现在各种神话传说与原始宗教之中,自古以来围绕富士山的各种神话传说可谓不计其数。众多的神话传说直接推动了富士山汉诗创作上的神化叙事。
考察富士山汉诗,我们发现富士山的神化叙事大致集中在四个方面:和日本国土以及民族起源有关的神话;和日本国名有关的神话;和佛教有关的神话;和富士山名称由来有关的神话。
(一)国土以及民族起源神话
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公元712年,太安万侣奉敕撰录)记载:天地形成之初,高天原(即天界)上诞生了十二代天神。前七代为独身神,后五代为偶生神,第十二代是伊邪那岐神与其妹伊邪那美神。二神立于天浮桥上,向大海投一长矛,然后搅动海水。提起矛时,矛尖滴盐成岛。二神降于岛上,树起“天之御柱”,建起“八寻殿”。此后二神合卺繁衍,日本民族由此而来。这就是日本国土以及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
由此可见“富士山源于天地伊始,是国土的御柱、万物之根本”。在世界古代流行的萨满式文明宇宙观里,宇宙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世界,分别居住着神灵、人类和魔鬼。联系天地的“宇宙中心”之“宇宙山”,山顶有无影的宇宙树,居住着天帝和各种神灵,山底为地狱。于是,山岳就成为人们心目中连接天地的天梯、天柱、地钉备受崇拜。这与富士山的情形极为相似,有诗为证:
宇野南村(1813—1866)《咏史·十首》(其一)
剑锋一滴化成州,天子天孙日月侔。
扬武屡征高丽国,挫凶曾覆黠胡舟。
芙蓉中立三千界,沧海四环六十周。
周鼎无人问轻重,依然万古旧金瓯。
诗中首联直接指出了日本国土以及日本民族的起源。其中的“剑锋”可谓语出双关,一方面富士山主峰即是“剑峰”,另一方面则隐喻伊邪那岐与其妹伊邪那美二神创造日本时所用的长矛。“剑锋一滴化成州”与《古事记》的“滴盐成岛”典故相互辉映,增强了咏史诗的力度,更渲染了富士山的神话色彩。“天子天孙日月侔”则是强调了日本民族随日月而生,乃是神的子孙。“芙蓉中立三千界”则是借用富士山的形状以及高度形象地暗示了富士山顶天立地,是“天之御柱”。(至于此诗的军国主义流毒,拟作另文探讨。——作者注)
(二)国名由来神话
在日语中,“日”是指太阳,“本”是基础、根本的意思。“日本”的意思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古代日本人崇尚太阳神(天照大神),所以将太阳视为本国的图腾。《旧唐书·倭国·日本国传》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圣德太子写给隋炀帝的国书落款“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也说明了日本“日边之国”的说法由来已久。此外,在汉语中,“扶桑”“东瀛”也是日本国名的别称,这些都与太阳有关,都有太阳升起之处的意思。
大田南亩(1749—1823)《望岳》
日出扶桑海气重,青天白雪秀芙蓉。
谁知五岳三山外,别有东方不二峰。
伊藤春亩(1841—1909)《日出》
日出扶桑东海隈,长风忽拂岳云来。
凌霄一万三千尺,八朵芙蓉当面开。
这两首诗首联都直接将“日出”和“扶桑”相关联,强调日本乃是“日出之国”,而富士山可以说是勾连二者的不二载体。富士山山顶就有大日岳,是富士山“八朵芙蓉”之一,日本的太阳信仰可以说来源于富士信仰,因为在日本观日出的最好地方当然是富士山山顶了,这里所看到的日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御来光”(高山日出)。古代日本先民也许正是在高耸入云的富士山顶看到红日东升震撼人心的情景,逐渐催生出了对太阳神的无限景仰。
(三)佛教因缘
莲花自古就是文人雅士“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的象征。在佛教中,佛经《百缘经》说释迦牟尼就是莲花王子,足见莲华与佛教的亲密因缘。可以说,莲花已经是佛国的象征与圣花。佛教于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富士山山顶正好环状分布着熔岩侵蚀而形成的八座山峰,日本自古就将 “富士八峰”比喻为佛教莲花座的八叶莲花,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就有“释迦岳”“药师岳”“经岳”“观音岳”等“富士八葉”的说法。这反映了富士山与佛教的深厚因缘。
柴野栗山(1736—1807)《富士山》
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
蟠地三州尽,插天八叶重。
云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峰。
独立原无竞,自为众岳宗。
《富士山》诗中“玉芙蓉”形象地描绘了富士山的银装素裹,不仅赞美了富士山独特的轮廓美,又与佛教的莲花宝座相关联,赋予了富士山神灵色彩;“插天八叶”中的“插天”一方面是形容富士山的高度,另一方面则是寓意富士山与神居住的“天”相通,是连接天地的“天之御柱”;而“八叶”则与江户时期的“富士八葉”相互印证,寓意富士山乃“释迦岳”“药师岳”“经岳”“观音岳”等“富士八葉”的母体,是众岳之宗,凸显其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
(四)山名的神话——不死的仙山
在日语中“不死”“不二”“富士”的发音都是“Fuji”。所以富士山也叫“不死山”“不二山”。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嬴政派徐福到不死山找不死药,以求长生不死。徐福在今日本伊势半岛的新宫市登陆,目标是到不死山去,也就是今富士山。尽管徐福当年采药到底去了哪儿尚无定论。但就笔者查阅的汉诗资料而言,徐福的确是去了日本,而且到了“不死山”即富士山。
安积艮斋(1790—1860)《富士山》
秦皇采药竟难逢,东海仙山是此峰。
万古天风吹不折,青空一朵玉芙蓉。
同时,与此诗创作年代相近的有草场船山(1819—1887)的《樱花》:西土牡丹徒自夸,不知东海有名葩。徐生当年求仙处,看作祥云是此花。此诗说明徐福当年的“求仙处”樱花烂漫如云。我们知道樱花是日本的象征也是日本的国花。所以“徐生当年求仙处”应该是日本。而《富士山》则直接指出“东海仙山是此峰”,进一步强化了富士山(FujiSan)就是不死(Fuji)的“东海仙山”。
以上总结了富士山汉诗神化叙事的具体表现。这些神话因素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富士山自身的地理因素与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以皇国、神国为核心的历史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富士山神化叙事的缘起包含两个因素,即富士山本身的自然地理因素与日本的神国史观因素。
三、富士山神化叙事的缘起
(一)自然地理因素
存在决定意识,文学作品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与提炼。作为富士山汉诗的叙事对象,富士山本身所具备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富士山汉诗神化叙事的自然地理因素。从富士山汉诗来看,这些因素主要表现为山之高、山之形、山之雪三个方面。
山之高。富士山的地理属性首先当属其海拔高度,3 776米。从世界范围来看,当然不能说是特别高的山,但在日本无疑是第一高峰。都良香(834—879)《富士山记》载:富士山者,在骏河国。峯如削成,直聳属天,其高不可測。歷覽史籍所記,未有高於此山者也。由于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峰,因此在日本汉诗方面,表现富士山高度的诗作较多,我们先看以下两首:
希世灵彦(1404—1488)《题富士山》
富士峰高宇宙间,崔嵬岂独冠东关。
唯应白日青天好,雪里看山不识山。
释泽庵(1573—1645)《望士峰》
富士山高甲大倭,中朝五岳亦如何。
峰临东海所何似?只见渔翁雪一蓑。
显然,这两首诗都着眼富士山的高度,以“富士峰高宇宙间”表达了“其高不可測”;以“崔嵬岂独冠东关”“富士山高甲大倭”明确了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峰。可见古代日本人对于富士山高度的仰止情怀。
另外,受古代中国山岳文化的影响,日本自古就称富士山为“岳”,以比拟中国的三山五岳,凸显富士山的“不二”地位。之所以称岳,一方面当然是基于富士山的高度,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岳”的宗教色彩,彰显富士山的神秘性,表达日本民众对富士山的崇敬之情。依据笔者所查阅的汉诗资料,富士山主要有“富岳”“日岳”“岳”“雪华山”等称岳方式,以及与“岳”地位相近的“蓬莱”别称,有诗为证:
室鸠巢(1658—1734)《富岳》
上帝高居白云台,千秋积雪拥蓬莱。
金鸡咿喔人寰夜,海底红轮飞影来。
山之雪。山巅皑皑的白雪可以说是富士山亮丽的名片。由于海拔高度的缘故,富士山顶“宿雪春夏不消”。日本自古就美喻富士山为“白扇”或“玉扇”,一方面是因为扇子原产于日本,“扇文化”在日本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富士山山体高耸入云,山巅白雪皑皑,放眼望去,酷似一把悬空倒挂的扇子。
石川丈山(1583—1672)《富士山》
仙客来游云外颠,神龙栖老洞中渊。
雪如丸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
此诗比喻形象、传神,堪称描写富士山雪的佳作。此外描述富士山之雪的汉诗还有:
龟田鹏斋(1752—1826)《望富岳》
富峰千丈雪,寒光落杯中。
倒饮杯中影,胸中生雄风。
山之形。从地质属性上来看,富士山是孤立的、非脉系延展型成层休眠火山。形状上属于标准的单体锥形火山,具有独特的优美轮廓。在富士山顶直径约800米的火山口周边,由于熔岩的作用,锯齿状分布有八座山峰,亦称“富士八岳”,即剑岳(剑峰,最高峰)、白山岳、久须志岳、大日岳、伊豆岳、成就岳、驹岳和三岳。这八座山峰宛如盛开的莲花的八个花瓣,所以很自然地“莲花”“芙蓉”就成了富士山的代名词。
秋山玉山(1702—1763)《望芙蓉峰》
帝掬昆仑雪,置之扶桑东。
突兀五千仭,芙蓉插碧空。
此外,还有诸如“白芙蓉”“雪芙蓉”“玉芙蓉”“秀芙蓉”等诗文,不必一一列举。
也就是说,由于富士山高,顶天立地,太阳又从这里升起,自然让古代日本先民认为那是天之御柱,是太阳神居住的地方;山之雪则是圣洁的象征;山之形酷似八叶莲花,两者结合则是佛教圣洁的莲花宝座。正是这些客观实在的地理特征培育了日本民族文化中朴素的敬山意识,对富士山的崇敬始终贯彻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这种敬山意识长期发展逐渐上升为“富士信仰”——富士山开始由客观实在走向主观神化。
(二)神国史观因素
如同日本汉诗诞生于中国古典诗歌一样,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繁衍与延展。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性,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存在感与压迫感,这促使日本文人与作家较早就产生了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皇国”(“神国”)观念,大日本主义及排外意识。
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学者北畠亲房(1293—1354)在《神皇正统记》一书的开篇就宣称:“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创基,日神传统矣。”他强调日本的国体和中国、印度不同,作为神国优越于万邦。被称为日本“国学”集大成者的本居宣长(1730—1801)则以日本最早的书纪《古事记》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排斥中国文化,宣扬日本“国学”的优越。本居宣长明确宣称:“世界虽有多国,但由祖神直接生产国土者,只有我日本……我国乃日之大神之本国,世界万国中最优之国,祖国之国。”现代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指出“不用说,把天皇作为一个活的神来加以崇拜是与国家至上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于在战败以后的今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仍然有他自己的地位。……只有在我们日本,从神话时代以来,国土与皇室就是不可分离的”。
也就是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一千多年的日本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日本至上、日本中心、日本优越的历史观。在这种神国史观作用下,富士山汉诗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神化叙事自然就有其内在的理据。宇野南村(1813—1866)的“剑锋一滴化成州,天子天孙日月侔。”诗句就是从史学的角度强调是神缔造了日本的原始国土(富士山)以及国民,后世的日本国土以及国民都与之一脉相承。一直以来,富士山都被作为日本之根本以及 “镇守日本的神”而被视为“宝山”。
芥川思堂(1744—1807)《咏富士山》
真是群山祖,扶桑第一尊。
满头生白发,镇国护儿孙。
《咏富士山》诗指出了富士山是群山的始祖,即日本国土的根本,在日本处于“第一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更肩负着“镇国护儿孙”的神圣使命。
结合日本今天的现实国体,我们不难发现如芥川思堂(1744—1807)《咏富士山》一样,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实际上是诗人神国史观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如前所述,在上古日本既已基于富士信仰而衍生出了太阳信仰,天照大神,亦称天照大御神、天照皇大神、日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与太阳女神,被奉为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这样一来,创造日本国土以及国民的神与统治日本的皇室就融为一体了,换言之,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客观上实现了日本国土、国民以及国体(天皇“万世一系”)的三位一体。
以上从诗歌创作的内在理据上分析了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是自然地理以及神国史观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叙事方式又会对汉诗文本的艺术建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四、神化叙事对汉诗艺术建构的影响
不同的文本叙事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我们认为,神化叙事方式对富士山汉诗艺术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本上的叙事性;意境上的奇幻性以及遣词上的宗教色彩三个方面。
(一)文本上的可视性
通常认为,日本文学的特点之一乃是“情趣性、感受性的极度发达”。所谓情趣性、感受性的极度发达,主要是意味着思想性、说教性、哲理性、逻辑性、叙事性的相对薄弱。可以说日本文学无论是长篇的物语文学还是短小的和歌俳句都注重情趣性、感受性的表达。有别于这一特点,由于“神”的意象元素的介入,富士山汉诗具备了叙事上的可视性特征。
秋山玉山(1702—1763)《望芙蓉峰》
帝掬昆仑雪,置之扶桑东。
突兀五千仭,芙蓉插碧空。
《望芙蓉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神奇的可视性画卷:在这里,至高无上的“帝”跨越空间的阻隔,掬起远在中国西部的昆仑山之雪,置之于日出之地的扶桑之东,帝亲手筑造的富士山突兀五千仞,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之下有如俊秀挺拔的芙蓉,直插云霄。在日本的古代神话传说中,富士山的创造者是居住在高天原上的神帝,而这些神帝同时又是日本皇室的发轫肇始。因此,这就为我们展现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奇异邂逅,也使得古代日本刻意宣扬皇室“万世一系”的圣人身份以及神迹的传说演进成一个充满隐喻的、奇幻的神话事件。
同时,“掬”“置”“突”“插”等动词的运用,赋予了文本强烈的动感与可视性,这与以玄幽、静寂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文学的静态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两首同样是描写富士山的日本传统文学之一的俳句。
正冈子规(1867一1902)
巍巍一秀峰,
残雪皑皑盖山顶,
分明一国境。
村井隆(1928一)
富士山蓝蓝,
雨云低低绕山巅,
快如疾风旋。
日本的俳句、和歌的形式十分短小,只能描写简单的物象,几乎不具备事象性,表现的都是瞬间的感情波动和心理感受。以上两首都是中译版本的俳句。在这两首俳句中,叙事方式几近直白,几乎没有任何可视性,作者要表达的重点也并不是富士山这一物象本身,而是以此为依托的个人情感,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物哀”、“玄幽”和“寂静”的意境与内心体会。
(二)意境上的奇幻性
如前所述,日本文学中弥漫的淡淡的哀愁、缠绵悱恻的情绪与中国文学及欧洲文学的社会化的严肃、印度文学中的宗教化的神秘,形成了迥异的格调。由于宗教、神话本身就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对文学在艺术上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赋予文学作品的奇幻性,使得文学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就富士山汉诗而言,由于富士山本身奇特的自然地理特征衍生了无数的宗教神话传说,富士山汉诗的文本建构自然就带有一定的奇幻性。这种奇幻性叙事又是通过诸如拟人化、拟物化以及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交互使用来实现的。
室鸠巢(1658—1734)《富岳》
上帝高居白云台,千秋积雪拥蓬莱。
金鸡咿喔人寰夜,海底红轮飞影来。
室鸠巢(1658—1734)的《富岳》与秋山玉山(1702—1763)的《望芙蓉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高居白云台的“帝”既是富士山的创造者又是富士山的主宰者,这是一个被千秋积雪簇拥的蓬莱仙境;在金鸡咿喔的拂晓时分,一轮红日已经从海底冉冉升起。我们知道日本自古就有尚白,即崇尚白色的文化心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白色代表希望、纯洁,是生命的象征,是神与人沟通的色彩。而对太阳的崇拜,我们从今天的日本国名以及国旗中就能明白,不必赘述。也就是说,在天上与人间、白雪与红日、神话与现实的交织对比中,上帝、白云台、积雪、蓬莱、金鸡、红轮等意象元素共同建构了亦真亦幻、色彩绚丽的意境。
富士山汉诗的叙事性与奇幻性增强了汉诗文本的动感性与可视性,可以说是对日本文学传统的感受性与内省性的突破;赋予了汉诗文本以逻辑性与可读性,使得具有王公贵族属性的日本汉诗开始走向庶民化与大众化,扩大了汉诗的受众群体,增强了汉诗在日本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遣词上的宗教色彩
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除了文本上的叙事性以及意境上的奇幻性之外,还表现在遣词上的宗教色彩。通过一些宗教色彩词汇的运用,诗人既可以渲染富士山的神秘性,也可以营造出奇幻的事境,增强诗歌文本的浪漫色彩。同时,遣词的宗教性赋予了汉诗文本以哲理性与潜移默化的说教性,因为宗教气息能让人安静思考人生、教化民众。
大田南亩(1749—1823)《望岳》
日出扶桑海气重,青天白雪秀芙蓉。
谁知五岳三山外,别有东方不二峰。
《望岳》从形态上将富士山比喻为青天白雪之下秀丽的芙蓉,更强调指出在中国的三山五岳之外,富士山才是独一无二的东方“不二峰”。诗中的“芙蓉”即莲花,如前文所述不仅赞美了富士山独特的轮廓美,又因为莲花是佛教的信物而与佛教相关联,赋予了富士山神灵色彩;“五岳三山”都是中国具有宗教象征的物象,诗人在这里点化借用自然也是为了烘托富士山的宗教色彩;“不二峰”中的“不二”则是语出双关,既是指富士山在日本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又是借助宗教用语的“不二”,凸显富士山的神秘,同时,在日语中“富士”“不二”以及“不死”三个词的发音都是“Fuji”,巧妙地利用语音上的关联性暗示了富士山乃是一座不死的神山。
结 语
综上所述,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日本人自古就有敬山意识,对富士山的崇敬更是在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下达到极致。基于朴素的敬山意识或单纯的宗教意识,富士山的神化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神化叙事是富士山汉诗的创作特色。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具体表现在有关日本国土以及民族起源的神话、日本国名来源的神话、佛教以及富士山名称由来相关的神话四个方面。这种神化叙事缘起于富士山本身的自然地理因素以及日本的“神国”史观因素,是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诗人将富士山神化叙事,显示为诗以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国力逐渐发展壮大,一跃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民族主义开始膨胀。对富士山的崇敬也渐渐由神化蜕变为异化。也就是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环境之下,日本近世文学开始与昂扬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结合,脱离了文学的轨道,成为了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汉诗也因此蒙羞,富士山也因此异化为文化国粹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唯我独大、目空一切的国粹主义的固化。有关这一点,拟另文论述。
注解【Notes】
①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夏目漱石文学叙事形态的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BWW027)以及2015年“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项目编号:J101131901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阴阳匹配、合卺生育产生的神。
③ 目前有韩国济州岛登陆说、西日本登陆说。参见伊東宏:《秦、徐福伝承の研究》(中),日本:人间环境大学,《人間と環境——人間環境学研究所研究報告》,1998年第1号,第33—45页。
④ 周兴彦龙(生卒年代不详,1358—1477年的诗僧),《画扇》诗云:画扇曾闻出日东,夏摸冬景暑尘空。轻罗一握拜君赐,相国寺中无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