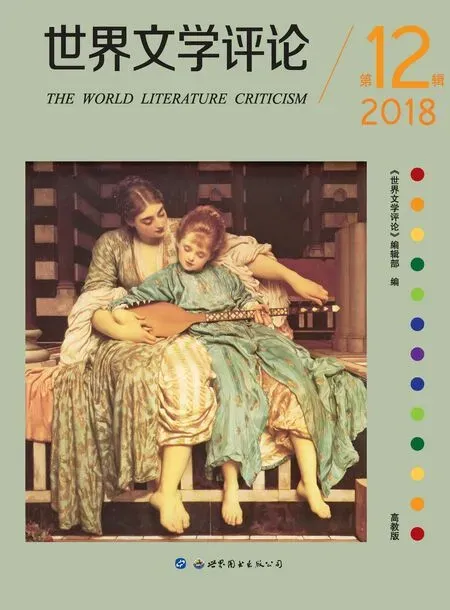光盘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及其意义
卢建飞
光盘作为广西“后三剑客”之一,他对人性的描写深刻而独特。翻开光盘的小说,仿佛打开了人性的潘多拉盒:险恶、怀疑、嫉妒、凶杀、隔膜、冷漠、温情、仁义、善良……一方面,光盘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人性在现代社会的异化。光盘对人性的描写不是随意的自由空想,而是有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具体体现为三重地理空间的建构:沱巴——玫瑰镇——桂城,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语境下表现出不同的人性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揭露了人的主体性消解以及民族文化衰落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人性异化过程。光盘小说表明了只有回归沱巴(沱巴为都市文化精神的原始母体,它是人性去伪饰的自然流露,是生命本真状态、自然状态)才是人性“美”之源,人才能得到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才能真正诗意地栖息于大地。
一、三重地理空间的象征内涵
(一)沱巴——人性至善至美的地理空间
“沱巴”在光盘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提到,如短篇《意外婚礼》《窗》,中长篇《野人劫》《洞的消失》《长寿之城》《美容》《请你枪毙我》等。不过,作品中没有明确“沱巴”具体的地理方位。《信号》中说“沱巴离桂林150公里,很近”。《长寿之城》提到“玫瑰镇下属有一个叫沱巴的村子”(76)。《野人劫》又指出“沱巴在玫瑰镇的东边,那是一个瑶族居住的地方”(156)。尽管“沱巴”的具体地理位置是不确定的,但多数作品都把“沱巴”指向为乡村。小说中,“沱巴河”是一个独特的地理意象。“沱巴河发源于距离沱巴村七八里的攀岩,那里仍是沱巴村的地盘”(78)。这条河孕育着沱巴人的生命。《请你枪毙我》中“我”深切地感激着这孕育着生命的河流。与城市河流恶臭、脏乱相对比,沱巴河的纯净、美丽、自然,孕育出了沱巴人美好的心灵和纯洁的灵魂。只要人来到沱巴,仿佛有了更强的生命力,人性展现出更加光明与自由的一面。“山里的春天比城里来的真实和显著。花艳、山绿、鸟更欢;目光所及之处全都升腾着一种生命的蓬勃气息。”(23)不过,沱巴并不是简单的乡村,而是瑶民族的聚居地。这里不仅仅是自然风光好,人性美,而且还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长寿之城》中,“沱巴”与世隔绝,民风淳朴,瑶人热情好客,待人友善。《请你枪毙我》中,“沱巴”爷爷是瑶民族的“活化石”,他的一生都在收集沱巴河流域所有的原创作品。“这些诗作不仅有歌颂纯洁爱情向往幸福的风花雪月之作,也有诉说瑶族历史和苦难之作,也有表现瑶族风土人情和灿烂文化的。”(11)爷爷收藏着瑶族传统文化瑰宝,而且还教“我”唱瑶民族歌曲《交趾歌》,以传承瑶族优秀文化。光盘所塑造的沱巴瑶族乡,自然美、民族美与人性美天然融合,令人神往。
(二)玫瑰镇——人性善恶对立渐进复杂的地理空间
玫瑰镇,是沱巴文明与桂城文明的交汇点,也是民族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合流处。这里既有沱巴人性美的一面,也有城市性复杂与恶的一面。玫瑰镇环绕着纯净的沱巴河,“九医院外低矮的青山与沱巴河融为一体”(51)。玫瑰镇长满了香气迷人的玫瑰,“春天的脚步已经来到了玫瑰镇,鲜花香遍满了山野”(167)。玫瑰镇自然风景依旧如沱巴般秀丽,然而人却不如沱巴那般唯善了。小说《枪响了》中,来自乡村的秘书赵铃铛,拥有沱巴人美好的品性:勤劳、朴素、善良、真诚,不为金钱和淫威所折腰。相比之下,腰缠万贯的城市人官建山,迷失于金钱与性。两者对比影射出城市的卑劣和龌龊,而展现出了乡村的善与真诚。《错乱》中奇声说:“做好人难啊,可是做不得我们也要做,我们不怕误会,人还是要凭良心。”(53)奇声、月红夫妇以个人力量,反抗集体道德的沦丧,坚守着人性道德的底线。《王痞子的欲望》玫瑰镇痞子不择手段地报恩,充分彰显人性的扭曲;《英雄水雷》中英雄与纵火犯的身份错位,衬托玫瑰镇人的愚昧与道德反常;《干枯的河》暗中“善手”的呵护,给予晓香与晓荷希望,波涛奔腾的河水也会干枯。《我是如何消失的》宋思水错认亲母却无怨的博爱与宋钢夫妇占有人子的私欲到心胸的开阔,显示玫瑰镇人性的回归。玫瑰镇就是这样的一个城镇,风景依然秀丽,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沱巴那样单纯、和善。光盘笔下玫瑰镇,有为利益而勾心斗角的人,也存在有良心的人,是人性善恶对立渐进复杂的地理空间。
(三)桂城——人性复杂纷乱的地理空间
桂城,现代化都市。由于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明显地恶化。“方庄原来在野外,现在哪里是人们周末的娱乐地。前一周我还去过,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早先那条河流已经断流,现在留着的是生活污水……城市河在他(妖)的笔下丑陋不堪,还有两岸的新建筑相互掐着。小时候,城市河多宽啊,绿树小岛,还有荆棘丛林遍布,充满了野趣,现在都被房地产老板开发了……”(41)桂城,自然环境受到工业与城市建设的严重污染,人仿佛也变得扭曲与肮脏。“他最雷人的画是一幅城街图,所有的高楼大夏都是变形的,行人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像个怪物,有的外露着内脏。”(42)桂城科协的陆刚,为“突出”科研贡献,以哑巴流浪汉为幌子,伪造“发现野人”的证据。桂城多少人,为获名获利,而不惜欺骗整个社会。《摸摸我下巴》中人们过着纸醉金迷的放纵生活,情欲与物欲滥觞于野。《穿过半月谷》揭露了都市文明的情感危机与虚伪婚姻。《谁在走廊》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的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的病态心理。李菲菲对丈夫陈水河种种不可理喻的不信任之举发出了绝望的呐喊:“这个世界叫人迷惘令人失望,卖淫和同性恋暴力阴谋欺诈天天发生,就是连与自己生活了十来年的老公也无法使人信任。”(89)这些作品深刻地揭示了“都市尽管有着繁华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人性沦丧和道德缺失成为一种社会病症”。在这样一个纷乱复杂、人性斑斓的畸形社会下,人与人之间感情隔膜、冷淡。整个现代都市表现出虚无、迷惘与绝望的病态心理。在桂城房地产赚大钱却精神错乱的孙国良,深深感受到,“桂城不是好地方,那地方容易把人弄疯”,回到玫瑰镇养病,“国良现在才感觉到乡下才是人生活的最佳之地”(55)。不过,桂城存在的不仅仅是人性的阴暗内容,善与真情在桂城还是拥有一席之地。如小说《桂林不浪漫故事》,由于小唐的真爱与善良,令周国忠远离艾滋的灾难。正如黄伟林所说:“《桂林不浪漫的故事》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正邪善恶各种力量的博弈,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爱的存在,这一切似乎表明,光盘的小说已经告别了单纯表现人欲横流,人性扭曲的状态,开始了对人性、对人生、对人道的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桂城就是这样的地理空间,人性复杂纷乱,善恶交织。
沱巴,作为原始民族地理空间,它保持着人性善原始、完整的状态。到了玫瑰镇、至桂城,人性随着现代化或城镇化的进程而产生异变。沱巴,是人性善的本源,玫瑰镇和桂城是人性异化的演变空间。这三个空间,揭示了沱巴至桂城地理空间的扩大,同时又在现代化和历史进程中,人主体性的消失,演绎了人性的一步步异化过程。
二、地理空间与人性分析
上述所说的三重空间内的人性形态并不是绝对的,不能认为沱巴人性皆善,玫瑰镇人性善恶对立,桂城人性皆复杂纷乱。但是,能得出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是基于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内,它呈现出的人性形态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因此,三重地理空间才能对应相应的人性形态,才能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一)自然地理要素
自然地理因素对人性情和气质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礼记·王制》中提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这表明了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质地貌以及水文条件下,区域民众存在不同的风俗和性情、气质。沱巴瑶族乡自然地理环境优美,这里有纯净的沱巴河,遍布山野的鲜花,一年四季青山绿水,鸟鸣花香,气候宜人。生活在这样优美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沱巴人自然性情温和、善良醇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生存状态。因此,沱巴民风淳朴、人性尚善。而玫瑰镇自然环境已经不如沱巴那般优美宜人,桂城的山川河流甚至遭受严重的污染。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生活的城市人,易发“厌”的情绪。城市人一方面掠夺自然,另一方面又渴望人与生态和谐,由此产生多样的性情与人格。
(二)经济要素
首先,经济因素直接影响人的精神气质与仪礼行为。《管子·牧民第一》认为仓廪实民则知礼节,衣食足民则知荣辱,反之民乃“菅”与“妄”,经济状况直接与人的道德荣辱与性情行为挂钩。其次,经济因素影响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理性精神。马克思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不仅产生物质的生产方式,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理性,思维模式等。这也说明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行动导向都深受经济影响。小说中沱巴远离城市,自然环境的优美,物产的丰富,这使得沱巴人可以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原始农业生活。“山里人大多时候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他们要那么多现金干什么?”(91)但到了玫瑰镇、以及更加复杂的城市桂城,人不可能直接从自然直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都市工业经济模式。一方面,他们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使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穿越半月谷》中,从前半月谷是一块处女地,自然朴素,小河是那么的清澈和浑厚,自从被开发旅游区后,现在“河岸枝条上挂着红的白的绿的黑的塑料袋,细心一看,你还能在岸边找到用过的避孕套”(142)。另一个方面则是工业的物质化生产带来机械性的生活方式,而引发人的异化。人变为焦虑、空虚、恐惧,人与人之间也变得相互不信任,冷漠,冷酷和猜忌代替了温情与信赖。在《雨杀芭蕉》中,“雨和芭蕉又吵了起来了。在这个贸易市场就他俩最爱吵架,他们像冷水和热锅,碰在一起就炸。他们都是做干货生意,摊点紧紧相连。人们都知道他俩吵架是为侵占对方的地盘,最后把对方挤掉,以便独揽干货生意”(87)。亚当·斯密说经济中的人是利己性的,经济因利己而发生。为了独揽生意,利欲熏心的雨和芭蕉兵刃相见。可见,在小农经济的沱巴中,人自足而乐,民多真诚、豪爽、真性情。桂城为现代都市经济模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经济理性消解人的审美诗性,从而使人的精神世界变得虚无缥缈,展现出的人性形态也五光十色、纷繁别样。
(三)民族文化要素
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语言的共同体,它形成和稳定的核心在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可以使优良的民族传统代代相传。遗憾的是,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异质文化的冲击和自身文化的矛盾,一些原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表现出工具化倾向的危机,认同层次链接的断裂,同一性基础的弱化等负向挑战”。而“人们之所以愿意追随群体的精神,是因为坚信以民族精神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能够满足个体成员最广泛的社会追求”。而当今现实生活中,民族没有给个体带来丰厚的物质回馈,而功利主义却使个人获得巨大物质财富。因而,在诱人的物质利益面前,人变得冷酷与贪婪,毫无人性可言,更谈不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了。如《请你枪毙我》的祖天,为了个人利益而搞各种阴谋诡计,余品华因其父亲阻碍瑶族文物倒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与之相比的是,坚守瑶族文化的“爷爷”,因为坚守瑶族文明,继承与发扬瑶族悠久文化,显得亲切和蔼,令人爱戴。盘染童追随爷爷步伐,追踪瑶家文化,与共同向往沱巴的万的沐相爱,他们瑶乡沱巴式的爱情真挚而又纯洁,与《穿越半月谷》《摸摸我下巴》的都市功利私欲爱情相比,沱巴式的爱情由于有瑶族文化底蕴,更显纯粹而美丽。由此可看出,民族文化对人性具有规约性作用。当对瑶族文化认同并坚守时候,人则显示出一种善与真的状态。而当摒弃瑶族文化传统,置身于都市的物质、功利争夺时,人性则异化,变得险恶与冷酷。
由上可知,基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内,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和民族文化三者引起了人性的发生和变化、发展。不同的地理空间对应形成不同的人性形态,是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民族文化要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光盘的人性观及审美理想
光盘小说对人性的深刻描写,离不开其独特的人性观。在不同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人性形态,本质上来说是作家的审美空间,是其寻求对人性异化困境突破的努力,并表达了他对人性善的审美理想追求。
首先,光盘为瑶族作家,1964年生于广西桂林全州县东山瑶族乡。东山瑶族乡位于全州县东北部,土地面积420平方千米,人口3.36万,其中瑶族人口占80.6%。这里保存着丰富的瑶族历史文化,如民风民俗“跳盘王”“爬楼”等,神话传说“盘瓠的传说”“千家峒的传说”等,舞蹈音乐如“寄歌”“铜鼓舞”等。东山瑶族乡的山水以及瑶族文化给予了光盘深厚的写作土壤。邹建军教授说:“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作家作品呈现出各种形态,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起作用,并且通过人文要素,在作家身上发生越来越显著的意义。”小时候生活在瑶族乡,美丽的山水浸染着光盘的童年,给予光盘美好的童年记忆。《跳盘王》中甚至有直接对瑶族盘王节风俗的细致描写:“一位身穿神装的师公上台主持祭祀大典,他口中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清听不懂,他向盘王像敬香,开坛请圣。随之鼓乐响起,手持法器法杖的另外两个师公上台。请完盘王,接着唱盘王。”(77)这些表明了地理基因在光盘身上有着明显痕迹。光盘如同《请你枪毙我》中的余品华,“第一次随回到沱巴,他就爱上了故乡。虽然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沱巴就是他的故乡,那个被他推下万丈深渊的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余品华对沱巴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96)。这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即是地理基因的结果。“大专毕业,我对瑶族历史瑶族祖先留下的文学作品理解就更透彻,时常有打通瑶人远古道路的快感。特别是这些年进省师大国学研究班,听专家教授讲国学,更加激发我对瑶族的历史文化的喜爱,甚至着迷。”(134)正因为对瑶乡的向往与追恋,光盘塑造了“沱巴”这个地理意象。笔者统计过沱巴在光盘作品中的出现次数,短篇小说58次,中篇672次,长篇561次。可见沱巴瑶族乡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瑶族乡的山清水秀、人淳心善,使光盘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美好的,人性之美的源泉在于沱巴瑶族乡。
其次,现代化进程带来人类的精神断裂。人类的精神生活在其历史过程中有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个断裂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即所谓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它构成了当代人生活的根本背景。中国社会强烈的转变,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感和危机感,处于城市中的人群普遍存在精神危机,其中的一种表现为强烈的焦虑感。人们的生存体现和状态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寂寞”“抑郁”和“无奈”的焦虑时代。作品《请你枪毙我》充分体现了城市人为了排遣这种无尽的精神空虚和焦虑不安感,纵身于纸醉金迷的生活,追求纯粹的感官享受,麻痹自我。同时,光盘生活在桂林二十多年,深刻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危机和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山水情结”油然而生。文学地理学认为,所谓作家心灵的“山水情结”,是指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生活或者生活过的自然山水的影响,包括那样一些很封闭的作家与诗人,他也不可能对自然山水视而不见,特别是人童年与少年时代。自然山水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与心灵中,就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久而久之,“山水情结”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无法消除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精神危机,光盘只能回到那记忆中的美丽瑶族沱巴乡村,“对于丰富悠久的瑶家文化,对于故乡的山山水水,都表现一种深切的迷恋和向往”。那里风光旖旎、人性纯净、生活自由自在。沱巴才能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解脱。于是,光盘书写沱巴,心灵飞回沱巴。在他眼中,沱巴犹如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仙境,给他极大的心灵慰藉和灵魂寄托。因此,光盘构建沱巴这个地理空间,构建他想象中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归宿,也是人性美的天堂。
最后,光盘人性观的矛盾性。他把人性判定为民族的、乡村的,即人性善且纯粹,城市则人性恶与复杂、不可捉摸,这仅是他个人的理想。因为在当代语境下,没有绝对的封闭空间,也绝没有永久的稳定民族文化(内部也可能分解),也绝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沱巴只是他审美理想而构建的想象空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沱巴还是哪个地理空间,都不可能抵制完全自我封闭的存在。并且,人性也不是仅仅存在单一的维度,人性中的自然属性、理性层面、德性层面、社会层面紧密相关相连。人性中不仅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要素,在不同环境呈现出来的状态不同而已,人性本身也是会变化发展的。因此,沱巴人性善的单一维度与人性固化本身就存在悖论。光盘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承认人性的恶,承认文化入侵,异质文明入侵造成人与人关系之间的隔膜与猜疑,社会的人情冷漠与阴暗。但是他又幻想存在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人性皆善,并且一成不变,善是永久性的。问题在于,现实中的沱巴,并不是那样的美好。在《美容秘方》《渐行渐远的阳光》《长寿之城》《请你枪毙我》中,沱巴受到现代化和异质文明的渗透,“然而令人悲伤的是,古老的沱巴文明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益沦丧,美丽的自然风景在旅游开发的大潮中面目全非,淳朴的民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遥远而悲伤的回忆”(142)。沱巴人也会异化,这当然不受光盘的控制,因为这是客观现实的结果。
光盘曾说过,沱巴是在大变革时代真在变或者不变的一块热土。书写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书写中国南方史。沱巴乡村与现代文明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小说故事时常漂移在城市和沱巴之间,写来着沱巴的城市人,写来自城市的沱巴游客。他们交织碰撞,冲刷出生活的底色。因此,他的人性观是矛盾的,一方面想建构美丽的乌托邦,一方面这个乌托邦又不能真实存在。虽然光盘的人性观是矛盾的,但是出于个人审美理想的追求,他还是试图建构这样的三重地理空间:一个人性善的沱巴;一个人性善恶对立的玫瑰镇;一个复杂繁乱人性之都桂城。这三重地理空间实际上是光盘想象空间与心理空间交织的空间体,“想象空间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事物往往是作家审美认识与艺术想象的产物,心理空间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作家的心理密切相关的自然山水空间,但主要是作家情感与心理的一种直接现实”。从本质上说,这三重空间也就是光盘所建造的审美空间。在人与地,人与民族文化、人与现代化关系失衡的客观现实下,他承认人性的异化,人性的恶,这是他无力改变的事实。但在他心中还是十分渴望永久的人善本性,渴望一个和谐无纷争的桃花源。因此,他通过建构审美空间来追求他的审美理想,即对沱巴式人性永恒善的追求,对都市人性纷乱复杂与罪恶的鞭笞。
注解【Notes】
① 光盘:《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