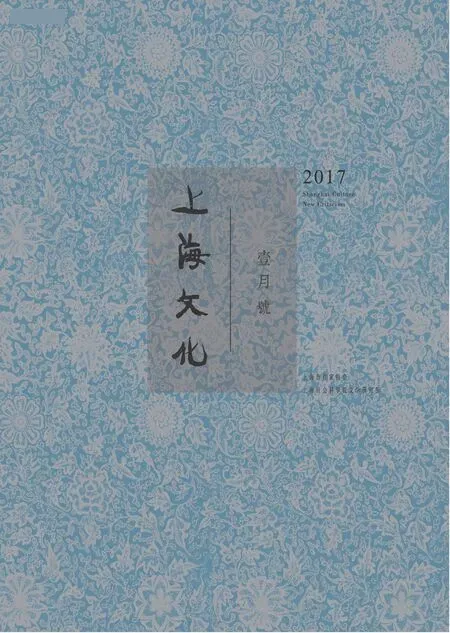非杰作阅读试验 王秀云的两个小说
骆同彦
非杰作阅读试验 王秀云的两个小说
骆同彦
《五卷书》的故事大多这样开头:在某个城市,有一个婆罗门;或是,在某个城市,有一个商人;要不就是,在某个地方,有一棵大无花果树;在某个树林里,有一只狮子;等等。然后故事套故事,蔓延开来,似乎可以无限绵长地讲述下去。这个世界也就在故事里仿佛没了尽头。用这样一个开头来引领一篇介于阅读印象与批评之间的文字,是缺少信心的表现。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去写。这样,我在进行这篇文字的写作中所经受的忐忑、踌躇、疑绝便更真实地传递出一种类似心跳的声音。这会让我稍许心安。
一
王秀云的小说《一合相》有一个既俗气又俗到别致的开头。她去写另一个故事,却在查县志时发现了另一个故事之外的故事,就把它写了下来。有点搂草打兔子的味道。
小说一般都有一个故事骨架。时下有一种理论干脆就把写小说说成是讲故事,基本是这样一个格式:小说=好故事。对这样的观点,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能把故事写好的人,在我内心,就应该得到尊重。但这并不等于我的内心没有好小说的标准。再退一步讲,起码有益的思考一直没有停下。小说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域界是否在收窄?讲究故事性的逼仄要求是否减弱了作品的艺术性?而一个平衡的基点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都是严肃的写作者不能绕过的尴尬和墙垒。
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缝隙中作家觅得人性的光亮或幽暗,让写作像钉子楔入木板一样带着人间特有的痛的速度锐进或受挫
读小说多了,或是说阅读小说的故事多了,就会发现,很多小说所写的故事基本上和《五卷书》那样的故事传统没多大差别,看来会讲故事的人所拥有的一个共同毛病——让故事在故事的展开中逐渐精彩,或是越来越糟糕,这样一种倾向,不仅在古老的印度也在其他国度四处泛滥。
人生遭际的意外总是大于现实境况下的人的合理想象。如果说“合理想象”生活是个公约数——也就是生活所能被量化的一个数值,那这个出现的数字的有效性对于统计学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写作则毫无价值。作家的着眼点也不在这里。他或是她更关注“合理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性——细小的存在裂痕或是缝隙,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缝隙中作家觅得人性的光亮或幽暗,让写作像钉子楔入木板一样带着人间特有的痛的速度锐进或受挫。
在《一合相》这篇小说中,意外性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叙事流脉,也决定了小说主人公大梁、大壮兄弟以及另一个主要人物小芹的命运,同时也成就了这篇小说的命运。
文革爆发了,一场政治运动意外地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文革结束,熬过运动折磨的父亲,却在政治生命得到平反、补发工资、可预见的生活前景一片光明时选择了自杀,这也像是意外。 父亲死了,母亲染上毒品因吸食过量而死,这无疑又像是另一种意外。但这一切却要两个在成长中的少年大梁、大壮在时间像似磨难一般的流逝中来面对和承担。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不应该的意外。就在兄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之时,一个女人小芹意外地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而这个小芹却有着一个看似荒谬的执着念头:“生一个有文化的孩子”(小说中文玩店老板语),这无疑是意外中的意外。这种小芹式的赤裸裸的文化饥渴是否还可理解为小说文本意义上对文革践踏文化的一种反衬与讽喻呢?
作者安排了每个人物的命运,让他们沿着故事的延展线索逐渐出离,而后又站回到属于自己的命运——那不可摆脱的影子中,在看似意外实则必然的归途指向中,完成一个小说人物得以生存或毁灭的可能。是她,在透过虚妄之障回望人生的真实之地。
这篇小说的语言完全可以再精致、润泽一些,作者有这个能力,但她却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很多生活原质的东西,粗粝未经打磨的人物语言、故意模糊的人物形象的原灰色调,都让小说不断发生阅读羁绊,给人一种像是食物糙粗难咽的短暂噎食感。这让我怀疑作者是在有意制造一种生活泥沙俱下的混沌状态,以此来尝试改变一种写作惯性或试图突破点什么。这也是一种写作的意外。
同时,这无疑是一篇具有隐喻质地的小说。《一合相》是在“小芹摔了那只碗”这样一句颇有隐喻意味的叙述中开始的。紧接着又在大壮的一句没有言明的心里话(一个更深的隐喻) “破碗比好碗更难对付”中得到加强。这样明显、生硬和不无夸张地使用某种手法,是很考量一个写作者才情和胆量的。我想作者一定设想了无数个开头,最终选择了这样一种开始。许多事物往往都是在破碎中获得重建的理由与可能。但这种技巧在写作中的使用、发生往往又不需刻意经营,它更像一种写作本能的潜在释放。
这样的例子在这篇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那个被109狱犯误称的“豪末”(大梁纠正其称赫尔墨斯)就具有典型的隐喻意味。就连那只出现在大梁身边的猫,在我看来也无疑具有一种隐喻性质。猫有九条命,这并不是说大梁也有九条命,而是暗示他的命运会像猫有九条命那样有跌宕。连小说中途出现的书报亭、煎饼果子摊、买书的假诗人、纯文学读物都身披了一层隐喻的幽光;即使小说最后大梁残忍地杀死小芹与诗人苟且所生的聪明女儿文雅,这一暴行也具有某种生命对抗精神荒芜、灵魂堕落、文化虚无的自甘毁灭的隐喻质地。
在阅读过程中,《一合相》这篇小说仿佛就整体笼罩在一团隐喻的云翳中。这种隐喻气息妨碍了小说阅读的流畅,在某些时候,我会觉得作者有一种执拗的想法,让每个词语、每个语句、甚至每个标点,都退回到一件隐身衣内,然后再经过她内心的痛苦排序重又回来。这种隐喻气息,也遮蔽着小说的场景设置。它让我们恍惚经历着——像似在透过列车的窗口看——正在经过中远去、回退的一截颓圮但仍顽强伫立的时代的旧墙面,看到那里残留的时间尘埃、岁月污迹,人和事物的呼吸、吐纳、熏染,某种渴望得到回答的秘密呼唤。
再回到小说《一合相》这个标题上(其实这个标题就是这部小说的最大隐喻)。按照作者的解释, “‘一合相’一词,来自《金刚经》,大意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因缘和合形成了我们置身的世界”。那么反观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它对应到故事中小说人物的生活场景时,不也暗喻了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悖谬吗?
小说《一合相》就是在人生无法躲避的隐喻幽昧中试图实现挣脱突围的一次冒险。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写作者与阅读者共同经历了某种错失机遇的失败,触碰到了某种无效性。
在谈到小说人物抗争命运的无效性时,我不由得想到一种写作的无效性。作者自己也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说道:“攀援不切实际的梦幻泡影,最终摔碎的是自己的人生……文学没有说的那么高贵,甚至,无意义。”这是否定,还是自省,我觉得这两种意味都有。这种对文学介入生活的悲观认知或绝望心态,其实就是对整个现实世界在一个光鲜表象下深隐的荒诞、乖戾和最终表现出的无效性抗诉。
其实说到文学的无效性,还会想起某些看似能够指导写作的饱满腔调。如“贴着人物写”这种论调。在某些时候会让人感觉它有一种跟从主义写作(我从不会诋毁或贬损各种主义的写作实践,只是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主义一旦与意识形态粘连后形成的权力话语部分)的原教旨意味,这看似是一条可以让写作安全着陆的路径,但我认为它有悖现代小说写作的多变性需要。当然在批评这句话的同时,一点也不能低估一个写作者的另类理解或是寻找其他可能出口的能力。这就是说进入方式的单一,并不一定会是预言结果乏陈可陈的前提。它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真能做到如此的优秀者,确是寥寥无几。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带着镣铐舞蹈,且有超绝的表现。
任何写作手法的运用无疑只有一个主题:适恰小说表达的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故事,作者试图揭示隐存在人性深处的悖谬与荒诞,并进一步挖掘难以究探的生命幽暗之地以及其他诸多可能。这无疑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优秀的作家就是在看似破坏的作为中怀着悲悯之心试图重建一个人世乐园。即便是无效的,她或他也仍会勉力为之。
如何处理人和世界那种相互依存又暗向背离的紧张关系,无疑是作家所要进行的一项带有宿命意味的工作。《一合相》这篇小说是诸多进行这种有益探索中的一部分。
二
布罗茨基曾告诫过他的学生:“千万别把自己当受害者看。”他自己也在这样做,只字不提有关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遭际。在《小于一》 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把有关成长的记忆叙述成库切所说的“麻木无聊”,但又是那么精彩。这就是作家所能记忆的精神成长史。王秀云的《我们的围栏》这篇小说,我认为关涉人的精神成长史问题。但它给我的感觉是:像个失败的例证。
初读这个故事,感到有些混乱。最直接地感触来自ABCD和abcd这些大小英文字母在文本章节上的混搭应用,这让我产生一种阅读发生错位或是迷失的恍惚感。等我分清了大写的ABCD是现在时(现实)的叙事文本,小写的abcd是过去时(记忆)的叙述文本之后,才像走出迷宫那样松了一口气(这种结构性技巧的东西给我的感觉是,不过如此)。但那一刻,我还有过一个严肃的想法,作家都是些善于建造叙事迷宫的人。只不过使用的材料不是砖瓦水泥,而是语言罢了。作家王秀云就用语言这种材质编织了一个故事, 《我们的围栏》。
那就置身事外来看看这个故事。
“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也就是“我”现身文本时有着母亲、妻子的双重身份,不仅擅长与“文倒”(文玩贩子)讨价还价,还像是做得一手好饭菜,家庭生活也淹没在如众生一般的平庸安静中。但女儿的一个危险举动却在瞬间就把这种平庸安静击碎。这个叫“小三婴”的女孩子要去干一件大事,拆除安装在小镇生活(或许还能说成是安装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的“围栏”。“小三婴”也就是“我”的女儿,此话一出,即刻吓住了“我”和丈夫“开尔”(奇怪的拆字游戏带来的昵称,“邢”姓分家的产物。他实名邢路,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寓意圈套中的姓名)。故事由此进入现实叙述(如何阻止女儿去冒险)与记忆叙述(回忆“我”和丈夫在一个尚有激情的时代所做的冒险经历) ——的交叉进行中。原来“围栏”像那些古老的传说一样在小镇存在由来已久。“我”就试图去拆过围栏,但经历了想象围栏、寻找围栏这样一个过程后,由一个像“小三婴”似的萌生过反叛意念的“革命”女孩,被时间和岁月雕琢成小说文本中的母亲、妻子,在“被一种巨大的挫败感羞辱着”的想象中,面对无力改变的生活,怀着一种时代原罪感 “羞辱”地活着。
真是这样吗?但不这样又能怎样?问和被问的短暂交集过后,一切又复归于沉默。这个时代真的在变轻吗?“小三婴”的一个起念“拆围栏”,就像围棋对弈过程中的一个“无忧劫”,兴致所至,她顺手放出来了。让接招的母亲“我”在时代和社会(还有记忆)这个棋局经历一阵莫名的紧张和混乱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女儿像随意游戏一番又回到恬适的梦境内。其实“我”虽然对女儿的反叛行为充满担心,并善意地提醒女儿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围栏”,但在内心还是对女儿的行为怀有期待。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一种精神承继的愿念渴盼。但女儿的叛逆行为最终却未发生。而莫名经历一次类似精神唤醒行动的“我”,事后,也只不过是想把早已睡不惯的一个古董红木硬床换成一个新潮舒适的真皮睡床而已,且很快就和丈夫默契地达成一致。理想不仅可以让人有入圣的想象,它还可以让人回到平庸。这像似很滑稽的一件事情。但它就这样完成了。在写作中合理地完成了。
在我心生羡慕之际,突然在大脑中冒出一句这样的话:文本是在被撕碎中获得重建的。这是闪念的结果。它若是个观点的话,批评家会乐意接受。作家不会这样想。《我们的围栏》这个作品,提供给我的能够感觉和认知到的事物也在告诉我,作家在很努力地想做一件事——把心中的故事之树成功地搬出来,让它到阳光充裕、土地肥沃、空气干净的环境里生长。但这个过程,却未必会顺遂心愿。有时还要作家承担于写作中自觉不自觉过分暴露“自我”的风险。这样,作家的劳动又回到庸常中去了。
作家笔下的人物却留在文本中不肯回头。
这个小说中的一干人物都没有脸面。我在怀疑,她——也就是作家是在故意抹去他们的脸面。她不仅抹去了人物的脸面(她只吝啬地给了他们思想和行动,以及与思想和行动有关的语言),干脆“坏事”做绝,把一干人物生活的场景——那个近似在虚拟中存在过的时代的脸面也给抹去了(这个时代的“脸面”景深很深)。要不是有着一个小说文本其他的基本要求,我怀疑她还会继续下黑手。她似乎有抹掉一切的野心,让整个世界都像一个空白文本一般虚无。
小说文本中的“我”,显然没有布罗茨基的大度:“千万别把自己当受害者看。”这个“我”挣扎在“把自己当受害者看”的阴影里。短时间内,她还无法脱身。在这个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内,不会回避记忆的黑暗之地,反而要不断呈现它。甚至想在一再忆起的过程中加强——试图让它躲过被遗忘的尴尬。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区别。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精神成长史轨迹,这种轨迹出现在作品里,就让写作变得丰富而诡异。
在这个小说中,还有几个地方撬动我的思维。在小写的e和f两个章节,写“我”和同学们走上街头轰轰烈烈地去“拆围栏”,恰在这时,无孔不入的商业行为 (金钱)介入“拆围栏”运动,这种经济关联一旦建立,人性中的利欲弱点就暴露无遗。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霍英,“我”的发小、闺蜜兼运动伙伴,“拆围栏”运动的领袖之一,伙同另一个男性运动头领卷款(商家赞助款)逃逸。而“我”的另一个重要伙伴刘畅,亦为发小、闺蜜,也在“拆围栏”运动出现危机后,万念俱灰,削发为尼了,其他伙伴皆作鸟兽散。这对“我”无疑又是重创。而在g这个章节,有“我”的一段挥舞指甲砍开一条困顿之路(也可称时空隔限),从而突围,重回家庭的描写。可以说,“指甲”这一意象的成功使用和确立,像这一大段叙述一样,非常饱满。
其实之前,我对这篇文章已经写好一个开头。按照这个开头发展下去,会是另一篇文章。但我发现,那是一个会让我产生偏离文本的想法。我放弃了它。但等到这篇文字快完成时,我意外发现它似乎又是对的。那个开头是这样写的:
“这个小说看完后我有点迷茫。也可说不知所措。也就是在这种不知所措中,我感到内心秘密涌动的惊异、不安还有兴奋。
“我遇到有话想说的文本时,一种情况是被刺激,被动起意想写点什么;再一种情况就是,看到了文本中有触动内心的隐秘感觉,它很微弱,却闪烁着诱引我去探寻的好奇。这是动力。
“在我看来,好的批评文字未必是来自对经典文本或经典作家的拆分和析解。优秀的批评者总是在那些看似并不出众的文本中能够找到有话可说的地方,而不是在那里自话自说,或是做谄媚之事。一个理论基点对应的是无数散置的文本要素,如何筛选找到适恰表达的东西,切入、展开,然后收紧,这就考验一个人的文本判断力和赏析能力。我只是说我能够遇到的文本。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朋友、熟人或是喜欢的人(作家)。但我是警觉的。适度的警觉让我不会逾越一个边界:它在那里。那是让我心跳平稳、内心安静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文本——我说了该说的话、能说清的话、对得起文学这个还有点神圣意味的事物的话。”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