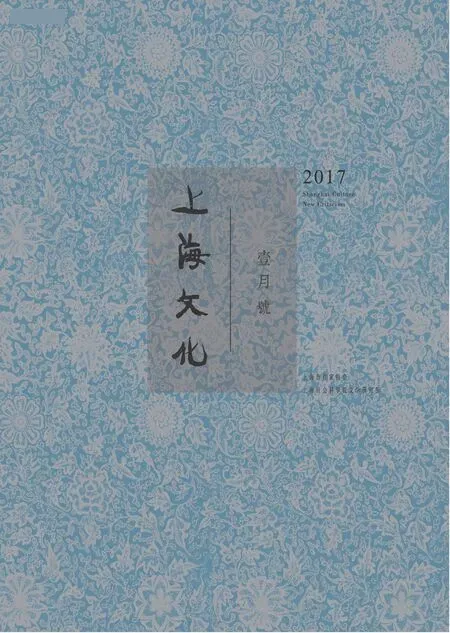如何批评
张定浩
如何批评
张定浩
1
在诸种属人的欲望之中,表达意见和沟通交流的欲望远远早于创造的欲望。古人类在岩壁上的乱涂乱画,和新新人类在微博、朋友圈上的唇枪舌剑,其实没有太大差别,都是一种意见表达和情绪交流,一种文明的遗迹(或新迹),并且都不在意原创性和署名权。很多作家都写日记,但不是所有写日记的人都乐意成为作家,这些不乐意成为作家的书写者在日记乃至类似日记的自媒体中愉快地议论时事、比较他人,也偷窥(浏览)他人类似的比较与议论。这些表达、交流、比较和议论,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构成广义上的批评,如果它们和文学有关,是因文学而起或落脚于文学,再稍长一点以至于可以填充报刊的版面,那么或许就会被称为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对于这种批评冲动似无好感,他恼怒于一项“前所未有”的事情,即“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自己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但我觉得,这种“前所未有”,或许只是因为之前很多世代缺乏当今如此发达的评论业,而非之前就没有这样的阅读他人评论的冲动,今天的读者贪婪阅读书评、影评,过去的读者在客厅和沙龙里交头接耳,其出发点并无二致。至于“努力作出自己判断”,这话永远都不会错,然而一个人的“自己判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不是通过感受、学习和钻研那些更为优异者在类似问题上的判断。我们会反复在不同场合听到某个人义正辞严地表示,“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可我们仔细再端详一下,便会发现那不过是中小学教材、电视广告外加三流肥皂剧一并灌输给他的判断,而他之所以敢于宣称那就是自己的判断,只不过是他太少阅读他人评论的缘故。再举个例子,在现代汉语读者阅读但丁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艾略特、博尔赫斯和曼德尔施塔姆奠基性的批评文章乃至诸多但丁学者的帮助,就像在阅读《诗经》的道路上缺少毛诗、郑笺、孔疏和集传的帮助,一个人所谓的“自己判断”,大约不过只是从中重复遭遇有限且已知的自身罢了。现代科学有缸中之脑的设想,可见人无往不在被洗脑之中,最后的差别仅在于你选择被谁洗脑,被智慧者还是被传销商。
每个作家在成为创造者之前,都是一个业余批评者,他大量阅读他人著作,吸纳和分辨他人的论断,从中慢慢孕育和丰富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和创造冲动相比,与其说批评冲动是一种次要的和附属的冲动,毋宁说,它是一种更为基础的冲动。而在一个基础性领域,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发明创造,而是某种最低程度的共识,以及对这种共识清楚明白的表述。
2
在文学批评领域,近年相继有两本基础性著作被译介过来,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和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How fiction works),这两本优雅而迷人的小书,难得又遇到认真有教养的译者,却似乎并未得到我们文学批评界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看上去既没有崭新理论构建又没有宏大人文关怀,它们被视为有趣和琐碎的闲书,几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值得那些关心文学的人,每个月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反复重读。
这两本书的题目里都有how这个词,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学性,一定程度上就是指用‘怎么说’来衡量‘说什么’”。也就是说,“怎么说”是某种量具,天平或量杯或游标卡尺等等,其具体状态取决于你衡量的目的,即“说什么”,通过这种量具的存在,我们得以成功地交流对某种事物的文学看法。想象两个猿人之间互相为一个苹果争吵,一个说,它是红色的,另一个说,它是圆形的,他们争执不休,以至于拳脚相向,我们若是看到这种情况,恨不能塞给他们一张色差表和一套几何画板。
色差表告诉我们很多种颜色的差异,我们由此才能在没有手握玫瑰和矢车菊的情况下,对类似“黎明垂着玫瑰红的手指”和“最深处的海是矢车菊的颜色”这样由荷马或安徒生描绘出的图景保持某种共识;此外,几何画板教给我们圆形和正多边形的异同;精密天平帮助我们感受一克拉和八克拉之间的鸿沟 (倘若被称量物是钻石的话)……也就是说,一旦谈到“怎么说”的问题,立刻就意味着对于很多种“怎么说”的收集、分类、比较和鉴别,意味着对于过去已经存在之物的熟稔,意味着某种基本的人文素养。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说”和“说什么”并非对立之物。作家天然地会先关心“说什么”,关心语言和事物的实体,而“怎么说”,即对这种实体所呈现出的文学性的多维鉴别与衡量,则是批评家更应该考虑和传达的事。但在中国,这个情况意外地颠倒过来,“怎么说”在某个阶段竟然成了小说书写者最关心和热衷的文学终南捷径,而批评家们,大多数时候却总是在为“说什么”而兴奋、焦虑,或争吵。
《文学阅读指南》分五章,“开头”、“人物”、“叙事”、“解读”和“价值”;《小说机杼》分十部分,“叙述”、“福楼拜和现代叙述”、“福楼拜和浪荡儿的兴起”、“细节”、“人物”、“意识简史”、“同情和复杂”、“语言”、“对话”、“真相,传统,现实主义”。从这些小标题,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其趣向,两位作者都尝试回到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都不认为现有的学院批评和文学理论已经解决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相反,他们认为学院批评和文学理论催生了很多成见。此外,他们虽然都条分缕析,却也都明白文学又是一个整体,如詹姆斯·伍德所言,“在谈自由间接文体时我其实在谈视角,在谈视角时我其实在谈洞察细节,在谈细节时我其实在谈人物,而当我在谈人物时我其实在谈真实,这是我全部探究的终点”,又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我在本书中考虑的是为读者和学生提供几样入行的工具,没有这些,后面很难往下走”。
这两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何为文学的分析和文学的比较。它们共同的前提是对于种种微妙细腻之处的强烈感受力,共同的方式则是拥抱和吸纳尽可能多的相近文本,从而可以在诸多拓扑式比较中达致最精准的定位。
据说伊格尔顿的这本小书,是针对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 (How to read and why)而生,伊格尔顿觉得布鲁姆的论述过于简单粗暴,遂针锋相对地同样是以how为题。就这两本书来讲,伊格尔顿更像一个称职的英文系教师而布鲁姆更像先知。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布鲁姆更能获得我们当下诸多批评写作者的欢心,我们总是渴求强硬而富有气势的判断甚于左顾右盼的分析。布鲁姆喜欢沃尔特·佩特,一位19世纪的批评家兼先知文章家,模糊了创作和批评的界限。此类先知文章家,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写作者,之前还有本雅明、罗兰·巴特、福柯、埃德蒙·威尔逊、乔治·斯坦纳,等等。他们当然可以给我们以教益,倘若我们不是仅仅断章取义地捕获一些金句。相比而言,先知文章家不断在刺激读者,在作出新的、肯定性的宣谕,但精通文章之学的教师则希望首先帮助读者达成某种共识,哪怕是否定性的共识。
在《文学阅读指南》和《小说机杼》中,洋溢着一系列精彩的否定性共识,这些否定性不是用来贬低,而是用来更准确的定义。比如在《小说机杼》 “人物”一节中,作者通过大量的小说文本,列举并审视了各种关于“人物”的既有标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等等,他让我们感觉到,很多言之凿凿的标准和结论只是源于小说读得太少,在小说人物这个话题上,他让我们暂时失语,而正是这种失语,让好的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有可能相互理解,并寻找到更为精准和独特的、表述“怎么说”的路径。
另一方面,我们在当下文学批评中时常会遭遇到这样一类批评样态,这类批评看似同样放弃或悬置了简单的标准和价值判断,却转身遁入某种历史主义和问题意识的荫蔽之中,不同级别和层次的、品质千差万别的文学文本遂拉平为同一平面上的史料、论据和事例。这也许是一种颇具生产(再生产)性的学理批评,但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前提和文学创作一样,是感受力,是对细微差别的辨识力,但它又不同于文学创作,它本身又是一项每个认真的读者都能从事的活动,只要你手上掌握合适的称量工具。就像不是每个人都能炼出黄金,但每个人都可以借助仪器来辨识黄金纯度。而伊格尔顿和詹姆斯·伍德希望提供的,或许就是某种基础性的感受和辨识工具,它们帮助我们考问和质疑在文学领域中诸多常见的预设,并慢慢形成自己更有效地谈论文学问题的方式。
3
当代文学批评在持续几十年的理论高烧之后,突然又有一种退回到最粗笨肤浅的主题批评的倾向,像洪水过后的蛮荒。这就是伊格尔顿的中译新书《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又是一个how)里所谈到的现象:“大多数学生面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通常所谓的‘内容分析’,他们解释文学作品描述了什么,或许在当中夹杂着少量评论。”这种现象,在中文的语境里,被称作“夹叙夹议”。我们稍有留心就会发现,它同样也正充斥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场,小说批评被简化为情节批评,诗歌批评被改造为思想分析。
这已经并非一个是否要细读的问题,而是说,作为一个批评者,他是带着什么样的感官和辨识工具在读,因为他不仅要感受和辨识,还要如何有效地传达这种感受和辨识。这很多时候和才华无关,只在于训练,而一切训练的秘诀都在于分解,将一个整体性的行为或感受分解为一个个细部,如将乒乓球运动分解为步法、挥拍、击球、还原,将一首乐曲分解为音调、旋律、和弦、配器,等等。同样,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分解,但不是粗暴地分解为内容和形式,而是进一步地、做文本符号学意义上的分解。这也就是埃科曾经说的,“得体的批评”。“它并不预设立场,也不会开出准则认定只有哪种作品才能提供阅读乐趣,而是向我们解释和展示文本如何生产出乐趣”。
如果说,《文学阅读指南》和《小说机杼》里提到的诸如“开头”、“人物”、“叙事”、“价值”、“细节”、“语言”、“对话”等等被分解的符号语言,在当代中国小说批评中多多少少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那么,在当代汉语诗歌批评领域,似乎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在布罗茨基关于奥登、哈代、弗罗斯特的文章中猛然体验到的那种令人晕眩的诗歌逐行细读能力,还可以勉强归诸诗人的特殊才能,那么,当我们在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这本著作中再次遭遇到类似的体验,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作为一种基本方法而非特殊禀赋或理论流派式的批评语言。诸如诗歌的语调、音高、强度、纹理、词汇、句法、韵律、节奏,乃至诗歌的意义、价值和道德,当这些元素性的细节被一一拈出的时候,当我们目睹它们是如何有效地相互作用之际,会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遭遇字母表或笔画偏旁部首的小学生,对于一个字的构成从此有了新的理解;或像是一个被拉进健身房的人,通过不同的器械重新认识身体各部分隐隐约约的肌肉群。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不同于创造,它是我们每个文学读者都有能力获取的基本技艺。
现在文学批评界时常会谈论批评的主体性,而倘若我们真想获得文学批评的某种主体性,除了直言的勇气之外,不如先搞明白“如何批评”的问题,先从几本谈论how的小书开始。
编辑/吴 亮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