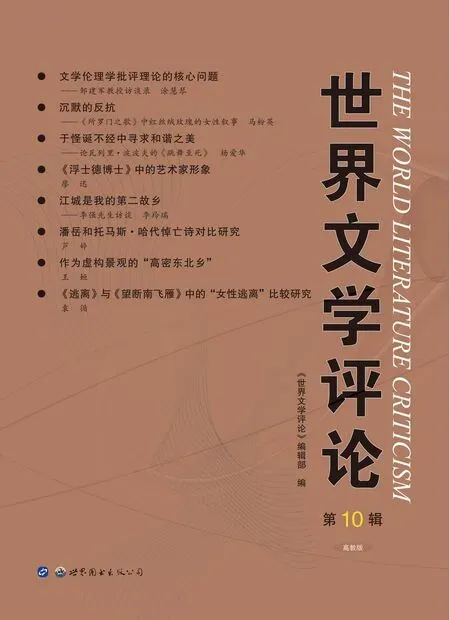推敲自我:菲利普 • 罗斯小说中的身体书写①
程海萍
推敲自我:菲利普 • 罗斯小说中的身体书写
程海萍
纵观犹太裔美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罗斯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创作,罗斯对自我的认知模式经历了从求同到存异的转变。求同是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和认同为目的的对他者的认同,与社会求同是本能的生存策略,主体以他者为视角认知自我,导致自我厌恶、身份困惑,甚至代际冲突和族裔隔阂。存异是主体认识到自我的独特性,接纳自我独特的精神需求,与社会认同达成和解。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罗斯通过疾病、衰老、死亡等主题强调身体感受和生命体验,将身体本身纳入自我的认知范畴,身心一体。在罗斯的创作中,身体是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主要社会身份标志,也是独特自我的鉴别标志。他者视角与身体视角是罗斯推敲自我的两个维度,它们反映了作者对少数族裔自我的认知发展,后者传达了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作者对个体独特性的关注和呵护。
身体书写 他者 独特自我
引 言
从195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集,到2012年宣布封笔,菲利普·罗斯(1933—)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罗斯创作主题从种族冲突、身份融合、代际隔阂到私密体验如疾病、衰老、死亡,关注视角由外部世界转至自身体验。创作主题的发展与视角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作者本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表达方式,且指向同一个问题:“自我”意义的探寻。哲学人类学家伯格指出,人是寻求意义的物种,他们要想维持生命,就必须有所作为,并赋予自身及其行动以意义,也就是说,要有意识地创造身体处境及自我的意义。随着现代性的高度发展,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身体研究(embodiment)”是“具体”和“体现”的综合,包括身体的物质特征和身体视角。身体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自我认同的核心,围绕身体所生发的体验、观念和关系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关键。罗斯对身体的现代性书写反映了“身体”隶属于理性的“物”的一面,而他对身体独特性的书写实现了身体从“物”到“思”的内涵衍变,将身体视为“可感的主体”,以身体体验取代理性反思,从而发现个体独特性与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自我内涵。
一、他者中的自我
拉康由他对婴儿“镜像阶段”的观察得出:人的自我意识一开始因为偶然一次与镜中“身体”的认同而得以萌芽,逐渐习惯于并努力在外界寻求认同的对象,来完成自我的构建。因此从镜像阶段开始,人始终在外界寻求某种形状,将它们视为“自我”。这样的“自我”基于对外在于我们身体的他者的认同,因此隐含了人类主体“分裂”的本质,构建自我的过程正是远离主体性和真实身体感受的过程。在戈夫曼的研究中,身体是充当人的自我认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特定的身体形式与表现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往往会被内化,深刻影响个体对于自我和内在价值的感受。外界价值与内在价值如不一致就会导致分裂的自我,表现为人的异化、人际冲突和自我认知的困惑。罗斯早期至中期的作品多以身处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犹太青年为主人公,着力表现个体在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冲突、妥协或异化。
菲利普·罗斯在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1959)中的主人公尼尔·克勒门是一个敏感的犹太裔青年,大学刚毕业,在图书馆工作,寄居在纽瓦克的舅母家里。小说以尼尔为第一人称叙述,展示一个犹太裔青年对自我的不确定感和对犹太身体深深的自卑感。他在游泳池边新结交了女友布兰达·帕丁金,他迷恋布兰达性感、健硕的身体,对布兰达所属的美国主流的生活方式充满好奇和向往。帕丁金家里各式的运动器材、冰箱里丰盛的水果、考究的餐具、轻松随意的餐间谈话,和格拉迪斯舅母家的节俭、拘束的生活风格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布兰达是典型的美国物质女孩,她通过鼻子整容彻底消除了自己身体上的犹太人特征,崇尚消费、个性开放,无视宗教、传统习俗。尼尔渴望融入他们代表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家庭,但也察觉到了自己与帕丁金家人在一起时的不适感受:“与这些‘大人国巨人’在一起用餐,一会儿我就感到肩膀仿佛削掉了四英寸,身高也矮了三英寸,更有甚者,我的肋骨好像已被切除,以至胸脯紧贴背部。”席间尼尔说话“像个唱诗班的男童一样”,“吃饭像只鸟”。作为美国移民的后代,尼尔自小接受美国自由民主的观念,但也清晰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在新教徒眼中,犹太族群被认为是身体孱弱、个性懦弱的。在和布兰达及他家人的相处过程中,尼尔愈发感到力不从心,他对布兰达患得患失,压制着“一直对她怀有的反感”,最后迁怒于布兰达,对布兰达进行语言攻击。他痛恨自己的羸弱苍白、懦弱无能。他对自我的认知在美国人与犹太人这两个维度间摇摆不定。尼尔的种族意识认知正是通过身体认知得到强化的。出于对布兰达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同时也担心被拒绝,他没有向布兰达直接求婚,而是让布兰达去安装子宫帽,以这种别样的方式试探布兰达的想法,同时给自己的犹豫不决留了后路。当尼尔在犹太新年前夕去波士顿看望并准备向布兰达正式求婚时,被告知布兰达父母发现了她遗忘在家的子宫帽,羞愧中尼尔狡辩责备布兰达,俩人黯然分手。尼尔于犹太新年的第一天回到纽瓦克颇具宗教意味,象征着尼尔对犹太身份的认同和回归。
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1969)中的主人公从小成绩优异,诚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且仕途顺利,受人尊崇。以社会和家庭的价值标准来看,波特诺伊是一个符合犹太价值标准的好儿子、好青年,但他私底下怨恨父母,以手淫摧残自己的身体、寻求发泄。他者视角下的自我认同是与身体自我的不断冲突和妥协,为获得社会和家庭的认同,他压抑了成长经历中的欲望和天性,导致了压抑的精神世界。波特诺伊向心理医生告白时的焦虑、恐惧和懊悔反映出他与生活世界完全撕裂的精神世界。
二、现代性下身体的缺席
为了更好地顺应环境,犹太移民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在一个较长阶段里遵循着与主流文化求同的规律。他们着眼于外界和他者,不断调整他们的身体表现及处境来重构或改变种族身份,这是犹太民族血液里的维存策略使然。对身体与其处境的塑造分为两个阶段:逃离原生家庭,重建个体身体处境。以下将通过对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美国三部曲”中的其中两部,即《人性的污秽》和《美国牧歌》的文本分析,展示罗斯是如何在其文本中通过犹太身体的社会化塑造完成他者视角下自我的认知构建。
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作为自我构成要素的身体特征体现为它的未完成性,是一个处在成为(becoming)过程中的实体。从另一方面看,现代性凸显了人类的自信: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逐渐加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规划身体、建构身体的意义,向外界发出自我认同的讯息。科尔曼与瑞典佬都成功地做到按照意志规划身体、完善处境,分别成为受人尊重的高校知名文学教授和成功企业家。
科尔曼是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他学业优异,不仅是跨栏冠军、短跑亚军,还是业余拳击手冠军。在东奥兰治的黑人社群中,他是被崇拜的偶像。他对自我的评价也极高,“他是科尔曼,伟大的先锋中最伟大的那个我”。当走出东奥兰治去霍华德上大学时,他遭遇到种族歧视,因为种族身份而导致恋爱挫折,这些事件彻底粉碎了他的理想自我,让他对原来的自我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排斥。在填报应征入伍的表格时,科尔曼利用自己较浅的肤色,谎报自己是犹太人。篡改种族身份之后,他从此逃离、背叛了家族,隐埋了黑人血统,以犹太白人的身份参军、求学,跻身于雅典娜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塞莫尔·欧文·利沃夫的外貌和体魄是犹太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融合:“虽尖尖下巴,呆板面孔,却金发碧眼”,是“橄榄球队的边锋,篮球队的中锋,棒球队的一垒手”,冠军篮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二战”时海军陆战队训练营教练。在纽瓦克社区,老老少少尊重和爱戴利沃夫,昵称他为“瑞典佬”。纽瓦克社区对“瑞典佬”的集体膜拜折射出“二战”期间身处美国的犹太移民对民族身份的集体危机感和复杂的心境:相比在欧洲战场上或身处险境的亲朋好友,他们庆幸自身当前虽不如意但也相对安全的处境。“瑞典佬”成为他们心目中联系犹太隔都与外部世界的纽带,“众人在这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希望的象征——是力量、决心和极力鼓起的勇气”。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瑞典佬”自我感觉良好,且自认为有别于其他犹太人。成年后的塞莫尔违背父亲的意志,娶基督教女孩多恩·德威尔为妻,搬出纽瓦克,购买了一幢地处郊区的、有两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子,实现了他的美国梦,开始他正式的美国生活。
科尔曼和塞莫尔利用身体的可塑性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和身份,在附和他者的认同中创造了新的自我。他们在抛弃原生家庭和种族身份的同时,也力图遗忘所有的身体经验,与自己种族历史一刀两断。也就是说,他者视角下所构建的自我是没有历史、没有体验的虚构自我。科尔曼更改种族身份、决定与家庭断绝关系是对自己所有记忆和经验的背叛。他母亲曾告诫他,“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无路可逃,你一切逃跑的企图只会将你带回你起步的地方”。母亲的话预示了自我与生命起点、自我与身体的紧密联系,任何刻意的遗忘都是徒劳的。科尔曼最后因为一次“无意过失”被控告“种族歧视”,被记录着他作为“白人教授”的二十多年辉煌业绩的雅典娜学院所辞退。对科尔曼来说,这个解雇的原因很讽刺,他辩解道,“我也许五十年前听说‘幽灵’有时用做指称黑人的贬义词,但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习语在现实中起着归类的作用,我们用这些词汇来归类他人,也用这些词汇来进行自我归类。“幽灵”是对黑人带有种族歧视的习语,被归为“有欠缺的”的社会成员,黑人自己也会被这种标签内化,形成相应的自我认同。戈夫曼有关污名(stigma)的分析表明,我们在领会自己身体的时候,往往就像是照镜子,而镜子里给出的映像是由社会的观点与偏见所框定的。这种他者视角下的自我执着于和社会主流中的他者观点保持一致,这种认知压制身体的真实感受,切断了自我的内向反省和认知,是一种单向的自我认知。
塞莫尔通过各种“越轨”的方式切断与父辈传统的关系,想像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是新教教徒”,而是当下的美国拓荒者。他选择远离纽瓦克,在郊区实现他自己美国田园式的乌托邦梦想,做真正的美国人。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混乱荒谬:此起彼伏的反越战恐怖活动、水门事件、能源危机,塞莫尔以他强大的理性“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戴上面具生活”,极力维护小家庭的秩序,在里姆洛克虚构出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他相信他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身份,也可以将家人从当时动荡不安的美国现实社会中拯救出来。但不幸的是,“他将孩子从现实中救了出来,可这孩子把他送回现实中”。女儿梅丽参加反越战激进组织,炸毁了当地邮局,成了通缉犯;妻子多恩绝望之中投向了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沃库特的怀抱。塞莫尔强大的理性使他偏执于虚幻自我的构建,以致切断了身体感受和真实世界的联系。
在与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科尔曼和塞莫尔利用了身体的可塑性成功地塑造了社会身份,但这种平面的镜像认同忽视了身体的另一个维度:历史性和经验性。当科尔曼和塞莫尔执着于他者的认同时,他们刻意压抑了种族自卑感和自我仇恨,而这些也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在认同与成长过程中或隐或现,无法回避。科尔曼与瑞典佬以各种方式逃离种族历史的同时,他们自以为切断了与民族历史和自身历史体验的联系,但这种狂妄的理性认同只会将自身投入虚幻的自我想像之中。
现代性是一场意义的危机,它让当下与传统彻底决裂,事物的意义失去了历史根基,也没有了原来的逻各斯中心。在现代性意义的废墟中,人类围绕身体重建意义,人类开放的意志一次次地突破身体的局限和界限,也让身体一次次地陷入意义的危机,这种身体知识和意义的循环互证产生了像“莫比乌斯环”一样的悖论,让人类陷入自我认知的尴尬境地。科尔曼的母亲说他,“你白得像雪,但却像个黑奴似的思维”。他再怎么样改变身体处境和身份,也抹杀不了他一路而来由对种族身份的自卑感而衍生出中的对种族的鄙视和仇恨。瑞典佬自以为能通过一次次的身份“突围”成为美国的拓荒级人物,将美国几百年历史置之脑后,最终却发现,“对于利沃夫家的人来说,进入美国每走一步,前面就有另一步要走,然而这家伙(沃库特家族)早在那里了”。事物意义只有在一定时空的历史中才显现,割裂历史的事物意义纯粹是现代人为满足膨胀的理性而虚构的一张自我的平面图。
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身体是潜在的、缺席的肉身,因为理性压倒一切,支配我们现代生活的行动往往是合目的的行动,我们总是趋向于维持生存和获得生存的意义。瑞典佬自我克制、压抑真实情绪,“致命关注他的责任”,“总是努力去做正确的事”,“一直从外面窥视自己的生活”,过着“双重生活”。科尔曼篡改的种族身份让他成功跻身于白人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但“幽灵事件”暴露了在他内心一直徘徊不去的对自我的恐惧和愤怒。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身体对于个体始终是一项规划,因为人是“向世界开放”的物种,要想维持生存,就必须完善自身,完善其处境。对身体的完善过程即是与他者求同的过程,但理性的规划压制了个体情感上的独特性,切断了自我在道德上、精神上、体验上的延续性和一贯性。
三、独特自我与身体的回归
在他者观照下的“自我”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属性,是社会文化对人的身心的驯服。罗斯的身体书写揭示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弊病,同时他也通过身体书写探讨自我的内涵,提醒我们尊重身体感官和生存体验的延续性,暗示“自我”具有历史体验的连续性和身体的感观独特性。菲利普·罗斯后期的作品如《凡人》、《垂死的肉身》和《乳房》等的叙事视角内倾,回归、立足于身体的生物属性,描写个体在边缘状态如面临疾病和死亡等的独特体验,通过双向甚至多向的视角考量自我的内涵。
在《乳房》(1972)一书中,罗斯以反讽和戏仿的写作手法聚焦于主人公变形了的身体:比较文学教授凯佩什突然变身为一只硕大的乳房,目不能视,不能行动,只能躺在医院里维持基本的生存。小说以第一人称生动地描绘了凯佩什教授在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身份之后的身体感受,以及他努力为自己身体的变形寻找各种解释。在一次次的阐释与否定中,理性的思辨和感性的身体针锋相对。约翰斯通在《自我问题》中说,自我只有在自相矛盾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说,在小说《垂死的肉身》扉页,罗斯引用了埃德纳·奥勃兰恩的一句话: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和头脑一样多。在罗斯的后期小说中,种族、性别身份逐渐隐去,小说中弥漫的是意志的无力感和对生老病死的躯体的悲哀。心为形役,这个时候意志无法左右身体,“自我”显露出自然真实的状态,文化符号逐一从躯体上褪去,人性接受读者无差别、无偏见的审视和拷问。
在《人性的污秽》中,科尔曼被大学辞退后又遭遇丧妻,一下从社会的中心滑到边缘,他的生活一度处于失控的状态。一个社会底层的女清洁工以她充沛的活力和原始的力量激发了科尔曼对身体的感受和关注,帮助他恢复了一直被理性所压制的激情一面,让他“从自己生活的残骸中,游出水面,重获自由”。身体通常隐没于我们生命体验的背景之中,不为我们所觉,只有当“自我”呈现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态或社会意义上偏离的形式时,身体才会被我们所觉知,身体的感受才会被自我所接纳,自我才显现出它感性与激情的一面。
罗斯在他七十三岁高龄时完成的《凡人》一书,以倒叙的手法从葬礼开始回顾了一个人的一生。罗斯没有给他的主人公命名,从头到尾以“他”称之。罗斯似乎要以这种佚名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的存在的普遍意义。“他”从童年开始屡屡遭遇疾病和手术,正是这些身体上的疾病让“他”的一生都在寻找不为肉身所羁绊的出路。“他”一次次出轨,以新的婚姻或情感暗示自己的新生命,将过去抛至脑后。“他”以追求性爱和艺术来回避对于死亡的恐惧,最后却发现:“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疾病和死亡将我们推到自身生存的边界,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赋予自己身体以及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不确定也不稳定的。鲍曼将这种境况称为“理性的终极失败”。因此理性与身体的对抗毫无意义,艺术也不能突破生命的有限性,只有与过去重建联系,增强对于生命、意义和死亡的反思,接纳自身的有限和独特,才能完整地认知自我。
身体的开放性让现代人可以自由创造自我的意义。但是这些关于自我的主观意义的构建在遭遇疾病和死亡等极端体验时,暴露出其意义的危机和“理性的终极失败”。罗斯通过让人物遭遇极端体验来提醒他们回到身体本身,将独一无二的生存体验和感受纳入自我认知,将对自我的认知回归主体。
他者视角与身体视角是罗斯推敲自我的两个维度,它们反映了少数族裔对自我的认知发展。身体视角解构了人物的社会身份,将自我认知回归身体层面。这是罗斯以文学虚构的方式推敲“身体”的意义,关怀自我和人性的方式。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以下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欲望的身体维度——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欲望主题研究(2016N13M省社科联社科课题);(2016年浙江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身体研究;(ZWZD2015005浙江省外文学会专题研究项目)推敲自我: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身体书写研究。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Goffman, E.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p.33.[2][美]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俞明理,张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美]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俞明理,张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4][美]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俞明理,张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5][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6][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7][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8][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9][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10][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11][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12][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13][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14][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15]A.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7.[16][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7][美]菲利普·罗斯:《凡人》,彭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8]Bauman, Z. "Survival as a social construct, 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
, 1992, p. 36.Title: The Study of Self in Philip Roth's Body Writings
Author: Cheng Haiping is from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hilip Roth,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writer, undergoes the change of self-conception from identifying with otherness to co-existence. Identifying with otherness is the efforts made to win acceptance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the minority group. The adherence to otherness leads to self-disgust, the identity bewilderment, generation conflict and even ethnic segregation. Co-existing with the otherness is the spiritual acceptance of one's unique self and balance with the social identi fi cation. Roth emphasizes the sensational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when dealing the topics such as disease, aging and death, which suggests his understanding of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writing. In Roth's works, boby is not only the symbol of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y, but also the sign of unique self. The above two perspectives are the two dimensions of exploring self. The development suggests the minority's changing concepts of self and the care they diverted to the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ody writings the otherness the unique self
程海萍,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