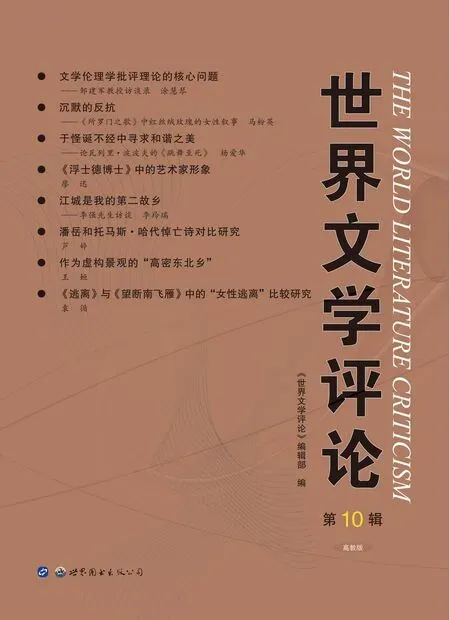中国古典直觉感悟思维视域下爱伦 • 坡推理恐怖小说的模糊美
刘婉仪
中国古典直觉感悟思维视域下爱伦 • 坡推理恐怖小说的模糊美
刘婉仪
在大众认知中,推理小说 是最具有逻辑推演功能的一种小说类型。而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用中国传统古典直觉感悟思维反观被称为“推理小说之父”的埃德加·爱伦·坡的推理小说,发现其推理小说“恐怖”的魅力很大部分并不来源于缜密的逻辑推理,反之,这种魅力一部分源自其小说所具有的相对“直觉性”与“模糊性”的特质,具体体现在语言上的超逻辑性、情节设计的模糊性以及思维的整体性。而针对这些特质的研究,不仅为爱伦·坡的研究提供了具有中国古典哲学特质的全新的研究角度,也为在当前消费语境下的中国推理小说创作、研究提供了新的创作灵感。
直觉感悟思维 推理小说 爱伦·坡 超逻辑
一直以来,推理小说都被认为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其中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语言都极具逻辑推演特性。也是因为这样的特性,推理恐怖小说吸引了很多读者的目光。但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说的艺术魅力远不仅仅局限在逻辑推演的严谨中,相反,很多推理恐怖小说中透露出一种超逻辑的模糊美。这种模糊美和中国古典直觉感悟思维视域中的审美方式非常相似。
中国古典直觉感悟思维的研究,在哲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尤其在人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西哲学研究者都发现逻辑思维的缺陷以及直觉感悟思维的有效性。正如叔本华提出直觉是一种“直接的了知,并且作为直接了知也就是一刹那间的工作,是一个appercu,是突然的领悟;而不是抽象中漫长的推论锁链的产物”。但是反观学界的研究现状,可以说对于这种在人类艺术创作、科学研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展开深入、有效的研究。显然,仅仅是举例、普遍性的讨论是无法满足需求的,这样的现状就使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更加迫切了起来。而从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研究的成果来看,几乎没有将这种思维研究与外国文学作品相结合的例子,这就将这种思维的研究局限在了中国古代诗歌和文论研究中。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式传统直觉思维研究的发展,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思维方式上来看。
爱伦·坡的研究则一直是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文化研究的热潮,坡的小说中的叙述技巧、死亡意识、哥特文化、魔性审美等问题被置于文化背景下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坡在读者的接受、市场接受方面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比较停滞的阶段。与当前研究热点相比较,国内多数学者并没有真正思考、研究过为什么爱伦·坡在中国读者群中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接受,以及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市场呈现非常好的接受效果,并且也没有深入这其中与中国传统直觉思维对于中国读者的深刻影响有何种层次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对于这种关系的研究,更容易突破以往大众对于推理小说的刻板印象,也更容易从思维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推理小说的创作提供新的思路。甚至能够彰显出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后建立比较文学属于“中国学派”的野心。
一、 语言上的“味外之旨”
在西方文论中,文学语言的超逻辑性实际上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的。这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们基于“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这两个概念所提出的“偏离常规”理论。当作者建立属于自己特殊的审美语言的时候,语言就是其中的“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就是指通过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主题旨意,这两个要素相互制约,使得文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作家采取一些技巧、手段来改变语言描写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与逻辑不相符合的状态,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偏离常规”的状态。什克洛夫斯基还指出:“如果这种破坏变成一种准则,它就会失去原有的作为障碍手法的力量。”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古典文论在论述文学语言的时候,则强调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使读者从表面语言体会出其背后的“味外之旨”,并且强调这种过程不是逻辑推论的过程,而是一种直接的审美之“悟”。二者对比可以非常明确地发现,在语言文字的审美上,西方的超逻辑性也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一种严密考量、计算的审美过程;而中国古典文论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直接跳跃过了“逻辑”这一步,强调文学语言在直觉思维审美下产生的艺术魅力。
在爱伦·坡的恐怖推理小说中,这种并非依靠逻辑而依靠直觉思维审美的文学语言特征非常突出,而这也是笔者认为爱伦·坡恐怖推理小说能够在推理小说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首先,爱伦·坡非常擅长使用对声音、光亮、颜色进行语言描绘,并且擅长用它们塑造恐怖的气氛。恐怖声音对于情节推动或者故事推理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却让读者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阴森可怖的恐怖环境中,这种语言则是从直觉思维的角度出发,读者很容易产生类比联想。比如在《厄舍府的崩塌》一开头,除了用生动的语意和感情色彩来描写乌云低压、荒径孤零中的凄凉的古屋外,还运用语音来加强这一气氛,强烈地刺激读者的视听神经,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幅恐怖的画面。
其次,坡非常擅长在小说中描写建筑,通过建筑本身带来的压抑感、恐怖感给读者带来某些并不愉悦的阅读联想,而这些建筑本身,与推理过程毫无关系,但是却成为了坡小说中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比如在《幽会》中,公爵府可以说是奢华异常,比如坡这样描写一束光进入这个房间的场景是“从上千个角度和那些熔化的银瀑布般缠绕在柱带上的窗帘折射而下,和人工的灯光匀称地交织,在一块看上去像流动的富丽的智利金色地摊上翻滚着,然后渐渐平息”。等等形容这所建筑异常华丽对小说内容可以说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发生了两人同时殉情的案件则加重了整个案件带来的诡异感、震惊感,使一起简单的殉情案变得扑朔迷离。这与苏轼所提到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非常类似。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厄舍府的崩塌》,这部基于建筑的小说,也先大篇幅地描写了关于厄舍府的建筑外观,包括它的尖顶、巨大的窗户,以及它无论如何目不能所及的高耸的天花板和拱顶,这都营造了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气氛,这种气氛在最后厄舍府的崩塌的一刻达到了顶峰,毁坏的不仅仅是这个建筑,更是故事中两位主人公的生命。对于建筑的描写,在这里是超越逻辑的一种审美建构,读者通过这种“味外之旨”的体会,将更能明白建筑之中人的心理的变态之可怕。
最后,坡也非常擅长用语言书写人内心的恐惧。这种心理恐惧的描写往往是毫无来由的,有时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病态,有时只是作者在语言上要刻意营造一种恐怖、扭曲的气氛。比如《泄密的心》中,“我”因为一直痛恨邻居老头的那只蓝色的“鹰眼”而将其谋杀,可以说这个谋杀原因非常荒谬,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主人公也备受自己的心理疾病的影响,不断产生幻听。谋杀的时候,这个声音是“一阵阵低沉声音,像是蒙着棉花的表的声音”(283)。而把尸体肢解后,尸体被埋在地板下,这时他又听到了嗡嗡的声音,最后那种“蒙着棉花的表的声音”又出现了。这也导致了主人公最后的疯狂,向警探坦白自己的罪行。这样的语言描写就将人物内心的恐惧成功外化,这里的语言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却在这样的语言下蕴藏许多令读者能够感受到的病态的、不可思议的内容。在《黑猫》中,这种病态则变成了酗酒的恶果,酗酒之后“那个善良的灵魂一下子就飞出了我的躯壳。”(286)这种相对抽象的语言描写反复出现,揭露了其杀猫、杀妻背后的病态心理。
二、 情节设计上的“顿悟突现”
在佛教中,灵感集中表现在禅宗的顿悟说中。“顿悟”是佛宗术语,与“渐悟”相对。“渐悟”指众生必须经过长期按次第修习,才能觉悟,这属于佛教的传统方法。“顿悟”指众生不必经长期修炼,就可以于偶然之中突发觉悟,即刻成佛。这种顿悟的过程属于直觉思维的一个部分,集中体现了直觉思维的在思维过程的模糊性、跳跃性。
这种顿悟在艺术灵感中,则被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家不断强化,陆机《文赋》中用“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生动地展现出顿悟出现的时候的情状。在陆机看来,文学创作中的顿悟非常重要。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的理念也是类似,俱是强调灵感的重要性。
在爱伦·坡的推理小说中,情节设计中经常会出现一种“顿悟突袭”的情况,这一过程与“感应之会”非常类似,在推理过程中用“顿悟突袭”代替严格的推理过程,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比如在推理小说《金甲虫》中,威廉·勒格朗一直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解读羊皮纸上的藏宝地点——“贝梭甫旅馆”,但是却一直一无所获,正在他非常迷茫的时候,“一天早晨我的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81),使他改变了寻找的方向,转而去查找贝索普家族。最终在贝索普家族的旧址找到了宝藏。而当他在羊皮纸上发现自己所画的甲虫和颅骨的位置发生了惊人的重合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惊,但是又一时无法解释这个重合,坡这样刻画了这时这位人物的心理:“在开头的一刹那,我似乎就有一种真相的概念,像荧光一样在我心底最幽暗最隐秘之处若隐若现。”(73)而在《玛丽·罗杰疑案》中,开头坡就写道“世上确有离奇古怪的巧合,很少有人不会被吓得糊里糊涂。”(27)整篇小说对于“香水女郎”死因的推理都是基于对几份报道了案件的报纸的分析而完成的,作者最后评价整个探案过程“不过是巧合罢了”(55)。这里提到的“巧合”,也是在强调整个案子能够破案主要是因为事件种种细节的巧合带来的灵感。在《毛格街血案》中,侦探迪潘也是因为发现了避雷针柱脚下的一根油腻的缎带才灵感突现,将前后的线索连贯起来,推理出凶手是船上水手养的猩猩,既合理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凶手力气惊人有异常凶残,又解释了猩猩的合理来处。可以说,这跟小小的缎带带来的“灵感特效”非常重要。
有时,这种灵光一现还是由于其他种种原因,有时是一种病态,有时是毒品带来的幻觉。例如在《贝伦妮丝》中,主人公尽管生活非常富裕,但是却非常痛苦,因为他患上了“狂想症”这种精神疾病,时常分不清现实和幻想,而这种病态中,主人公产生了只要拿到自己爱人贝伦妮丝的牙齿就能够“恢复平静,回归理智”(131)的灵感,这样的灵光一现毫无道理,充满了病态,但是也正是这样诡异的灵感使得主人公变成了疯狂的盗墓贼,盗走了自己妻子的牙齿,将整个故事的荒诞诡异更推进了一步。在《莱吉亚》中,主人公“我”因为常年吸食鸦片而难以区分现实和幻觉,在看到莱吉亚的鬼魂的时候产生了“是因为长时间的劳累而让我的想象力变得极其活跃而产生的一些生动的联想罢了”(149)这样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也使得最后莱吉亚还魂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更加重了许多。
在坡的推理小说中,一方面这种“顿悟”或者“灵光一现”的情节设计在推理难以突破时作为推动情节的工具。这主要是基于这种“灵感”式情节本身所具有的超逻辑性,探案如创作,灵感向来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直觉思维在思考过程中体现为思维主体对于思维对象的直接把握,这也就使坡的小说在“灵感突袭”的一时间产生了逻辑思维上的空白,这对于小说情节的设置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尤其出现在以求全求满为主要要求的推理小说中。这种空白一方面展现了人类思维本身所具有的真实特性——超逻辑、超理性的直觉的真实存在。正如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说:“直觉是面向内心深处的,一般人会借助它意识到内在生命的持续,某些人的直觉更强烈,它把他们带向我们存在的根基,从而领悟普遍生命的法则。”这样的情节设计使推理小说变得不再机械、固定,而是充满了真实。
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灵感并不一定是推理出谁是凶手,有可能仅仅是凶手的病态心理或者药物效果,比如在《贝伦妮丝》、《莱吉亚》中,灵感本身也成为了增加案件悬念、制造恐怖气氛的一个重要因素,灵感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模糊性的美学。坡的推理小说整体也给人带来一种“模糊”之感。这种模糊跳出了严格的推理形式,使整个故事处于一种荒诞、诡异的氛围之下,这也正是坡独特的小说艺术。
三、 思维上的“天人合一”
从内容上说,中国古典直觉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这种整体性思维主要是指思维主体本身作为整体进入思维过程中,主体的理智、意志和情感有机统一在一起而发挥作用,表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一的过程。
爱伦·坡的小说则用这样的整体思维闯进了人类心灵的地狱,他不满足于停留在人物外部世界的描述上,还打开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大门,并且将这种人的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人物心理空间的压抑与物理空间的幽闭相结合,可谓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魅力。
首先,爱伦·坡在物理空间的选择上,不仅使其包含了哥特式小说梦幻的因素,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大肆添加了暴力和压抑的成分,突出了恐怖怪诞的效果。坡选择的空间都具有密闭性的特点,这是最能达到恐怖效果的空间形式。比如《威廉·威尔逊》中的布兰斯比学院,《厄舍府的崩塌》中的厄舍府,《黑猫》中的古宅,等等,这样的古堡、古宅、墓穴等本身就是带着物理空间的幽闭属性,往往也是在这样的物理空间中,主人公的精神走向了崩溃。坡的小说物理空间与故事的整体基调是符合的,在这里,空间已经成为了小说主体和主题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地点,它还体现了主题,是主体的一部分,这样的物理空间设计,与直觉思维的整体性特性中“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部分具有非常相似的部分。
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哥特小说喜欢选择的空间包括神秘的城堡、阴森的密室和诡异的墓穴这样的特点的同时,但是坡给小说所植入的“心理化”和“内在化”的因素却是发展了传统的哥特小说,他极力描绘了人物心灵的密室或墓穴,他将那种阴森诡异的气氛搬进了人物的心灵深处。
通过上面三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出爱伦·坡的推理小说在创作层面上所体现出的属于中国古典直觉思维的特征,无论是在语言、情节设计还是思维上,他的推理恐怖小说所制造出的美学张力绝不仅仅建立在逻辑与理性之上。相反,笔者可以推论出,坡的侦探小说本身就有着“反侦探小说”(anti-detective fiction)的特质。这些小说颠覆“理性主义”,表现理性的穷途末路和捉襟见肘的困境,着力展现人在荒诞现实下的悲剧处境和悲剧事件里的荒诞意味。比如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就是典型的反理性、反逻辑的侦探小说。讨论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侦探小说鼻祖”的爱伦·坡本身就具有“反侦探小说”的特质,这与中国古典哲学魅力遥相呼应从而构成了坡小说复杂的美学特征。
对于中国当代推理小说创作者而言,最大的难题不在于“诡计”的设计,也就是说,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逻辑的缺失。在当代科学思维教育影响下的这一代推理作家,在逻辑方面是丝毫不输给国外作家的。为什么在推理小说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的时候,在邻国日本的推理小说屡屡登上我们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的推理小说?有人会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推理的土壤。笔者认为,不妨去研究一下被称为“推理小说之父”的推理小说,就可以发现,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土壤”,相反,我们正在一片极具艺术张力、想象力的直觉思维的肥沃“土壤”中。
总而言之,正如马尔克斯在他的一篇散文《侦探小说的奥秘》中说道“最巧妙的侦探小说也会使自己失败,因为它的奇特性恰恰就是它的神秘性,它必定被逻辑这么简单而愚蠢的东西所识破。”本文的研究,也希望能为推理小说的创作提供一点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灵感。
注解【Notes】
①爱伦·坡:《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集》,王丽君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宋)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关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50页。
[2] [法]茨威格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3]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4] [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5] [法]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王作虹、成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6]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散文选诺贝尔奖的幽灵》,朱景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Title: Fuzzy Beauty in Poe's Detective and Horror Stor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lassical Intuition Thinking
Author: Liu Wanyi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Wuh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ss cognition, the mystery novel is one of the most logical func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use Chinese classical intuition thinking in Edgar Ellen Poe's mystery novels, found the mystery novel "horror" charm very much is not derived from logical reasoning, careful and part of the charm of the relative "intuitive" from the novel with the "fuzzy"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uper logic, fuzzy and plot design thinking as a who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Chinese with classical philosophy attributes of th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Poe, also provides a new inspiration for the cre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a mystery nove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intuition thinking mystery novels Poe Ultra logic
刘婉仪,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