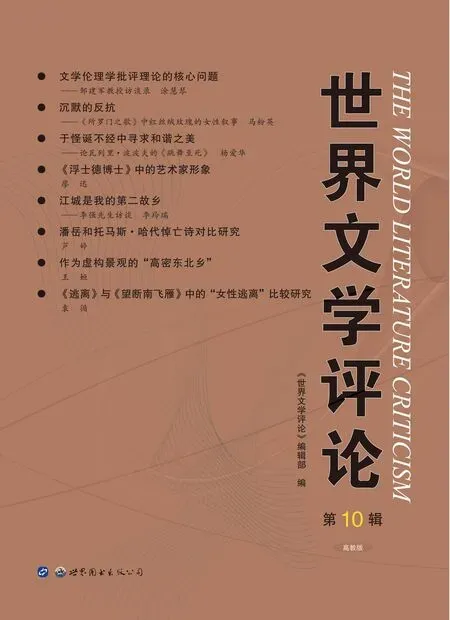论地理环境对废名小说创作的影响
沈 闪
论地理环境对废名小说创作的影响
沈 闪
在废名小说创作中,山水自然风景和人文社会物象是其关注的两大主体。山水自然环境大部分来源于废名幼时居住黄梅时的地理记忆,也是其小说故事情节展开的背景。由独特的佛禅文化、民俗风情等构成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废名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其小说创作中。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废名小说创作,并借此探讨其审美经验和美学视镜,或许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废名 小说 地理环境 影响
废名(1901—1967),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小说的鼻祖。其前期创作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常被学者归入乡土文学范畴。“诗化”、“散文化”是其前期创作的主要特征,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手法常出现在其中。此种创作手法运用到《桥》时达到顶峰,小说结构精心雕琢且文辞简约幽深,既平淡朴讷,又生辣奇僻。后期创作以极具写实性、佛禅文化色彩的《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为代表,因晦涩难懂而著称于世。废名在小说创作中所关注的有两大主体,一是山水自然风景,一是人文社会物象。山水自然风景大多来源于废名幼时居住黄梅时的地理记忆,同时也是其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背景;由独特的佛禅文化、民俗风情等构成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废名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其小说创作中。但目前众多论者对废名小说创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叙事技巧、文章结构等方面,而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重新解读废名小说创作,并借此探讨与之相关的审美经验和美学视镜,或许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这是一次对文学地理学研究实践的回应,以期在废名小说研究方法的创新上、批评方式的建构上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人的一生,可分童年、中年、晚年等不同阶段。童年虽然短暂易逝,但作为人生历程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对我们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等特征的形成发展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幼时的记忆和情感,往往成为写作者轻而易举就可得的写作素材,因此童年时代的地理记忆是作家的创作来源之一;反言之,童年的记忆及情感也是研究者批评的对象。废名也曾说过,“我想来以为一个人的儿童生活状态将影响于他的将来非常大”。然而,人们的童年大多在故乡度过,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风俗民情,都渗进作家纯真而敏感的童心里, 溶化到其血液之中。
其中,废名童年时代的黄梅将是笔者讨论的重点,本文将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影响废名小说创作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主要是指由于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原始自然物象,如山、河、湖、海、太阳、月亮、星、辰,以及大地上动物和植物”。黄梅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废名小说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是废名小说创作的“地理故乡”。
废名嫡侄冯健男在《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中指出,“正是家乡那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孕育了废名的创作。”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强调:“作者生长在湖北黄冈,所采取的背景也仍然是那类小村庄方面。譬如小河、破庙、塔、老人、小孩,这些那些是不会在中国东部的江浙和北部的河北山东出现。”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整部《桥》二三十万字,都是田园山水画的连缀,一幅幅描山绘水,写意传情,故事情节甚少纵向的推进,三五人物的活动几乎成了串联这些山水画幅的绦带。”废名自己也曾在文章中强调“自然”对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只有‘自然’对于我是好的,家在城市,外家在距城二里的乡村,十岁以前,乃合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往’,而成就了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1416)废名自出生至16岁离家去外地求学期间,一直居住在黄梅。1937年抗战爆发后,又避难黄梅近十年。
黄梅因域内有黄梅山、黄梅水而得名,隶属于湖北省黄冈市,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尾南缘,鄂皖赣三省交界,南临长江黄金水道,自古有“七省通衢”“鄂东门户”之称。黄梅一带的山川草木是废名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竹林的故事》中非常茂密的竹林,《桃园》中随处可见的桃子,《河上柳》中枝繁叶茂的柳树,《菱荡》中满布传奇色彩的洗手塔,《桥》中养育史家庄儿女的河及河上的桥、芭茅,《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描述的五祖寺、东山,皆为废名故乡黄梅真实风物的写照。现如今,曾频繁出现于废名笔下的塔、大枫树、五祖寺等仍可寻见,有的早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此外,小说中的人物从三哑叔到浣衣母,从采菱老汉到卖菜姑娘,从种桃父女到店铺小伙计,描绘的无一不是黄梅当地最普通的乡民。
废名笔下的“外家”即为岳家湾。岳家湾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乡村生活宁静闲适,一方面熏陶着他的性格,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成为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岳家湾对废名之重要,正如‘鲁镇’之于鲁迅。”岳家湾不只一次地出现在废名小说创作中,仅从下面引用的两例可见一斑。废名在前期小说《柚子》中是这样描写岳家湾的:
外祖母的村庄, 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河东约半里,横卧着起伏不定的山坡。清明时节,满山杜鹃,从河坝上望去,疑心是唱神戏的台蓬——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24)
此处既写了岳家湾, 也描绘出岳家湾四周的环境。在《桥》中被唤作“史家庄”的村庄实际上是废名以“岳家湾”为原型的。《桥》中有一个从远及近描写“史家庄”的“特写镜头”:
站在史家庄的田坂当中望史家庄,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她在那里绿。站在史家庄的坝上,史家庄被水包住了,而这水并不是一样的宽阔,也并不处处是靠着坝流。每家有一个后门上坝,在这里河流最深,河与坝间一带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尽是垂杨。迤西,河渐宽,草地连着沙滩,一架木桥,到王家湾,到老儿铺,史家庄的女人洗衣都在此。(477)
据冯健男回忆,1937年废名避难黄梅时曾与他相伴游菱荡圩。
菱荡圩算不得大圩, 花蓝(篮)的形状, 花蓝(篮)里却没有装一朵花,从底绿起,——若是荞麦或油菜花开的时候,那又尽是花了。稻田自然一望而知,另外树林子堆的许多球,那怕城里人时常跑到菱荡圩来玩,也不能一一说出,那是村,那是园,或者水塘四围栽了树。项上的树叫菱荡圩的天比地更来得小,除了陶家村以及陶家村对面的一个小庙,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207)
在废名的小说中,类似这种对黄梅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还有很多。自然地理环境与废名小说创作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正如冯健男所说:“废名得之于‘自然’又归之于‘自然’的美。”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在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 常常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是作家及其作品产生的前提条件。童年时期,黄梅留给废名的地理记忆是美好、纯真的,废名笔下的故乡多是充满诗情画意,给人带来美感。抗战后动荡混乱的黄梅带给废名更多的是不安与警醒,这一时期的小说则多了几分苦涩与昏暗色调。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在作家创作中起直接作用的同时,也巧妙地通过人文要素在作家身上碰撞出夺人眼球的文学火花。人文地理是在自然地理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与其共同构成地理环境的两极。因此,人文地理对于作家文学活动的干预,同样是十分重要而巨大的。
二、影响废名小说创作的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人的创造、与文化传统、风俗民情相关的物象。从广义上来说,文学作品里所体现的特定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同样也是地理基因的关注点之一。黄梅地区独特的佛禅文化及风俗人情通过四祖寺、五祖寺、打杨柳、扎柳球、放猖、送路灯等众多人文物象反映到废名小说创作中,使其作品意蕴丰富、自创一格。
(一)佛禅文化
长久以来,黄梅即为人们心中的“佛教圣地”。庙宇众多,信徒广泛,佛禅文化浓郁是黄梅给人的几大印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僧尼常与乡民百姓混杂而居,而不是隐居山林。在古代,大诗人陶渊明和高僧慧远就曾闻其名而游历于此,并留下纪念诗文传诵至今。并且,在佛教史上拥有一席之位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皆在此传授衣钵、造福百姓。
东禅寺、文公庙、城隍庙、四祖寺、五祖寺等众多寺庙皆为供黄梅乡民百姓祈愿礼佛之地。其中,最为百姓乐道和敬拜的五祖寺对废名影响甚巨。“五祖寺是我小时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回来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五祖寺更是那么的有名,天气晴朗站在城上可以望得见那个庙那个山了。”(1410)
家庭是儿童现实意义上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等家人则是第一位老师。家人的生活习惯、家庭环境的文化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儿童的成长。废名出生于佛禅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之中,其祖母、外祖母、母亲皆虔诚拜佛。废名的母亲法号还春,常在家打坐修行。废名自幼熏陶于其中,自然佛禅意趣对其意义重大。废名与熊十力论佛,后撰写《阿赖耶识论》表明立场。他也曾借莫须有先生之口称许佛教具有育人功能,“你们(纯、慈)长大了,顶好也信佛教,学做人也顶好亲近佛教的道理”(962)。
“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1154),佛禅文化是培育废名小说文学世界的另一肥沃土壤。幼时废名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信佛参禅之人常出现在小说之中。但不同的是,他们常因生活所迫而成为僧侣,身上仍保存有俗世生活的气息,比不得真正坐禅修行的僧人。因此在废名笔下的僧尼形象自然与一般不同,《沙滩》里恋世的尼姑常怀念过去美好而悲哀的爱情;《火神庙里的和尚》金喜每天都为生计所苦恼;更有甚者,城隍庙里的僧侣竟与混迹社会的老油条四火联合起来欺骗前来祈愿的汉子。佛禅文化对幼时废名的影响还促使成年之后的他极其关注儿童世界,《桥》中纯真而洒脱的细竹,《桃园》中多病但善良的阿毛,《竹林的故事》中乖巧而勤劳的三姑娘皆为儿童世界的一个侧面。小儿女的童真童趣、纯良自然与佛禅的守本真心、冲淡修心殊途同归。周作人曾指出:“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的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3407)所谓的“隐逸性”,即为佛禅文化影响的结果。
佛禅文化对废名思想的影响更多表现在其思维方式和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上,他身上浓重的佛禅审美倾向一直为研究者们所关注。社会黑暗、生存艰难、生活贫瘠常常是传统乡土小说关注的重点,但在废名小说中则很少看到它们的影子。他也表现悲哀,但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凌驾于悲哀之上、自然闲适、达观洒脱的处世态度。《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无论在语言风格、结构特征还是在意境营造上都蒙有一层禅趣的外衣,个人参禅悟道的意味浓重。如《桥·狮子的影子》中的描写:“有一回,母亲衣洗完了,也坐下沙滩,替他系鞋带,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他两手捂着母亲的发,静静的望。”(1047)这里,人物心灵与自然意象相互映衬,寂静空灵,自成一体,禅境也。朱光潜曾指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二)风土人情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民俗。文学的特点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包括思想感情)。”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所说,作者对一地民俗风情的生动刻画和详实记录,在丰富小说等文学作品内容的同时,也为风土民情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废名生在黄梅,长在黄梅,故乡独特的风俗民情深深扎根于废名心中,且在其文学创作中开枝散叶。
自古以来,黄梅人生性活泼,常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闻名中外的黄梅戏即发源于此。黄梅位处丘陵地带内有大片茶园,乡民们在采茶之时竞唱山歌民调以此助兴。黄梅戏在当地也称为采茶戏,后在安徽发扬光大。众多不明真相之人认为黄梅戏是安徽本土戏种,其实不然。常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天仙配》《打猪草》《罗帕记》在黄梅时就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剧目。民间文艺对废名的影响极深。《河上柳》描绘的以唱木头戏为生的老艺人,《竹林的故事》中热闹非凡、万人空巷的“赛会”盛况,《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的停前看会片段等等,都具有独特的黄梅地域文化色彩。
看鬼火、送路灯,包粽子、放猖、打锣、上坟、摸秋等众多活动都是黄梅当地的风俗。童年时代,废名常是众多看热闹与参与者之一。因此,这些民俗也常常呈现在其小说之中。黄梅百姓在过清明节之前,有“打杨柳”“扎柳球”的传统习俗。“打杨柳,孩子们于各为着各家要打一个大枝而且要叶子多以外,便是扎柳球。长长的嫩条,剥开一点皮,尽朝那尖头捋,结果一个柳球系在白条之上。不知怎的,柳球总归做姑娘的扎,不独史家庄为然。”(483)待到清明节之日,故乡黄梅的上坟秩序也异于他处。“清明上坟,照例有这样的秩序:男的,挑了‘香担’,尽一日之长,凡属一族的死人所占的一块土都走到;女的就其最亲者,与最近之处。”(497)“放猖”则是中秋佳节迎神赛会上的一个重要“节目”。“会上还是以‘放猖’为主,不过是规模更大的放猖罢了。加了‘大头宝’,加了‘地方’,加了‘土地老’”,“县城里以大头宝最出色,乡下则土地老最神气。”(931)“地方”即“活无常”,他“不是假面具,涂了甚重的粉脸,眉毛则黑,两唇亦甚红,穿了白鞋,白布衣,大步,而如时间不够似的,要赶快走”(931)。民间放猖是为驱除瘟疫,且时间多在午后。游猖则为夜间活动:受人敬仰的神在五猖保护下,伴随着锣鼓和喇叭,围绕着村落走一圈。收猖在最后,至此,一个完整的放猖才告一段落。废名对这些风俗民情描述的如此生动具体,原因何在?“打杨柳”“扎柳球”“放猖”本就是黄梅当地传统习俗,废名笔下所呈现的即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场景。废名对风土民情如此细致的描绘,现已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旧时黄梅地方文化的材料之一。
从根源上来说,文学的发生一定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一个作家所受出生地、成长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将反映到其所写文本结构和语言特色中。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决定文化基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文学发生的基础。
童年时代的地理记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它不仅是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还影响着作家的气质、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废名童年时代的地理记忆是其小说创作的基础,特别是他童年在黄梅的自然地理记忆。自然风景、风土民情、人物形象、各人物之间的情感与矛盾、人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资源。废名曾借莫须有先生之口表达其对故乡黄梅的热爱:“你们有谁能像莫须有先生一样爱故乡呢?莫须有先生的故乡将因莫须有先生而不朽了。”(818)只有对故乡山水的一往情深,对故乡百姓的熟悉与热爱,才会有《竹林的故事》《桥》《菱荡》等优秀作品传世,文坛上也才会有如此优秀的作家诞生。废名的小说向我们再次证明,一个人从小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会成为一位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注解【Notes】
①王风:《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4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6页。
[2]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载《黄冈师专学报》1993年第13卷第3期,第3页。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
[5]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6]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载《黄冈师专学报》1993年第13卷第3期,第3页。
[7]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载《黄冈师专学报》1993年第13卷第3期,第3页。
[8]朱光潜:《〈桥〉》,载《文学杂志》1937年第1期,第3页。
[9]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页。
[10]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0卷第1期,第29页。
[11]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6页。
Title: The In fl 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Creation of Fei Ming's Novel
Author: Shen Shan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Wuh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he basic theory of writing.
In the creation of Fei Ming's novels, landscape natural scenery and human social objects are the two main subjects concerned. Mos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landscap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geographical memory of Huangmei when he was a young child, and also the background of his novels. The uniqu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in fl uence the way of thinking world outlook and the values of Fei Ming.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re fl ected in his novel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to re-interpret Fei Ming's novels, and to explore it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mirror, may be a meaningful attempt.
Fei Ming nove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fl uence
沈闪,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写作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