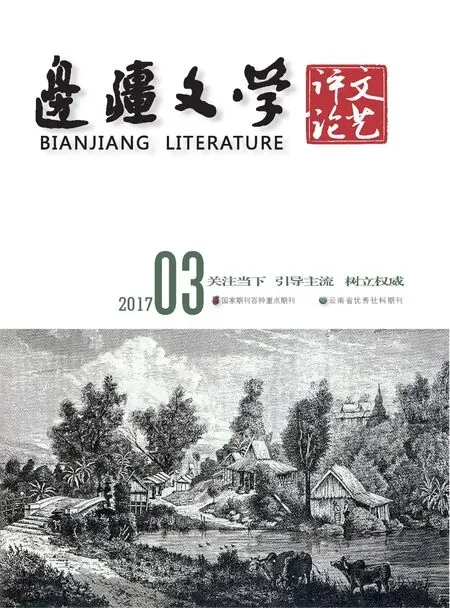人肉的两种吃法
——鲁迅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吃人”意象比较
李 英
经典重读
人肉的两种吃法——鲁迅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吃人”意象比较
李 英
·主持人语·
李英的文章《人肉的两种吃法——鲁迅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吃人”意象比较》,通过对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火车上人吃人纪闻》的比较分析,提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文章认为:“鲁迅先生与马克·吐温就‘吃人’这一主题,达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共识。又因为各自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不同,他们在‘吃人’的未来趋势这一问题上,分道扬镳。”文章观点鲜明,说理性强,分析透彻,是一篇好文章。
《野草》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也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名著。青年学子任瑞卿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围绕《野草》文本从体认与超越两个方面,分析鲁迅的超越虚无之路。论文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对《野草》文本的阐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第一部小说,2003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喜爱,成为美国2005年排名第三的畅销书。刘永松的文章认为:“阿米尔的赎罪的行为其实也就是净化灵魂,不断和人性弱点做斗争的过程,通过斗争,最后达到一种净化灵魂的效果。”文章立论较好,如果第二部分“英雄与虚伪”的分析再厚实一些,整篇论文就更完备、更理想。(李骞)
一
马克·吐温是我最喜爱的美国作家之一,几乎读过他的所有作品,尤其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印象十分深刻。如今重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时,毫无疑问,我真的喜欢。最先吸引我的是其中一篇标题叫《火车上人吃人纪闻》的小说,特别是标题上的“吃人”二字。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跟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有关。众所周知,《狂人日记》是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或者说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据我能查阅到的资料,《狂人日记》受到过俄国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影响,鲁迅先生曾这样说过:“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找不到《狂人日记》与《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之间有任何师承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比较这两个文本却发现,它们竟然惊人地相似。
二
首先是它们的双重叙事。
值得一提的是,“狂人”所写的“日记”固然是《狂人日记》最核心的部分,但“狂人日记”之前的那段文言文的小序在叙事的层面上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才是整个小说的开篇,不容忽视。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这段小序至少告诉我们,《狂人日记》的叙事者并不是“狂人”,而是这个“我”,“狂人”的日记是“我”引用的,“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再来看《火车上人吃人纪闻》的开头:
不久前我去圣路易斯观光。西行途中,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换车后,一位绅士,样子温厚慈祥,年纪大约有四十五岁,也许是五十岁,在一个小站上车,然后在我身边坐下了。我们谈笑风生地山南海北聊了大约一小时……
……
我说我不会打岔,于是他讲述了以下这件离奇的惊险遭遇。他说的时候,一会儿很激动,一会儿很愁郁,但始终带有感情,显得那么一本正经。
不难看出,这段开篇跟《狂人日记》中的文言文小序具有相同的功能。两个文本的第一重叙事主体并不是“狂人”和“绅士”,而是这两个“我”。在《狂人日记》中,“我”直接引用“狂人”写的日记;在《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我直接引用了“绅士”讲的故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前者引用的是文字,后者引用的是语言。小说开好头之后,就进入了正文。《狂人日记》的正文自然是“狂人日记”,《火车上人吃人纪闻》的正文,“我”将它命名为“陌生人讲的故事”。
说到“直接引用”这个词,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两个文本的另一相似之处:“狂人日记”与“陌生人讲的故事”,采用的也都是第一人称,都是通过另一个“我”来讲述的,出现了第二重叙事者。当然,这种叙事手法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很多作家都用过,就连我先生在写小说时也常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属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小说一开头,“我”在收集民间故事时邂逅了正在犁田的福贵,然后听福贵来讲述他们一家的种种遭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但是,这两个发表时间相隔了51年的文本,在拥有了相同的形式之余,又指向同一个主题——吃人,窃以为,不可不察也。
三
在讨论《狂人日记》与《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在内容上的相似处之前,有必要对它们的第二重叙事者进行比较。无独有偶,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狂人日记》中,“狂人”患的“盖‘迫害狂’(应该是被迫害症或受迫害狂——笔者注)之类”;《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绅士”患的是“偏执狂”。不同之处仅在于,《狂人日记》开篇就交待了“狂人”的身份,而《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则将“绅士”的身份之谜放在了小说的结尾处由列车员道出。
现在,我们来对比两个精神病人的讲述,其内容都是“吃人”。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本都没有涉及到“吃人”这件事本身,都没有描写如何将一个人开肠破肚、如何烹饪、如何咀嚼,等等,两个精神病人所讲述的内容,全都发生在“吃人”之前与之后,对“吃人”的细节都绝口不提。
事实上,“吃人”前后的故事远比“吃人”这个动作本身精彩,正是它们提升了小说的审美高度。在《狂人日记》中,“我”对赵贵翁与赵家的狗的种种揣摩与仇视、“我”关于“狼子村”佃户吃恶人的传闻的“研究”、“我”对“郎中”的无声反抗、“我”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对话、“我”对“大哥”的“劝转”,等等,大都是“狂人”的意识流,“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陌生人讲的故事”要完整得多,还交待了吃人的原因——火车被暴风雪所困,二十四位乘客在求救与自救无果后,不得已而为之,为了以示公正,他们召开选举会议,经过提名、投票表决等一系列看似非常正规合法的方式来选举出“哪一位为其余的人提供食粮而牺牲”,而选举委员会又分为两派,两派的意见常常起冲突,最后综合所有选民的利益,以实际票数的多寡为准绳来确定最后人选。
显然,以幽默、讽刺与批判见长的马克·吐温,不可能在文本中单纯地对人性进行拷问。跟《狂人日记》一样,《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也是在针砭时弊,也有明显的抨击对象。两个文本,都写“吃人”,却都不写如何“吃”这个动作,而是将具体的“吃人”升华为抽象的“吃人”。这是它们在内容与主旨上的相似之处。如果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那么,《火车上人吃人纪闻》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让“吃人”合法化,或者说它通过这个荒诞的“吃人”故事,表达出对美国两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合理性的怀疑。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两位作家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度里,但二者的批判精神是相同的。
从具体的“吃人”,到抽象的“吃人”,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飞跃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文本再一次不谋而合。鲁迅先生与马克·吐温,他们都找到了隐喻。这些种隐喻的符号,在两个文本中都很明显。比如《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尤其是“赵”,鲁迅先生似乎特别钟爱这一符号,在《阿Q正传》就有赵庄、赵太爷,赵太爷骂阿Q时说:“你也配姓赵?”《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这种符号的数量虽然少一些,但也足够醒目,如:选举会议以及会议中的两个派别。
四
当然,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同样是“吃人”,但两个文本中吃人者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在《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人“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而在《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吃人者要坦然得多,他们甚至还可以在事后对比不同人的肉在味道上的差别:“我可以说一句,再没谁比哈里斯更配我的胃口,再没谁比他更使我感到满意了。梅克西很好,虽然香料放得太浓了些;但是讲到营养丰富,肌理细腻,我还是更喜欢哈里斯。梅克西……他太老了!”
此外,《狂人日记》与《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与一个不同之处,都体现在对主人公的处理上。
先说相似点。两个文本都有大量的留白,供读者去思索,就连留白的手法都很相似——均是跳入文本中的叙事者所为,原因或主观或客观。在《狂人日记》中,开篇的文言文小序已经说得很清楚,“狂人”留下的日记共有两本,而“我”只“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那么,“狂人”从犯病到“赴某地候补”,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心理转变?我们不得而知。在《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由于火车到站,“绅士”下车,不得不提前结束讲述,“要不是刚才已经到了站,非下车不可,这会儿他会把那一群人都吃得一个不留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剩下的人是如何被吃的呢?尤其是在只剩下主席、秘书、提名委员会成员与膳食主管的时候,他们都是权力的拥有者,该如何选举出“为其余的人提供食粮而牺牲”的人呢?我们同样不得而知。
事实上,不同点与相似点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为了主人公兼第二重叙事者这个人物的命运服务的。之前说过,《狂人日记》在开篇就交待了“狂人”的身份,而在《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中“绅士”“曾经是国会会员”则在结尾时才道明;《狂人日记》一开篇就说明了“狂人”有病,而《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则在倒数第二自然段才说“绅士”“变成偏执狂”。最应该注意的,也正是此处要说的不同之处,“狂人”病好之后,被他深恶痛绝的封建礼教招安,抑或他自己主动拥抱封建礼教,“赴某地候补”;而“绅士”原本是国会会员,犯病后不再是了。这两人不同的结局,似乎可以反映出鲁迅先生和马克·吐温在创作时的内心世界。鲁迅先生对他抨击的那种社会制度充满了绝望,就连“狂人”这样的清醒人士也因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加入了他们;马克·吐温则对他所讽刺的社会制度抱有希望,吃人者或臆想吃人者终将从国会除名。据我所知,马克·吐温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再乐观,那是1876年至1884年之间的事,1884年,他出版了他的重要名著《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这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的重要转折点,而鲁迅先生对封建制度的绝望,则是在他父亲去世时就已经有了萌芽,从不相信中医开始。
五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发表于1867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相差51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之间有某种师承关系,我们也无法知道鲁迅先生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是否参照、借鉴过《火车上人吃人纪闻》。而它们却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上文中提到的不同之处,其实都是用于烘托它们的相似之处。因此,我只能说,鲁迅先生与马克·吐温就“吃人”这一主题,达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共识。又因为各自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不同,他们在“吃人”的未来趋势这一问题上,分道扬镳。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更愿意接受《火车上人吃人纪闻》,不仅因为它没有设置太多阅读障碍,读起来相对轻松,还因为它让人看到了希望;而《狂人日记》太过沉重,每次阅读,都给人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负重前行之感。
【注释】
[1] 见《〈呐喊〉自序》
[2]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3] 马克·吐温:《火车上人吃人纪闻》,见《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4] 参见《阿Q正传》
[5] 参见张友松:《〈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序》,[美]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6] 参见鲁迅:《父亲的病》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