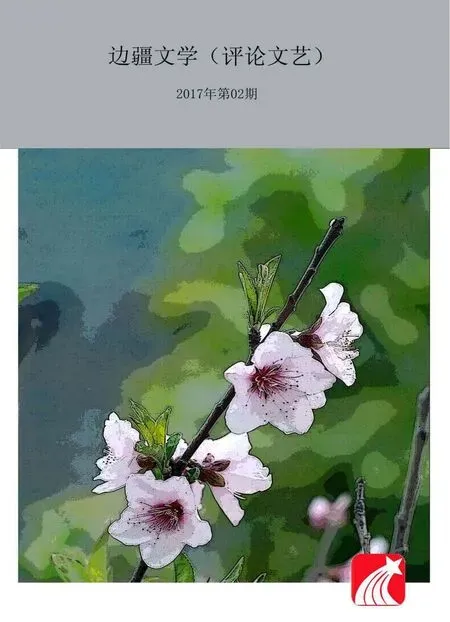论黄代本小说地域性四重存在水乳交融的特色
夏 玲 曾子芙
论黄代本小说地域性四重存在水乳交融的特色
夏 玲 曾子芙
黄代本作为一直坚守在昭通本土的作家,其小说的昭通地域性特色十分鲜明,是很有个性的地域文化小说。他的系列小说围着泥鳅河畔的莲花村写作,他多层次地深入书写了昭通的地貌、人情、风俗、历史、宗教和文化的独特性,塑造了一系列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黄代本作为一名小说家,虽然“在溢满云南,乃至全国的昭通作家群中,黄代本并不像……一样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熟知”。但他的作品在昭通本地人中却有为数众多的读者。
并不是昭通籍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就是昭通地域文化小说,“地域文化小说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性的区划来归纳小说和小说家,也不是单纯以小说的文化类别和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而是通过这个杂学学科派生出一种新的小说内涵特征,地域文化小说要具备地域、种群、小说三个要素,而且还包涵各种各样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的……文化的内涵。”,我们说黄代本的小说是地域文化小说,正是因为他的小说从地域存在的若干方面,反映了昭通地域特殊的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的内涵。
一、地域客观物质存在的细节真实表达
黄代本的小说是非常有个性化的文字,他的小说整体虚构,而细节处处真实可靠。他的写作是在写作空间上有中心有边界的写作,围着他心目中的故土写作,虚构了泥鳅河畔的莲花村,但是这个村庄的自然存在物,如这个地方的地理地貌特征,村子前的风水树、龙尾的麻柳湾、龙头的卧佛山、五尺道、断山筋的垭口、被烟枪打死的耗子等,都是他具体观察过的自然存在物,他写的乌蒙山区有地理地貌上的真实性,我们从黄代本的作品中可以读到乌蒙山的大山大水带给人视觉上的震撼,更多的我们还可以读到这种封闭而艰难的自然环境的神秘莫测之外,给人的生存带来的苦难。黄代本笔下真实的地理存在,来源于他对这些地理存在的走遍乌蒙式的反复野外考察,他笔下的山川大地,是人物真实的生活环境,是人物肉体生活所在的具体的地理环境。
黄代本笔下的人类创造出来的存在物,莲花村的一所房子、一个农具、一个石磨、漏雨的瓦房、门背后的火塘、雨后很滑的山路、苞谷糊糊上长出的人工菌等莲花村的物质存在细节,在他笔下,每一点一滴都是真实的。他笔下半岩上的村庄、何天麻和何半夏两兄弟住的院子是乾隆三年修的、两岔河村的诸葛石、阴沉木棺木、雁鹅派出所、葫芦口夜总会、古螳螂山、挑水巷等等,都是蕴含昭通历史痕迹的真实而特殊的物质存在。
我们再来看,他笔下一身汗臭穿毡褂戴毡帽的老者是用黄铜烟枪抽大耆老的叶子烟,富的村民则是抽花腰杆的龙泉烟和绥江雪茄,村民的一餐是“煮了一锅洋芋,烧了一把青辣子,煮了一锅酸菜红豆汤”,而送人的则是天麻、打屁虫、红富士苹果。“他家祖上在大清年间是出过镇守使的,留下了一顶红顶子,何十五一直很珍视这红顶子,当作传家宝一样收藏。”当然,仅仅对这些昭通特色的物产存在进行展示也是没有意义的,黄代本的小说中,这些物产给人带来的地域性情感非常厚重。我们来看:“吴常兰说,要得,我活了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进过城,哪天也进城看看去,听说城里月中桂糕点厂有种东西,名字我叫不出来,我也是前个月回平滩子听郭彬家妈说的,是糯米做的,放到嘴里就化了。”还有:“何中贵的父亲感慨地说,为了供你读书,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喝过酒了,你哪天回来的时候,整一斤盘河的燕麦散酒来给我喝。”“老汤圆背着昭通的荞粑粑上访”,月中桂的绿豆糕和燕麦散酒作为人物向往的一种物质存在,读来让人心酸,而荞粑粑作为上访道具,帮助了人物的形象塑造。这些叙述常常有剔骨爆伤,深入事物本质的地方,读之让人陡然惊起,如冷水浇背,但是又有慈悲心怀。
他对这些物质性的存在的感受,在小说中的描写也具有体验上的真实性,如“一个人睡在山上,就觉得十分的静,静得连自己心脏的跳动都像在打雷,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声音都像泥鳅河涨水了一样。”如“从农村出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农村觉得是干净的衣服,穿着进城的时候,走到半路就觉得不太干净了,到了城里,就觉得直接是脏衣服了。”“到了乡政府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路时觉得脚是脚手是手的,就像电影上的机器人。”他小说中类似细节描写,保证了他的小说人物所见所闻所嗅所感的细节真实性,而这些细腻的感受和经验,是小说打开读者经验世界的重要元素。
他笔下的物质存在再现了昭通的风土人情和历史遗迹,有浓重的地域性及现场感,这些表现昭通地方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的物质存在,还带着神秘的传说,给现在生存其间的人心理上带来影响,如黄家天井“在廊檐之下,有八根圆木支撑的互相连通的供黄氏弟子读书的书楼”。昭通的耕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住在其中的年轻人。再如“树下有一个大石头,村子里的人称为诸葛石,村子里的人说的是诸葛亮火烧藤甲兵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当时的彝族兵马全部被烧了滚到两岔河里,诸葛亮坐在这块石头上泪流满面感叹说自己要折寿,果然五十四岁死在了五丈原。诸葛亮在死后,经常回到这儿,下蒙凇雨的时候就出来夜游,老百姓说诸葛亮由于后悔伤生太多,成了这儿的夜游神。”昭通民间文化因素被很好地吸收在小说中,成为小说的趣味神秘的细节。
小说反映了昭通地域的客观物质存在,也反映了人们在这个地理空间中的生存困境,写出了底层人物物质上的贫乏和生命的不舒展,写出了人物对自然和环境的细密感受,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呼啸、呐喊、挣扎和雷霆。
二、地域历史文化存在的厚重深入表达
黄代本小说中激情和理性都十分充足,这种充足来源于他对地域性历史文化存在的充分了解和反省,他小说的灵性来自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他对昭通地域历史文化有认真的野外和案头的调研,也能用当代性眼光重新审视自己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以本地经验和宽广的文化视角来关注和表现地域性历史文化,很好地表现了昭通文化的多元混杂性。
他的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文化信息,涉及到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诸方面”。他的小说是一幅幅有醇厚泥土味的农村生活风俗画,他笔下的地方风物的细节采集于现场,对地方性的风水、算命、宗教、丧葬、婚姻等习俗的描写精彩,如婚俗就写了“网兜亲”“挂角亲”“顺水流”“水倒流”“倒插门”等,对花脸婆娘收魂,巫师登坛耍马等风俗进行场景再现,对昭通的集市文化、大清朝封建文化的残余、农耕经济也有许多饶有情趣描写。这些风俗描写后面是人物的精神世界,如老汤圆要过生日时说:“将城里有点身份的亲戚请几个来坐坐,也给村里面的人看看我老李家在张张船上都有蒿杆,做事说话就会少一些阻力。”又如:“老者在走的时候,是倒退着出门的。出了门,在下院坎的时候,老者还作了两个揖。”地方风俗文化成为了人物的生存之根、命运之根、文化之根和心灵之根生长的土壤。他笔下的人物共同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域,血缘关系链条对人捆绑很紧,人际关系密集,而地域上的封闭和物质资源的紧缺,让人际关系更加复杂,人物对权势的崇拜和向往特别强烈。
他的几个代表作,都深入到了地方文化风俗,如《鱼在枝头鸟在浪》从陈代理找大地寻龙点穴说起,围绕着老汤圆在风水宝地上盖房展开,众多的人物在紧张的对峙中出场,对乡间风水迷信、民间信仰和现代社会的法律公正的矛盾,进行了深入描写。而老汤圆过生日时吹拉弹唱将半个村子搞得笙歌满地,扭着秧歌唱《十二杯酒》等细节描写,也保证了小说场景的活灵活现。而“有一首山歌唱的是,山高不过卧佛山,水深不过白龙滩。龙滩边有一棵古树,龙滩的水草中有游鱼,古树上有鸟儿,古树倒映在龙滩里,就给人一种鱼在枝头鸟在浪的感觉。”则是对昭通地方文化趣味的表达。因为迷信,老汤圆要在风水地修房子,也因为迷信,村里面的人将白龙滩水的变浑归结为老汤圆修房子,就没有人想过会不会是白龙滩反背龙洞河沟夏二娃的开山炸石,而老汤圆修房子和白龙滩的水变浑没有因果联系的真实性,也让故事的荒诞性引发读者的思考。
黄代本笔下的人物往往有复杂的主观性文化存在,人们的精神气质有地方色彩,他通过人物的宗教信仰、迷信、讲究风水等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主观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是精神上不自由的人,他们想象的世界和向往的世界常不真实,但是,他们又在用自己的已经打上了虚幻烙印的主观世界打量自己、周围、他人、自然、人性。另一方面,他在对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理深层结构的影响进行探究时,不动声色地对民间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批判。《入土为安》的刘毡帽,生前子女甚至不能保证他的温饱,最后以八十高龄自杀死了,默默向世人诉说着不尽哀怨和无奈,但最悲哀的是,他死了也还是不能被世人理解,因为他的丧葬还很风光,村里人认为“刘毡帽这辈子值得了”。
他笔下对昭通丰富的地域性文化的挖掘,让他的文本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他笔下的人物有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多维度地方性特色。他观察体会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他自己的存在之地和生存发展之地,这个具体地方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地方的标本,解剖这一个标本,可能会有更大空间上的普遍性意义,如果形成一定的气象,也许就会有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如莫言的高密乡一样。
从历史文化的厚重表达来看,黄代本的作品是有一定的宗教、哲学、社会、道德的综合意义的,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文学意义的多重性,我们应该把文学的意义同政治的意义区分开,更不能把政治意义强加给文学,但政治意义以外,文学的意义和哲学、社会学、风俗学、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意义有许多重叠难分的地方,文学和这些学科的最重大的意义区别是文学通过丰富多样的个性化的人生、人性、人格的描摹来实现他的多重意义。
在他的小说中,陈代理带着问卦、预言、宿命等日常细节,来到作品中,给小说的审美价值多了一重神秘文化的空间,对神秘文化的现场体验,是黄代本这部分写作的基础,他对民间文化中迷信层面和宗教层面的影响有许多了解,对他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神秘文化显在或隐形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他们受这个神秘世界的左右也在这个世界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黄代本一再在小说中表现逝去的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如小说中的神迹、传说、符号等文化传统的表达,给作品增加了文化厚度和神秘的审美感,而“一般用于神秘主义的话,也适用于美学”。比如《空心的大树》《蒙凇雨》《找水》等小说,就有一种东方的魔幻现实与轮回观念的双重神秘氛围,黄代本小说中宗教感渗透着冷静清凉的诗意,在神秘氛围中表达苍茫博大的人文情怀,常常从命理命相角度,表现一种观察生命和人性的独特视角,表达人物的人生观,他自己人生哲学也常在小说中通过人物表达出来,在文本中灌注的一种大气、禅意、自然、厚重,同小说中的神秘的氛围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三、地域主观精神存在的超现实主义表达
黄代本小说中的人物有精神世界的立体性,人物的感受、观察和想象的表达齐头并进,深层次表达人物,给他的人物增加了一种超现实的现实主义特点。
他描写的莲花村卑微的底层民众挣扎生存的小说,总体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些人物的生存环境是原生态的,黄代本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富有特色的好玩得富有哲学味道的名字,如陈代理、阳桃子、背阴李、金白龙、老汤圆、剐狗匠、桃花、金雀花、何天麻等等,这些人物有漫画特点,且都是有移花接木的客观存在原型的。比如在黄代本的多数小说中,陈代理常常作为一个经常串场出现的人物,在真实生活中,陈代理是黄代本随时可以请来和我们聊天的朋友,他说的话他的神秘的预言和算命推事的技能和小说中一模一样,读者不信,那天我也可以约他来和你聊一聊的。
他在小说中将真事隐去,让假语存在,是一种写作策略。同时,黄代本小说中这种像“陈代理”这样的真实人物经常出现的半隐半现手法,对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的表现有一种特殊陪衬作用,小说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更为本质地表现内在真实,而他用真实人物来串连虚构人物,是为了剥开现实罩在人物和事件上的重重迷雾。除了陈代理外,黄代本小说中真人真事真名随处可见,如在《用神》中:“何中贵在学校里是凉风台文学社的负责人,他的班主任夏玲在学生科当副科长,见兰花商场来要文字功夫好的,就推荐了何中贵。”这是我的一次出场,我的名字和身份都是真实的,这种小说细节、人物、环境、物象的虚中有实,让读者形成独特的阅读感受。
在黄代本的小说中,底层人物在从事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时,却有一种宗教追求在其中,这些活动是底层人民抵挡险恶的自然环境和不幸命运的一种缓解药剂,他在处理这些人物时,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感,很好地表现了民间文化的神秘神奇的魅力,因“对于民间的一些信仰和宗教活动,如果我们轻率地将一些神奇的东西都认定是迷信,是否过于残忍和武断了”。他常常通过一些风俗民情的描述,表现了人在精神产物和宗教仪式面前的批判、选择、信奉、褒贬,呈现昭通人精神现实的客观性,也让小说中呈现哲学色彩和宗教情怀,通过人物追问人生意义。
他的小说是虚构的,但人物的生命轨迹却不是编造出来的,事件和细节都是在生活中错位发生过的,是作者成长过程中见到或遇到的。如《太阳出来瓦上霜》中的金白龙这个人物就有他自叙传的特色,这个人物很有郁达夫小说笔下人物的自我观察自我表达的特点,那是许多学生进入社会初期都会有的共同的经历,他把那段岁月自然呈现了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不过是把刚刚踏入社会时,别人如何整我,我感受如何,怎样行动写了下来。白金龙走入社会的迷茫、困窘、痛苦,对现实的失望感挫折感,和环境的不融洽等等,也是曾经属于大家。他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经验,从感觉层面,从自己所见所闻层面,写出人的感情的动作性外现,用文学去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黄代本笔下的富贵、荷花、丁心兰、秋生等互相关联的人物个性是丰满的,也是复杂立体的,这些人没有全好的人,也没有全坏的人,都是些为了生存为了发展,被命运推动,被欲望推动,而产生了或者荒诞或者悲惨故事的人,他们的分裂的生命多厄的命运和时代的喧嚣混乱有关,也和自身灵魂的善与恶的斗争有关。有的人物在社会中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和道德困境,有关背阴李的系列小说,表现了年轻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撕裂感,小说叙述中反讽语气下悲凉弥漫。《沼泽》中二秋梦想着女儿通过读书成为像金白龙一样的人,为了筹集女儿上大学的学费,他不惜借高利贷,导致倾家荡产,但是女儿中专毕业后回到了乡村,在女儿的婚事上,二秋也努力抗争,可女儿最终还是嫁给了他当初极力反对苹果状元刘大河,女儿未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是从最初的起点开始经过一番挣扎艰辛最终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上,现实违背了人的理想,陷入了一个不能摆脱命运的怪圈,陷入一个越陷越深的沼泽。《丁心兰脱贫》叙述丁心兰靠生了五个孩子而一步步盖起大瓦房,一步步脱贫。《荷花荷花》叙述供养不起孩子上学的家庭,在坏人的诱惑威逼下,成了繁华大都市那些罪恶的灵魂的性工具。
黄代本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姿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贴紧了人物进行写作”,而且是贴紧了人物的自然生活空间来写,但是却又深入到了人物的精神空间。在文学作品中一定要有人的精神轨迹,要有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要有形而上的探索,人不能在空间中孤立,也不能在时间中孤立,但是,我们现实的空间时间常常让人的灵魂难以居留,而神圣的东西最常让人体会虚无,面对生命中的黑暗面,需要提起勇气,从虚无中超脱,完成人生升华。
他贴着人物写作,他在展示人物的无能、卑微、寒碜、无聊和阴暗中,文字充满了悲悯色彩,人物被隐秘痛感左右,人物的文化处境艰难,人物有精神传统的复杂性,让人物产生生命力坚韧而强大的效果,源于他和小说中无奈挣扎的人物共悲欢。小说中人物的心理体验,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发自内心的生命感悟,对人物命运的深层次关注,让他能够借助文字抵达人物心灵的根部,
他的写作是朴素的,是平易近人的生存状态,是真实生活中人的悲欢离合本真呈现。他的地域性写作,让人物的生命时间和地理交融,更加深入具体细致的切入人性和生命的各个切面。从一种意义上说,他的小说也是他自己的一部隐秘的成长史,他用自己的心灵经历过作品中人物成长的痛楚、屈辱和伤害,他是疼痛着一颗心,写自己的人物,他对人物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和人物心理行为有非常准确的或者黑或者灰或者带点彩色的把握。
四、地域性语言存在的富有韵味的表达
黄代本小说中对方言给予了过滤性的积极的创造性的使用,小说语言表现出方言和雅语结合的特点。黄代本的古文功底和方言功底都非常厚实,让方言和古雅的文言同时出现在小说文本中,语言风格在雅俗之间游刃有余交替使用,让小说中的雅人说雅语,让小说中的俗人话方言,保证了他写作语言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昭通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存在,一种现实中群众还在使用的语言,在黄代本的小说中,体现出来是民间语言的丰富和博大。他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大量地使用鲜活的真实的昭通人的家常话,我们读他的小说,感受到昭通民间语言的诙谐幽默中特有的粗犷机智,昭通民间语言中自然存在的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动作性强,读来亲切有趣,如形容人“灰嘴灰脸”“贼眉鼠眼”“虾腰虾胯”“鸡胸雀腹”“一脸猪相,心里明亮”,说人英俊是“特别是鼻子长得好,就像一座坟一样,不像是坏人”。说一个人高傲是“一块死人脸,面无表情,脑壳抬多高,就像大山包的雁鹅一样,很不好接近”。
他小说中的民间语言,有三川半的特殊风味,有云横雾锁的连绵乌蒙山的味道,有酸甜苦辣打翻了五味瓶的人间烟火味道,如“喜鹊老鸦含来么,还要张张嘴嘛,怎么尽想吃清净食。”“说到粑粑要面来做,要不然就是空口讲空话了。”“这个人成了火塘边的药渣了。”“恨不得将这人烧成灰来点荞子”“心急吃不得热稀饭,他巴不得一耳巴打进嘴里去。”读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可以充分的体会到昭通民间语言在宣泄、自嘲、幽默等上的出色表现力。
他的小说人物也常常享有语言上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感,有时甚至上升为语言的暴力和语言的困境,如爆粗口、说脏话,不多举例,这种语言也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更为鲜活、肉感、生动,表现出一种野性野蛮野趣,这些方言是底层人内心幽暗的真实表达,而黄代本通过这些民众语言,对其生存状态进行独特的描写。
“反正喊死了,不要你负责,见人家在抬东西,就过去搭个手,特别是要笑,好笑不好笑的都要笑,将脸笑成一朵菊花,像弥勒佛一样。”“有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他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常常让人读之忍俊不禁,“靠兄弟如纸上谈兵,靠父母如画饼充饥。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何中顺伸手就拿到的东西,何中贵跳起来都还够不着。”“当官就像萤火虫爬尿罐,爬上去么就高高在上,爬不上去落下来落在尿罐里么就又脏又臭。”“半夜起来做法事,不要装心头不明白,说得脱,走得脱,说不脱,就拌着脚。”“单位是一棵爬满了猴子的大树,从高处往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脸,从低处向上看,看到的就全是屁股。”类似的机趣幽默的假语村言,在他作品中比比捡拾,表现出民间人物的幽默达观,民间存在的一种朴实的人生智慧。这些语言的使用,更能揭示事态,用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吸引住读者,是小说的一个基本功夫,也更为切近生活。
而这样的语言“一颗草有一滴露水,大树脚的酸杨梅没有一点阳光,时令到了,他都有红起来的时候。”“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河里来的江里去,江里来的水里去。”“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好还是不好,一直要看到老。”读来还很有诗意,“语言、生命、诗本是三位一体的东西,真正的语言是诗的语言,真正的诗性是人的本性。”民间语言的丰富后面是生活的丰富,这些民间语言的诗意后记是生命的感悟,同时,民间语言后面,有丰富的地方文化印迹。
黄代本小说中的方言使用地道,而且不影响阅读。《山花》在最后定稿时,将黄代本小说中自己删除了的方言一一恢复,说明他小说中的昭通方言,是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的。我阅读黄代本作品,是没有阅读难度的,而且经常因为感受到昭通方言的幽默生动,而得到阅读的快感。但是,我有时还是遇到了问题,比如在《用神》中何中顺美丽的妻子叫杨潴留,按照我的推测:这个人物的名字一定有一定隐喻性,但是,我不知道“潴留”这个名字的意思,又是如何和女主人公的美丽联系起来?后来我问黄老师,他告诉我:潴留是一种非常机灵的小动物,类似松鼠,十分可爱。这就印证了我的推测,我想,以后这样的地域性方言词汇,如果估计普通读者有理解困难,可以加个注释,这样就可以解决外省读者的阅读问题,有利于作品在省外刊物的发表。
【注释】
[1]周明全.西部文字西部之魂.太阳出来瓦上霜[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p249.
[2]丁帆.二十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J]学术月刊.1997年9期.p97.
[3]吕崇龄.散文集《我的河山》的地方文化特色[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12月.p44-49.
[4]乔治桑塔耶那.美感[M]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p75.
[5]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N].2004年3月12日.
[6]鲁枢元.超越语言[M].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 p88.
(夏玲系昭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曾子芙系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责任编辑:万吉星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文学的地域性”阶段性成果。(2014Y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