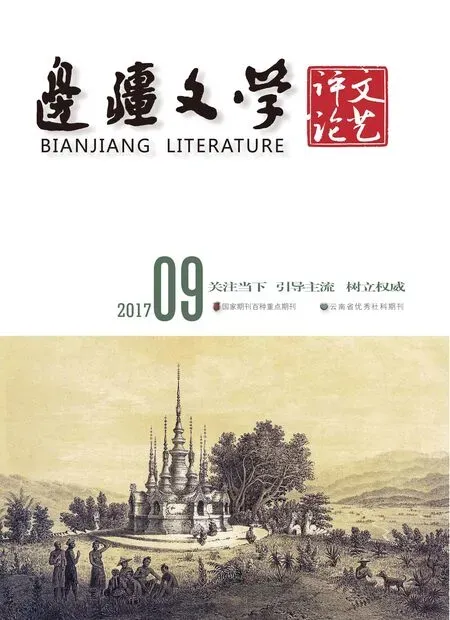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
纳张元
边疆阅读
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
纳张元
左中美依托坚实的云南红土地,步向生命的纵深,用敏锐的女性感知、温厚的母性情怀和诗意的灵动笔墨,追求表里如一的美丽,歌吟云起云落的从容,展现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与过程,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的人文情怀,她的文字宛若漾濞的核桃,散发着亲情的香气,浸润着温馨的民间感情。
早年间,读她的第一部散文集《不见秋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部书写家园、心灵和生活五味的书,左中美在书中洞察社会,解读历史;她超越民族性与地域性,感悟人生,审视文化。其后,她又陆续出版了《时光素笺》和《拐角,遇见》两部散文集,技巧愈加娴熟,行文得心应手,但眼界明显窄了,胸襟也小了,自我陶醉的孤芳自赏多了一些。这次读到她的《安宁大地》书稿,让我眼前一亮:她又重新开始关注大地,凝视乡土。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说,乡土性贯穿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于是,包含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文化底蕴的乡土世界成为“家”、“母亲”的象征,在二十世纪的工业文明的凯歌高扬里构成文人们的心灵支撑与价值依托,沈从文的边城白塔、萧红的呼兰小城、汪曾祺的荸荠庵、孙犁的白洋淀、刘亮程的遥远的村庄,无不忠实反映着中国文化的乡土韵致,乡土田园牧歌世界成为现代中国追寻理想的载体,一如海子诗歌中对昔日故乡的热烈追忆:
和平与情欲的村庄母亲昙花一现
村庄母亲美丽绝伦
五月的麦地上 天鹅的村庄
沉默孤独的村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这就是普希金和我 诞生的地方
理解中国文化的乡土特性,也就理解了《安宁大地》作者为什么魂牵梦绕于自己的故乡,她在书中用纷繁的文字保留了弥足珍贵的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这些乡土记忆,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像人类断片化的记忆形态本身,碎片化、零散化,建构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生态文学世界,充溢着边地乡村的安宁寂静。乡村、房舍、田野、花朵、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匠人、竹林里的手艺、屋角院落里的草叶露珠、蜿蜒流淌的溪流、勤劳的农人、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还原出原生态质朴淳厚的乡野气息,一个令现代社会他者感到真实而亲切的乡土,如作者所说:
“我知道,这块大地是永远不会丢弃的,只要家还在村庄里的一天,一家人,就会一代一代地把它守下去。挂掉电话,我在心里想起这块大地旧时的样子,包谷在雨水里哗哗生长,在不断前来的时光里,深情地迎风歌唱。”
流泻在作者笔下的,是一章章零散又真挚的乡土记忆。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各种大地的馈赠,“这大地上生长的许多东西,最终,都要回到朴素的神灵那里。木耳是其中的一种。”田野的植物被人们用精巧的手艺变成一件件实用的生活用品,“我在村庄出生,长大,看着人们一年一年砍下竹子,制成各种各样的器具,可是,当我回忆起来,竟忆不起村庄的哪篷竹子开过那样一串一串褐色的状若叶蕾的竹花。村庄的那些竹子都还翠绿着。家旁箐里有一篷龙竹,风大时常常吱嗄鸣响。只是,不管夜里再刮多大的风,我已经确信那竹子其实不会倒下。天亮出门,村庄一切安好。”乡野大地以地母的温厚胸怀收纳各种生命,成为每一种生命尽情展示活力的舞台,“萤火虫,这夏夜里的精灵,我曾在白天时细看过它,那是一只在夜晚被捉到的萤火虫,它的样子实在是其貌不扬,全身呈浅浅的土灰色,一对椭圆形的短翅下面,坠着一个鼓鼓的肚腹,这肚腹的后半部分,据说便是它夜晚发光的所在。而造物的圣意是这样的巧妙,就是这样一只只看上去灰扑扑的小虫子,到了夜晚却是光华闪耀,为村庄和大地点亮万盏闪亮的萤光,与夜空中漫天清澈的星光遥相呼应。”作者用原初的目光呈现日常世界,以“乡人”的自觉与自豪保留乡村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如同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评论:“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下来了,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安宁大地》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为本土地域文化留下了生动立体的剪影,这是作者的灵气之所在、作者创作源泉之所系,也是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得以被流传的福气。
丁帆说:“前现代式的农耕文明社会文化结构仍然存活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虽然刀耕火种式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不复存在,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仍旧在延续着。”云南也是中国西部的一部分,较为缓慢的发展速度,令农耕文化得以更完好的存留。《安宁大地》中尤为珍贵的是对乡土日常生活中民俗仪式充满诗意的细节描写。比如,“上梁的吉时一般在正午未时至申时之间(下午三时左右)。那根最后的正梁(又称“喜梁”)架在院子正中的一对木马上,正中部以一块画了八卦图的正方形红布以棱形包上,且中间包以一个包有五谷和硬币的祝愿富贵吉祥的“梁包”,两头拴上长绳。主人家备好一只大公鸡,一提篮拌有硬币、五谷和各种糖果的饵块粑粑,一桶水。饵块粑粑当中,有两只大的饵块筒子,其中一只里面包了硬币。”作者还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上梁时候的种种吉语歌谣:“金丝梁、金丝梁,你在山中做树王,主人取得黄道日,把你取回做中梁。”“祭梁头,文登科,武封侯!”“祭梁中,代代儿郎坐朝中!”“祭梁尾,金玉满堂多富贵!”风俗与节庆是乡土生活的重要部分,是民间恒常的生活习惯,也最能表现民间的价值观念。作者把记忆中的生活细节还原到细致入微的地步,通过作者对乡土手工艺和风俗仪式的不厌其烦的描绘,令人充分感受原生态乡土生活与丰厚的乡土经验。乡土生活的深层意义就在风俗、传说、宗教仪式中,它们维系着乡土世界的恒常感以及与过去时代的连续感,原生化的乡土经验与乡土叙述是中国记忆中弥足珍贵的内容,
现代性生存与农耕文明混杂共生的时代,全球化与边地文化交叉互渗的转折点,作家们往往用乡土书写来抵御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对他们仍有价值的东西做代价。早在19世纪,德国古典浪漫诗歌先驱荷尔德林在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的末途,依然以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
人就会仰天而问:
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
是的。
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
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
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
但还诗意的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这首名为《人,诗意地栖居》的诗经过海德格尔阐发演绎成为几乎所有人共同向往的哲学命题,也成为中西哲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不倦思索与美好理想。对“诗意栖居”的追求是工业时代以来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追求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也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生存价值信念进行的解构与重建。
人与土地是生死相依的共同体,土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也是滋养精神的母地,作者对古老乡土的情愫与自己心灵的脉动遥相呼应,用生命与土地融为一体的热爱来歌咏着故乡。因此,在安宁大地上的人们,在生养自己的大地上,获得心灵的踏实,养育单纯而质朴的生命追求,建构起天性的惬意,这是工业社会背景里的一种奢望,因为奢侈,这种诗意的记忆更显温暖。作者拥抱当下的生活的温热,却不拘囿于生存的狭促,而是与生存境遇拉开距离,进行审美关照,扩展穿越时空的纵深视野,确立个人主体地位,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沧桑中,守护原始生命的质朴,在现代文明的建构中,纳入传统边地民族精神的伦理,建构现代人价值共同体和民族精神的重振,保持诗意与时代性结合的完整。诗意让栖居更美好,人如果没有了诗意,大地就不再是家园;精神就会变得平庸,不再有幸福。
弗洛姆认为:“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断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所以文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为人类提供情感慰藉,提升人性,塑造理想的人类生活。人类的理想应该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人的商品化实现程度,因此人类需要在理想的精神家园中得到情感抚慰和智性反思。《安宁大地》尝试着承担了这一文学使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学普遍泛化的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诗意的乡土与灵魂的憩园,无论社会怎样地发展,文明怎样地进步,寻找精神家园才是人类最终的永恒的需要。
责任编辑:杨 林
(作者系大理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