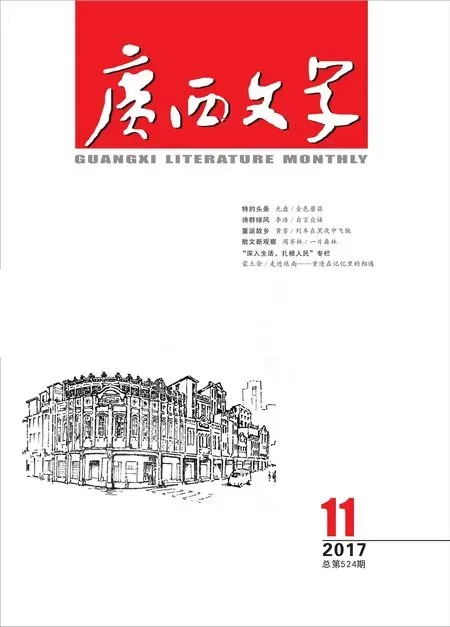散文新观察之周齐林篇
刘 军/著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白话文学初期形成一股否定“父权”的潮流,“父亲”形象作为腐朽、专制的封建性符号遭遇了批判性的审视,逐渐从儒家人伦秩序设定的神坛上落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文学新思潮兴起之际,对“父亲”形象的解构从制度、人伦层面转向了人性层面,更加暗黑的涂抹方式渐次发生。方方中篇小说《风景》中的父亲是一个浸泡于码头文化中的恶棍形象,《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的刀锋更加锋利,作为一个父亲,孙广才本质上就是一个蛮横残暴的流氓无赖。他虐待父亲,迫害儿子,侮辱儿媳。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作为父亲本应承担的责任,父亲的形象、尊严、权威在此轰然倒塌。当孙光平愤怒地拿刀追赶父亲时,一个忍无可忍的儿子,最终走向了弑父的道路,传统的父权神话在此也被彻底颠覆。除了方方、余华之外,苏童、朱文的小说中,皆有弑父主题的集中处理。尽管在后来,相关“父亲”形象的建构各自有所回归,但观念的洗礼业已发生,作为神权符号的父亲形象无疑遭受剥落,回到人本的立场上来。作为比照,散文中的父亲、母亲形象几乎岿然不动。作为亲情的维系与情感投射的镜像载体,父爱与母爱的主题尽管在处理上由一味地抒情走向了丰富和驳杂,但是,“爱”的情感主题则恒定如初。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写作,母爱因其如一性和单向性,如同宽厚的大地,如同平静的川流,在处理上往往没有父爱的主题出彩,毕竟,父子之间更像是落差极大的山河,其中有飞溅,有对抗,还有特定阶段发生的和解。一句话来总结,在现实关系上父子之间要比母子之间多出更多的戏剧性要素。也因此,散文中的父亲形象更容易趋于厚度、深度与宽度。汪曾祺的《父子多年成兄弟》,北岛的《父亲》,贾平凹的《酒》,玄武的《父子多年》,庞余亮的《半个父亲在痛》,李颖的《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皆是书写父亲的佳作。
周齐林的《一片森林》延续了父亲形象的惯性处理方式,这里出现的父亲是隐忍的、沉默的,也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他的身上有两大特性,一方面,父亲作为农耕时代乡土中国最后一抹微红而存在,其生活历程与精神特性具备了某种象征性。就个体而言,作品中的父亲与其说是一种本我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位置和角色,是经过长期人伦规训下群体意识的符号载体。父亲始终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而非现代性所强调的自我指向。面对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剧变,父亲身后崛起的新一代人,城市化、城镇化成为必然的潮流,无论农民的身份是否得以改变,自我意识的突出以及实利主义的价值准则,必将取代人伦准则至上的信条,也将取代群体意识下的自我牺牲精神。因此,最后一抹晚霞的定义并非夸张之言。这篇散文在塑造父亲形象之际,也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展开,比如一以贯之的诚实守信准则,对待乡邻,对待父亲与母亲,对待儿女,父亲皆是表里如一,恪守伦理要求,不越雷池,也不退后一步。另一方面,尽管有多年的外地打工经历,但父亲始终如同河南作家李佩甫笔下的人物,是一株顶着泥土在城市行走的植物,在遭遇了意外受伤、暴力胁迫、身份歧视之后,总是一个人悄悄地吸纳、融化诸种伤害,回到朴素、老实本分的人生本色上来。在父亲这里,苦与痛如同被咽进肠胃的食物,就是活着本身。因此,忍耐就构成了植物的某种根性,也构成了父亲形象的基本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