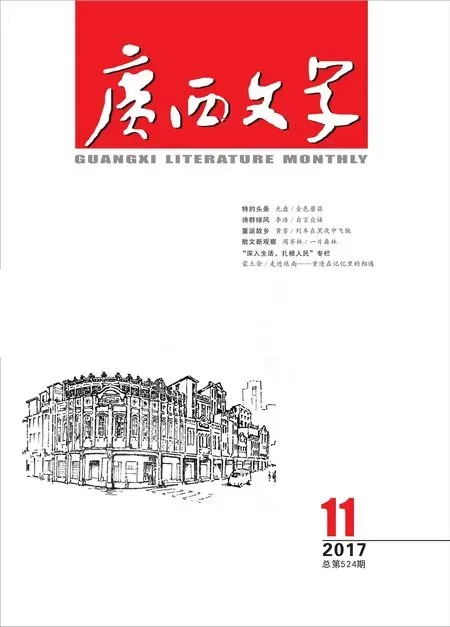自言自语(组诗)
李 浩/著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他们都知道这属于毁灭,一种慢性的,毁灭,像潮水,
像缓缓扩散着的癌……只有我的母亲后知后觉。只有我
和她一起积聚无效的沙子。我们用它来建筑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当然还有树桩,水泥,疲劳,以及在我们的时间里
已经被融化的那些物质。
他们都知道这是无效的,但却施以援手,递给我们贝壳的锁链,
仿佛有另一个西西弗斯的诞生,哦,她具有了新的母性。
母亲的双腿沉陷在幻觉的海水里。它在生锈,牡蛎撕掉有了锈迹的皮
掉落下去。
……那时间我正处在另一重的毁灭之中,我的怀里拥有瓷器,拥有生出汁液的乳房,一顶大过年龄的帽子。我不惧怕火焰,我用脚趾试探:所谓痛,
所谓伤,所谓裂痕或者,所谓地狱。
那时间我在醉心于此,瓷器们裂痕的样子让我着迷,疼痛其实也是。血液真是一条发育良好的蚯蚓,它甚至比酒更为浓烈,更有弥漫感——只有
疼痛能够唤醒我,否则我只会一直在睡。
那时间,我穿好有了破绽的袜子,然后脱掉。那时间,我赤脚走下燥热的阁楼,让燥热用更直接的方式进入身体:生活是可怕的,而母亲和生活一样可怕
“她曾经过度地热爱生活”——而我不是。虽然
我依然会和她一起,积累着那些琐碎而消磨的沙子。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想想或许好笑,但我就生活在这个好笑里面,
它就像不断冲刷的水流,而我是鱼。
跟在后面,我需要吞下多出的盐,苦、涩,被不断泛起的沙子,
可食用的或者无法食用的腐质。他们知道这些
他们的存在就是灾难。就是灾难本身。就是那些黑压压喧闹着的孩子
偶尔,他们也是这堤坝的部分,早就松动的部分,一起呛满了海水。
那时间,我讨厌梦里的海水和现实的海水,讨厌有着双腿和在疲惫中睡熟的母亲,讨厌疲惫也讨厌睡熟。我讨厌那匹马,无论是它身上的气息还
是死亡,讨厌它尾巴上的泥团和尿渍。我讨厌没完没了的夏天,讨厌没完没了的蚊蝇,讨厌草丛,埋伏在里面的蛇。
我讨厌蛇和我的肋骨,尽管我并不想控制。我讨厌一切岌岌可危,它总是
由诱惑生成,尽管我会品啜其中的水分。我讨厌约瑟夫和让·阿哥斯迪,
讨厌所谓的血脉:这真是奇怪的厌倦,可就是如此。
当然,我也讨厌那个……他带来了另一种危险,留声机,他们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我讨厌有花边的帽子,讨厌涂了指甲油的手指,讨厌
当然,我也享受我的讨厌。我时常和它相处得很好。
我,我们,这些被强制移植到生活里的人,总是来不及扎根。
何况是建筑。可用的只有这些:树桩,水泥,疲劳,时间与疾病,不断被冲走的沙子。和巨大的命运比较起来,我和母亲
我和母亲的泪水,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苍老的品质。
“她曾过度地热爱着生活”
“正是她那持续不懈、无可救药的希望,使她变成了对希望本身完全绝望的人”……
他们知道这些,更早地知道。他们都知道这属于毁灭,一种慢性的,毁灭。
而我,别无选择地和她站在了一起。
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长篇小说的书名。其中的引文也是她的。
告别之诗
一年了。我和赘肉代表的命运有过抗争,但更多是妥协,一次次迁就
心灰意冷。十二月,上帝还把一只鸣蝉塞进我的耳朵,虽然还小
虽然,它只停于右侧,只是生活所用的钝刀子的一种。
它是叫抑郁的病,还是杞人的病?哪一年,它会被我养大,并且占据
并且,长成繁殖的骨头?……
一年了,我平静生活,却品尝着较之以前更多的炎凉、耻辱和痛苦
我所携带的假面型号略小,和他们的不同。
思想是一剂毒药,悲悯也是,恐惧更是,麻木已经管辖了我的舌头
但我所携带的假面型号略小,仅遮住一半儿,妻子说
“你比以前更爱哭了。也更容易,在墙角处愤怒。”
一年了,我还在书写,在电脑前发呆,把懒惰与勤奋粘成粗糙的镍币
一年了,我也还在玩“暗黑破坏神”的旧版游戏——之所以
将它们并提,是因为二者消耗的时间基本一样,更重要的,
是另外的相似:
我在重犯刚犯的错误,仿佛被某人的大手扼住脖颈
向上的瓶口让人窒息。“我是否的确缺乏才能?我呆板的存在
是否会像另一层沙,在时间的风口注定虚无?”
“我不怕失败,只是……”怎么会,我怕,这得承认,尽管不甘
我怕失败于平庸,它已经取走半生,接下来,依然是
我怕失败于平庸,反抗它,只是证明了它的强大,以及自欺的荒谬
一年来,我在患失和可能之间荡着秋千,不敢轻易松手
一年来,我将自己分开,分成儿子、父亲、丈夫、下属、读者和诗人
然后,我再给它们分配定语,按照规则需要的配比:
将狂妄的部分交给火焰,将热情和痛苦交给僵硬的颈椎
向父亲和他们低头,向儿子和他们让步,躲避黑暗也躲避光
包括一切有力量的事物。当然,这一年
我也在暗中,和父亲他们争吵,承担虚拟的罪与真实的罚
把蛇芯上的汁液一次次吐出,又一次次吞回到腹中
这一年,软壳蜗牛的习性进一步发挥,背负的房子并不阻挡暗箭
而是,更多地接受。时间的车轮总那么快,宽大而厚重
即使我有过试图——
这一年,我曾幻想转折,幻想过蜜蜂的蜜而不是尾部的刺,
幻想狐狸丢下多余的坚果,雾霾下的冬天并不太冷。
这一年,我面对不同的水流,它湿到了鞋子但没有将我冲走。
这一年,我还在收拢星光和灰烬,保持着
虚荣的虚荣、虚荣的天真和虚荣的自尊
在新的一年里,它可能,依然是我可依靠的支撑。这一年
我还未能攀到树上,脚趾,却已被树皮硌得生疼……
晦 涩
我知道,经历一场火焰之后所有都是余烬
这当然是现在才知道的。
它毁掉了我的码头,它生出了太多的刺——
真是,这个时刻,我还忘不了比喻。
我是负责运送蓝色海螺的船,不靠岸的时间里
海螺的肉体慢慢变臭,我分给盘旋的海鸥
让它们替我叫喊——在镜子里翻舞,像煤质的
纸片。
真是,这个时刻,我还忘不了比喻。
我知道洋流的下面有层出不穷的鱼。
它们的眼圈发红,肯定,火焰曾烧到过水中,
它们分享了它:只是
不肯等到腐烂才开始。
只是,我的疑问一直得不到解决:待在船上
卡在喉咙里的鱼骨从何而来
它是我咽不下的,还是,从我的语词里新生的刺?
真是,这个时刻,我还忘不了比喻。
真是,这个时刻,我还忘不了比喻:
你有海水的反光,厚厚的云影也遮不住你。我成为纵火者
同时,又是唯一被火焰烧焦的受害人。
仅有这扇门的把手获得了幸存,我不能从里面打开
而外面,是黑夜将至的大海。
“我已经厌倦独处”
我已经厌倦独处。
“我”是骨头和椅子,“已经”是一条胶质的皮筋,“厌倦”则是
树叶上爬满了撕咬的虫子,密密麻麻,它们开始吞噬另外的自己。
至于“独处”,我的理解就是,此刻
阿黛尔,一杯苦茶,闪烁着白光的电脑:我又消除了刚刚写下的字。
“谁如果在此时孤独,就会永远孤独。”
我已经厌倦独处。
“我”是骨头和椅子,“已经”是条流动的河,时间的沙砾上晒着它的鱼头,
眼眶空洞而且幽深。
“厌倦”则是,让黑熊也皱起鼻子的气息。
哦,至于“独处”,我的理解就是
空荡荡的房间,我是只与自己说话的哑巴,并且没有谁能够收留
没有目标的思念。
“谁如果在此时孤独,就会永远孤独。”
我已经厌倦独处。
“我”是骨头和椅子,这一点,我不愿意做出修正。我让这个字,保留着
硬质的部分,而忽略肥硕的脂肪。虽然脂肪一直
拉扯,让我感觉日常之丑和生活之累。
所谓“已经”,则是散发着霉变味道的旧积木,越高越摇晃
所谓“厌倦”,则像臼齿的病痛:丝丝缕缕,偶尔会连绵数日。它不是来自异乡的异客,而是影子一样跟随
所谓“独处”,我的理解是渐渐苍老,习惯了单曲循环,一遍一遍。
所谓“独处”,是茶水已凉,而臼齿的病痛电脑并不关心。是,秋已深,
我把自己的脚趾放得很冷,它们在颤抖
在它们的下方,是同样寒冷而细小的星辰。
谁如果此时孤独,谁就会,坠落进夜晚的核心。
没有稻草可以阻挡一下,只有更重的孤独,会让速度更快……
是的,我已经厌倦独处,可我能做的,也只是把这个句子,像玩具那样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