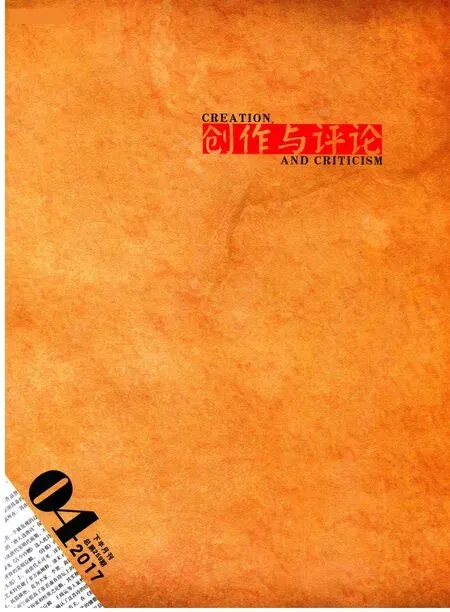在火热的文化市场面前:对青春文学当代研究的思考
○孙桂荣
在火热的文化市场面前:对青春文学当代研究的思考
○孙桂荣
尽管已成为一种“显性”文学潮流,但如何界定青春文学,学界还是有一定争议的。有人从写作主体的年龄角度,将“80后”“90后”一代的写作笼统地称为青春文学,但有些“80后”“90后”作者所写的并不指涉青春主题,有些青春指向的写作又并非由“80后”“90后”一代写成。也有人用相对传统的少年文学概念,不管写作主体是青少年还是成人,只要关涉青春生活就是少年文学,但它遮蔽了青春文学近年来形成潮流的根本原因是其独特的生产机制——青少年惊人的阅读消费能量“倒逼”着主流社会对之进行关注——这一事实。命名一个事物就是承认和强化了它的存在,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如此多的观照青少年生活的文学作品,但只有青少年读者市场足够强大的新世纪才出现了青春文学的命名,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所以,笔者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对青春文学的界定应该由写作主体转向阅读主体的看法。
当将青春文学的界定由写作主体转向阅读主体时,为青少年所欣赏、迷恋、热衷便是青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孕育、1990年代初汪国真诗歌的初露锋芒、1990年代末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跳跃式发展之后,新世纪以来青春文学终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井喷式发展阶段。2004年,青春文学以10%的品种占畅销书市场70%的份额,文学销售前5强中,以“80后”作家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了4席,成为虚构类图书中最大赢家,并直逼某些非虚构畅销品牌。此后,青春文学的辉煌蔓延到了整个青春读物市场:《最小说》《17》《鲤》《悬疑志》等青春写手主办的青春杂志一经推出即迅速占据销售排行榜前列,与传统期刊的困境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几米等人的青春绘本在读图时代屡掀狂潮;青春动漫、青春影像书更是借助科技力量,将文字、图画、音乐、影像,甚至“书模”“选秀”融为一体,对追赶潮流、热衷时尚的青少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最近几年,国内大众文艺类图书年产值每年达500亿元左右,青春读物约占5亿元的市场份额,多个机构或个人的图书排行榜亦调查显示“青春主题图书是近七年文学类畅销书的主流”,前景十分巨大。
新时期以来青春文学繁荣热销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点:一是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青少年对课外阅读有着更多和更高的要求,而素质教育的推行,又使得他们相较于以前有着更多的时间和闲暇进行课外阅读;二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投资在中国家庭占据异乎寻常的比重,这为青春读物制造了一个强劲的“买方市场”;三是目前青春读物普遍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客观上刺激了其广阔的市场需求。
然而,与青春文学在市场上的异常热闹相比,文学研究界表现出了某种犹疑与尴尬。或者说青春文学在市场销售与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是极端不平衡的。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与当下读者群的阅读景观中,青春文学代表了一种盛况空前的乐观画面;另一方面,青春文学在中国主流批评与研究领域中非但不受重视,而且被边缘化、贬抑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比如它们的写作者往往不被称呼为“作家”,而是“写手”,“‘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在少数作家‘倒下去’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将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写作者称为“写手”,是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似乎通行的一种文化惯例,它以一个并不严肃的包含轻慢之意的“写手”一词来指称青春文学写作者,既以“命名意识形态”的方式昭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界对青春文学的深刻漠视与敌视,又表明主流学术界对溢出了自身传统与研究范式的青春文学感到了某种深刻的无奈与无力(高等院校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青春文学部分更是被“弃之若敝履”)。以郭敬明研究为例,伴随其商业成功的是各种批评质疑之声。中国文联发布的“2013年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明确和直接地将《小时代》称之为“伤风败俗”之作。“《小时代》重场面、轻情节,对浮华都市时尚元素过度渲染的同时,情节则显得矫情而单薄。”同官方相比,某些批评者的言辞更加激烈和尖刻,“即使拜金主义也高估了小时代,它没有出具任何价值观的能力和努力,或者说,它完全就是没有内在逻辑的价值观”“来自文本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健康生活方式”,从性别角度,它造成了女性进步的大倒退,“它是妇女地位的大跃进式后退”。
造成这种青少年阅读与专业批评间“冰火两重天”两极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谈一下青春文学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的选择问题。不客气地说,依然沿袭传统格局的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新媒体语境中青年亚文化的青春文学之间已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尴尬错位:
1.“作者中心”的知人论事研究传统与青春文学赖以维系的“读者中心”原则之间的矛盾。作家论是传统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尤其是针对经典作品的研究,从作品写作的社会、时代、环境,以及作家的个人经历中寻找作品的意义,将文本内外的世界进行互证互释,是一种屡试不爽的研究方法,像至今仍然非常活跃的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等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基本上都是采取作家生平、传记考证、文献考据等作家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但对于产业化的青春文学来说,这是一种因为过于严谨而显得“迂腐”的研究方式。对于根据“顾客就是上帝”“消费终端决定一切”的现代商业原则,以多卖书、赚取稿费和版税为主要和根本任务的青春文学而言,青少年读者(而非作者),是关注与取悦的中心与本源。如郭敬明所在的柯艾公司便成立了名为“刻下来的幸福时光”的官方论坛,以时刻保持与读者(消费者)进行实时的沟通与互动,该论坛目前已有20万多注册用户,郭敬明本人也经常看帖、发帖,并根据读者建议与喜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他的铁杆粉丝还成立了全国性的“时光后援会”,在主流批评界对他们的写作不置可否或不屑一顾的时期,读者评论机制早已成了引领柯艾公司文化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采取签名售书、与读者座谈交流、奖励优秀的读者评论等方法刻意保持“读者中心”模式,以便在争取最大限度的市场购买力中获益。
2.寻找与阐释创作个性的作家个性化研究与青春文学集体化作业、文化工业式大生产的矛盾。传统上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工匠式”生产,作家依据自己的才情、趣味、经验、喜好进行具体的选题、立意与写作,而文学研究则是挖掘作家这种个性化风格的过程,像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对鲁迅的研究、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对茅盾的研究等,作家写作时真诚地投入自己的创作个性,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则是深刻地挖掘与阐释出这种创作个性,并进行必要的学理总结,比如学界经常提到的“知人论事”“风格及其人”等文艺理念,便是由文论及人、由文品论及人品,由作品个性论及作者个性的传统文学研究范式。然而,这一研究方法与青春文学的集体化作业、文化工业式大生产之间产生了深深的矛盾。青春文学的公司化运作模式,生产、宣传、销售、发行“一条龙”的营销方式已打破了个人化“工匠式”文学模式,作家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往往被集团化、工业化作业方式所淹没,甚至不少作品已难以提供真正性和唯一性的作者名单。像郭敬明主导的最世公司,正在遵循资本逻辑,试图建立新的“1+1〉2”的利润生产模式,以“集团化作业”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以“团队”方式打造文学作品,集体创作的单个文学作品,如2010年由最世公司筹备的《我们约会吧》的小说与剧本,郭敬明先独立完成剧本创作,根据剧本衍生出来的同名小说则由郭敬明、笛安、落落、爱礼丝等创作风格不甚一致的多位写手共同完成,据悉他们曾将共同创作的过程比作“武林大会”,在讨论、磨合中完成了作品的最后定稿。多人写作一部作品的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鲜有先例,除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集体创作“有利于破除创作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有利于“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才得到“鼓励和提倡”。郭敬明团队的集体化创作模式显然与政治高压下的“写作小组”不可同日而语,它所体现的是文学产业化之后的大规模、集约化商业生产模式。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协作链条,它把作家、策划人、出版人和销售商等不同的参与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通过分工合作,使艺术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又以商业价值的实现过程促成了艺术价值的传播与实践。产业化模式创制出来的文学作品,其作者并不是唯一,其创作初衷更不是作者个人情怀的尽情展现,传统的寻找与阐释创作个性的作家个性化研究,及“知人论事”“风格及其人”等研究方式似乎更无从谈起。
3.“文本中心”的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遭遇产业化文学“作者偶像化、读者粉丝化”的新传播语境的挑战。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一直作为专业文学研究的“大本营”而存在,因为它们所针对的是文学不同于其他艺术或非艺术类种的“文学性”问题,是对文学主体性、本体性的正面阐释,它将研究视域更多倾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与价值上,与其联系紧密的是语言学、语义学、文体学,如杰弗森曾说“自19世纪后期起,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的批评家想要忽视语言形式问题已越来越不可能了,与此同时,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大大开拓了语言对文学研究的解释能力……。”的确,那种反复推敲,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力争审美最大化的文学传统,如果不以细致、繁复的文本细读,不以深刻的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对其非日常化文学语言中蕴含的丰富隐喻、含混、象征、悖论、张力、反讽等修辞方式进行系统阐释,便无法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内涵,也无法破解文学流传千古的魅力之谜。这是最鲜明体现经典化、精英化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当然这一研究方法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值得”研究的,是创作者以认真、严肃、虔诚的姿态来写并努力灌注进自己生命激情的文字,鲁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笔下的经典文本是此类研究方法的最佳研究对象。青春文学呢,无论其文本形态,还是创制过程,都距离经典文学十万八千里,其几个主要作家均已偶像化、明星化,“作家明星化”意味着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文学形式,甚至文学作品本身如何并不是决定这一作家人气旺盛与否的重要性与决定性因素,其像影视明星一样,外貌、穿衣打扮、兴趣爱好、私生活等“外围”于文学的因素更容易成为商业卖点的中心。或者说,“明星化”的作家与其说依靠作品本身赚钱,倒不如说以其所树立的“自我偶像化”方式赢得受众认可。当然,这里的读者、受众也不是普通的读者、受众,而是“粉丝化”的读者、受众。以郭敬明为例,从2002年推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开始,郭敬明就受到了一众粉丝的热烈拥戴和追捧,这里有其作品本身的因素,但这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缘自其深谙传媒时代青少年心理的文化运营方式,像他甚至大肆炒作自己的身高和性取向,以各种方式博得粉丝的关注,而对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等却关注不多。《小时代》的媒体运作更近乎闹剧。可以说,文化场中的郭敬明树立了自身的明星品牌,即使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因为在整体人物关系、“12个主要情节”“57处一般情节和语句”上与庄羽《圈里圈外》相同或相似,在2004年被法院判决侵权、剽窃事实成立,都没有驱散和冲淡“郭敬明热”,狂热的粉丝们明知他抄袭还是力捧他,最后在粉丝的支持下以郭敬明“赔款但不道歉”的方式结束。这一典型事件表明,不论是偶像化的作者,还是粉丝化的读者,他们无视、漠视、盲视传统文学一贯讲求的思想性、深刻性、独创性等文学性原则方面似乎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而既然作品本身如何,有没有原创性等并不为作者与读者多么看重,甚至不少作品就是一种精心炒作下的漫不经心之物,在此情形下,“杀鸡焉用宰牛刀”,何以再用言之凿凿的严肃学理化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或者说,面对这样的写作与阅读,再以言之凿凿的严肃学理化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做文本细读是否会让人倍觉荒诞?曹文轩教授曾说:“我们所掌握的那一套,是研究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的,是研究托尔斯泰、鲁迅的,是研究《战争与和平》《阿Q正传》的,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二流的、三流的作家和一些小罗卜头,是一些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没有多大说头的作品。”青春文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些不太适合用“我们所掌握的那一套”进行研读的“小罗卜头”的作品。
4.从青春期心理出发的青春文学阅读机制与更多关注社会价值的青春文学研究机制之间有一定话语裂隙。青春文学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研究者则主要是成年人、理论工作者。青春文学阅读是青少年缓解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的一种自发行为,依循的是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情感吸引力”,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偏执或忧伤感怀的心理也让他们特别偏爱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这是文化研究中所说的“相关性”原则,“不是文本的特质而是文本的功能性,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但青春期已过的研究者则往往不会自发采取这一原则,尤其对于有一定生活和学术积淀、习惯于传统文学阅读的学者而言,文学文本的思想意义等社会价值与功用是他们首先会考虑到的研究视角,像批评家郜元宝在一篇评论郭敬明《爵迹》的文章中这样写到:“我想探测一下何以在我感到茫然,在别人(尤其是其粉丝)却倍感亲切,以至要誓死捍卫?他们究竟在郭敬明作品中看到了什么?倘若郭敬明和他的粉丝们真有一种我看不懂的青年亚文化,那它的核心究竟为何?”在无限玄幻、超验、惊悚的情景中体验快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对于习惯了严肃阅读的学人来说。西方有句谚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对应中国国话里的俚语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过这种“趣味无高低”之类在目前的文学批评语境中尚不能真正贯彻下去,最起码青春文学的阅读趣味没有被有效阐释出来。布迪厄在他的《区隔》中指出,文化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的阶级和阶级群体,并将这些区隔在美学或是趣味的普遍价值中加以定位,借此建构这些区隔的社会性质。青春文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鲜明体现了这种文化区隔的存在。
正如古语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物体在不同视角之下有可能呈现出相差甚远的形态面貌来。人们通常从自己的经验和视角阅读文学作品,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客观与非理性的印记。笔者看来,青春文学既不像其粉丝认为的那样好,也不像某些专业批评家批判的那样拙劣不堪。它们是时代的产物,也为这个时代所左右,往往以一种相对夸张的手法顺应了青少年偏执叛逆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心理,其负面性是明显的,但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释放了被主流体制压抑的青少年心声。因此,青春文学研究要改变目前对其捧杀与棒杀的两极化批评理路,以客观、公正的心态面对新媒体语境中的这一青年亚文化潮流。
注释:
①黄云生编:《少年儿童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陈进:《1999-2009:中国青春文学十年——以“先锋”与“常态”模式阐释》,《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③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④陶东风:《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新时期文学30年》,《博言天下》,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1页。
⑤孙桂荣:《青春文学教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改革》,《中国大学教学》2014年第1期。
⑥中国文联:《“2013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批“小时代”矫情》,《北京青年报》2014年3月27日。
⑦吴筱燕:《资本的狂欢与价值的缺失——关于〈小时代〉系列电影的一点思考》,《上海艺术家》2014年第6期。
⑧吴孟思:《浅析〈小时代〉道德价值取向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戏剧之家》2014年第7期。
⑨《〈小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大跃进式后退》,《电影世界》2013年第8期。
⑩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⑪杨玲:《当代文学的产业化趋势与文学研究的未来——以青春文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⑫杰弗森等著,包富华等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⑬孙桂荣:《现状与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实践》,《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
⑭《〈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事件始末》,见http://www.s1979.com/m/ent/yulebagua/2010/0422/29570.shtml
⑮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⑯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⑰郜元宝:《灵魂的玩法——从郭敬明〈爵迹〉谈起》,《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