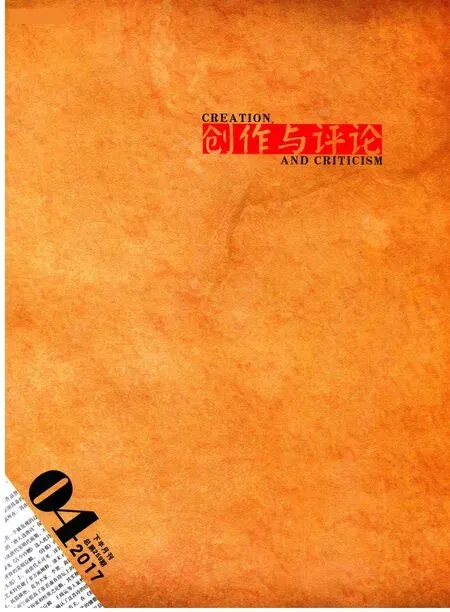不会讲故事的批评家不是好学者
——赵勇批评印象
○魏建亮
不会讲故事的批评家不是好学者——赵勇批评印象
○魏建亮
如果说北师大赵勇教授是一位理论家,大概没人会有疑义:《透视大众文化》《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大众文化理论新编》《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著作的问世无疑已使他成为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专家;如果把他归入批评家阵营,也许有人会有疑惑。但事实上,他不仅在批评领域努力经营,笔耕不辍(从1985年公开发表第一篇评论始,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这个领域“辛勤工作”,据笔者大致统计,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大大小小的批评文章百余篇),而且还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其批评曾获1988年首届《批评家》优秀论文奖,2007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给当下略显疲软又有些浮躁的批评界注入了一股活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批评就像“讲故事”
赵勇批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读”:文字活泼灵动,叙述巧妙流畅,善于在细节处开掘,而且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最后“曲终奏雅”,点破“包袱”,让人恍然大悟。看他的批评如同听“讲故事的人”在“讲故事”。他是个会“讲故事”的批评家。唯其会“讲故事”,他的批评才有特别的魅力和吸引力。在他年轻时期的批评中,这个特点已露端倪,如在《一个青年作家的足迹》中,他就巧妙运用了“起承转合”的讲述技法,对张承志作品的主题进行了分类和分析。一般而言,在主题批评中,批评者都会将某一作家的作品主题进行分类,但是,能够按照人的心理接受规律,将主题分析予以“起承转合”布局的有,但不多见,年仅22岁的赵勇却做到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先从张承志的作品中提炼出了“美”/“赞美”的主题,然后又承接到对“丑”的否定中,接着话锋一转,延伸到对作品思想的博大和深刻的论述,最后回到对其作品主题(和艺术特色)的综合判断上。至此,一个优雅的“起承转合”动作完成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该文的语言、论述还有些稚拙,但其批评特点或曰批评风格已从这里“启程”。尔后,赵勇又通过不懈地书写实践对它进行了锤打、锻造与淬炼,时至今日,该特点俨然已成为他的批评“招牌”。我们可再从他的批评文章中抽取一篇来“欣赏”这一特点。《电话、情书、身体与数字化时代的爱情》是他对张者《桃李》进行批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像论述张承志那样对其进行宏观鸟瞰,而仅仅分析了文本中的“李蓝之恋”,而在具体论述中,又把火力瞄在了“李、蓝”两位主人公的四次打电话上(他们的通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我爱你”的问候和对方“哦”“呸”等的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切口。从这个小切口向外衍生、扩散,赵勇为我们饱满地演绎出了数字化时代爱情的物理状貌和精神症候,“当电话成为‘我爱你’的传播工具时,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电话与这种有着特殊内涵的示爱话语存在一种同构关系。我前面已经说过,电话主要是一种事务性的媒介,它不适合承载和传递更多的情感信息;而由于李雨特殊的‘恋爱’动机,他的‘我爱你’不需要也不可能携带更多的情感信息,所以,电话就成了一种理想的媒介。当李雨在电话中说出‘我爱你’时,它已被卸下了情感的重负,但是又逼着对方做出即刻的回答,这种速战速决毫不拖泥带水的表达方式很像是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几个回合之后就可以成交,这应该是数字化时代爱情的涵义之一。”如此论说,一览无遗地将他卓越的文本细读功夫和细腻的分析阐释能力展示出来,也将他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本领公之于众。当然,在当代批评界,以语言文字的活泼灵动取胜的批评家并不少,以即时性和沟通性为基本特征的批评也特别需要能巧妙驾驭语言文字的批评家的出现。但赵勇与他们不完全相同:他的文字虽然“好读”,但有温度,是对批评对象倾注了全部情感以后的理性抒发,删除了情绪与冲动,熔铸着他强烈的生命体验;他的文字虽然“好读”,但有厚度,是对批评对象进行了理论观照后的择机而出,洗尽了浮躁与肤浅,镌刻着他独特的生存智慧。
二、学者气质的彰显
于是,有厚度,或曰厚重,就构成了赵勇批评的另一特点。(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把“厚度”“厚重”拎出来界定他的批评时,它们就超出了话语语法学的层面而进入到了语用学的领域)纵览他的批评,我发现,他不像有的文学批评家那样,一味执着于对作品/现象的浅层次描述,公式般地分析人物形象、考察故事背景、解读思想内容、凝练艺术特色;也不像有的道德批评家那样,一味沉溺于对文本思想性的单向挖掘,以致陷入传统道德的枷锁中、人际伦理的囚笼中不能自拔也不自知;还不像某些媒介批评者那样,一味抢热点、抓眼球,“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与社会“死磕”或主动投入它的“怀抱”;更不像有的理论批评家那样,一味“掉书袋”,用晦涩、专业理论术语的“腾挪跌宕”硬撑起干巴巴的文章骨架,还美之名曰“深刻”。而是,充分发挥理论家的身份优势,运用多种理论资源和视角,一点一点地析解批评对象,并剔除遮在它们身上的重重迷障,“拨云见日”,将其本质内核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的批评因此就有了深刻的学理秉性和浓郁的学者气质。也因此,他的批评与前三种批评就有了很大差异——它们在形式和旨归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但与最后一种批评的差别就不好区分了,因为在形式上,他们同属法国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 意义上的“职业的批评/教授的批评”,或当下的“学院派批评”。我们知道,这类批评的最大特点是拒绝平面描述,以对理论的东征西引、文献的考据考证为本,进行有深度的理论再建构。不容否认,从他的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理论的偏爱,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萨特的“介入”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以及知识分子理论等,更是频频出现于他的笔下。但他的批评由此就晦涩了吗?“掉书袋”了吗?没有!我从中看到:由于征引了相关理论,多了一种打量的视角和武器,他的批评反而充满了穿透力,比大多数同题批评有深度、有看头。比如,同是面对21世纪初一度火热的“红色经典”改编,不少文章都是在说改编有多难,改编应遵循什么原则,改编如何忤逆了群众“口味”,引起他们的不适,等等。赵勇当时也介入到了讨论中,但他没有被这些“权威”的表面说法迷惑,也没有跟在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利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理论,深入到上述问题的背后进行再发掘。经过发掘他发现,之所以在当下会形成“红色经典”改编难的现状,是因为长久以来隐藏在民众心中的“政治无意识”在暗中推动着他们对“红色经典”的拥护。很明显,这种批评与上述“理论现象两张皮”的批评不同——这是赵勇批评学者气质的一个维度。其学者气质的另一维度表现在他能有效运用理论,从对作家作品或现象的分析中再提炼出一定的理论模式来。这种批评难度很大,最考验批评者的理论功力,也是理论家批评与一般批评家批评的最大不同。《莫言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写于1996年的文章中,赵勇运用自己创制的记忆历史和现实历史两个概念,经过细致绵密的阐释分析,归纳出莫言创作中的两极美学图式。“从人物设计上看,这部小说塑造了两类人物:英雄和小丑。前者是战争环境的产物,也是作者幻觉经验的结果;后者既被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打磨再造,也进一步被意象形态武装到牙齿。从美学风格上看,这部小说的两极趋向是崇高和滑稽(或荒诞)。前者的形成得益于象征性环境的营造与人物(尤其是人物之死)的同构关系,后者的出现则诞生于反讽性环境的建构以及人物与环境所构成的那种乖谬而尴尬的关系。通过这种两极图式,作者呈现了自己的审美(丑)观和价值观,但其核心依然是‘美本位’而不是‘丑本位’。”不得不说,在大量的对莫言作品,包括《丰乳肥臀》的批评阐释中,这个说法准确到位、独树一帜,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对莫言创作美学的总结。因为我发现,若将该两极美学图式扩大化,代入莫言的其他一些作品,如《蛙》《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是基本适用的,这充分说明赵勇对《丰乳肥臀》的此番理论“提纯”站得住脚——起码在莫言的现有作品那里如此。这两个维度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赵勇批评的厚重的学者气质。不过,此厚重非彼厚重,它不沉(重)也不笨(重),而是言之有物的深刻,鞭辟入里的深邃。
三、知识分子情怀的渗透
平心而论,在当代批评界,分别具有以上两个特点的批评并不是“凤毛麟角”(但也没有“汹涌澎拜”),赵勇的长处是把它们做了有机结合并进行了精细打理。那么,赵勇批评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他的知识分子情怀,以及在此情怀的烛照下体现出来的尖锐的批判意识。由于有这样一种情怀和意识,在面对批评对象时,他就常常不走寻常路,而是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对其做出社会层面的批判。比如,《〈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的张承志与知识界划地绝交的原因,并勾勒、描画出了文本中那个不与俗世妥协,永远处于抗争中的主人公的“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立法者的奇妙组合”的面相定性;《从“老板”到“叫兽”》通过分析《桃李》 《教授》中的主要人物,展示了学院知识分子,即高校教师是如何在外部环境的引诱下从“辛勤的园丁”一步步堕化为“砖家”“叫兽”的;《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或聂致远的书生气》分析了《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聂致远的心理痛苦与行为摇摆:作为普通人,他身不由己地受到周围的钱、权诱迫,作为知识分子,他又不甘心就此放下身价,与世俗“同流合污”,在他心里还有一条坚固的“底线意识”在发挥着作用……如此高密度地对作家作品进行知识分子维度的阐释,在当代批评家中并不多见。而之所以他要选择这样一个维度,在于赵勇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在借评价他者的外部行为,表达自我的内心想法——学院中人不仅要“成为学者,还要成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具有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这是区分知识分子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作家的重要标志。”由于在学者身份之外,他主动承担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因此他还屡屡跨出文学批评,将批判的触角延伸到文化领域,由此形成他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版块——文化批评。我以为,谈论赵勇批评不谈他的文化批评不合适,也没有道理,因为他在中国当代的文化批评领域极其活跃,是该批评家族中的重要一员。而且他的很多有价值、思想性强的批评也是以文化批评的面貌出现的:对《百家讲坛》的质疑,对“红色经典”的反思,对手机、博客等新媒介的考量,以及对诸多文学文本,如《明朝那些事儿》《手机》等等的文化分析,都很有分量。更可贵的是,知识分子的角色承担,还让他以人性的良知和学者的敏锐为准绳和武器,对社会上的各种“失义”“无义”“不义”现象展开了尖锐的文化批判,借以“抵抗遗忘”,警醒世人(这方面的文章已结集为《抵抗遗忘》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阅读该文集中的批评文本,我分明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幅景象:一位正义之士,正在以压在纸背的心情奋笔疾书,他时而义愤填膺,化笔为剑或以笔为旗,时而温情脉脉,又将剑作帛或挥旗施粥,对大千世界的众生相展开尖锐地批判,或温情地解说。他在启蒙,在践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他就是赵勇。
那么,赵勇是怎样成为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赵勇是怎样炼成的呢?若仔细检视他的文章和别人写他的文章,就会发现叛逆和批判是他的天性(可参考其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但天性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后天习养。这些习养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尤指他的大学和研究生年代,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时期,对赵勇来说,这个时期位于1980年代(1981-1985,山西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7-1990,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众所周知,1980年代是个充满激情而又追寻理性、崇尚民主自由又可大胆言说,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空前强大的时期。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如涓涓细流又如狂风骤雨对当时的大学生进行了精神施洗,“喷头”下的赵勇必不可免受其“淋浴”。另一部分来自他勤奋不辍地学习修炼,相信只要看过他《一个人的阅读史》的人都会有此感。笔者曾有幸参观过他在北京的家——那座“工地书房”:书房就不用说了,客厅、卧室也是书架,而且地上堆的、窗台上搭的和床头上摆的也全是书。那些著作和理论家、作家们必然会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给赵勇提供给养,让本已充满批判天性的他如虎添翼,要知道,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人曾经是他认真“交往”过的朋友,借助他们,他写出了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萨特是他大学时代的“密友”,后来又多次“造访”于他。于是,在叛逆天性的基础上,途经后天多种方式的打磨,知识分子赵勇终炼而成。
走笔至此,赵勇批评的特点已立于眼前,简言之,即好读、厚重、有情怀。据我观察,在当代中国,能把批评写得“好读”的人不少,写得“厚重”的也不少,但是,能把批评写得既“好读”又“厚重”的则不多。而在“好读”和“厚重”的双重根基上,再把知识分子情怀搭于其上、渗入其间的就更少见了。难能可贵的是,赵勇就是这种批评的践行者。
注释:
①赵勇:《一个青年作家的足迹——略论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
②赵勇:《电话、情书、身体与数字化时代的爱情》,《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③赵勇:《谁在守护“红色经典”》,《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④赵勇:《莫言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⑤赵勇:《〈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⑥赵勇:《从“老板”到“叫兽”——新世纪学院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演变》,《博览群书》2012年第12期。
⑦赵勇:《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或聂致远的书生气——重读〈活着之上〉》,《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⑧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