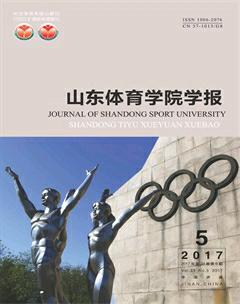论体育处罚规则设定的法治化
韦志明
摘 要:体育组织应在法治视域下设定处罚规则。体育处罚规则内生于体育的游戏竞技性,其又以行业自治为前提。从法治化考虑,体育组织设定处罚规则时应尊重法律设定的法律保留原则,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进行“立法”,在权利让渡的边界上,不得对人身权设定体育处罚规则,其设定的处罚规则的效力对象以体育组织内成员为界。从设定的合理化考虑,体育处罚规则的设定要注意它的功能性、专业化和正当性问题。在功能化方面要准确把握它设定的“度”问题,既不能设定得过于严格,也不能过于疲软。在专业化方面,应贴合体育的专业特性来设定,以增强处罚的有效性。在正当化方面,其设定对内要建立在组织成员的合意或同意认可基础之上,对外要建立在法治正当化基础之上。按照章程规定进行“自主性立法”是理解体育罚则设定的正当化前提,进而在正当程序化方面,应尽可能地在程序设置上能保证所有成员平等地参与到处罚规则的制定中来。在处罚规则各类设定的正当化方面,一是正确理解体育罚则设定的“自主性立法”性质,二是不得对人身罚进行设定,三是应根据体育的专业特性来设定声誉罚、行为罚和财产罚。
关键词:体育处罚规则设定;正当化;法治化;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5-0001-08
Abstract:Sports organizations should set penalty rules in the context of legalization. Sports penalty rules are born in the sports game competition, which is based on industry autonomy. In view of the rule of law, sports organizations shall respect the law of legal reservation principles and shall not set penalty rules beyond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law; on the boundary of the right transfer, the objects subject to the penalty rules shall be sports organization members and no penalty rules on personal right shall be set. To be rationalized, the setting of the regulations of sports penalty should consider the functional, specialized and legitimate issues. In terms of functional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limit", not to be too rigid or too weak. In the field of specialization,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should be put in plac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nishment. In the context of legitimac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s is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r consent of the organization members as well as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e of law. Legislative "autonom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is the premise to understand the sports penalty setting, and in terms of proper sequencing, all members are equa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ule setting wherever possible. As for the legitimation of all kinds of rules, it is prominent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sports penalty rule legislation "autonomy" nature; personal penalty shall not be set and reputation penalty, behavior penalty and property penalty shall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sports.
Key words: setting of sports penalty rules; legitimation; legislation; rationalization
在我國,职业体育活动的管理主要通过各单项体育协会制定的自治规范来实现。其中,处罚规则(简称罚则,下同)在职业体育管理中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最能体现职业体育行业的治理特征,因为职业体育行业治理的有效性主要通过它来保障。
职业体育罚则是以职业体育行业协会制定的自治规范为表现形式,对行业成员以及行业以外社会成员所施行的惩罚性规则。表面看来,职业体育组织根据章程设定惩罚性规则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自治权问题,但其实却是一个极为让人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的设定一方面影响着职业体育组织对内的有效性管理,另一方面又牵涉到与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等国家法体系之间的协调和权限划分的合法性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法治化基础上设定处罚规则,才能既实现职业体育对内的有效性管理,又能满足职业体育对外的合法性审查。endprint
1 职业体育罚则的正当性之源
社团罚则对于行业协会行使自治管理权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界有关社团罚则的正当性来源有多种解释,较为普遍的解释是,行业协会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在关系网络中,非法律的惩罚(即社团罚)比法律惩罚更有效。在普特南(Putnam)看来,在一种关系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总体上是倾向于合作而非背叛。他的理由是:第一,人们在关系网络中持续的交往容易形成“重复博弈”关系,其更愿意考虑长远利益而非短期利益。第二,社团能为人们提供互惠关系和“重复博弈”的稳定环境。第三,社团的沟通媒介作用有助于人们选择合作。第四,社团提供的集体记忆有利于改进集体行动的策略。[1]
但这种解释较为抽象。与其说体育处罚规则产生于成员之间的关系性互惠,毋宁把它解释成是产生于体育的游戏竞技性更为直观。任何一种游戏都要有其自身的规则,否则游戏无法进行,但体育运动特别需要规则,因为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游戏活动,它需要游戏规则来维系,这便是体育规则。可以说,体育规则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存在的必要前提,也是判定竞技各方胜负的规则依据。如果没有体育规则,体育运动是不可能有序地开展起来的。而体育运动的竞技性特征又内在地要求要有处罚规则来维护体育规则的有效施行和保障。竞技性是体育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独具魅力之处,是体育的吸引力所在。体育的竞技性内在地要求体育活动在公正的环境下进行,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公正进行,它不仅需要制定相应的体育规则来使体育运动得以公正地进行,也内在地需要设定相应的处罚规则来保障体育规则的有效施行,这是体育规章制度得到有效遵守与执行的制度性保障。科尔曼早就指出:“如果任何行动者不服从规范,必须对其施行惩罚,只有这样,规范方能行之有效。[2]”张宇燕在分析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原因时也指出,有效的赏罚规则,可以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障碍,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3]
更进一步地说,职业体育组织对处罚规则的设定是行业自治所需。和其他社会自治组织一样,职业体育组织也是一种契约自治,在职业体育组织内,组织成员的活动和行为主要受组织成员以合意或同意达成的共同协议(组织章程及相关规则)而不是法律的拘束。为了保障职业体育组织的有效管理,需要制定相应的处罚性规则来保障职业体育组织对管理规则的有效执行,“制度要有效能,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4]48”。而在职业体育规则的施行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机会主义,在机会主义者看来,只要存在能逃脱制度约束的一线机会,他(她)就不会放弃冒险去尝试。尽管有国家法律强制力的威慑存在,但是如果危险是实在的,却是遥远的,机会主义者就敢于铤而走险。这样,就必须在职业体育自治体中设置相应的非法律处罚规则,才能对行业成员形成近在眼前的制度约束力。不管是职业体育组织制定自治规则还是处罚规则,它的前提是职业体育组织要有自治的权力和权能。职业体育的这种契约性自治,也得到了国家法的合法性确认,《体育法》第36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织和开展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在第49、50条中进一步规定阐述了设定职业体育处罚规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该法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以及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
换一种角度来说,只有建构了有效的处罚性规则,才能更有助于职业体育协会实行行业自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业协会没有建构自己独特的非法律惩罚机制,对违规者的任何处罚只能依赖于法律规定及国家机器,可能就会使外部机构借协助惩罚之名行干涉行业协会内部事务之实,行业协会自治自然难以落实。另一面,也会助长行业协会对国家的依赖心理,终将使行业协会丧失自治的独立精神和品格。相反,如果行业协会建构了自己的非法律惩罚机制,随着它的功能渐趋完善而有利于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行业自治的内在要求。[5]
概言之,职业体育罚则设定的正当性源于体育行业自治的内在需要。
2 职业体育罚则的边界
有关社团罚则的设置问题,在德国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弗卢梅为代表的否定论,认为单独的社团处罚措施不合法。社团只能作无损成员名誉的罚款,并且这种罚款对该成员不构成重大的财产损害。另一观点是以拉伦茨为代表的肯定论,认为社团处罚措施与违约金不是一回事,社团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必须有能力对成员违反群体要求的行为作出反应。后一种观点是德国的主流观点[6]。现在看来,随着第三部门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社团设定非法律处罚规则的合法性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我国《体育法》也在第49条和第50条认可了体育组织设定这种处罚规则的合法性。
但这并不等于说职业体育组织就可以任意设定处罚规则,它仍然有个边界问题。职业体育罚则的边界涉及到行业的自我规制以及与外部规制的相关问题。从法治化要求来看,职业体育罚则边界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处罚规则与国家法的关系;行业处罚规则与公民可让渡权利关系;处罚规则效力对象的合法性。
2.1 职业体育处罚规则与国家法的关系
这里要界定职业体育制定处罚规则的法律边界问题,即职业体育组织不能设定的事项止于哪里?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律设置法律保留原则说起。在法治社会里,在国家法律中设置法律保留原则的本意是用来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张问题。行政权的主动性特性使其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倾向,需要在法律上规定某些事项只能由法律来进行设定,不能由行政立法对此类问题作出规定,此所谓法律保留原则。在法治社会里,为了杜绝和防范行政权力滥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法律上设置这种保留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对公权力尚且需要法律保留制度来划定行政立法的边界,那么对于社会私权力的职业体育组织设定处罚规则的也同样应该适用。因为职业体育行业协会的自治管理权虽然只是在其共同体内具有权力效应,但它对共同体成员的自治管理仍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也同样面临着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从法理上说,国家是充分的自治共同体,社团是不充分的自治共同体,国家与(体育)社团是交叉包容性关系,国家的法律具有终局性效力。既然在国家共同体中尚且要设置法律保留原则来防范国家行政权立法滥用的可能性,那么作为不充分的职业体育共同体当然也应该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划定的这个界限,法律保留原则的设置标明了体育组织设定处罚规则的权力边界。此其一。其二,职业体育处罚规则与法律虽然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系统,但职业体育处罚规则也不需要僭越宪法和法律来重新分配正义,因为法律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与行业自治体对正义的理解是一致的[4]51。更何况,基于法治化的考虑,职业体育组织在制定自治处罚规则时,也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进行“立法”,作为“下位法”的职业体育组织在设定处罚规则时,它的边界即应止于此。但需指出,这里的“下位法”不得超越、抵触上位法边界应指作为“下位法”的行业自治“立法”是不得超越、抵触作为上位法的宪法、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而不是具體内容。当然,如何作为上位法的宪法、法律的具体规定已作了专属性规定或法律保留规定,则作为“下位法”的行业自治“立法”也不得超越、抵触作为上位法的宪法、法律的具体规定。endprint
现在我们再以上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足协章程第51条(2014年修改版)规定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国足协章程第51条规定,中国足协会员不得把行业性争议诉诸法院,换言之,它完全排斥了法院对此类争议的管辖权。但我国《立法法》已经以法律保留形式把诉讼限定为只有法律才能对它进行设定。《立法法》第8条第7款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其他任何公权力均不能对之进行设定。既然对公权力尚且如此设定,那么作为社会私权力之职业体育组织就更应该没有权力来设定限制会员(同时也是公民)的诉讼权利。可见,中国足协在章程中作了这样的设定限制,有涉嫌突破法律保留原则越位“立法”之嫌。
2.2 职业体育罚则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合法性
这个问题会涉及到职业体育行业协会在制定处罚规则时,可以限制或剥夺会员的哪些权利?哪些权利是不能通过行业处罚规则加以限制或剥夺的?它的界限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权利有级别之分,既有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权利之分,也有可转移权利与专属权(不可转移性权利)之分,还一般性权利与特殊性权利之分。虽然法理上说权利可以放弃,但从权利让渡上来讲,却不是所有的权利都可以自由处置和让渡的,有些权利可以让渡,有些权利却不能让渡。但也不是说基本权利就必然地具有不可让渡性,一般性权利就必然地具有可让渡性。一般来说,出于对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保护以及对人类底线伦理的维护,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人身权不可自由让渡。所以,法律为了保护个体的生命健康权可以强制汽车司机系安全带,强令摩托车手戴头盔,强令进入建筑工地的人员戴上安全帽,而同样是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却是允许权利人自由转让,比如赠与财产。前述已论及,职业体育是一种契约自治,成员通过自愿合意加入行业协会的同时,也同时以让渡的方式转让了一部分权利给职业体育协会以集体的名义对行业及其成员进行管理,职业体育协会也因此获得制定内部规则进行管理的权力,其中就包括制定处罚规则对成员的某些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的权力。但职业体育协会同样面临着权利让渡的限制问题,从法治化考虑,既然在法律中就规定了人身权具有不可让渡性,那么作为非充分共同体中的体育社团成员当然也不能拥有对这部分权利进行转让或让渡的权利。从而对于职业体育行业协会而言,在它设定处罚规则时也就不能对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作出行业罚则的设定加以限制或剥夺,此即职业体育处罚规则在权利让渡上的边界,是设定处罚规则的红线。
2.3 体育罚则效力对象的合法性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职业体育行业协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制定的处罚规则的效力可及于哪些主体?处罚规则效力涵摄的主体范围止于哪里?哪些主体不在体育处罚规则的效力范围之内?
中国体育行业协会是中国境内从事体育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它对行业内的管理是一种行业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中国各单项体育协会与其管理相对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一种广义上的行政关系。按照行政法原理,由于形成了这种行政意义上的管理关系,职业体育组织对其成员(管理相对人)的处罚才具有正当性,而处罚规则的效力则取决于这种规则的性质。从契约理论上说,职业体育组织是一种契约性共同体,职业体育组织的内部治理本质上属于契约自治,所以,职业体育组织制定的自治规范的正当性应建立在成员的合意或同意基础上,同时也决定了这些自治规范的效力也只能及于与职业体育组织形成契约性关系的社会主体。换言之,如果没有与职业体育组织形成契约性关系,它就不是职业体育组织的成员,职业体育组织的自治规范(包括处罚规则)就对其没有规范的约束力。职业体育组织之所以成立,也是因为这些职业体育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契约性关系,在这种契约性关系中,职业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成员的部分权利让渡。非職业体育组织成员因为没有对职业体育组织让渡权利,其既不能享有共同体内的权利,当然也不必负有义务,自治规范也就不能对其产生规范效力。这就是职业体育组织设定处罚规则的效力边界。在中国,与各单项体育协会形成契约性关系的相对人(这里借用行政法中“相对人”概念更有针对性)有:会员协会、俱乐部、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经纪人、管理人员等。比如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2011年)第四条规定,其处罚规则效力主体有:(一)中国足球协会所属各会员协会;(二)各会员协会所属成员,尤其是俱乐部;(三)运动员;(四)官员;(五)经纪人;(六)比赛官员;(七)中国足球协会授权的任何人,尤其是和中国足球协会组织的比赛、赛事或其他活动相关的人员。①
现在我们再用这种行业契约性关系理论去分析中国足协诉《无锡日报》案事件就会发现,中国足协在2006年制定颁布的《全国足球比赛新闻采访规定》中第7条有关记者义务的处罚规定就有越权“立法”之嫌。因为该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发现记者制造、散布、刊发假新闻,影响干扰赛区、球队工作的记者,中国足协有权给予批评、警告直到收回其采访证。也就是说中国足协可以对“违规”的记者处以批评、警告、收回采访证的处罚措施。但是从主体的性质来说,中国足协仅仅是一个行业组织,它进行行业管理的前提是要相对人与之形成契约性关系。然而,记者群体并没有加入中国足协,他们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也就不可能与中国足协形成契约性的管理关系,因而中国足协制定的处罚规则的效力不能及于这些非中国足协会员(即记者)。如果有关记者出现了违纪行为,那也应该由中国记者协会来处罚,而不是中国足协,因为记者与记者协会才形成行业管理关系。因此,从立法理论上说,中国足协根本没有权力来制定针对非足协成员(如记者)的自治规范,此处针对记者制定的《全国足球比赛新闻采访规定》欠缺“立法”的合法性基础。
3 职业体育罚则设定的合理化
对职业体育处罚规则的设定,除了要稳妥地将其把握在边界之内,以防止出现合法化危机,还需要考虑其设定的功能化、专业化、正当化问题。这些问题均属合理性范畴,但处罚规则设定合理与否影响着规则适用的有效性,这里的有效性又直接反映着职业体育行业的自治能力问题,所以这里的合理化仍属于法治化问题,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种良法状态,法治化本身就是合法化与合理化同时并行的努力过程。endprint
从规则的功能化来看,设定处罚规则时要掌握适当的“度”,这就要求对职业体育处罚规则的设定既不要过于苛严,但也不能过于软绵无力。过于苛严的设定会使行业的自治功能发挥不出来,因为行业的自治管理是以成员的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对自治规范的自愿遵守,过于严责的处罚规则很容易使职业体育行业组织蜕变成纯粹的暴力执行机构,有损行业治理的自愿合作初衷,成员对它的自愿合作度也随着减损,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也会随着减弱。但是如果处罚规则设定过于软弱则又容易滋生机会主义,同样不能发挥其治理功效。当然,对这个“度”的把握又是一个很复杂的实践理性问题,需要职业体育组织的“立法者”根据各单项体育项目的专业特性来设定。
从专业特性看,职业体育处罚规则的设定应贴合职业体育的专业特性来设计,这样才能增强处罚的有效性。不同的体育项目有不同的专业特性,因此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育项目特性来设定处罚方式的多样化。有些竞技性体育项目需要比赛双方同时参与才能有效进行,如球类项目的比赛,针对此种特性可以对此类运动中的违规行为设定一些能影响其参赛能力或结果的处罚方式,如取消比赛资格、扣分、直接判定双方胜负、取消比赛结果、比分作废等。很多体育项目具有即时性特征,因此可根据这种即时性特征对比赛中的违规行为设定一些能影响违规者即时参与比赛活动的处罚方式,如足球、篮球等项目中的禁止随队进入比赛场地工作、罚令出场(红牌)、停赛、 禁止进入运动员休息室/或替补席、 禁止进入体育场(馆)等。这说明,越是能根据体育项目的专业性特征来设定处罚规则及其方式的多样化,其处罚的效果就越能显现,就越能增加职业体育的自治能力,发挥行业的自治功效。
职业体育罚则设定的正当化是尤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有关正当性概念,我们比较认同这种定义,正当性一般是为法律、法治及统治秩序尋求道德论证[7]。如果说正当性是一个静态的词,那么正当化就是一个动态词语,它是一个过程,是对制度(如法律等)、法治、统治秩序进行道德论证的过程。按照新修辞学的观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8]。说服的判断准则取决于其中的道德论证能否获得民众的同意或认可。职业体育组织设定体育处罚规则的正当化过程也是一个说服论证的过程,对于契约性的职业体育组织而言,其最低限度的正当化是要取得共同体内成员的同意或合意认可。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经过法治过滤的正当化仍然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职业体育行业组织也一样,它不可能在真空中存在,它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它还需要在社会中接受法治的审查,这个过程就是法治正当化过程。
3.1 职业体育罚则设定依据的法治正当化理解
必须指出,职业体育罚则的设定应以自治章程为依据,而不是法律,这是正确理解职业体育罚则设定依据的前提。《体育法》已在第49、50条中确认了这种合法性依据。但是如何在法治的限度内把握职业体育行业协会“按照章程规定”去设定处罚规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既然法律授权职业体育行业协会按照章程进行设定,那就意味着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设定处罚规则是职业体育行业协会的自治权问题。由于职业体育行业协会的契约性,其设定处罚规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体育行为的共公利益,维护行业组织的管理秩序,因此,职业体育行业协会设定处罚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就是它能否获得组织成员的同意和认可。只要这种罚则的设定符合章程的规定,又获得职业体育行业协会成员的同意和认可,且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其就属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我治理问题。因为法律已经授权了职业体育行业协会可以按照章程规定来进行处罚,那么职业体育行业协会就可以在章程规定范围内实行“自主性”自治,只要处罚规则的设定经过了组织成员的“合意”选择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它就是法治认可的“自主自治”问题。
但是,这里的“不违反法律规定”不等于说对职业体育罚则的设定一点都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这无疑会束缚行业自治效能的发挥。我们认为,只要职业体育行业协会根据体育规律进行设定的罚则,而且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它仍然具有设定的法治正当性。因为职业体育行业协会设定处罚规则的事由最重要的是如何根据行业特点富有成效地通过制定处罚细则来把自治章程中所要达到的自治效果发挥出来。要达到这种自治效能,就必须赋予职业体育行业协会必要的自主治理权能,使职业体育行业协会能在法律划定的界限内自主地根据行业特性来设定处罚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业体育行业协会自我管理效能。这样做不但没有违反体育自治规则以宪法和法律为上位法的法源位阶关系,而且这正是宪法和法律等上位法所肯定和认可的行业自治问题。因为行业自治的本意就是指在尊重宪法和法律等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根据行业特性来实行自我管理的,如果没有一点“创设性”的自主治理,那就不是行业自治了,与法律的直接治理无异。从法理上讲,职业体育行业协会的“立法”属于“自主性立法”而非“先行性立法”,也不是“实施性立法”。既然是“自主性立法”,那就应该给予这种“立法”一定的“自主空间和权限”,否则就不称之为“自主性立法”。基于此种理解,职业体育行业协会遵守上位法的参照标准是“不抵触”而非“依照”。不抵触和依照是两回事,“依照”的要求是下位法只能根据上位法来制定,没有上位法的授权,下位法不能“自己设定”而只能“依法作出规定”,显然这已经不是自治了。“不抵触”的要求是下位法可以突破上位法的具体规定而“自己设定”处罚规则,只要与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要求不产生冲突即具有合法性,这才是真正的行业自治。因为“‘抵触一词,在古汉语中意指冒突、顶撞。它的实质是要求合乎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朝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向发展,地方立法顺着这个精神和方向去补充、增添、延伸、完善,尽管不一致,甚至有了新规定,国家法律都是允许的,能容纳的,从根本上讲就不存在抵触的问题[9]”。但是,这里的“自主性立法”也不应该是完全的“自主”,如果已有作为上位法的法律规定,则这里的“自主性立法”仍然需要遵从法律的规定而不能与之抵触。那么,又如何把握体育行业的“自治性立法”与法律规定的“不抵触”关系呢?这里还需要运用“法律先占”理论来进行完善处理,该理论的最基本主张是,在法律与条例的关系上,“对于国家法令明示或默示先占的事项,若无法律明示的委任,即不得制定条例。[9]”依照法律先占理论,以下情形的条例与国家法令相抵触:第一,条例所规范的内容与国家法令的规定明显违背,如专属于国家的事务;第二,国家法令设有一定的规范基准,而条例与国家法令针对同一目的、同一对象时,条例设定了更高的规范基准;第三,国家法令对于某一对象已经进行了规制,当条例与国家法令基于相同目的时,条例的规定更严格,干涉程度更强;第四,条例基于国家法令的授权而制定,但是逾越了授权的范围[10]。这里的国家立法与地方条例立法的处理原则也可以适用于体育行业自治“立法”与国家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按照这种“先占理论”,只要国家法律已有规定,则应从尊重国家法的权威性出发,作为“下位法”的职业体育行业“自主立法”不能与作为上位法的法律规定相抵触。“不抵触”标准使职业体育罚则的设定做到了既对已有国家法疆域的尊重,对法律保留的治理能力给予信任,同时也能为行业自治的实效性提供施展空间,这正是平衡处理法治与行业自治的基点。endprint
3.2 职业体育罚则设定的程序正当化
在法治环境中,被赋予正当性的程序,应具备良好的功能,能使实体问题通过争辩、交涉的途径得到理性、平和的化解。在这一过程中,既能充分保证决定者应有的裁量余地,也能有效地限制决定者的恣意与武断,通过容纳、消化各方当事人的不同主张来增强结果的可接受性和決定的权威性[10]。职业体育罚则的设定也应当贯彻程序的正当化要求。这是因为,职业体育的行业自治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性管理,从应然性要求来看,对它的制定应该最大限度地把所有组织成员的意见吸纳进来。它的方法路径是利益各方代表要能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来,并且对处罚规则的设定要拥有表决权。一般来说,对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的参与方式有两种:投票制和谈判制。其中代表制为多数体育组织所采用,比如美国田径联合会(USATF)规章规定,下列人员在USATF会议上有投票权:1)董事会成员;2)USATF的5个委员会主席;3)USATF过去的主席们;4)外国运动员在代表总数的比例应不低于20%(第7条);5)USATF承认的会员组织,每个组织可以产生10名代表;6)每个会员协会产生12名代表,如果会员协会的会员超过1 000人,则每增加1 000人可再增加1名代表;每个会员协会的代表必须不少于20%是运动员,如有可能,这些运动员中至少有1名国际运动员;会员协会代表应包括教练员,如有可能应有高中教练员;会员协会至少还应选择1名成员来代表本协会); 7)其他组织每个组织产生1名代表。这里的亮点不在于它的代表的广泛性,而在于它为了保障每类代表成员的表决权而精心设计的代表员额规定,以确保规章的制定是真正的会员“合意”选择的结果。谈判制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这些体育组织的规则是利益各方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作为弱势一方的球员组织自己的自治组织——工会,代表运动员参与到体育组织中的谈判对规则的制定[11]。无论是哪一参与种方式,保证组织成员参与到对规则的制定是行业自治对程序正当化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国职业体育组织对体育罚则的设定不符合程序的正当化要求,或者说不按照正当程序来设定处罚规则,这样就必然影响职业体育罚则设定的正当性基础。其中,尤其不把受处罚相对人吸纳到对处罚规则的制定程序中来,几乎成为我国职业体育组织设定处罚规则的通病。以中国足协为例,它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就排除了中国足协纪律处罚相对人的参与。根据《中国足协章程》规定(第16、11、18条),只有足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司库、各专项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些工作人员和会员协会的代表对中国足协章程的制定拥有足协会员代表大会的表决权,中国足球的利益各方,如俱乐部、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经纪人等对章程中权利义务的分配没有任何发言权,俱乐部也只能旁听,不能行使表决权。总之,对中国足协章程的制定掌握在足协工作人员手中,而规则的相对人则根本没有权力参与其中。至于对章程以下的各种处罚细则的制定,则处罚相对人就更没有参与制定的机会,因为这些处罚细则的制定与修改压根就没有通过会员代表大会来制定或修改,它直接交由足协下设的某些机构或委员会来负责设定(如纪律委员会)。以“足坛刑法”之称的中国足协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的制定为例,从2004年以来,该条例已修改了七次,分别是2003年制定、2004 和2005年修改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办法》;2006年制定、2009年修改的《中国足协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2010 年制定、2011年修改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2015年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②,这七部罚则均以足协通知的形式发布。虽然从通知的形式以及内容中都无从得知这些纪律罚则的制定和修改的主体是谁,但是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在2010 年 2 月 23 日宣布对涉赌球队处罚决定时,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周明律师无意中的几句话却透露出了此类罚则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他说道:“在2010年2月20日,我们纪律委员会在香河开了一个会议,由7名委员参加,这个会议的议程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是对2009年处罚工作的总结和回顾,第二是讨论相关的处罚,第三是对现有处罚条例进行修订。[12]”这表明中国足协纪律处罚条例的修订者就是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可想而知,中国足协这些年制定的纪律处罚规定的正当性基础严重不足。从法理上说,既然惩罚规则要对相对人作不利的处罚后果,那么从正当性程序要求来看,就应该允许处罚相对人有机会参与到对处罚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通过理性商谈的办法产生规则,这样对相对人才是公正的,促使受纪律处罚的相对人从内心上体认这种处罚的尊重与遵守。需要指出的是,在体育罚则中,处罚内容相当严格,从警告到终身禁赛一应俱全,这些体育处罚不仅可以影响到相对人的财产和声誉,而且也影响到相对人的工作选择权,甚至是生存的权利。但是罚则的承受者(相对人)却没有机会参与到罚则的设定中来,这与法治的正当程序要求不符。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职业体育罚则设定的程序中缺少相对人的参与,就没有对职业体育组织形成有效的结构性制衡力量,很容易导致职业体育组织权力的扩大。
正当的体育罚则设定程序,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设定处罚和罚则的修改主体正当。以中国足协为例,中国足协罚则的设定应该由中国足球运动各方参与者共同制定。具体应该包括这些成员:1)中国足协;2)各地方足协;3)各足球俱乐部;4)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比赛官员和经纪人等,以及中国足协授权的任何人。上述四类成员,均属于足协处罚对象,理应让其共同参与对处罚规则的设定程序中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持该成员的利益。第二,在罚则的设定中应保证各参与主体的地位平等,制定或修改的罚则应经全体会员同意或认可。为了实现各主体的地位平等,有必要像美国田径联合会的章程规定那样,对不同成员的参与员额比率和投票权作出硬性规定,至少在规则的设计中有这方面的体现。
3.3 职业体育处罚种类设定的正当化
从理论上讲,职业体育组织基于自治管理需要在行业内设定处罚规则,只要经过行业组织成员的合意或同意就具有了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并不必然具有法律合法性,要使这种设定具有法律合法性,就需要从法治化视角来审视自治规范及处罚规则在处罚方式和内容上的合法性问题。endprint
首先要从社团罚则设定的惩罚权的权力来源来判定其合法性问题。根据社团罚则的权力来源不同,可把社团罚则分类为授权性罚则和自发型罚则。授权性罚则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行业组织在授权范围内设定处罚规则。因为这种惩罚权力来源于国家法的授权,是公权力在社团内的延伸,在性质上是一种“执行性立法”,即行业组织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设定细化的处罚规则,如拍卖师协会根据《拍卖法》的管理职权授权而制定的具体处罚规则即属此类。自发型罚则是指社团成员在合意或同意的范围内自行设定处罚规则,在性质上属于“自主性立法”。因为这种“立法权力”纯粹是自治意义上的契约性权力,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一致同意,而非外部权力的授予,因此,它在恰当的边界内就可自由地设定惩罚性措施的形式和内容。
虽然《体育法》授权体育组织对体育活动进行行业管理,但是这种授权只是一种概括授权(有别于具体授权),本质上并不是公权力的转移,而是法律对体育行业自治权的确认。所以,体育组织对处罚规则的设定应属于“自主性立法”,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就可以自由地设定处罚的方式、类别和内容。
其次,职业体育自治罚则不得对人身罚进行设定。人身罚对于个人的生命健康的侵害具有不可修复性,基于人权保护需要,这种权利具有不可让渡性。基于法治考虑,国家公权力独享人身罚的设定已成为共识,《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以及处罚,只能由法律(此处的“法律”是狭义上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法律)制定。《立法法》的规定表明,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能亨有制定限制人身处罚的规定,其他任何公權力机关如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权力机关等都没有权力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规定。这里,《立法法》对人身权作为保留规定,那么,作为社会私权力的体育组织是没有权力来设定对人身权利的处罚措施。
着眼于职业体育组织的“自主性立法”特性,除了人身罚具有不可设定以外,只要职业体育组织根据章程设定,不与宪法、法律的原则与精神相抵触,应该容许职业体育基于自治需要,自己发挥创设处罚方式与内容,并且,对其“创造性”设定应持鼓励态度。职业体育组织可以设定的处罚种类主要有如下几种。
1)声誉罚。由职业体育组织向违规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规行为,对其信誉、名誉、荣誉施加影响,如通报批评、公开曝光、号召业内抵制等,以引起其精神上的警觉。此类处罚着力于从精神层面或影响声誉方面设定处罚方式,这些处罚方式看似较为轻微,但对于职业体育组织受罚成员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借助于现代媒体(纸媒、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的传播力,体育活动越来越趋于全民化、娱乐化,一个稍微的负面影响就能通过媒介的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越是具有受众效应的运动员,或者民众喜欢的运动项目,声誉罚产生的功效越明显。基于这种考量,职业体育组织可以从专业特性出发,多设定一些声誉罚。
2)行为罚。是指职业体育组织限制或剥夺违规成员某些特定行为能力或资格的处罚。在所有处罚类型中,行为罚是与体育专业性产生关联性最强的种类,设定的种类最多,在体育比赛中的使用频率也最高。以中国足协章程设定为例,它设定的行为罚有:警告、停赛、禁赛、禁止随队进入比赛场工作、限制从事足球活动、扣分、判对方本场比赛3 ∶ 0获胜、取消比赛资格、取消公开比赛资格、取消主场比赛资格、取消主办或承办比赛资格、取消转会资格、降级、取消注册资格。可以看出,中国足协对行为罚的设置较为合理,从轻微的警告到轻量限制的停赛、禁赛、禁止随队进入比赛场工作、限制从事足球活动,再到中度严重的扣分、判对方本场比赛3 ∶ 0获胜,最后到最严厉的取消比赛资格、取消公开比赛资格、取消主场比赛资格、取消主办或承办比赛资格、取消转会资格、降级、取消注册资格,它的处罚严厉度呈梯级递增。基于行为罚是最能契合职业体育的专业性特性,职业体育组织应发挥积极能动性,创设性地设定结构合理的梯级行为罚体系。
3)财产罚。这是一种在体育运行中运用得最广泛也是最有效的处罚方式。它是指职业体育组织在其设定的处罚规则中规定违规成员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一定数量的物品,或者限制、剥夺其某种财产权的处罚(如退回奖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财产罚和法律中的财产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这里的设定不存在重复设置的问题,其在职业体育处罚中的设置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职业体育组织用自己的(财产性)处罚方式对这种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这种行为不仅(有可能)是违法的,而且在职业体育组织内,该种行业也是违规的,旨在表明职业体育组织对这种行为的否定评价,同时可强化成员对这种违规行为的责任,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成员行为的理性化。
不难看出,体育处罚种类繁多,方式多样,但最关键的是其能否够根据职业体育专业属性来设定,这才是职业体育组织在设定处罚规则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中国足协在根据专业化设定方面做得确实比较好,除了上述介绍的处罚方式以外,它还按处罚对象不同分为三种类型,即适用于自然人的处罚方式、适用于法人的处罚方式和可同时适用于自然人和法人的处罚方式。根据不同种对象设定不同的处罚方式,可做到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如仅适用于自然人的处罚方式有:罚令出场(红牌)、禁止进入运动员休息室和/或替补席、禁止进入体育场(馆)这些处罚方式只能适用于自然人,不可能适用于运动队俱乐部。而诸如进行无观众的比赛、在中立场地进行比赛、禁止在某体育场(馆)比赛、 取消比赛结果、比分作废、 扣分等则只能用于法人成员。
注释:
①其实,中国体育纪律处罚的对象还包括对赛区的处罚。
②相关资料均从中国足协官网中的“公告资料”下之“联赛文件”或“其他公告”栏目中查找,http://www.fa.org.cn/bulletin/index.html。
参考文献:
[1]陈健民,邱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J].社会学研究,1999(4):67.
[2]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注册[M].邓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14.
[3]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0.
[4]方洁.社团罚则的设定与边界[J].法学,2005(1):48.
[5]鲁篱.行业协会经济自治权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2.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38.
[7]刘杨.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辨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3):29.
[8] 解亘.正当化视角下的民法比较法研究[J].法学研究,2013(6):9.
[9] 孙波.地方立法“不抵触”原则探析——兼论日本的“法律先占”理论[J].政治与法律,2013(3):127.
[10] 李杰.刍议正当程序对于法治建设的意义[J].前沿,2011(14):91-93.
[11]韩勇.体育纪律处罚研究[J].体育科学,2007(4):88-89.
[12]“足协正式公布处罚决定 四队受罚蓉穗正式被降级”[OL].西部网,http://sports.cnwest.com/content/2010-02/23/content_2820539.ht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