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
杜思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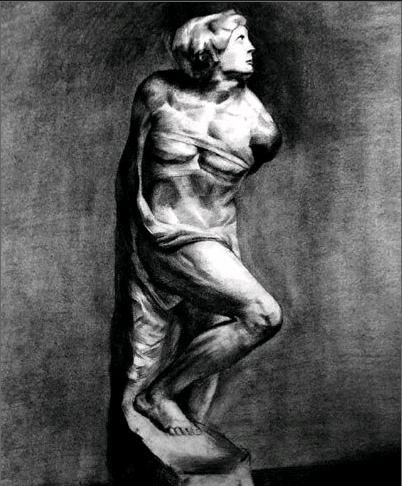
1984年的夏天,太阳毫无遮拦地喷出烈焰,夏蝉热得叫一阵歇一阵。
平时,乡村孩子最有趣的游戏,就是抱着一块生石灰石放到坑塘里,碳酸钙立刻与水产生化学反应,生发出巨大的能量,骤然冲出水面,冒出咕咕嘟嘟的热气,引发出一阵快乐的叫声。但是这个快乐的游戏那一天对于十三岁的我来说并不快乐,我和二十一岁的姐姐拿着铁锹耙子,在浑身冒汗的午后时光里,要把一大卡车生石灰全抛进水坑里,让它们经过反应变成熟石灰,用来盖房子。
那一天高粱刚刚收割,村民们弯腰弓背把一车车高粱拉回家。父亲给我和姐姐下的命令就是必须在下午把这些生石灰下完。我光着脊梁,穿着短裤,脚上蹬着黄色的呱嗒板橡胶拖鞋,在小山样的生石灰堆上一块一块向水中抛。午后的村庄,除了蝉鸣和我们抛石灰进入水中的扑通声,剩下的就是生石灰和水反应时发出的咕嘟声。一阵阵水泡从塘中冒出,缕缕热气在水面蒸腾升起一片白雾。坑塘像烧开的铁锅,咕咕嘟嘟。水里的鲫鱼、白条、泥鳅被沸水煮熟,随水波动荡而漂浮,一晃一晃的。
高处的生石灰被抛下去,一些地方的碎石灰要用铁锹来铲。我爬到高处,挥动铁锹向下铲,那些原本堆砌起来的石灰块突然如山体滑坡般向下倾泻,毫无防备的我随着石灰块向下滑。慌乱中,我急忙挪动双脚向上爬,可是脚上的拖鞋却不听使唤。扑通一声,双腿如同两根筷子直挺挺插进了沸腾的水塘里。“妈呀”一声惨叫,立时锥心刺痛传来,火辣辣深入骨髓。我不知道娘亲在哪,条件反射拼命地向岸边爬,爬起来一点却又接着陷进去。在坑侧边的姐姐听到哭喊声,大喊着我的名字“二娃”!向我奔来,声音里满是惊慌凄厉和恐惧。在沸腾的热气中,我看到了姐姐拼命伸过来的手,像拽住救命稻草似的紧紧抓住。姐姐趁势把我拽出了沸腾的坑塘。惊慌颤抖的她拉着我,哭喊着跑到路西边的小水沟,把我拉到水中,想用这里的水洗去石灰,降低热度。然后她又飞跑到石灰塘边,用耙子捞我的拖鞋。泪眼里,看到姐姐一边捞鞋一边痛哭。当耙子从坑里捞出橡胶拖鞋时,拖鞋软得像一坨面团。
姐弟二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惊动了村人。有人飞快回去喊我母亲。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了,只感到天昏地黑,双腿似乎还在滚水里面煮,在辣椒里浸泡着,一阵紧迫一阵的疼,似乎是铁爪子在剐削我瘦弱的骨头,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浪比一浪持久。有人跑到离村庄三里地外的诊所,喊我当医生的叔叔回来给我治疗。
那个炎热的暑假里,天气再热我也没感到,因为唯一的感觉就是疼。这种疼在之后的三天里,一阵紧过一阵,从大腿到脚趾头全是泡,层层累摞,腿弯处的皮肤烧掉了,露出里面的筋肉,膝盖上的肉已烧熟,腿肚处烧伤二度,皮肤一碰就脱。学烧伤的叔叔施尽看家本领,石灰烧熟的地方用镊子夹棉球清理了很长时间,头上的汗擦了一遍又一遍。可上了药,麻凉的烧伤药我却丝毫感受不到凉,叔叔说这是最好的药。水泡好治,熟肉只能让烂掉。在起初的两天里,我一眼没眨,不住地哀号。当时根本没有止疼药,我不知道有什么能止住痛。呻吟声、哭泣声在农村简陋的柴门小院里传出,一刻也没有停止。六十多岁当过兵杀过日本鬼子的守陈八爷来到家里,把父母狠训了一顿:“你们咋让二娃去卸石灰!咋当的爹娘!”父母无言以对,哪里能辩言。对于农村孩子,不干活就没有吃的。小脚八奶挪着小步子来到我家,安慰我道:“娃儿遭罪了!”
三天后,疼痛逐渐好转,痛感慢慢轻下来,但有些地方开始发痒,有时痒得钻心,伸手摸一下,立时又疼得冒冷汗。缠满纱布的伤腿,像两根白木桩弥散着药和腥臭的混合味道,让人恶心。我只能躺在床上,偶尔看看书来打发疼痛。每三天,叔叔从村外回来,带上烧伤药品给我换药。整个夏天,疼痛无奈和伤感包围着我,掺杂着失望和恐惧,有时,钻心的痒和痛交织在一起,让我想動又不敢动。每次换药时,金属镊子的触碰,都让我如触电般满身大汗,犹如死去一样,我只能咬紧牙关。每换一次药,叔叔总是慢慢解开绷带,揭去纱布,再忍着腥臭,蘸上酒精用镊子揭掉腐烂的死皮,用药棉擦去化脓的腐肉。深度烧伤的腿无法蜷曲,只能平放,没有麻药,没有止痛片。深达筋骨的三度烧伤,让我的左脚面至今有些粗厚的青筋隐露。
那一年闷热的夏季,我躺在农家粗糙的麦秸秆编织的蒿荐上,仰望长天,度日如年,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九月份开学了,伙伴们一个个背上书包上学了,我吃喝拉撒不能自理,只能躺着。两个月后,我才被大哥背进了课堂,在伙伴的照顾下学习。
当年的伤早已结痂脱落,但,那疼却清晰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