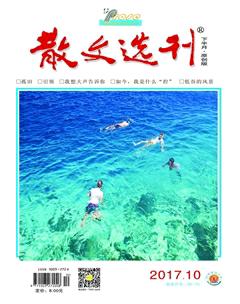一代风雅,从此终归不朽
罗胸怀

我的睡眠习惯大多是晚睡晚起,一般是七点多起床,今天奇了怪了,清晨五点就醒来了。看看窗外,在一片轻柔的雾霭中万籁俱寂,本想再睡上一会儿,可硬是睡不着,索性就起了个早床。一番洗漱,吃过早点,习惯性地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闲来无事,找出几个月前写的一篇小文《少日同窗侣》传到博客上。这是一篇追忆同学的文章,题目则取自钱钟书先生《寄祝許大千七十》。他的这首诗全篇如下:“少日同窗侣,天涯一故人。振奇风骨卓,坦率性灵真。早卜仁能寿,遥知德有邻。白头望好在,迹旷愈情亲。”
到了中午的时候,朋友圈有人帖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立刻闪现了一句话:“他们仨,终于团聚了。”
三十年前,大概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因为读《围城》知道钱钟书这个名字,继而知道他的夫人杨绛。说到《围城》,这部长篇小说问世于上世纪40年代,1949年后,一度绝版三十余年。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们这个小城的书店一个不起眼角落里。上世纪90年代,《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更多人是借电视剧的播出才了解到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小说,钱钟书也就此名贯天下。后来,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一个“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一个“守住门为他挡客”,足以认定和证明,他们对名利的淡薄,对内心的坚守。难怪杨绛曾感言:“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写的一部作品,作品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以及一家三口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也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她在书中说:“‘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她的《干校六记》讲述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杨绛夫妇受尽折磨侮辱,但整部作品并没有控诉,没有难抑的悲愤和无尽的哭泣。当她回首往事时,有的只是淡泊而深远的所感所思,以娓娓的诉说描绘着人世间的友谊、温情,以温馨的笔调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
杨绛在96岁高龄的时候,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初看这样的书名就有一种触及人的内心深处疼痛的感觉,打开书页弥漫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书中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记录了她对人的本性、人的灵魂以及人性中灵与肉斗争而又统一的思考。她在书中写道:“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傻蛋、笨蛋、混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恶人当权得势,好人吃苦受害。”有评论家称赞她:“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面对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如果说她的文字是人生的自问,那她用行过世纪的安宁与淡泊写出了自己的答案。生活中的她几近是“隐身”,低调至极,这种低调是本色的,是发乎内心的自然,不是给人看,更不是经过装饰。杨绛生活中不仅如此,在她的文字中也能找到佐证,那就是她的散文《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那莫过于一件隐于市的“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心于专用治学之事。
杨绛曾经翻译过英国诗人蓝德的《生与死》,流传甚广,虽说她不是原作者,但也无不是写下了她对人世最后最真情的告白:“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一代民国知识分子淡薄和从容以及与世无争的风雅,从此终归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