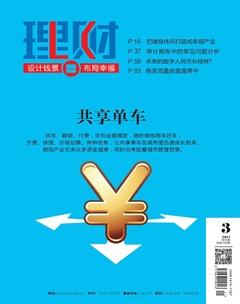古“三户”今考——范蠡故里是界中
刘宏羽
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家鼻祖”的范蠡,其故里究竟何在,多年来国内学界众说纷纭。近年来,随着对范蠡研究的不断成熟,范蠡故里在南阳宛城的结论已被世人所接受。但其故里到底在宛城何处,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则系以于金献先生为代表主张的“黄台岗三十里屯”说,一则是以孙凤阁先生为代表主张的“瓦店界中”说。笔者则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笔者认为,“黄台岗三十里屯”说属于假借“三十里屯”村庄名和《史记》“宛南三十里”之说的推定,并无其他真凭实据,明显不能据此认定范蠡故里之确切所在。“瓦店界中”说则是建立在扎实充分的史料记载和实物证据基础上的科学判定,应该得到史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现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说起,以正视听。
一、司马迁的《史记》和袁宏道的《宏道日记》两部史学巨著的记载足以相互佐证“范蠡乃范蠡乡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此言即是说,范蠡的故里,在春秋晚期楚国宛城的“三户”。另一明代史学家袁宏道则在《宏道日记》中写道:“从林水驿(今瓦店)发,过光武故里,经范蠡乡,宛三户也。”从该处的史学记载不难发现,春秋时期的宛城“三户”,就是明朝时的“范蠡乡”。结合该两处的史学记载能够足以证明,范蠡的故里,春秋时期名字叫“三户”,明初“三户”改为“范蠡乡”。
二、孙喜公墓志铭和“古范蠡乡”匾额等系列实物证据的出现,能够确凿无疑地证实,“古范蠡乡”就是现今的南阳宛城区“界中”
界中古镇的孙氏家族早在1971年,曾出土了一块《孙喜公墓志铭》。该墓志铭现存放在界中村民孙满坡家。其制作时间是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距离现在已有417年了。此墓志铭一开始就赫然镌刻着“翁姓孙氏,字世美,西河叟其别号也,世居于郡之南界冢镇,古称范蠡乡焉……鸱夷子(范蠡自称鸱夷子皮)未尝呆于桑梓之乡,乃兹地历千有余岁犹垂其名不休”。该墓志铭的作者是朱诰(明万历十四年进士)。文中“界冢镇古称范蠡乡焉”,结合下文“鸱夷子……”,足以证明,范蠡故里就是今日的“界中”。
1955年,界中村11组村民孙道魁向大家公布“古范蠡乡”匾额一块。原来,该匾额曾镶嵌于旧时界中南寨门外侧,上面刻着繁体楷书“古范蠡乡”四个大字,落款为“清乾隆二十七季(年)桂月立。”此匾额从前遗落在界中小学门前的水坑里,妇女们常在上面洗衣服,后被孙道魁先生搬回家用作红薯窖盖用,该匾额也因此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说起这块儿匾额,还有一段故事。界中原称“界冢”,因此地位于原南阳县与新野县交界处且有一土冢子而得名。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距今255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途经界中,夜宿界中南门外西侧华严寺里。寺中住持古道热肠,见客人精神欠佳,亲手煎制姜丝香醋茶以祛风寒。次日,乾隆爷龙体康健,行前重金答谢,住持坚辞不受。乾隆皇帝身感此地民风淳朴,遂手谕“免除界中三年赋税”和“古范蠡乡”四字匾额。有趣的是,乾隆帝书写时一不小心却将“界冢 ”误写为“界中”。因皇上一言九鼎,故从此“界冢 ”就易名“界中”至今。笔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该匾额在界中的发现,使范蠡故里就是界中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得到了又一历史实物的印证。
三、其他证据也都共同指向一个方向,亦即范蠡故里就是瓦店镇界中
除上述历史记载和实物证据能够证明范蠡故里是界中之外,笔者还发现,由孙凤阁先生目睹、探究并主持复修的“范蠡坟”正位于瓦店镇界中。时任清朝知府叶佩荪的《界冢范蠡庙》诗作名句“界冢何年少伯庐”,以及界中民谣“川林魏巍,淯水泱泱。唯我家园,范蠡故乡”的佳话,还有界中地名下方标注有“范蠡故里”的《清光绪年间南阳县境全图》均一致证实,范蠡故里确是瓦店镇界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范蠡故里是界中不仅有历史文献记载,而且有历史实物证据相印证。
盡管时代多有变迁,原先的“三户”名称也多有变化,但不变的是范蠡故里的地理位置永恒,此即现今的“界中”。其证据扎实充分,不容置疑,应该得到史学界和学术界的依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