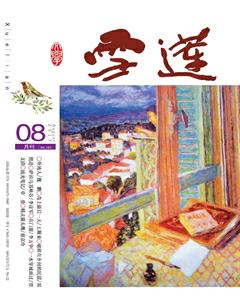长生椅
吃过晚饭,做灵屋的人就回家去了,爸爸跟往常一样去找朋友赌钱。黄小炜偷偷地拿了一支彩笔和一张纸。他躲在房间里,把那张纸裁成许多单片儿。
他趴在床上,铺开一张纸片,用彩笔抵着下颌,然后转头望了望窗户。窗户外面是一弯儿明朗的月亮,月亮旁边围着几颗影影绰绰的星星。他还听到山风正轻轻地吹着,吹得屋后的毛竹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接着,他便开始画了。他要画一条长生椅——这是从山里斫来几棵毛竹,剃去竹节,刳开,打眼,上好楔子,做成的专给临终的老人用的躺椅。这种椅很低,很平,两头留着方便抬动的长把手。
黄小炜五岁时,见过七古佬的儿子和媳妇把他放到长生椅上,抬到大门口晒太阳。七古佬躺在长生椅上,像一架傀儡,一动不动,涎水从唇角溢出来,把衣衽浸得湿湿嗒嗒,儿媳就往他脖颈围上一条毛巾。一天里,儿子会给他翻几回身,转几回向,到了夜晡,再抬回房间。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黄小炜记得,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老人躺在长生椅上。他还小,胆子不大,半夜里梦见七古佬流口水的样子,还有他那双眼屎糊糊的眼睛便哭着惊醒过来。这时,奶奶会轻轻地有节奏地拍他的后背。黄小炜没有妈妈,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听奶奶说,在他脱奶那年的八月节,村里请过一个山歌团,他妈妈山歌唱得好,台上台下对过几回荤荤素素的歌子,八月节过后,山歌团离开了,她妈妈也就跟着跑了。
黄小炜七岁时已经略略懂事,胆子也稍稍大了些。不过岁月却把奶奶的一头黑发全染成了雪白,她的手背也跟裹了层松树皮一样,皱得要剥落下来。
奶奶终究还是奄奄一息地躺在了门板上。从此以后黄小炜就搬了一条矮脚凳坐在奶奶身边。奶奶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他记得奶奶以前总是好多话。从小到大,黄小炜就没有跟别的孩子去捉过虾,也从来没翻过螃蟹,不过爸爸脾气很差,黄小炜经常无来由地遭一顿打。“奶奶哟!奶奶哟!”他使劲朝奶奶的房间跑,一面哭,一面喊。奶奶把他揽在怀里,拍着他的后背讲讲古,说点往事。听奶奶说,她年轻时长得很标致,结过婚后,爷爷也一直待她很好。有一天,爷爷在门口剖柴,剖着剖着,就被不知哪儿来的一帮人抓去当了兵。爷爷被抓走时才二十出头。半年后奶奶生下了爸爸——可婆婆待她很不好,逢人就说,“做太婆,做骆驼”……那时候是大冬天啊,飞了一地的雪,门口的河也结了厚冰——
“咳——坐月子也得抱一堆衣服去河边,搬大石头敲开冰动手洗咧!
“……好冷的水啊!”每次讲到这儿,奶奶就免不了掉下几颗眼泪。
然后,奶奶会摸着他的头说:
“你爸爸一点子大的时候呀,很爱哭!白天哭,夜里哭,没停没歇,好不容易眯一会子,又要被哭醒过来。真是苦日子哟!种下了一身病……”
如果听了这些黄小炜觉得还不够,他就会让奶奶唱那首歌。黄小炜喜欢那首歌,而奶奶每回唱起它也不再落眼泪。奶奶唱一句,他跟一句:
“天乌乌要落雨”
“天乌乌要落雨”
“阿婆举锄要掘芋”
“阿婆举锄要掘芋”
“掘呀掘,掘呀掘”
“掘呀掘,掘呀掘”
“掘着一个大石头”
“掘着一个大石头”
唱着唱着,黄小炜就睡着了。
可是现在,奶奶就躺在他身边,一句话也不会说。
奶奶是从他六岁时开始变得很不记事的——不洗澡,也不换衣服,还经常用手抓菜吃——爸爸看到了,会把菜连着盘子一股脑儿扔到门口去,骂奶奶是神经婆,是老不死的害人精。后来,每次奶奶用手抓菜吃,黄小炜就会站在厨房门口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黄小炜看见爸爸来就哭得更厉害了。
“你个哭死鬼!”
黄小炜知道,说完这句话爸爸就会一巴掌盖下来,然后他的脸上会生出火辣辣一片热。不过这算不上是最严重的。他记得有一次爸爸抓住他,操起竹条就抽他的大腿——那是因为爸爸赌钱输了,加上喝了一点酒;而且那时候自己正在院子里放着纸飞机。就这样,他的双腿顿时爬满了一条条红印,让他瘸着走了好几天路。
不过,奶奶全不顾这些,照样一日一日痴呆下去。有一天,她竟搴着锄头给门口的一畦大蒜培土,土越培越高,差些儿埋了大蒜。爸爸气得直喷响鼻,骂道,“老不死的东西!有闲工培土怎不去后山挖墓圹!“然后抢过了锄头,一跺脚,锄头把儿就断成了两截。
村里的大人都说奶奶成了癫婆,见了她就问:
“玉金妹,今年几多岁啊?”
“四十五啦!”奶奶笑着说。“今年四十五啦!”
這种千篇一律的回答每次都要惹那些大人哄堂大笑:
“年年四十五……哈哈……真个癫嬤!哈哈……”
这个时候黄小炜就会躲在门后,从门缝里远远地看着奶奶站在那儿和笑她的人一起哈哈大笑。别人走远了,她还一边笑一边说,“四十五啦!四十五啦……”仿佛还有谁在跟她说话一样。
一天早上,奶奶磕磕碰碰地走出房间,跟爸爸说自己的眼睛坏了,看东西模模糊糊,就像蒙了一层薄膜。黄小炜对爸爸说,七古佬眼睛也坏过,到医院住几天就看得见东西了。爸爸说,送医院要花很多钱,人总归是要老的,眼睛也总归要坏,古时的人不动手术日子也照样过。就这样,不到半年,奶奶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着了。
爸爸一点儿也不担心,他觉得变瞎了反倒省事。
他从杂物间翻出一块破门板,横在两条长凳上,让奶奶躺到上面。
奶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小下去,会发出死老鼠一样的臭味,嘴唇也耷拉到了下巴,整天嗫嗫嚅嚅地说着听不懂的话。
黄小炜却照例一天天,从朝晨到夜晡,寸步不离地坐在奶奶身边。有时候他抬头望望天空。他看到天上的白云慢悠悠地,一朵接着一朵藏到了山后,然后又一朵接着一朵冒出来。有时候云朵里会飘出一个讲故事的奶奶,接着出现无数个奶奶……
可是,这些奶奶又突然消散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单调的蓝天。
有一天,奶奶的屎尿都屙在了身上。黄小炜并没有去叫爸爸,他踮起脚给奶奶翻身,可是他实在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大,结果擦得到处都是。爸爸回家后大为光火,黄小炜被提了起来,悬在空中吓得哆哆嗦嗦。
那天下午,爸爸并没有去上工,而是在院子里把奶奶躺着的那块门板锯了一个窟窿。奶奶的衣服也被脱去,换成了棉被。再把奶奶放到门板上时,她的屁股便对准了那个窟窿,而窟窿底下是一个大木盆。
半个月后,奶奶走了。
旧门板空落落地摆在那儿。
几天后,来了一个做灵屋的人。这里的风俗是,人老后要烧化一条长生椅和一栋灵屋,给底下的鬼魂享用。那人就在大厅里,把细竹篾编屋架,糊上彩纸,在上面描灶头,窗户,床榻。活做得很精,就连床头的戏水鸳鸯和勾金边的兰花也都看得清清楚楚。而那人把做活用的纸和彩笔都搁在神龛上。
夜已经很深了。
爸爸还没有回来。黄小炜再次望了望窗户,月亮躲到不知哪儿去了,星星也没了踪影,只有毛竹叶子还在发出响声。
黄小炜画了一张又一张。他画得很用心,一开始还画得不算太好,一张歪了点儿,一张太小了些,还有一张他觉得不够精致……不过总算画出了令他满意的一张。接着,他又端详了一会儿,觉得还缺点什么,便又画了一条毛巾——他已经很累了,很累了……明天他就会把满意的那张画藏到灵屋里头……如果声音也可以画出来的话,他肯定也会画上那首歌。不过没关系,至少奶奶很快就会有一张舒适的长生椅了——想到这儿,他便安心地睡着了。
【作者简介】黄建强,笔名一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有多篇小小说散见于《齐鲁诗歌》《当代校园文艺》等报刊杂志,曾获黄海文学短篇小说征文比赛优秀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