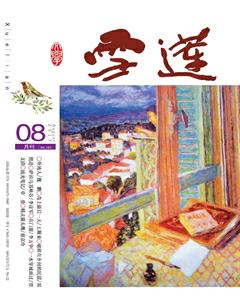外地人
她一个箭步,像亡命的兔子跳到了小船上。小船哆嗦了一下,船上的人也哆嗦了一下,仿佛寒夜里被谁掀去了被子,一哆嗦就醒来了。
一眼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本地人没有这身打扮。她脚穿方口青布鞋,青裤子,风衣也是黑色的,宽敞的衣襟一直垂到膝下,有点像日本的和服及古装戏里的服饰。一个半新不旧的绿色帆布包背在风衣里边,沿着风衣倒数第二个纽扣子地方,露出半个包来。那个帆布包不太鼓,也不太瘪,看上去好像有半包的东西在撑着。她齐耳短发,倒是那个时代乡下流行的发式。甜瓜子般的脸上似乎蒙着一层薄薄的风尘,看上去已不那么光洁了,仿佛用手一摸,就会留下指痕。两只眼睛也是失神的样子,就像流落街头的乞丐,似乎比乞丐还要迷茫。
外地人站在船尾,转身看看身后的路。那条路像蛇一样弯曲,从船尾向河岸蜿蜒而上,一直隐没在岸上的树丛里。树丛之外,还有天,还有地,还有她走过的路,但站在船尾的她,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苍茫。
外地人上船时,船上只有四个人。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孩子眼睛大得不成比例,头发枯黄得像一丛野草,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但孩子很懂事,偎依在女人的腿边,不时地喊着妈妈,仿佛除了喊妈妈,就不会说别的话了。女人身穿泛白的劳动布裤子,裤子的两个膝盖处,分别打上了长方形的补丁(补丁旧得已看不出是补丁了)。女人扎着一块灰布头巾,头巾有点像半条裤腿,把半个脸包得严严实实。
紧贴着船帮,摆放着两条条凳。女人和孩子,坐在一条条凳的一头;另一条条凳当中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中年男人脚边横放着一条桑木扁担和两个摞在一起的空筐。中年男人眼盯着空筐,眼里比空筐还空。中年男人低头弯腰,仿佛陶罐似的死灰色的天空一直压在他的头上。
摆渡的是个老汉。老汉的脸是方的,头是白的,身上的衣服是补丁摞着补丁的。摆渡人脸上的沟壑又粗又深,仿佛是用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沟壑里全是风声和水声。摆渡人的手心和手背一样粗糙,粗糙得像古树皮,裂纹里的灰尘怎么洗都洗不净的样子。此时,摆渡人两只粗糙的大手正捧着一锅旱烟,在有滋有味地吸着。
不用问,他们都是本地人,也都是渡船上的常客。他们的家,不在这岸,就在对岸,离岸不会超过十里。摆渡人住得最近,像许许多多的摆渡人一样,对岸河堤上有个四面透风的茅草棚,那就是摆渡人的家。
外地人站在船上向水里看,没有看到一条小鱼,没有看到一根水草,连一朵浪花都没有看到。河水不分昼夜地从西向东涌动,但在外地人眼里仿佛一动不动,连脚下的渡船也像钉死在水面上一般。外地人看了一袋烟的工夫,就抱着头,坐到了女人和孩子身边。
两袋烟的工夫,渡船上又上了三四个人。他们与船上的人打着招呼,嘴里说着“嗯”和“啊”。有的喊摆渡人“大叔”,有的喊摆渡人“大哥”,摆渡人蹲在船头,像木雕似地一动不动,只是“嗯”“啊”地应和着。听口音,他们也都是本地人,也都是摆渡人的熟人。
最后一个上船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男人脚穿一双黄球鞋(两个大脚趾头伸到了鞋外),肩挑两捆枯树枝。他把柴禾放到两条条凳的中间,也就是两个摞起的空筐两端,就扬起胳臂擦额头上的汗水。这时,外地人看到他的右额上有一条闪亮的刀疤,像一条虫子似地趴在眉毛的上方,眼看虫子就要滑落了,但始终没有滑落。在外地人看刀疤时,刀疤也看到了外地人。刀疤眼睛一亮,比刀疤还亮:“你是外地人?”外地人没点头也没有摇头,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仿佛没有听到刀疤的问话。
刀疤一时觉得无趣,心里虽然不爽,但脸上却笑了。一笑,脸上就多了褶皱,仿佛在刀疤的下方又爬上一条虫子。刀疤心想:外地人也许是个哑巴。也许不是哑巴,只是不愿开口,因为一开口,口音就会亮出她外地人的身份。
摆渡人猛地吸了最后一口旱烟,像做完一件大事似地磕掉还冒着火星的烟灰。烟锅滚烫,他就用烟锅烫了烫泛黄的脚趾,然后把烟杆斜插在腰带上,一声不响地站到了船尾。
摆渡人仿佛在等着刀疤,刀疤一上船,他就熄灭了旱烟,摇动船桨了。船桨啪啪啪地拍打着水面,像女人哄孩子似的,节奏匀称,不紧不慢。而条凳上的女人和孩子都把渡船当摇篮了,三摇两摇,就把母子摇进了梦乡。两只船桨在摆渡人手里轻如蝉翼,摇摆自如,仿佛孩子在摇摆玩具。
渡船一离河岸,水面就起了波浪。一浪赶着一浪,前浪刚一抬头,后浪就把它淹没了。紧接着,淹没前浪的后浪,也遭到了跟前浪一样的厄运,被又一道波浪所淹没。河水仿佛在做着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无休无止。越来越远的河岸像一面墙,墙上长满了荒草,草里有条毒蛇,毒蛇在草丛里出没。慢慢地,这面墙就变得越来越矮,越来越矮,最后变成了一条线。这条线也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多久,就低到了河水的下边。从渡船上向岸边望去,看到的是水面,水面,还是水面。
若是天空晴朗,也许还能看到河岸,也许还能看到河里的落日,但那天已由晴转阴,是入秋以来的第一个阴天。天色比空筐男人的脸色还要阴沉。空气里都是水,水面上还是水,船上人管这种水叫水雾,或雾气,或雾气昭昭。如果这雾再浓一些,就成毛毛细雨了。
阴沉的天空飞着几只水鸟,水鸟忽高忽低,有的从渡船上一掠而过,像燕子;有的在空中划着弧线,像岸边飞来的石子。水鸟的叫声单纯、细短,仿佛开头连着结尾,始终都是一个“啊”字或一个“了”字,耳朵还没有听清,水鸟就不见踪影了。外地人不认识水鸟,仿佛从没有听过这样的鸟语,她一会儿看水一会儿看天,把眼睛看成了两团水雾。
渡船像摇篮,在河面上摇着,摇着,仿佛已摇了千年,仿佛永远都摇不到对岸。摆渡人并不着急,仿佛他的一生,就是从渡口到渡口的距离。风平浪静也罢,惊涛骇浪也罢,晴空万里也罢,阴雨连绵也罢,都不能缩短或延长渡口到渡口间的距离。摆渡人不急,渡船人也不急,本地人也罢,外地人也罢,仿佛都是一身的清闲,谁也没有急着要办的事情,或是急着要辦的事情,在上船前都已办完了。endprint
刀疤似乎不肯闲着,一闲着就要惹是生非。他坐在外地人对面的条凳上,不时地抬眼看着外地人,目光透过一捆柴禾的枝梢,在外地人的脸上、身上扫来扫去,仿佛要扫尽全身的風尘。刀疤边扫边想:整个渡船上,就数外地人最有钱,上下的衣服竟找不出一块补丁。那个半新不旧的帆布包,也许装的全是钞票……外地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是投亲?是奔友?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的眼里只有水,只有雾,甚至还有一只飞鸟,但没有本地人,本地人似乎都不放在她的眼里……
好像是突击间想起什么似的(刀疤常会突发奇想),刀疤突然站了起来,夸张的动作差点撞倒了一捆柴禾。刀疤三两步就来到了摆渡人脚边,从摆渡人脚边端起一只白瓷碗(碗边掉了几块指甲大的瓷片,像狗啃掉似的),乞丐般地端到渡船人面前。本地人不用开口都明白,刀疤在替摆渡人收过河费了。白瓷碗里已有三五个大大小小的硬币,硬币底下还压着一毛钱的票子。
一个本地人向破瓷碗里扔了一毛钱的票子,又拿起硬币把票子压住。又一个本地人也向破瓷碗里扔了一毛钱的票子,也拿起硬币把票子压住了。破瓷碗端到空筐男人面前时,男人才把空洞的目光从空空的筐上收回,又把目光定定地盯着破瓷碗里的硬币和票子,像看着半碗毒药一般。刀疤把破瓷碗晃了晃,空筐男人就从怀里掏出一张两毛钱皱巴巴的票子扔进了碗里,又从碗里拿回了一张一毛的同样皱巴巴的票子塞进了怀里,然后才拿起破瓷碗里的硬币,把两毛钱的票子压住。
不知是谁,一下子向破瓷碗里扔下了三五个大大小小的硬币,把破瓷碗砸得叮当作响。这声音毕竟是金属发出的声音,又悦耳,又冰冷,又响亮,一下子就惊醒了条凳上的母子。做妈妈的连忙掏出两个五分钱的硬币,轻轻地放进了破瓷碗里。破瓷碗在她面前晃了晃,并没有移开的意思,不但没有移开,反倒晃动不止,还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这一晃,大大出乎做妈妈的意料,于是她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刀疤说:“小孩子,也收钱?”刀疤端着瓷碗,比乞丐伸出的手还要固执,依旧在母子面前摇晃。“刚才坐车,都没收孩子的钱!上次过河,也没有收孩子的钱!不信,你去问问摆渡的大叔!”女人越说声音越高,但话一出口,就被一阵秋风给吹跑了,刀疤好像一句都没有听到,依旧端着破瓷碗在母子面前摇晃着。直到空筐男人叹息一声,把刚才从破瓷碗里找出的一毛,又重新放回破瓷碗里,破瓷碗才不再摇晃,才心满意足地移开。做妈妈的感激地看了空筐男人一眼,让孩子喊他一声“叔叔”,又让孩子连说两声“谢谢”。
当破瓷碗移到外地人面前时,外地人却视为不见,就像一些不愿向乞丐施舍的人一样,甚至还把头脸转过去,去看水,去看天,去看天空的飞鸟。刀疤很无奈,晃了晃破瓷碗就把伸出的手缩回了,但缩回不多会,仿佛缩回的拳头又伸了出去——刀疤再次把破瓷碗端到了外地人面前。这一次,外地人低下头来,看了看破瓷碗里的毛票和硬币,又摸了摸自己半鼓的帆布包,眼里的水越聚越多,终于像泪珠似地滴落下来,有一滴恰巧落在破瓷碗里的硬币上,打得硬币直想哭,却怎么都没有哭出声来。
破瓷碗终于移开了,移开后就没有再伸过来。刀疤不知道有一句诗叫“一枝梨花春带雨”,如果刀疤知道这句诗,他也会用这句诗来形容外地人的。外地人看到破瓷碗终于离开了,悬起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地上,眼里尽是感激。迷茫的目光回到了手上,手回到了膝盖上。膝盖轻轻地摆动着,痉挛般地摆动着……
刀疤把破瓷碗端回到摆渡人的脚边,像孩子玩过的玩具又放回到原处,只要放回原处就会得到大人的夸奖。但摆渡人对刀疤却没有夸奖的意思,摆渡人不知在想什么心事,好像没有看到刀疤把破瓷碗端走,也没有看到刀疤把破瓷碗端回。
河水静止般地流着。渡船在河面声飘摇,像只漂浮的野鸭。摆渡人弯着腰,像打拍子似地摇着船桨,船桨像渡船的两只翅膀,在水面上扑扇着,不时地发出“啪——啪——啪——”的声响,仿佛是抽打水面的耳光。
“船上有个外地人……”刀疤对摆渡人说。
“啪——啪——啪——”
“外地人身上没有一块补丁……”
“啪——啪——啪——”
“外地人的风衣里边有个帆布包……”
“啪——啪——啪——”
“外地人是个哑巴,一句话都没说,一分钱都没给……”
“啪——啪——啪——”
刀疤在破瓷碗边坐了下来,仿佛在替摆渡人出主意。他想:外地人不给钱不行!少一分都不行!其实,摆渡人很少向过往的行人要过钱,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他都张不出口来,每到收钱时,他也会变成哑巴。但渡船人都很自觉,过来过去都会向那个破瓷碗里放进一毛钱。有时放进五分,放二分,放一分,摆渡人也不计较,就是一分不给,他也不会张口要钱的。只有刀疤在船上,才会一分不少地替摆渡人收取过渡费,每人一毛,不管老人还是孩子,一分都不少。刀疤每次都能把钱收齐,当然,除了他自己,仿佛他替摆渡人收费,就是为了自己能省下一毛钱似的。
“外地人不给钱,就……”
“不给就不给吧!”摆渡人说,“你不也没给吗?”
“她是外地人,外地人装哑巴!”
“啪——啪——啪——”
“外地人不给钱也不怕,就把她带进茅草棚里,把她给睡了!”刀疤兴奋地说。
“啪——啪——啪——”
“你不睡,我睡……”
“啪——啪——啪——”
“就这么办!”刀疤摸着刀疤,刀疤更加光亮了。
“你敢!”摆渡人瞪着刀疤说,“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
摆渡人的话,刀疤没有听到,仿佛被沉闷的空气压进了水里。刀疤从破瓷碗边站起来,看到了对岸摆渡人住的那个茅草棚。此刻,那个四面透风的茅草棚对刀疤来说,犹如天堂。
渡船还没有靠岸,岸边就有人向摆渡的招呼了。
岸边有一个老妇人带着几个男人,男人还抬着一个难产的女人,正着急地等在渡口。渡船刚一靠岸,他们就七手八脚急急忙忙地把产妇抬上渡船。摆渡人一句话都没说,操起双桨就向对岸划去。船帮边的男人们,都把手伸进河水里,像鸭掌似地不停地扒水。
从渡船上下来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全都张大了嘴巴,吃惊地看着船桨在河水里扑腾。船上的产妇又哭爹又喊娘,仿佛爹娘死了似的,喊声和哭声在水面上飘来荡去,久久不肯沉没……
第二天,摆渡人就病倒了。
第二天,刀疤成了摆渡人。刀疤摆渡,仿佛只是为了等一个人,一个外地人……
当外地人再次来到渡口时,刀疤就把外地人带上了渡船,犹如带外地人进茅草棚一样,只是外地人的脚步不再犹犹豫豫了。
只是,渡船还没有划到对岸,就翻了。刀疤和外地人像饺子似地落进了望不到底的河水里……
又过了几天,摆渡人的病就痊愈了。
在下游二三里的地方,摆渡人找到了外地人背过的那个帆布包(帆布包绕到了伸进河水里的一支老树根上)。摆渡人打开一看,包里是没有颗粒的几穗高粱——高粱穗把帆布包撑了起来……
【作者简介】魏鹏,在《诗刊》《散文百家》《短篇小说》《雨花》《延河》《草原》《鸭绿江》《文学界》《上海文学》《天津文学》《陕西文学》《黄河文学》《绿风》《星星》《诗林》《诗潮》《扬子江》《诗歌报》《青春》《芒种》《文学港》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有作品获奖并收入多种选集。著有诗集《艳艳和她的姊妹们》《斑斓的日子》《魏鹏诗选》;散文集《缤纷世界》《寸草寸心》;随笔集《红楼梦人情事理》;小说集《白与黑》等。现为江苏作协会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