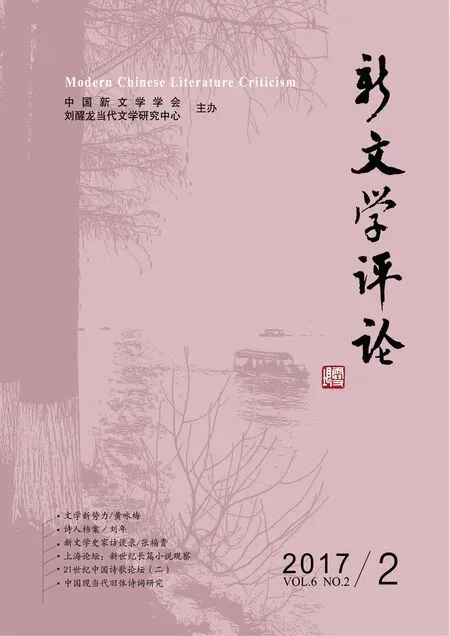新世纪女性诗歌形象的塑造及现实意义
◆ 尚 群
新世纪女性诗歌形象的塑造及现实意义
◆ 尚 群
新世纪女性诗人采取的个人化本真创作模式,使她们在诗歌中塑造了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呈现出女性诗人内部的多元取向以及话语差异。因而,本章重点针对路也、施施然、郑小琼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详读。从诗歌中女性形象塑造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角度把握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上的新走向。其中,路也通过塑造执着追求爱情的痴女形象,完成与后工业时代中人类尴尬生存境遇、精神困境的对话。施施然诗歌中所塑造的古典美女形象寄寓了诗人守护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求与信念。而郑小琼从其打工者的亲身经验出发,通过在诗歌中塑造一系列底层打工妹形象,反思当前中国劳工阶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一、 追逐爱情的漂泊者
黑格尔曾说:“女人把全部精神活动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尼采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女人理解的爱情十分明确:“它意味着全身心的、毫无保留的、不顾一切的奉献。这种对爱的无条件性让爱情变成了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女人在爱情中确认自我,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可以说,爱情对于女人而言具有等同生命的意义。因此,对爱情的追寻仍是新世纪女性诗人永恒的诗歌题材和生命主题之一。当前,情感上的迷惑已经成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的一个侧影。在个人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的主导下,我们学会了冷漠、敌视、猜忌,也变得冷静、追求精神独立。但爱却沦为人类生疏的体验,遭到放逐和冷遇。金钱社会扫除了包括爱情在内的一切多余的情感,女性被欲望俘获,在爱的名义之下,而甘于作为男性的他者。性也沦为人类麻痹自我以及宣泄过剩精力的工具。我们不是不想去爱,也不是完全放弃对被爱的期待,也希冀高贵、自由的爱情,只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和勇气,而这也是悲剧的深刻性所在。因此,女性诗人对爱情题材的共同关注,并非是她们视野狭隘,而是对当下女性普遍的情感困境的揭示。
基于对女性的情感以及命运的关怀与忧虑,路也在诗歌中更多地把在情感中陷落的主体设置为女性。她的爱情创作让我们看到飞速奔跑的眩晕时代中,爱情内部的复杂真实,从而构成对虚假、矫情的世界的无声抗议。但路也诗歌创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诗歌并非简单地呈现爱情这一单一维度。她以歌唱爱情为基调,把爱情书写上升为对女性群体的情感状况和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体意识、尊严问题的反思,更把爱情书写与自然书写相结合,在对人的身份进行反思和追问的同时,揭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命主题。从而,路也诗歌创作的重量以及难度就得以凸显。
路也在她的爱情诗中塑造最多的女性形象是毫无顾忌、豁出性命去爱的痴女。比如《外省的爱情》,“我爱你,我隔着中国最长的河爱你/隔着中国最雄伟的山爱你”。深情款款的女主人公大胆直白地向恋人表露炙热的爱慕之情,有一种对爱情的忠诚与单纯。在《还会》中,路也塑造了一个爱到极致,仍不由自主地去爱的女性形象。“怀揣着我的热情像怀揣着炸药包/千里迢迢地去寻你这根导火索。”而女主人公这份为爱献身的可爱和可怕的执着,这种跨越纬线和温度带的爱情,最终甚至“扰乱了气象云图/引起等降水量线的挪动和季风进退的紊乱”。在诗歌《我想去看你》中,路也写道:“我想去看你/我很贫穷/从今天开始要省吃俭用/攒足去你那里的盘缠……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要去看你/看你一眼就回来/从此以后死心塌地地/埋下头,继续孤孤单单/一天一天苟活下去。”从诗中多次反复提及的“我想去看你”到最终抒情主体坚定意志“我要去看你”,表现了女性主体战胜了内心的冲突与纠葛,直视自己的情感,为纠缠的情感做最后一搏。从“想”到“要”,更是呈现出抒情主体的情感冲突的动态过程。“我是一个卑微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路也诗歌中的女性主体在爱情上缺乏自信,自轻自贱。但这种以谦卑的姿态去挽留爱的方式,这种痴心的固守与灵魂的激荡,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女性主体异乎寻常的强大与高调。而这正如西蒙娜·波伏娃所说的:“女性不再逃避自我,而是发掘自我,在表面的贬低自我的内里,实质是在展现自我,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爱。这样,爱情对于女性来说,不再是致命的、危险的源泉,而是生命之源。”因此,即使在感情中受到了伤害,路也诗歌中的女性主体再也不扮演控诉者的形象,不再把男性视为幻想的敌人。在诗歌中,抒情主体即使已经知道“继续孤孤单单”的结局,也要省吃俭用,攒足盘缠去看“你”,既有坚守爱情的自豪,也有掩盖不下的难言的悲伤情绪。
如果说路也早期作品中常常塑造的是带有童话梦幻般的想象,等待爱情出现的女性主体形象,那么新世纪之后,路也诗歌中的女性主体的爱是成熟的女性之爱,褪去了少女的懵懂与羞涩,增添了一份豁达与宽容。在《结束语或者跋》中,路也写道:“在心里像勾掉罪行那样/狠狠勾掉一个名字/过去已经消失,来日屈指可数/我和他难得再见/如果偶尔在人群里相遇/要做到礼貌、客气、周到/互问‘你好!’”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对于爱情的渴望仍是溢于言表的,但诗人追求的并不是感情的圆满,而是强调自我在经历情感挫败后的成长,更要高度提升女性的尊严问题。爱情的挫败是生命中必经的历程,当爱情之火熄灭,女性主体不再哀怨叹怜,而是决然地发出自强的声音,预言自己今后与恋人再次相遇,定会“做到礼貌、客气、周到/互问‘你好!’”诗歌中的“空空地等呵等/像等铁树开花/像等沧海桑田”暗示恋人在这段感情中不对等的关系,女性主体在这段感情中受到了伤害。而诗句中的“狠狠勾掉”说明女性主体至今仍未平静,依旧耿耿于怀,但最终表现出一种不怨恨、不纠缠的豁达态度。可以说,这首诗歌在写出了女性主体曾经失落爱情时的沉痛、悲伤的同时,也传达出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的顽固与坚定,体现了路也在对爱情进行深刻体认之后的理性认知与把握自我的过程。一场痛苦的爱情经历,使路也完成对自我的质询、责问与确证。“没有谁值得我去把青春虚掷。”她开始有了警惕性的冷静、谨慎。正如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吕西·依利加雷所说:“靠近他,同时远离他。以一个完整的我回到自我。”女性只有在爱情中,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生命完整,才能最终获取自我生命的价值实现与精神提升。
观察路也的爱情诗歌,会发现诗歌中的女性主体大多处于寻爱的出走状态。对于她们而言,爱情并不是完全的归属所在,只有在充满清新温润的自然景观的江南,女性主体才能最终获取灵魂的归属感。可以说,诗人是采取恋爱中的女性视角去关注自然。与男性相比,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使她们与自然之间存在天生的契合与共通。而路也幼年时期短暂的山区农村成长的经历,以及成年之后偏远郊区的工作以及生活环境,更是奠定了她的自然之心的创作基调。

二、 传统文化的承载者




所以,无论是“民国”、“穿旗袍的女子”抑或“柳如是”、“青衣”,都只是一种符号,一种意象,并非实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华文化中某种精神内涵的隐喻,具有对现实生存的间接暗示性。在民族、传统、文化、语言被迅速掩埋的今天,在慢下来向后看的自觉中,施施然在吸收现代派诗歌的技艺和精华的同时,坚持民族化、个人化的本位创作,探寻既包含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创作技艺的汉语诗歌创新方法。她对诗歌的中国性的强调立足于全球化以及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把民族的生存历史、精神品质与现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进行对接,接续了民族的文化根性,在表达解构、重构当前社会的诗性愿望的同时,为重塑既已沦落的中国人的精魂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 社会底层的苦难者
当前,中国进入过度消费女性隐私以及女性身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按照资本运行逻辑,大众传媒塑造着“苗条”、“靓丽”、“充满诱惑”的女性形象,从而与其营造的富裕、时尚的都市图景相匹配。而这种中产阶级式的女性形象逐渐成为社会评判女性的审美标准,也构成了大众对女性群体的笼统认知。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更是映射出当前媒体对富人生活的渲染以及对穷人生活的忽视。在这样的文化生存环境背景之下,贫穷的“不可见阶层”的女性命运被忽略。在中国南方,上千万女工工作在自动化流水线上,她们面对的是每天都有可能被机器断指,人近中年失业、失婚的命运。然而,在大众传媒的喧嚣声中,这种日常生活中身份的“阶级差异”被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悄悄缝合。 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已造成新型的身份差异以及利益分配的失衡,城市执意且冰冷地拒绝给予进城务工农民以平等的身份。在他们付出了青春与健康,徒剩苍老的肉体与灵魂之后,只能打道返乡。这些曾为民族崛起而奉献血肉之躯的底层民众,这些促进中国城市飞速崛起的参与者,同样也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牺牲者。他们的命运在今天充满着辛酸与愤懑。
郑小琼在诗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为贫贱的、被压榨的底层女性。对她们极为艰难的生存景象的再现,对她们精神的消亡与病变的诉说,对她们虚无渺茫的未来的揭示,对她们生命的怜恤以及对她们的尊严的捍卫都构成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母题。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郑小琼诗歌作品的精神气质得以显现:她思索底层苦难的根源,使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忽视或者视而不见的处于社会边缘化生活空间之中的不可见的女性以及她们的生活浮出现实地表,进而代表沉积在社会底层而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劳苦大众发出向社会讨还公正与尊严的真切声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②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③路也:《山中信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④路也:《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 长征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⑤路也:《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 长征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⑥路也:《山中信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⑦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⑧路也:《结束语或者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567d701000947.html。
⑨吕西·依利加雷著,朱晓洁译:《二人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页。
⑩路也:《山中信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海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