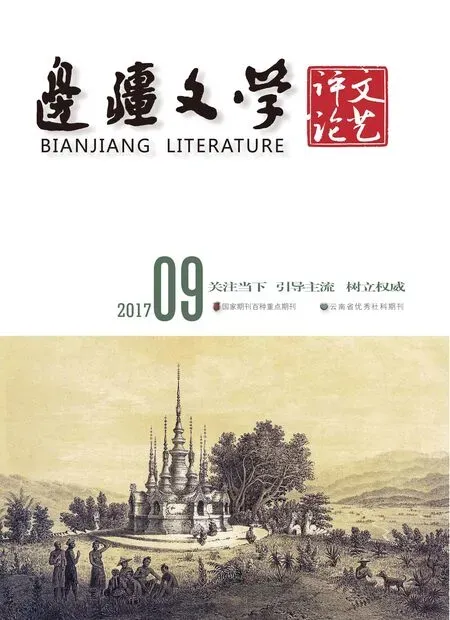文学应当引导人类仰望星空
张 伟
学人观点
文学应当引导人类仰望星空
张 伟
·主持人语·
文学评论与创作一样,都是用真心去体味真心,用善意去激扬善。本期推介的《用善良替灵魂赎罪》,就是通篇贯穿着正能量、传递着温暖和爱、昭示着舍己为人的善良的人性道德情怀。论者高度赞誉作家陈仓在用一颗善良的心书写着一部有温度的作品,用文字表达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其在创作谈中说到的:“善是一味药,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这种思想很有价值。余德庄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在生活的深水静流中会有更多令人惊艳的文学绽放!”也是很有意思的思想。(蔡毅)
一
从古到今,人类的生命都充满了诸多痛苦:必须在大地上长年挥汗劳作,才能够获取衣食;人与人之间充满欺诈、掠夺、杀戮和不平等;要受到无穷无尽的欲望的驱迫与煎熬,却又不可能都获得满足;要受到生老病死的折磨,最终回归尘土;作为一种有主体意识的动物,人类总有一种追问生命意义的冲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确定的生命意义,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追问生命的意义也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正因为人类有太多的痛苦,所以许多悲观主义哲学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的意义,认为人完全不值得活,生命是上帝赠给人类的最坏礼物。比如中国古代的庄子就是一位登峰造极的悲观主义者,他曾讲述过一个“髑髅见梦”的故事:“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之上,无臣之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可见庄子对人生的否定是多么彻底!古今中外为人类的苦难处境发出过悲悯太息的哲人还不知有多少。
尽管个体的生命旅程短暂、痛苦且终有一死,但人类毕竟还是战胜了一切苦难,繁衍下来了,并且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这固然是因为人类有顽强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意志,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还有一个富有诗意的理想境界,让人类的灵魂能够栖息其间,荡瑕涤垢,净化自身,获取勇气和力量,从而战胜苦难。这个诗意的境界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建构的。文学是人类痛苦的心灵中绽开的花朵,现实世界有许多的假,文学世界却有赤子之真;现实世界有许多的恶,文学世界却有最高之善;现实世界有许多的丑,文学世界却有无尽之美。能够在平庸、龌龊、痛苦的现实世界之外建构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之源。文学不同于宗教,世界各地的宗教虽然流派繁多,教义不同,但一些主要的宗教流派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告诉人类:一切皆苦,现世的生活没有意义,只有刻苦修行,皈依宗教才能获得最后的解脱,永恒的幸福。所以宗教尽力贬抑此岸世界的生活,而另外建构了美好的彼岸世界。宗教能让人类感受到天国的光辉,当劳苦抑郁时,可以仰望着冥冥的苍天进行祈祷。但宗教的彼岸世界是那么遥远,它的各种戒律又是那么严酷。当肉体回归尘土之后,灵魂究竟能否升入天国依然是一个谜,但这个渺茫的天国却让人类不得不忍受此岸世界痛苦的煎熬。所以除了少数意志坚定者以外,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如宗教家倡导的那样,做一个苦行者。文学却与此不同,虽然它也可以建构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但它却又美化着我们此岸世界的生活,使平庸的生活富有了色彩、诗意、情爱和美。可以说,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一方净土,对现实的龌龊感到悲观绝望的人们,可以在文学这一方净土里寻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有了文学,今人可以与古人进行精神对话;有了文学,足不出户的人们可以将思绪放飞到远方;有了文学,异乡漂泊的游子能够感受到家园的温馨;有了文学,住在茅草屋里的人们能够把屋前的小菜园想象成百花盛开的花园;有了文学,被爱情遗忘的灰姑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美丽多情的白雪公主;有了文学,陷身于罪恶泥潭里的人们也能感受到神圣的召唤,从而幡然悔悟,弃恶向善。文学可以直接描写并讴歌真善美,文学也可以通过描写并否定假丑恶来间接地讴歌真善美。古往今来,诲淫诲盗的作品并不少,但那种沉湎于假丑恶之中而看不到理想光辉的作品是不配进入文学的神圣殿堂的。如果不是在始终不渝地鞭挞着假丑恶,讴歌着真善美,那么文学早已死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作为一种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人类虽然不能彻底摆脱自身的动物性,并因此使得世间充满了假丑恶,但人类毕竟是天地间唯一具有精神性的动物,高度的精神性注定了人类身永远不会以不完美的现实为满足,正如诗人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内心必然要追寻真善美,则是毫无疑义的,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的动物,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冲动是不可能取得完全成功的。非但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甚至可能招致惨重的失败,这使得历史充满了悲剧意味。人类的心灵固然有可能因为悲剧而气沮,但不同样也可能因为悲剧而获得净化与升华吗?神秘的真善美之山啊!哪怕你的脚下倒下了一千名追求者,第一千零一名追求者又来到了你的脚下。莫笑世人的执著,因为这正是人类的特征啊!除非把心灵从人类的体内取走,使其只剩下一个躯壳,否则人类怎么可能停止追求真善美的脚步呢?如果停止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人类还是人类吗?文学是表现人类心灵的,又怎么可能不讴歌、不追寻真善美呢?正是因为文学能够建构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千百年来,文学一直在净化着人类的心灵,建构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使人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依然能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二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里,依然有作家在执著地讴歌着真善美。比如沈从文,他以一颗悲悯之心,建构了一个由青山绿水,白塔渡船,古老风俗以及朴素淳厚的人间情爱组成的充满自然美、风俗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其中还有最美丽纯真、执著专一的爱情方式。这个世界一出现,就获得了悠久的艺术魅力。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里,它宛如一个世外桃源,是战乱与饥荒中的人们心中的一方乐土。而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时代里,人类远离了自己的童年境界,在高速度、快节奏、世俗化、功利化的生活中精神无限焦虑,因而返朴归真的浪漫心弦不断在灵海深处奏响。湘西世界又获得了新的美学意蕴,它宛如一汪甘冽的清泉,滋润着现代人干涸的心田。又比如女作家冰心,她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时代里,依然用温婉的笔,讴歌着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正如她在小说《超人》中说的:“天下的孩子都不是彼此疏远的,而是彼此结合的。”这使她的作品成了一曲曲爱的颂歌。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与残杀使这种爱的颂歌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幼稚可笑。但不正因为如此,爱的颂歌才如此可贵吗?又比如徐志摩,在“一个荒歉的年头”里,不断地讴歌爱与美的理想,信仰“人与人之间互助的动机一定会超过互杀的动机”(《新月》发刊词)。为寻找爱与美的理想,他不怕“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冲入了茫茫的黑夜”,最后竟以身殉了。他的生命虽然如划过长空的流星一般短暂,但他留下的讴歌爱与美的清丽诗篇不是让许多心灵感受到了艺术的恒久魅力吗?
但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指出,由于时代的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真善美。文人们起初则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理想,将千百年来的无数哲人关于仁爱的训诫抛到了九霄云外,卖力地鼓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他们希望在人间建立天国,但根本不明白依靠血腥的相互残杀,不可能杀出一个人间天国。即使天国降临人间,也会被滔滔血河卷走。
其实人间就是人间,人间不可能建立天国,在人间进行天国实验,收获的只能是千百万人的尸骨和血泪。后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无数夫妻相互告密,朋友相互出卖,子女批斗父母,学生殴辱老师的事件,以及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知而又暴戾的青年发狂一般横行神州大地,使得无数人成了人间天国的祭品的惨剧,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那些擅长挑拨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的政治人物当然要负更大的责任,但作家们真的清白无辜吗?作家的责任应当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爱啊,为什么要讴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呢?为什么不干脆改行去充当刽子手呢?在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被发挥到了极至的时代,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却创作出了震撼人心的《古拉格群岛》,对人迫害人的现象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为人类的相互迫害推波助澜的中国作家们能不感到惭愧吗?
等到乌托邦理想坍塌,消费主义的时代来临后,作家们则又放肆地嘲弄一切的理想与崇高,以为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现世的感官享乐才是真实的。以《废都》而言,那就是一个肉欲至上精神颓败的世界,那里并不缺乏文化人,但那些文化人只会为了权力、地位、金钱、女色而进行无休止的欺诈与争夺。那里只有卑贱污秽,而没有高贵纯洁的心灵。其他大多数作家的作品也差不多,他们甘愿充当精神上的侏儒。与群星璀璨的古典文学相比,现代尤其是当代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却只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平庸、卑贱、狡诈、虚伪、堕落、残忍,却难以看到诗意的理想的光辉。当代作家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感悟和抒写真善美的能力,而几乎被污秽淹没了。或许这不全是作家们的错,是中国的现状本来如此,我们所处的本来就是一片干枯的荒漠。但作家难道不能把心中的真善美理想化做甘泉,从笔底滔滔流出,浇灌脚下这片干涸的土地,让它滋长出浓密似锦的花木吗?替堕落中的人类守护住一片精神圣地,是作家们的神圣职责,否则为什么要当作家,不去做商人、政客呢?
中国现当代文学什么都不缺,不缺狂热、血腥、淫秽、龌龊、卑鄙、无耻,独独缺乏一种执著地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品格,就像久旱的稻田缺乏霖雨一样。为什么现代文学不能向我们提供一个具有美好圣洁心灵的人物形象呢?也许后代的人们会把现代文学当作研究我们时代社会风貌与精神状态的资料,但作为文学作品,它们的生命将会是十分短暂的,也许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三
我们当然知道,在人类的宗教精神早已失落,乌托邦的理想也已坍塌,物质主义席卷天下的现代社会里,人心充满了卑琐的欲望和污秽的东西。人类整天追逐的不过卑俗的感官欲望的满足,已经没有什么高尚的精神追求了。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精神境界不但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提升,反而日趋污下,人性的丑恶面是赤裸裸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既然现代社会里充斥的是由污秽的灵魂里流溢出来的污秽言行,那么要文学完全脱离现实就是不可能的。以爱情而论,它本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无数的作家曾经向往它、追求它、赞美它、讴歌它。但在我们时代,爱情早已被性取代了。爱情本来也应当包含性的因素,这是我们承认的事实,但在当代社会里只剩下了性,爱早已不见了。当纯真的爱早已在人间消失之后,当代作家怎么可能写出爱情的美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中的污秽,不过是人心和社会的污秽的写照罢了。文学除非想粉饰现实,否则就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我们反感作家们粉饰现实。有一段时间歌功颂德的作品连篇累牍,泛滥成灾,将丑恶的人间地狱妆扮成了美丽的尘世天堂。时过境迁之后,此类作品终于引起了普遍的厌恶,被扔进历史的废纸篓里去了。但文学并没有回归真正的真善美,而是跳进了另一个污水潭里,乐此不疲地写放纵、写物欲、写堕落,挑逗读者的感官欲望,迎合读者的粗鄙心理,满纸龌龊。当然他们说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现实如此,文学也只能如此。但问题是,文学只需要实录现实的丑恶就可以了吗?
否!文学绝不能失去理想性,因为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如果仅仅是照抄现实,甚至以欣赏的态度来描写生活中的假丑恶,文学就只能为人性的沦丧推波助澜,而根本不可能净化人的心灵世界。现实可以是龌龊的,但文学永远应当是纯洁的。文学应当是淤泥浊水中盛开的洁白的莲花。《红楼梦》不是也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丑恶吗?但它却建构了一个无比纯洁的女儿国。如果文学仅仅是照搬现实,而没有更高尚的东西在里头,那么人类还要文学做什么呢?人类曾自诩为万物之灵,但一旦丧失了精神的追求,那么跟低等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
在现代社会里,有太多的东西诱惑着人类,使人类降低自身的尊严,甘心做粗俗欲望的奴隶,人心充满了冷漠、贪婪和丑恶。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学才更需要真善美。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冷漠、贪婪和一心追求粗俗物欲的人类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鸡虫得失以外,还应当有真诚、善良、淳朴等美德,应当有纯真的爱情,以及其他许多比物欲的满足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当人类的心灵被卑琐的欲望填塞了,变成了一个黑暗世界的时候,文学是可以照彻人心的一束普照光,如果文学都堕落了,那么人类的精神境界还有一丝一毫提升的希望吗?人性可以堕落,而文学却不能跟着时代一起沉沦,只要文学领域还保留着一份圣洁,那么人性就还有一丝提升的希望。如果文学也彻底沉沦了,那么人类精神将重新落入茫茫的黑暗之中,并永远沉沦下去。“哀莫大于心死”,难道这将是人类最后的结局吗?
这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假丑恶曾经把自己妆扮成真善美,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捉弄着愚昧的人类。而真正的真善美却被不断泼上了污水,以至于人类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真善美的存在。所以现代人类如同生活在一个虚无的荒原上,像幽灵一样漂浮着。作家也是人,有人的各种欲求,也有人的各种缺点,我们并不奢望作家们个个都是圣人。但毕竟创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作家们能够秉持良知进行创作,让作品中少一些偏激、暴戾、诲淫诲盗,让笔下多一分温暖、多一分情爱,多一些真善美。
即使是一个假丑恶充斥的鬼蜮世界,只要作家的心灵中有真善美,他也会在一个鬼蜮世界里开辟出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我们也必定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真善美。可怕的是作家完全被假丑恶同化了。
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统治的时代,人类的性灵在工具理性的重压下呻吟着;这又是物质主义的时代,人类沉湎于对物欲的追逐,似乎已经忘却了神圣的事物,也忘却了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而仅仅在物质世界里自娱自乐,所以需要一种力量把人类从平庸卑贱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人类能够仰望天空,仰望星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描绘过宗教衰落后人类的精神状况:“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从精神的如此易于满足,我们就可以估量它的损失是如何大了。”在一个人类的心灵茫然无归的痛苦时代,文学对真善美的讴歌,或许并不足以引导人类踏上通向真善美的征途,甚至只能给人类带来无名的哀愁、诗意的伤感。对人类的心灵来说,无名的哀愁、诗意的伤感也许是一种重负,但对人类的长远生存来说,它们也许并不完全是不祥之物,而是不可或缺的。当文学平面化了,再也没有无名的哀愁、诗意的伤感,乃至对于神秘命运的敬畏,那么生命将变得多么苍白!
在当代社会里,那些挑逗性的文字或许能引起轰动,真正的文学是寂寞的。真正为了坚守人类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人,就不要期待鲜花、掌声和其他各种世俗的功利。作家应当像夜莺在黑暗里歌唱一样,执著地讴歌真善美,讴歌人类古老的美德和理想,哪怕没有听众,也要为之呕心沥血,无怨无悔。只要有一个读者在读了你的作品以后,变得更纯洁,更高尚,更仁爱,更景仰真善美,你就功德无量了。我们的社会充满了贪婪与丑恶,人心需要净化。文学至少可以用真善美的光辉,照烛幽暗的人心,净化被贪欲污染的灵魂。文学应当引导人类超越尘世的得失,去仰望美丽的星空。

王光林 日常no.3 46x69cm 纸本水墨 2015年
(作者单位: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
责任编辑:杨 林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乡土小说创作研究》研究成果 类型:基础性研究,项目编号:2016ZZX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