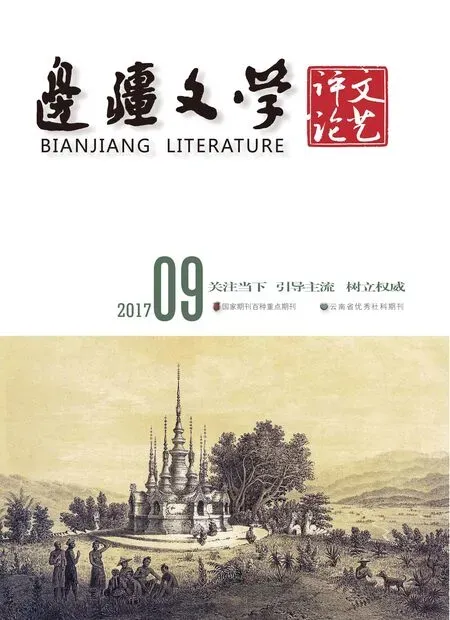论诗歌的外观审美结构
李 骞
理论前沿
论诗歌的外观审美结构
李 骞
诗歌外观结构是由诗歌的语言组合而成的审美结构艺术。诗人通过语言对外在物象进行复制,将自然物体中的外貌、骨架用形象的语言诉诸读者。从文本学的意义上说,诗歌是给人阅读的,但阅读的过程又包含有“看诗”的意义。因此,作为一种文字的排列组合,诗歌本身就有一个外观的结构形式。由于诗歌语言的能指功能比较特殊,因而我们读诗的第一个感觉是:这首诗是什么样的外观形式?也就是说,诗歌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由有序的文字组合而成的一个视觉空间的外在形状。因此,视觉美对诗歌外观结构形式的构成是极为重要的,诗的视觉艺术性也是诗歌技巧的一种创造。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由一视觉形象所传达的情感,必须像这个视觉样式本身的特征一样显得清晰。”意思就是说,每一首诗都必须表现出一种特定的思想感情和内容,所表达的内容又必须和诗歌的外观结构保持一致,而且诗的主题内容必然要超出诗歌表现的对象本身。当然,诗歌的内容是通过形式表现的,因而诗的外观形态对诗歌创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因而把视觉与诗歌结构艺术放在一起来讨论,对研究诗歌的艺术价值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视觉美不是“绘画美”,尽管绘画美可以带来视觉的美感,但视觉美的外延和内涵都较为丰富复杂。比如视觉美还包含有整齐划一的建筑美,包含诗的排列,包含诗的整体形象等内容,正是这些因素组合成了诗的外观结构。
一
绘画美是视觉美的重要条件之一。现代诗歌的绘画美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过,尤其是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新月诗派,他们都认真地提倡和实践新诗的“格律化”,闻一多甚至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美”的主张。从诗的外观形态上说,诗的视觉美是由画面最先构成的。古代诗论家们非常注重诗的直观感知和形象空间结构的造型,欧阳修主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情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意思是说,诗歌在叙写难于描绘的外在物象时,要让读者通过阅读感觉到所描述的景色如同在眼前一样,这样诗歌才可能有表达不尽的含义,读者才可能在字面之外发现还有更深的蕴涵。中国古诗论中的“视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绘画美,古诗中的“视境”是以看得见的画面来表现诗歌的艺术价值的。所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论及王维的诗时说道:“家辋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二者同一风味,故得水乳调和。”[3]这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绘画美的宗旨,也就是时间艺术的空间化。古人创作诗歌很看重物质的现实感,主张有固定的造型,明显的实体,强调感情状态的具体化。注重“情中景,景中景”的艺术境界和“以小景传大景之神”的形象描绘,这些都是诗歌视觉美的审美范畴。
外国文论家也重视诗歌的视觉美,波兰现象学研究者诺曼·英伽顿认为:“假定艺术家或观察者采取一种适当的行为,那么它们会使作品的具体化得到一种几乎是历历在目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从而使富于美学价值的那些性质的自我表现成为可能。”所谓“历历在目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就是指诗歌的外在视觉。尽管画是视觉艺术,诗是听觉艺术和想象艺术,两者有一定区别,但诗歌的精神必须通过艺术形象来完成,而形象的实体性特征首先应该是可观可感而又历历在目。诗和画尽管有着自己的艺术规律,但在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方面总有相通之处。诗歌是时间艺术,绘画是空间艺术,但是空间的绘画能够暗示时空观,而作为语言文字构成的诗歌同样也可以传递出空间的美学信息。优秀的诗人在“画境”的艺术表达上比较成熟,他们总是自觉地追求“诗中有画”的艺术形式,使作品达到虚实相生的韵味。如顾城的《诗情》:
一片朦胧的夕光
衬着暗绿的楼影
你从雾雨中显现
带着浴后的红晕
多少语言和往事
都在微笑中消溶
我们走进了夜海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诗歌中的绘画视觉,是由线条、构图、色彩三者共同完成的,这三个因素又是通过语言的言说传达出来。顾城的《诗情》借助诗歌语言的力量,勾画出清晰的线条,同时,又用绘画的空间艺术原理,描绘出鲜明、活泼的艺术画面。这首诗的构图十分精妙,前两句“朦胧的夕光”是诗,而“暗绿的楼影”则是画,两者互相转换,完成了诗歌的外形意境。同样,“你从雾雨中显现”的“你”所指的不是人的活动,而是一种诗歌现状,而后一句“带着浴后的红晕”,则是用色彩来描摹“诗情”的外在形态,“红晕”是象征雾雨后的感觉,这个词组映红了诗歌中的外在景物,将一幅“浴后的红晕”图推到读者的视野中,让“多少语言和往事”成为过去,“都在微笑中消溶”。最后一节采用静中有动的构图,行动和景色互相溶汇,具有中国画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我们走进了夜海”,如同画的框架,“夜海”是静的物象,“走进”是动感,同样,“繁星”是外在物象,“打捞”是一种行动,一动一静都被巧妙地组合在一幅幽静的框图之中,视觉的美感十分逼真。整首诗歌就是一幅静中有动的“诗情”图。“用景写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构图传统,有一种“意无穷”的美妙,而作品清爽的视觉美增强了诗歌的结构审美功能。由于诗中有画,所以作品中有一种“浮雕”的感觉。诗人以广角式镜头在静而远的空间构制图景,“夕光”、“楼影”、“雾雨”、“红晕”、“夜海”、“繁星”,这几组富有静态感的景物,镶嵌在一个整体框架中,呈现出一幅极富层次的视觉图景。
别林斯基说:“纯抒情的作品看来仿佛是一幅画,但主要点实则不在画,而在于那幅画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情。”外观视觉美的诗歌结构不是纯粹的画,而是由语言为媒介勾勒出来的艺术形式,因此,线条、构图、色彩所产生的画面感与诗歌中的画面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诗歌中的画面感是能够引起读者再创造的审美情感。由于整个图面是由富有弹性的语言完成的,因而诗中画面所产生的视觉美具有联想的审美空间。而且诗中的线条、图景、色彩与诗人的想象、情感有着紧密的联系。卡洛琳·M·布鲁墨认为:直线突然转折,会产生兴奋或狂怒的感情;而曲线和较为缓慢的线条,则容易唤起温柔、悠闲的情绪;方框有牢固、稳定的感觉;倾斜则是运动、变化的感觉。诗中的线条、图景、色彩是与读者的大脑打交道,也就是在欣赏诗的过程中,读者通过诗歌的语言感受线条和构图,经过大脑的审美过滤,形成一定的情感图形,再经过联想获得诗歌的绘画视觉美。当然,诗歌中的“视觉构图”一般来说不是十分明眼,但是只要认真阅读,却能够感觉到诗歌中有线条、有构图、还有色彩,甚至有音乐的流动。诗中的画是一种无形的画,全凭读者的审美感觉去揣摩。因为诗歌中的色彩不是对自然物象色彩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有诗人独到的审美情感,是观念的化身,是诗人“情感价值”的体现。如林徽因的《山中》:
紫色山头抱住红叶,将自己影射在山前,
人在小石桥上走过,渺小的追一点子想念。
高峰外云在深蓝天里镶白银色的光转,
用不着桥下黄叶,人在泉边,才记起夏天!
也不因一个人孤独的走路,路更蜿蜒,
短白色房舍像画,仍画在山坳另一面,
只这丹红集叶替代人记忆失落的层翠,
深浅团抱这同一个山头,惆怅如薄层烟。
山中斜长条青影,如今红萝乱在四面,
百万落叶火焰在寻觅山石荆草边,
当时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相信
那三两句长短,星子般仍挂秋天里不变。
这首诗的色彩繁多,一幅多色调的立体山水乡村图迎面扑来。诗中的带有色彩的物象有“紫色”、“红叶”、“深蓝”、“白银色”、“黄叶”、“短白色”、“丹红”、“青影”、“红萝”、“黄月”等,每一个色彩的符号都有着外在物象的背景意义。诗人从景物的表象提取出本质的色调来构筑诗歌结构的视觉美,诗歌中的每一个图形都是诗人以心观物的情感体验。
这是一首借山中秋天景色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全诗透过客观的秋景与主观的意念展开描写。第一节是写“自己”在紫色抱住红叶的山头独自漫步,当“自己”的影子在山前晃动时,眼前的秋色触动了珍藏于人生中的记忆,特别是“人在小石桥上走过”时,捕捉到昔日的“一点子想念”,而这个“想念”是来自夏天的故事。由秋天的色彩回忆夏天的情感,引出人生的无奈与渺小的感叹。第二节表层是写人在山中孤独的漫步,其实是暗示“自己”内在情感的寂寞。“也不因一个人孤独的走路,路更蜿蜒”,描述独自地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因为是一个人,山路显得更蜿蜒,因此人的孤独感有增无减。“白色房舍像画”只在“山坳另一面”,是喻指昨天的人生已经成为过去,而眼前外在的秋天物象“丹红集叶”成为自为“记忆失落”的替代物,在这样“深浅团抱”的山头上,惆怅的情绪“如薄层烟”缠绕在秋日的山顶,也缠绕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第三节表面上描述山中秋天的景色,实际是触景生情,由山中的景色引出夏天的“斜长条青影”。夏日山中林荫小道上的松萝、茑萝仿佛“乱在四面”,一点痕迹也找不到,而脚下的风景却是深秋的“落叶火焰”布满“山石荆草边”。那个迷人的夏日景致已经成为过去记忆,而眼前“天真的青年人情话”却如“星子般仍挂秋天里不变”。夏天的思念似乎很遥远,而眼前青年人热恋的情话成为秋天山中小路上的一道永恒风景。《山中》是一幅色彩斑澜的油画,自然的背景是深秋的大山,人文的背景则是“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画面色彩清晰,线条明白,诗人对山中秋色的深沉思考尽在不言中。读这首诗,有一种深沉的心灵感受,而诗中的画面所唤起的“秋色情怀”,有一种“冲然淡远”的审美效果。
线条、构图能表现诗的绘画美,但是比起色彩来又略逊一筹。因为绘画本来就是以色调来突出形象,而且从视觉原理上讲,色彩是最先进入人的视知觉的。所以,诗的绘画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运用明朗的色调唤起读者的审美视觉,力图在读者的想象空间,构制一幅色彩鲜艳的意境,通过画意来解释诗歌的主题。像林徽因的《山中》就是色彩调配得比较好的作品,是用多色调来完成诗歌结构的视觉美。诗人在多色调的秋天山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画中有景人有人,构图更是明显,几种色彩叠加出一幅“秋日情画图”,其诗歌的主题凝重而深远。
二
用对比色彩来构图也是现代诗歌结构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这种构图法容易引起读者的想象。比如满山的绿叶虽然显眼,但因为太多在视觉上就会感到太平常,但如果满山绿叶中有一朵红花,那就显得明艳芬芳,光彩夺目,诗中的构图更是显眼,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结构美感。当然,优秀的诗人在色彩构图上,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方法,而是根据诗歌的题意尽情发挥。有时,诗歌中出现各种颜色的组合体,用多种色彩来绘制一幅灿烂辉煌的外观结构图,这样,在鲜明的画面对比中就具有画中“神韵”的理想效果。
在构成诗歌视觉的各种因素中,色彩是主要因素,因为诗中的色彩绝大部分都是带有审美感情的,而色彩在视觉艺术上最能传达出诗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色彩的鲜浓、明暗能够影响读者阅读时的视觉感知,并唤起不同的情感。而且各种色彩的交替使用,诗歌的外观结构就会出“杂色图”的外在画面,色彩的美在诗歌的构图中就更为醒目,读者在视觉上就会产生深远而又绚丽多姿的美感效果。当然,色彩美是建立在自然界一切物体的色彩之上,但是,诗人对色彩的光线要有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要做到不仅仅是对自然色彩的简单临摹,因为客观物象所呈现的色彩是不带任何观念和情感的。在这个问题上,布鲁墨在《视觉原理》中说得更明白:“色彩唤起各种情绪,表达感情,甚至影响着我们正常的心理感受。”他甚至认为:“有些色彩对人们有着普遍的心理影响,但同时有些人对色彩的反映是专断的、个人的,或受社会影响。”诗歌创作中使用彩色艳丽的语言符号,能够唤起读者的感情经验,从而在诗歌构图的结构上就能够起到某种特殊的审美效应。因为在诗歌创作上,不同文化修养、不同审美感情的诗人,在色彩的选择上是有差异的。如冯至的《新的故乡》:
灿烂的银花。
在晴朗的天空飘散;
金黄的阳光
把屋顶树枝染遍。
驯美的白鸽儿
来自什么地方?
它们引我翘望着
一个新的故乡:
汪洋的大海,
浓绿的森林,
故乡的朋友,都在那里歌吟。
这里一切安眠
在春暖的被里,
我但愿向着
新的故乡飞去!
“新的故乡”是这首诗歌的中心意象,也是作品的结构骨架。但是这个骨架的审美信息却是由各种色彩传递出来的,由于对原物的准确复制抓住了被复制对像的整体特征,诗歌的外观结构因为色彩视觉形象的成功而转变成一个“新的故乡”的形象概念。作品的第一段是中心意象的外在描述,银白色的“灿烂的银花”在新的故乡的“晴朗的天空飘散”,这是故乡外部空间的视觉色彩,接着“金黄的阳光”由远而近,“把屋顶树枝染遍。”诗歌中“新故乡”由“银花”、“晴朗的天空”、阳光的“金黄”色组成,整个视觉形象完美而明显。第二节是对故乡往昔的诗意联想,是一种时间上的“新的故乡”的记忆,而这个记忆是由“驯美的白鸽儿”引起的。“白鸽儿”是和平自由的使者,不管它“来自什么地方”,都会“引我翘望着”思恋不已的“新的故乡”。接下来诗人用极富色彩感的两句诗告诉读者“新的故乡”的形状:面对蓝色波涌的“汪洋的大海”,背靠一望无际的“浓绿的森林”。由这两句诗构成的视觉形象的审美意义,向读者解释了“故乡的朋友”为什么“都在那里歌吟”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外部环境是那样的如诗如画。鲁道夫·阿恩海姆说:“只有当你获得里面的这些东些的视觉概念的时候,你创造出的该物体的视觉样式的外部形象,才能与这个物体的内部情况一致。”冯至的《新的故乡》的“视觉概念”与它的“内部情况”是同步协调的,诗人对“新的故乡”色彩描绘是一种对自然物象的模仿,而且这个被模仿的视觉形象所传达出的情感与视觉样式都一样清楚明晰。正是如此,诗歌的第四段才有了特殊的审美目的。因为“新的故乡”的一切都“在春暖的被里”安眠,诗人才立志要向着“新的故乡飞去”!诗人的这种内在情感真实地彰显了“新的故乡”的符号意义,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而这一切都是诗歌外观结构的视觉审美力量的原因。
色彩的感情意义和象征意义不仅因表现对象不同,而且还有诗歌的审美倾向包含在其中。现代诗歌对自然色调的摹仿,是根据诗人自己的情感进行选择,同时还要注意到读者的适应性,因为每一个人对色彩的经验和情感的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地方,但由于审美理想的差异,不同的色彩往往又暗示了不同的情感。诗歌中的线条、色彩、构图,都可以通过想象在阅读者的头脑中重新唤起可感的视觉画面,这种读者的再创造,实际上就是通过视觉式样对某些事物进行结构的再组合。当然,这视觉结构的再组合决不是对外部物象的简单复制,诗人用诗歌的形式再现客观事物时,不是机械地、原封不动地对所表达的对象进行复原,而是寻求隐蔽在视觉形象中的思想意识。诗歌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作品的任何形式都受诗人审美感情的支配。诗的外观形式是诗歌视觉美的最初表现形式,读者或批评家在阅读诗歌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诗句的排列组合在整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虽然现代自由体新诗不讲押韵,字数自由,节拍随意,排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框套套,但色彩的符号意义却超于了诗歌的外观形式,其可视性图画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如雷平阳的《晚秋的白色》:
山神的毛发白了,燕麦白了
西凉山的秋天也跟着白了
充军人的后裔,霜迹在脊梁上
白了,像冷风的胚牙
就要长大成冰凌
抽我肋骨,凿一根笛子
空我的胸膛,多一座粮仓
都白了,爷爷和奶奶住在山上
他们坟顶上的长草也白了
一层白土盖着,他们活着
像死者一样,白得彻底、荒凉
都白了,倮伍家的小妹空身下楼
高高山上,一盘月亮
我这汉人,一个打工仔,空手返乡
绕了一圈,眠于草垛旁
都白了,笛孔里的血滴儿
都白了,粮仓里的耗子骨
这是一幅“白”得耀眼的高原生活图,图中有历史、有现实、更有诗人内在的审美情感。这是一幅西凉山晚秋的完整图,厚厚的黄土地上,作为大山守护者的山神的“毛发白了”,地上的庄稼“燕麦白了”,甚至山里的秋天也“跟着白了”,充军者们的后代子孙裸露的脊梁不但“白了”,还会“长大成冰凌”。白色包围着南方的高原大地,诗歌中的词组“白了”作为情感的象征意义,是依靠诗人的联想而实现的。第二段“抽我肋骨,凿一根笛子”是诗人自我情感的介入,愿把自己的肋骨化为一种音乐的声音,在大山里吹响,而“空我的胸膛,多一座粮仓”则是少年饥饿的记忆。第三段是家族长辈的人生描述,爷爷和奶奶曾经住过的山上,他们坟顶上的草“都白了”,而他们活着的时候更是“白得彻底、荒凉”。第四段又回到现实,无论在山里守着“一盘月亮”的“倮伍家的小妹”,还是作为打工仔的“我这汉人”的“空手返乡”,在实际的生活中“都白了”。不同的是前者白富有诗意,“高高山上”有“一盘月亮”伴随着她,而“我”的“白了”是一无所有,只好“眠于草垛旁”。诗歌的最后一段是情感的高度凝集,也是前四段的总结,“都白了,笛孔里的血滴儿”是暗示自我的人生在大山上完全耗费,把精血都奉献给了故乡,“都白了,粮仓里的耗子骨”则是叙写了无论是人、动物,乃至所有的生命,都免不了最后的死亡。在诗歌中“白了”的色彩虽然荷载过重,但读者在强烈的“白了”刺激下能产生一种接受的兴奋美感,特别是反复使用“都白了”这一含义深刻而又层次分明的词组来暗示西凉山的色调,不仅强调了西凉山晚秋生活现实的突出性标志,而且将自我的人生经验内化到外在物象的描写中,让生命去感受这“都白了”的外在影像的美学力量。
在诗歌的外观审美结构中,诗人没有对外在的自然色进行鉴别,而且是根据情感的不同赋予它以相协调的色调意义。诗人用心灵去抒写自然物象的各种色彩,在情感的支配下,原来的色彩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人性的感情色彩。诗歌的视觉美有时还隐藏于视觉形象之中,视觉美往往还包容着一个深层次的审美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包含有诗人的感情、诗歌的色彩、诗诗歌的分行排列的综合形象。诗的视觉形象与绘画、雕塑不同,绘画、雕塑给人的形象是直观的,而诗的外观视觉结构却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达,而且诗歌中的这种形象不一定以人物、外在象物作为审美对象,而是在作品分行排列的过程中暗示出来。优秀的诗歌必然具有外在的物象和内在的气质,外在的物象直接呈现给阅读者的是形状,内在的气质则是指诗人的审美情感灌注于外观物象,从而形成诗歌的外观结构形态。诗歌艺术的精髓就是隐藏在外观中的内在气质,这个所谓“内在的气质”就是指隐蔽在外观视觉中的深层的审美形象。
三
色彩的时空叙事也是现代诗歌审美结构的艺术原则,由于人的视觉会在色彩的引导下行成一种时空观念,因此,诗歌的外观结构常常会在作品中不同时间的叙述中产生出新的诗性意义。英国结构主义学者特伦斯·霍克斯认为:“时间和空间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连续系统,没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疆界,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按照自己特有的结构来划分的解释时空世界。”色彩也是一种语言,诗人用什么样的色彩构图来改变时空的疆界,主要与他的审美素养有一定关系。但是不管如何改变,时空的轮廓总会在诗歌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展示出来,而这个轮廓的展现又与诗歌的分行、节奏有一定关联。由于诗歌的分行是最初给人感官上的印象,这个印象是视觉感知的初步审视,能否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关键就要看诗的分行的色彩美不美。当然,诗行的长短、分节,主要是诗人根据自己情感变化、情绪的起伏来调整的。诗行的排列实际上就是诗人的情感世界的一种外化。而且诗歌的分行、分节是不拘形式的,或长或短主要取决于作品中时空色彩的自由组合。用分行表现诗歌的外观结构,用什么样的色彩在分行中描写时空,与诗人对外在物象的感情表达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实际上色彩的力量并没有这么强大,但是诗人通过色彩的变幻来暗示某种审美意识时,自然的色彩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视觉感。
诗歌的外观审美结构形态如果与作品中的色彩协调一致,在空间上就会构成流动的视觉美,诗行的排列就别有一番诗味。特别是诗歌中表现的自然物象与诗人的主体审美情感融会贯通,并达到“物我同一”的效果时,诗歌的外部结构对所表现的客体必然进行审美定位,还原成一种富有质感的外观形式,作品的外观视觉美就更突出。如波德莱尔的《深谷怨》:
求你怜悯,你,是我唯一的爱恋,
我的心已坠入黑暗的深渊,
这是铅色地平线上的阴郁的世界,
是漂浮着亵渎与恐怖的黑暗。
无温的太阳在上空笼罩半年
其余半年只有黑夜覆盖大地;
这是靠近两极的不毛之地;
没有野兽,河流,森林和草原!
世界上没有任何恐怖超过
这冰冻太阳的残酷的寒冷,
和这古老混沌似的茫茫黑夜;
我妒忌最卑贱的动物的运气,
它们能够投入昏沉的睡眠,
我们时间的线纱却摇得如此缓慢!
这首诗的空间是“空谷”,时间是整整一年,“无温的太阳在上空笼罩半年”,而下半年则是“黑夜覆盖大地”,整个时空用黑色传达出一种令人压抑的情绪。在作品中,“色彩作为传达情感的力量获得了不断增强的独立性,它激起反响,无须借助传统形式。”作品通过黑色渲染,创造出象征的艺术效果,诗人“情感的力量”在一种审美表象的隐喻里获得了“独立性”表达。每一种色彩都会传递某种情感,《深谷怨》中的黑色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表现,诗歌中的“黑暗的深渊”、“恐怖的黑暗”、“黑夜覆盖大地”、“茫茫黑夜”,虽然都是同一种色调,但在诗歌的具体语境中又有不同审美情感的陈述。诗歌的第一段是一种黑暗世界的爱情表达,“求你怜悯,你,是我唯一的爱恋”,这是对爱的企求和呼唤,作品中“你”是被爱的对象,而“我”则是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是爱的企求者。“我的心已坠入黑暗的深渊”,表达的是求爱不得的一种内心世界的孤独和无奈,所以才感受到社会是“阴郁的世界”,而“我”的现实生活则处处“漂浮着亵渎与恐怖的黑暗”。第二段是时间的表达,上半年“无温的太阳在上空笼罩”,下半年“只有黑夜覆盖大地”,整个一年的生活都在无爱的时光中度过,成为人生的一种“空谷”,而这内心的“空谷”如同“靠近两极的不毛之地”,没有生命存在,“没有野兽,河流,森林和草原”,只有孤单的寂寞。第三段是一种超现实的表达,“我”的人生“空谷”是如此苍白,“世界上没有任何恐怖超过”,因为在这个空间里,太阳是冰冻的,现实生活如同“古老混沌似的茫茫黑夜”,而作为人的“我”,连“最卑贱的动物的运气”都不如,动物没有思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投入昏沉的睡眠”,而“我”因为生活中的“空谷”没有爱,在恐怖和黑暗的岁月里度日如年,感觉“时间的线纱却摇得如此缓慢”,生命的意义里除了“黑暗的深渊”之外,一无所有。
诗歌的外观结构除了色彩的作用外,句子的排列组合形式,从外观上也能唤起读者的强烈感觉,尤其是排比句的大量使用,更能增强感观印象。但从形式上分析,诗歌的外观结构特征必须借助诗歌语言的分行排列来表现,特别是诗歌的分行排列如同匀称整齐的建筑群,抒发的是一种整体的情感。诗歌的外在行列与内在精神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诗人的情感有一定联系,正是感情与形式的统一,使诗的分行成了有意味的外观结构形式。诗人有什么样的生活感受,就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但是诗人所选择的形式必然包含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尽管诗歌和非诗歌的区别从外观上的分行排列中可以分辩出来,但从审美本质上讲,诗的分行还是由诗歌传达的内容和诗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诗歌句子整齐划一的排列实际上是诗人对外在物象一种幻像,正如法国结构主义代表罗朗·巴尔特所在《结构主义活动》所说:“结构实际上是这个客体的幻像,而且是一个直接的、有利害关系的幻像,因为被摹写的客体使某种过去看不见的,或者说在自然的客体身上无法理解的东西呈现出来”。按照他的观点,诗歌分行排列时,就要对所表现的客体进行“幻像”,而且把事物的本质特征显示出来。诗的“幻像”是诗歌外观形式的重要标志,由它来向读者提供审美信息,使读者的心理活动产生一种与客观物体相类似的形体。一旦诗歌的外观结构切人读者的心灵,阅读者通过经验的自我认同,那么诗人用来阐述诗歌排列分行的外观形式,就会在视觉美上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人在分行排列上自觉地追求“行列美”的外观形式,自然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如闻一多的《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在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是作家闻一多先生的代表作,是一首外观结构整齐划一,而且彩色明显的一首力作,也是诗歌“三美”卓有成效的探索之作。作品的中心意象是“死水”,而且是“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作为诗人主观审美的一个“幻像”,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比如用“绝望”二字表达诗人对腐败不堪的旧社会现象的强烈不满;用“破铜烂铁”、“剩菜残羹”、“珍珠似的白沫”等意象暗示旧社会的不可药救;用“半点漪沦”、“绿成翡翠”、“几瓣桃花”、“一沟绿酒”、“几分鲜明”等不同色彩组合而成的意象复合体,表达诗人火热的试图改变“死水”现状的审美情感。总之,诗歌中有绝望、愤慨,也有希望“死水”早点死去,春水早日来临的慷慨激昂的激情。作品中的“小珠们”、“花蚊”、“青蛙”都具有各自的含义,“小珠们”是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隐喻“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之后的生存者的暂短快乐,但是这一点难得的快乐很快被破坏者“花蚊”咬破。在恶劣环境中唱歌的“青蛙”是“死水”现实生活中新的希望,是改变“一沟绝望的死水”的新生力量,但“青蛙”们的抗议最终还是未改变“死水”。正义的力量无法改变“一沟绝望的死水”,诗人怒其不争,以毒攻毒,“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至于丑恶者“造出个什么世界”,那是无法预测的。《死水》虽然暗含了一种呼唤自由美好的新生活的愿望,但是更多的是表达了诗人对丑恶现实的愤激情绪。死水之“死”,是黑暗的旧中国的总体象征,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憎恨是这首诗歌的主旋律。
闻一多是新诗格律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主张新诗要具备“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死水》是“三美”的代表作,全诗分五段,每段四行,每一行都是九个字,外形整齐,外观结构的可感性明显。每一段的第二行和第四行押大致相同的韵,读之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音乐的旋律美。诗歌中的许多意象色彩感强,外在物象在各种色彩的衬托下,具有绚丽的绘画美。总之,《死水》是色彩和句子的排列组合形成的力作,在分行排列上具有创造性的突破。当然,作为诗人情感的一种外化形式,诗的行列美所传达的审美信息毕竟有限,尽管结构主义把诗的分行看作是诗歌“定位”的标志,但是诗歌并不是完全靠“图像”取胜,再好的形式,再好的“图像”,如果没有诗人的感情参与,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再好的“图像”也代替不了感情。而《死水》则是外观行列美、图像美、诗人主观审美情感三者融汇一体的成功的新诗典范。
外在的形象美是现代诗歌所具备的美学特征,尽管诗歌视觉美的深层形象在作品中很难体会出来,但只要认真领悟,同样能够发现。从诗的本质特征上看,多维的抒情形象更能表现诗人丰富复杂的感情,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一个物体的形状,从来就不是单独由这个物体落在眼睛上的形象决定的。”这就说明,要描绘某一物象,单靠平面的叙述是不够的,尽管平面的抒情形象也有它的审美价值,但在现代社会,人的情绪已经由单一性走向复杂性。诗歌表达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社会环境,作为诗歌艺术的外在视觉结构,所传达的对象是丰富复杂的,所体现的价值功能当然是主体的全方位的。当然,诗人有时会用密集的意象来打破图画形象的单一性,让诗歌中的形象产生一种雕塑的美,用一系列富有质感的语言和群体意象,来完成对抒情形象的塑造,追求诗歌象征的多义性,并以此来完成形象的立体感,以求给抒情形象带来多侧面的立体美学特征。我们所说的抒情形象,当然是指诗人的审美感情与客观物象融合之后的复合物。因此,无论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都是诗人审美感情的显现。不同审美感情的诗人,诗歌中自然会有不同情感的抒情形象。但是,无论是平面的抒情形象还是立体的抒情形象,都是诗人审美化了的自我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诗中的抒情形象,就是诗人情感世界的表现。
视觉美作为诗歌的外观结构审美特征,是初次启发阅读者美感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每一首诗歌都能体现视觉美,因为诗人的情感有深浅之别。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诗人在技巧的运作上虽然圆熟,却因为情感的虚伪而缺少审美价值。“发乎情”是现代抒情诗的审美主题,这个主题的目的是否达到,全仰仗诗人对于语言的运作。只要诗人能自觉地将线条、色彩、构图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的视觉系统,作品就能抵达诗歌“发乎情”的内在意蕴的艺术境界。
【注释】
[1][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第213页,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2]欧阳修著,《六一诗话》,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卷第244页,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3]王夫之著,《船山遗书·夕堂戏墨》卷五,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本。
[4]王夫之著,《夕堂永日绪论》,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卷第301页,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5][波兰]诺曼·英伽顿著,《现象学美学》,王逢振译,转引自《最新西方文论选》第29页,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6]顾城,《顾城的诗》第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7][俄] 别林斯基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75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10月出版。
[8][美] 卡洛琳·M·布鲁墨著,《视觉原理》第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9]林徽因著,《山中》,原载1937年1月29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10][美]布鲁墨著,《视觉原理》第67页,张功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8月出版。
[11]冯至著,《十四行集》第3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12][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第210页,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13]雷平阳著,《雷平阳诗选》第7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14][英] 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23页,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15][法]波德莱尔著,《波德莱尔诗选》第74页,苏凤哲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16]R·S·弗内斯著,《表现主义》第21页,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
[17][法]罗朗·巴尔特著,《结构主义活动》,盛宁译,转引自《最新西方文论选》第106页,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18]闻一多著,《死水》,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1月出版。
[19][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第56页,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责任编辑:杨 林
云南批评家
·主持人语·
本期《云南批评家》推出冉隆中评论专辑,可能是一组比较好看的文章。冉隆中在本刊主持“争鸣广场”专栏,久而久之,其人其文,似也有所“争议”。比如自己明明置身在体制文联之中,却不时要在一些批评文章中,说点关乎体制文联、文人或作品的“怪话”——“叫人与鬼都惊诧莫名地吓一跳。”冉隆中曾一度将时间精力大量投放在“田野调查”的批评文本写作中,所发表的系列文章,也是引出大量的“好得很”或“糟得很”的声音。文学批评,或许也要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冉隆中的批评实践,可能会带给我们某些启发。(蔡毅)

冉隆中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评论家、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现任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创作出版的作品有《文本内外》《底层文学真相报告》《重九重九》等十多部著作,以及“从前有座山”、“早年间”、“中国传统节日绘本”等系列儿童文学作品二十多册。主编和策划出版《昆明的眼睛》《昆明读城记》《昭通文学三十年》《七彩云南儿童文学精品书系》《七彩云霞红飘带》等系列图书上百部。作品多次获得云南省文艺基金奖一等奖、云南省精品文艺图书奖以及《文学自由谈》大奖等。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