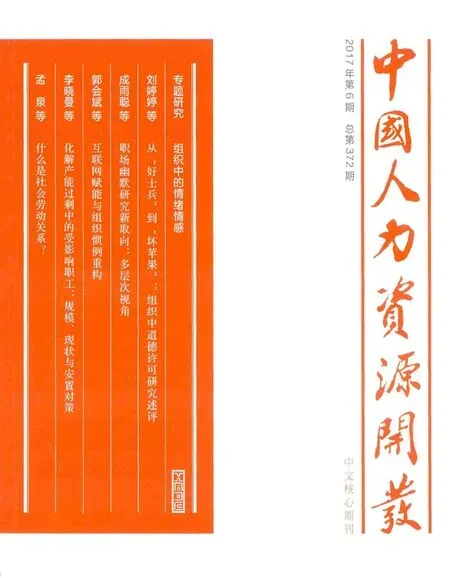快乐的音乐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中介作用
● 罗旖颀 苏方国 余子逸
快乐的音乐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中介作用
● 罗旖颀 苏方国 余子逸
现有研究大多针对在工作场所中音乐对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影响,但缺乏探讨音乐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本文聚焦在音乐对一个决策群体中人们采取合作行为的影响。基于两个扩展20回合的公共产品实验的研究结果证明,快乐的音乐对人们采取合作行为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情绪与合作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情绪在快乐的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音乐 员工行为 合作行为 情绪
音乐资源的用途非常广泛。例如,大量消费者行为领域的研究表明,在零售店,商店经理和广告商会小心翼翼地选择播放那些愉快的、会刺激消费者行为和态度的歌曲来尽可能增加商品的销售量(Munichor & Rafaeli,2007;Strick et al., 2015; Wansink & van Ittersum, 2012)。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零售店工作的员工也同时接触到了公司所选择的音乐,音乐是否对员工行为产生影响呢?正确音乐的选择除了可以起到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的同时是否能同时对办公场所的员工的某种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呢?音乐又是如何影响员工行为?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回答。
在工作场所中,人力资源管理者们最看重的莫过于是如何构建一支高效精良的工作团队了,而充足的证据表明,一个工作团队往往受益于同事之间的相互合作(Grant, 2013)。近来的研究也显示出一个组织的环境物理特征对促进合作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Ashkanasy et al.,2014;Kniffin et al.,2015)。Kniffin et al.(2016)就大胆的假设了快乐的音乐对员工的合作行为将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并得到了实验结果的证明。但他的实验被试局限在美国本土学生,忽略了各国文化差异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就是在改良Kniffin et al.(2016)研究的基础上检验音乐对员工合作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建立在两个主要理论框架基础上来理解环境特征与团体中个人决策的关系。实验1是建立在动态参与理论(DAT)基础上(Jones & Boltz, 1989;Large & Jones,1999)来检测是否同步听有节奏的音乐活动将大大有助于激发合作行为,而实验2是建立在情感事件理论 (AET) 基础上(Weiss &Cropanzano,1996),以测试是否被快乐的音乐所刺激的情绪与亲社会决策之间会有积极的关系。在原来的有关情感事件理论(AET)的介绍中,Weiss 和 Cropanzano 研究者已经列出了一系列会影响情绪的重要环境因素的目录,像温度、湿度、污染物和拥挤等。我们的研究恰好同时整合了动态参与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音乐从研究对个人行为到对团队合作行为的影响
关注临床结果的大量心理学研究探索了音乐对于个体层面的思想、感情和记忆的作用 (Houston & Haddock,2007; Weiss et al.,2012)。例如,临床企业的“音乐疗法”旨在利用音乐帮助人们克服一系列的心理挑战 (Gold et al.,2009)。用音乐帮助人们应对压力是另一种常见的方法(Ratcliffe et al.,2013),特别是在医院为病人播放音乐的设置(Devlin & Arneill,2003)或在顾客等待的时候为其播放音乐的设置 (Niven,2015)。同样,在营销人员中,他们熟悉使用“歌谣”帮助人们记住商店名称、口号或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音乐是被故意用来影响人们行为的(Yalch,1991)。之前的研究往往只关注音乐对个体层面的行为, 而Lang et al.(2015)的发现很有趣,因为他们发现有节奏的音乐似乎可以激活“人际关系运动耦合”,使得人们与合作伙伴的行为和态度更容易达到同步。
(二)对以往音乐与合作关系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回顾
一些之前的实验室实验已经探索了音乐与工作团队的潜在相关关系,例如,Brooks 和Schweitzer(2011)使用来自电影《惊魂记》的主题曲作为启动刺激用于研究情绪对谈判的影响,发现诱发型焦虑症的被试往往会产生次等的结果。Au、Chan、Wang 和Vertinsky (2003)通过让被试听一些冗长的、不重复的“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音乐来研究交易行为,发现人们面临不愉快的音乐时往往愿意承受更少的风险,获得更少的奖励,并在一系列模拟交易的研究中表现出相对较少的信心。Wiltermuth 和 Heath(2009)关注合作,在五轮决策实验中发现(i)听国歌可以增加合作行为(ii)与群体内部的陌生人同步一起唱歌可以进一步增加合作行为。Krahe和Bieneck(2012)同样发现,快乐的音乐可以让人们减少攻击性。实际上,实验对音乐的研究倾向于证明音乐能引起“有着温暖光辉的给予”,让人们参与从事利他行为并从中产生个人享受。
(三)假设发展
早期关于动态参与理论(DAT)的研究通常专注于基本模式如节奏和时间知觉之间的关系,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用不同方式探索节奏诱发的同步行为和一次性合作任务、感觉到信任和喜欢、整体的认知和运动技能之间的关系。例如Kokal et al.(2011)发现,当被试和他的合作伙伴同样成功地、有节奏的保持每节拍敲10鼓时比没有同步敲鼓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从事更多的亲社会行为。Launay et al.(2013)与Kokal et al.研究的不同是,它允许被试自由选择是否保持节奏,允许被试在随着音调拍手时可以与他的合作伙伴同步或不同步,最后发现与合作伙伴同步拍手的人相比与合作伙伴不同步拍手的人展现出更加信任他们的合作伙伴。采用类似的方法,Hove 和 Risen(2009)发现,那些被要求用他们的右手食指敲击与被试合作伙伴敲击同步的人比(i)与被试合作伙伴敲击不同步的人(ii)被要求与一个被试合作伙伴的节拍器敲击同步的人更倾向于喜欢被试合作伙伴。Valdesolo et al.(2010)则进行了一个更体能化的研究实验,要求被试两人一组进行跑步,被试可以选择与被试合作伙伴跑步时的歩幅保持同步或不同步,最后发现歩幅一致的被试者倾向于在跑后实验任务中展示出掌握了更多的认知和运动技能。有趣的是,Valdesolo et al.猜测,通过只是观察歩幅一致的跑步者就会比观察歩幅不一致的跑步者可能掌握更多的认知和运动技能,但是他们没有测试这个猜想。我们关注的存在于周围环境中的音乐研究正是给Valdesolo et al.的猜想提供了测试。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研究相比那些通过活跃的任务,如打鼓,敲击,或同步跑步不同的只是让人们被动接收的、快乐的、有节奏的音乐是否同样能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关注它一个重要且实际的好处是,相比之前的研究焦点因素的运动性特征,在工作场所听音乐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更自然的活动。我们研究的结果变量合作行为是对之前的一系列经济决策研究结果变量的补充。合作行为像是一种同步活动,它从逻辑上扩展了以前的研究的同时又对当代组织显然是重要的(Kniffin, 2009)。因此,我们提出了创新的猜想即当人们听到快乐的音乐时会比没有听到音乐或听到不愉快的音乐时表现出一种享受“社会联系”好处的状态,促使团队成员趋于一致从而采取合作的行为。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快乐的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于情绪的测量,我们是出于之前的一些显示音乐和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考虑到是否情绪可能会对我们实验中的因变量产生正向影响。更具体地说,我们预期更好的或更高的情绪水平将对团队贡献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之前已经有学者研究过情绪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但证据不一(Hertel et al.,2000)。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更高的情绪水平与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Thompson et al.(2001)发现听古典音乐和在空间测试中表现更好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的关系堪称“莫扎特效应”——它充分解释了为什么要更仔细地分析音乐所产生的高昂的情绪和激励水平。且不像自变量音乐属于外生性变量,情绪是属于内生性变量。通过情感事件理论框架(AET),我们可以预期被音乐诱导所提高的情绪会显著影响快乐的音乐和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情绪在快乐的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二、实验1研究介绍
(一)被试和实验过程
我们招募的被试来自美国南卫理工会大学,因为这所学校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细分招募被试的方法来兼顾文化因素对实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招募的88名被试中特意挑选了26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18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16名来自印度的留学、10名来自沙特的留学生以及美国本土的18名学生,以上这些海外留学生均选择来美国不超过三年的学生,尽量避免美国文化对其的干扰,在88名被试中,其中有39名女性,其中让47名被试听快乐的音乐,41名被试听不愉快的音乐。
为了评估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潜在影响,我们要求被试说明他们的性别及登记他们的年龄属于以下哪四个类别之一:18-22(1),23-29(2),30-39(3),和40岁以上(4)。我们也要求被试报告他们的专业或专业领域,因为根据之前的研究显示,学经济的学生在公共产品实验中往往会比学其他专业的学生做出更自私的决策(Wang et al.,2011)。当然,被试还被要求说明他们的国籍,由于过往文献都认为各国的文化会对个人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例如美国的主导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Taras et al.,2010)。且有人研究过中国人受集体主义文化熏陶行为趋向于集体主义,而美国人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行为偏向个人主义(Oyserman,Coon&Kemmelmeier,2002)。
我们把被试分为两组,一组播放快乐的音乐,另一组播放不愉快的音乐。通过一个集中的音频系统,我们能够确保音乐的音量是统一听得见的,且音乐的音量大小控制在一个被试能感觉到舒服的范围。
被试需要登入弗吉尼亚大学公共VECON实验室网站(veconlab.econ.virginia.edu),在上面直接进行网络决策。在实验室被试的桌子上放了一些私人头套,用来确保被试每个人的决策是独立完成的(避免他们用余光扫视到坐在他们附近人的决策结果)。
被试参与实验除了可以获得部分课程学分,有时还能偶尔获得现金补偿。我们实验的现金补偿的平均额是每个被试5美元,额度范围控制在每人3美元到7美元。实验进行时间平均为20分钟,被试完成的时间从18到22分钟不等。
(二)自变量
作为刺激物,我们选择了四首“快乐”的歌曲(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卡翠娜与波浪乐团的“阳光下漫步”;范·莫里森的“褐眼女孩”和“快乐时光”的主题曲),每一轮播放总共是12分钟。另一组“不愉快”的歌曲是由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重金属”乐队演唱的(攻击攻击乐队 的“Smokahontas” 和 Iwrestledabearonce的“You Ain’t No Family”)。每一轮播放总共是8分钟。我们从88名被试中抽取了48名(15名中国留学生,9名日本留学生,8名印度留学生,5名沙特留学生以及11名美国留学生)作为被试样本让他们分别听来自这两组类型的两首歌曲并进行等级评定打分(量表由两位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博士进行双向翻译并对其进行语言润色,以提升测量项的可读性和易读性,其中美国被试者和印度被试者拿到的是全英文量表,中国留学生被试者拿到的是全中文量表,日本留学生拿到的是全日文量表,沙特留学生拿到的是阿拉伯语量表,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825。)根据我们所评估的每个测量项,两组类型的歌曲的平均等级分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快乐的歌曲,被试表示他们更同意:“这首歌是快乐的”(F= 547.3,p<.001)和“我喜欢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F= 52.6,p<.001)。更不同意:“这首歌是愤怒的”(F= 322.9, p<.001)。被试当被问到“你认为你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寒冷的”还是“温暖的”时显著多的被试选择了“温暖”(F= 141.0,p<.001)(Fiske et al.,2002)。
我们评估的三个与动态参与理论(DAT)相关的测项也表现出显著差异,特别是与Khalfa et al.(2008)提出的节奏是快乐音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观点吻合,显著多的被试同意:“这首歌是很有节奏的”(F= 62.8,p<.001),“这首歌让我随音乐的节拍也不自觉动起来(例如:拍腿、拍手或点头)”(F= 34.7,p<.001),“这首歌是很好的舞蹈音乐”(F= 43.3,p<.001)。
(三)因变量
为了测量因变量合作绩效,我们采用了一种传统的被称为自愿贡献机制(VCM)的公共产品实验(Isaac &Walker,1988)。每轮实验,每位被试会收到一定数量的代币,在没有被明确告知一共有多少回合的情况下被试可以在每一回合选择将代币作为团队之用或个人之用,被试需要决策不同用途的代币数量。在我们的实验中,每个被试被分配到总共10 枚代币(代币具有实际的现金价值),他们每轮实验需要将这10 枚代币进行分配,每一回合可以选择从0到10枚代币作为团队资产或个人资产。
由于VCM的一部分设计旨在激励和奖励合作,我们在软件中设置了参数,3个被试一组,当3个被试都选择将代币作为团队资产时,团队资产将变为1.5倍,即每个被试最后都将得到15枚代币。但若三个被试都一致选择将10枚代币留为己用时,每个被试最后得到的就仅限于这10枚代币。每个被试将与随机分配的两个固定的被试作为一个决策组进行20回合的决策,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告知被试另外两个被试者的身份,被试也不允许和另外两名合作伙伴进行交谈,因为之前的VCM测试发现,即使是被试之间相对少量的随意的谈话也往往会增加被试对团队资产的贡献 (Messer et al., 2007)。被试同样不被告知总共的回合数,目的是为了避免“最后一轮效应”,如果被试知道这是最后一回合了,他们将代币留为己用的机率将大幅增加,因为在这种特别情况下(Hollenbeck et al.,2012),对于被试来说,之后就没有潜在的互惠主义的期望了,大可“欺骗”团队和从事纯粹的自私行为。我们分析的目的是关注于在20轮决策中个体层面对团队的贡献。尽管值得注意的是,88个被试的观测结果中只有第1回合的结果可以被认为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个人决策在第2轮到第20轮都将受到前几轮结果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能够考虑到共1760种决策(88名被试×20轮)是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与被试采取决策行为后实际得到的资产分配有关。在这方面,我们遵循共同的VCM的分析方法(Messer et al., 2013)。整个过程采用的是盲测,被试是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在考察合作行为的。
(四)结果
表1显示了播放快乐的音乐和播放不愉快的音乐的两个组的人口统计变量值没有显著差异,即年龄、性别、国籍、是否主修经济学专业这些控制变量对结果影响不大。这恰好符合我们随机分配被试进行实验的安排。通过观察第1、5、10、15、20回合决策的结果显示,被试在听快乐的音乐时比听不愉快的音乐时将代币贡献于团队资产的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t检验表1中只有VCM 5的t值是显著的;作为表1的补充,我们将各回合的效应值列出:.23(第1回合),.67(第5回合),.29(第10回合),.20(第15回合),.18(第20回合)。通过对均值、标准差、效应值的分析,两组均值不显著的差异使我们认识到需要采用更广泛和更强大的方法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我们进行了实验2。增加了一个不播放音乐的控制情境以及一组情绪的测项。增加的不播放音乐的控制情境有助于我们解释实验1两组均值不显著的差异的结果。例如,如果我们发现被试在不播放音乐的控制情境下与在听快乐的音乐的情境下采取的合作行为一样多,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快乐的音乐对采取合作行为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听不愉快的音乐对采取合作行为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罢了。另一方面,如果被试在不播放音乐的控制情境下比在听快乐的音乐的情境下采取的合作行为少,我们则可以推断出快乐的音乐对采取合作行为有一个积极的正向影响。

图1 实验2三组情境下团队贡献均值折线图
三、实验2研究介绍
(一)被试
和实验1一样,我们招募的被试同样是来自美国南卫理工大学。这次一共招了200名被试(97名为女性),其中有62名中国留学生,36名日本留学生,28名印度留学生,19名沙特留学生,以及55名美国本土学生,这批被试与实验1的被试是完全不同的一批人,其中随机分配76人听快乐的音乐,69人听不愉快的音乐,55人不听音乐。被试中91%的人年龄在18 - 22岁之间和5% 的人年龄在23-29岁之间。
除了增加了一个不播放音乐的控制情境以及一组情绪的测项,实验2其他的程序和实验1所描述的过程是一致的。
(二)自变量
关于增加的自变量情绪的测量我们使用的是Peterson和 Sauber(1983)的四个题项的量表(量表同样经过双向翻译,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839。),用来评估被试在实验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情绪变化。这4个题项分别是:“目前,我心情很好,”“当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我感觉到快乐,”“出于某种原因,我现在不是很舒服,”和“在这个时刻,我感到急躁或易怒。”被试根据这4个题项进行等级评定打分,分值是从1分(强烈不同意)到5分(非常同意),其中第三和第四题采用反向计分,最后4个题项的总分越高表明被试拥有更积极的情绪。
为了测量被试整个实验过程中情绪的变化,我们首先是快速地测量了被试在第一回合VCM进行之前的情绪(情绪1),实验期间还快速地测量了被试在第10回合和11回合VCM之间的情绪(情绪2),最后又立即测量了被试在最后一回合VCM的情绪(情绪3)。从可靠性分析(情绪1:α=.78;情绪 2:α=.76;情绪 3:α=.74;)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

表 3 回合数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4 情绪的回归分析结果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三)结果
如表2、图1所示,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被试在听快乐的音乐的时候比另外两个情况下采取了显著的和持续的更高水平的合作行为。更具体地说,从被试做出多少团队贡献的行为可体现被试之间合作的不同程度,这些发现支持了假设1即快乐的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通过最右一栏的图基事后检验法分析数据可看出没有明显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所以我们在三个实验情境下随机分配被试是可行的。从情绪的测量数据可看出,情绪1、2、3都较之不听音乐受不愉快的音乐影响更持续且更强烈。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从图1可以看出第1到第20回合VCM中,被试做出团队贡献行为总体趋势是递减的。因此我们在图1的基础上,又通过三个模型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视角来分析实验的回合数对被试做出团队贡献行为的影响,如表3所示:
作为对表2只提取了实验中五个回合(1、5、10、15、20)的数据,表3则是对实验中20个回合的数据汇总进行了回归分析,表3中第一个模型表明,在回合因素被考虑的情况下,快乐的音乐和团队贡献行为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个和第三个模型分别把第1 到第10回合和第11到第20回合的数据分开来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快乐的音乐和团队贡献行为之间还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所有的三个模型中,回合这个因素是重要的且是消极的,因为从整个样本数据中观测到随着实验回合数的增加,被试做出团队贡献行为是逐渐减少的。然而,表3整体表明了即使存在实验回合数对被试做出团队贡献行为逐渐减少的影响,但一点也不妨碍快乐的音乐对被试做出团队贡献行为的积极作用。
从表2可以发现,播放不愉快的音乐相比播放快乐的音乐和不播放音乐明显地引起了更糟糕的情绪。因此,表4给出了两个模型,用于研究情绪在三个不同播放音乐的情境下独立的作用。模型1我们将被试个人每一回合的团队贡献值作为因变量,并且分别用情绪1和情绪2的均值来测量其对被试从第1回合到第10回合个人的团队贡献值的影响,以及用情绪2和情绪3的均值来测量其对被试从第
四、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及理论贡献
我们进行的两个实验研究是建立在动态参与理论(DAT)和情感事件理论(AET)基础上的。在DAT理论的支持下,通过20回合的实验室研究,我们发现快乐的音乐对团队中的合作行为有着持续和积极的影响。在AET理论的支持下,我们还发现,情绪对团队中的合作行为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不影响快乐的音乐对团队中的合作行为的独立功能。关于情绪在快乐的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的发现挑战了认为快乐的音乐只是诱发了有利11回合到第20回合个人的团队贡献值的影响。模型2则简单的将被试个人20回合的团队贡献的均值作为因变量,将被试个人情绪1、情绪2和情绪3的均值作为自变量。从表4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音乐的作用是独立的,因为我们的实验设计中音乐是外生性的影响因素,而被音乐所影响的情绪是内生性的因素,因此,这两个变量不应该被认为是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同的独立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显示出了情绪对团队贡献行为的显著性影响,然而它的效应值是表3中快乐的音乐的效应值的1/17,而且当在模型2中观测的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情绪的作用变为了不显著。这些发现提供了对假设2即更高的情绪与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部分支持,同时表明快乐的音乐对合作的行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对假设1和2的直接测试的补充,我们也用了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测在控制回合数的情况下情绪在快乐的音乐和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图2说明了快乐的音乐和情绪呈正相关关系 (β=.45,p<.01),此外,情绪与合作行为也呈正相关关系(β=.21,p<.01)。相比快乐的音乐和合作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呈正相关关系(β=.17,p<.01),整条关于音乐、情绪和合作行为的间接影响路径也呈正相关关系(β=.08,p<.01)。因此,情绪在快乐的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得到了支持。于产生合作行为的情绪的研究 (Thompson et al.,2001)和其他认为情绪和合作行为之间没有关系的研究 (Hertel et al.,2000)。针对Kniffin et al.(2016)研究忽略了各国文化差异这一不足,本文将实验被试做了进一步细分,划分为在美国南卫理工会大学就读的世界各地区留学生(包含中国、日本、印度、沙特)和美国的本土学生两类学生群体进行实验对比研究,得出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该结果补充证明了Kniffin et al.(2016)的研究结论在其他文化领域情境下同样适用。
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多元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认识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存在的共性,交流合作成为了目前的世界的主流沟通方向,而本文的快乐音乐理论对多元文化交流的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是一种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贡献之一。同时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在团队人力资源管理中快乐音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快乐音乐能够促使人们的心情变得舒缓,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气氛,融入到团队集体中,本文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指导团队人力资源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对团队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启示
音乐是无处不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们也不可忽视音乐在工作场所对员工行为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企业出现工作任务加重、员工压力指数升高、亟需要平复员工们焦躁的情绪、调动员工们的积极合作行为以提升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情境下,管理者们更需要将能够提高员工们情绪水平、激发员工们团结合作的办公室音响系统的价值充分利用起来。很多管理者们都会在户外团队建设、素质拓展上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构建员工之间的合作精神。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管理者们还可以通过每天早晨选择一些有节奏的、快乐的音乐在工作场所进行播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带来愉快高效的雇员和更融洽的团队,激发员工们配合默契、共同决策和与他人协商的合作行为,而当这种团队合作行为是员工出于自觉自愿时,它必将会产生一股强大而且持久的力量。
目前在团队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团队成员无法求同存异,达成相互认同,难免会出现个性与能力都非常强的成员之间形成恶性的竞争,而非良好的合作,从而不利于个人价值与团队目标的实现。从团队角度而言,团队需要对团队成员之间的差异性进行鼓励,以便可以利用不同成员的知识、个人技能,使整个协作更为有效,但同时也需要不同成员之间进行积极的合作,以使团队工作更有利地完成,使团队绩效得以最大化发挥。通过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结合快乐音乐理论,将其应用在团队日常运营管理中,愉快的心情能够有效的促进工作的效率,对于负责运营管理的领导要根据当前的工作环境选择合适的音乐背景缓解大家紧张劳作的心情,从而极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使员工创造更多的价值。
同时本文的研究成果同样对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领导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对文化建设意识还很淡薄,未能把企业核心文化的建设纳入人力资源管理,使企业文化在一个企业中所具有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动力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人力资源的负责人需要更加重视员工的主动积极性,通过结合快乐音乐理论,重塑和构建企业文化氛围,定期播放快乐的音乐,吸引大家进行团队合作,另外通过不同人对于快乐音乐的反应,可以清楚地了解每个人目前的心态,从而更好地组建优秀团队,并及时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本文提出的音乐手段进行动态调整,全方位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1.我们选择的音乐类型可以有更多精细的划分。例如,集体主义主题的快乐的歌曲相比个人主义主题的快乐的歌曲可能将产生更多的合作行为(Sela et al., 2012)。2.我们没有考虑被试的性格差异、被试对特定音乐类型的熟悉程度和相对喜欢程度,未来的关于音乐、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将受益于把一些行业和公司员工相对独特的个性、员工对音乐类型的偏好考虑其中。3.对于假设2,选择关于情绪更多维度的测量( Gooty, Gavin, & Ashkanasy,2009)将比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情绪测量的4个题项的量表提供更深入的发现。4.对音乐与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实地研究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我们进行了20回合的实验研究,但这远远不如把实验场地转换到一个真实的工作场所去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未来的研究调查应侧重在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音乐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5.未来研究可以扩展关于音乐在工作场所的影响导致的结果变量的范围,不要局限于“合作行为”。研究在工作场所播放的不同的音乐类型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的变化影响将是有价值的。6.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把视角投向那些营销学家们强调的其他环境特征(例如:好闻的气味:Doucé & Janssens,2013)在零售和非零售工作场所对员工行为的潜在的影响。
1.Munichor, N., Rafaeli, A. Numbers or apologies? Customer reactions to telephone waiting time fi lle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 92(10): 511–518.
2.Strick, M., de Bruin, H. L., de Ruiter, L. C., & Jonkers, W . Striking the right chord: Moving music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transporta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015,21(4):57–72.
3.Wansink, B., van Ittersum, K. Fast food restaurant lighting and music can reduce calorie intake and increase satisfaction.Psychological Reports, 2012,111(7): 1–5.
4.Grant, A.. Give and take: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uccess. New York, NY:Penguin Books, 2013.
5.Wilson, D. S., Knif fi n, K. M. Altruism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S. G.Post, B. Johnson, M. E. McCullough,& J. P. Schloss (Eds.), Research on altruism and love. Radnor, P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2003:117–136.
6.Ashkanasy, N. M., Ayoko, O. B., & Jehn, K. A..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work and employee behavior: An affective event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4,35(2): 1169–1184.
7.Knif fi n, K., Wansink, B., Devine, C., & Sobal, J. Eating together at the fi rehouse:How workplace commensality relat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firefighters. Human Performance, 2015,28(5):281–306.
8.Kniffin, K.,Yan, J.,Wansink, B., & Schulze, W.The sound of cooperation:Musical influences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6,17(9):32–64.
9.Jones, M. R., Boltz, M. Dynamic attending and responses to tim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96(11):459–491.
10.Large, E. W., Jones, M. R. The dynamics of attending: How people track timevarying events. Psychological Review,1999,106(13):119–159.
11.Weiss, H. M., Cropanzano, R.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In B. M.Staw, & L.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n annual series of analytical essays and critical reviews . US: Elsevier Science/JAI Press,1996:1–74.
12.Houston, D., Haddock, G. On auditing auditory information: The in fl uence of mood on memory for music. Psychology of Music, 2007,35(6): 201–212.
13.Weiss, M., Trehub, S., & Schellenberg, E.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sings:Enhanced memory for vocal melodi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23(4):1074–1078.
14.Gold, C., Solli, H., Kruger, V., & Lie, S. Dose response relationship in music therapy for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9,29(8):193–207.
15.Ratcliffe, E., Gatersleben, B., & Sowden, P. Bird sound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perceived attention restoration and stress recove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3, 36(3):221–228.
16.Devlin, A. S., Arneill, A. B. Health care environments and patient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3, 35(7):665–694.
17.Niven, K. Can music with prosocial lyrics heal the working world? A field intervention in a call cente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5,45(12):132–138.
18.Yalch, R. Memory in a Jingle Jungle: Music as a mnemonic device in communicating advertising sloga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1,76(15):268–275.
19.Lang, M., Shaw, D. J., Reddish, P., Wallot, S., Mitkidis, P., & Xygalatas, D.Lost in the rhythm: Effects of rhythm on subsequ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Cognitive Science in press. 10.1111/cogs.12302,2015.
20.Brooks, A., Schweitzer, M. Can Nervous Nelly negotiate? How anxiety causes negotiators to make low first offers, exit early, and earn less profi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115(14):43–54.
21.Au, K., Chan, F., Wang, D., & Vertinsky, I. Mood in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cognitive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3,91(12):322–338.
22.Wiltermuth, S., Heath, C. Synchrony and co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20(1):1–5.
23.Krahe, B., Bieneck, S. The effect of music-induced mood on aggressive affect,cogni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2,42(10):271–290.
24.Kokal, I., Engel, A., Kirschner, S., & Keysers, C. Synchronized drumming enhances activity in the caudate and facilitates prosocial commitment—If the rhythm comes easily. PLoS ONE, 6 e27272,2011.
25.Launay, J., Dean, R. T., & Bailes, F. Synchronization can influence trust following virtual interactio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13, 60(14):53–63.
26.Hove,M.J.,Risen,J.L.It’s all in the timing:Interpersonal synchrony increases af fi liation.SocialCognition,2009,27(6):949–961.
27.Valdesolo, P., Ouyang, J., & DeSteno, D. The rhythm of joint action: Synchrony promotes cooperative a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0, 46(13):693–695.
28.Kniffin, K. M.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salary dispersion within firms.Journal of Bioeconomics, 2009,11(2):23–42.
29.Hertel, G., Neuhof, J., Theuer, T., & Kerr, N. L. Mood effects on cooperation in small groups: Does positive mood simply lead to more cooper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0,14(5): 441–472.
30.Thompson, W. F., Schellenberg, E. G., & Husain, G. Arousal, mood, and the Mozart e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1, 12(4):248–251.
31.Wang, L., Malhotta, D., & Murnighan, J.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greed.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Education, 2011,10(8): 643–660.
32.Taras, V. Kirkman, B. L., & Steel, P.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A three-decade, multilevel, meta-analytic review of Hofstede’s cultural value dimens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95(11):405.
33.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2,128(16): 3–72.
34.Khalfa, S., Roy, M., Rainville, P., Dalla Bella, S., & Peretz, I. Role of tempo entrainment in psychophysi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happy and sad mus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08,68(13):17–26.
35.Isaac, R., Walker, J. Group size effects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103(15):179–199.
36.Messer, K., Zarghamee, H., Kaiser, H., & Schulze, W. New hope for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mechanism: The effects of contex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91(8): 1783–1799.
37.Hollenbeck, J., Beersma, B., & Schouten, M. Beyond team types and taxonomies: A dimensional scaling conceptualization for team descrip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2,37(4): 82–106.
38.Messer, K., Suter, J., & Yan, J. Context effects in a negatively framed social dilemma experiment.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3,55(7): 387–405.
39.Peterson, R.,Sauber, M. A mood scale for survey research. In P. Murphy, et al.(Eds.), 1983 AMA educators’ proceed-ings. Chicago, Illinois: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83:409–414.
40.Sela, A., Wheeler, S., & Sarial-Abi, G. We are not the same as You and I:Causal effects of minor language variations on consumers’ attitudes toward brand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39(3):644–661.
41.Gooty, J.,Gavin,M., & Ashkanasy,N.M.Emotions research in OB: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9,30(12):833–838.
42.Doucé, L., Janssens, W. The presence of a pleasant ambient scent in a fashion st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hopping motivation and affect intens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3,45(14):215–238.
Impact of Happy Music on Cooperative Behavior——The Mediating Role of Mood
Luo Yiqi1,Su Fangguo1and Yu Ziyi2
(1.School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ersity;2.Business School,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Music as an environmental aspect of professional workplaces has been closely studied with respect to consumer behavior while spars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its relevance for employee behavior. In this article, we focus on the in fl uence of music upon cooperative behavior within decision-making groups. Based on results from two extended 20-round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we find that happy music signi fi cantly and positively in fl uences cooperative behavior. We also fi nd a signi fi 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ood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Besides, we discover that the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of mood between happy music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
Music; Employee Behavior;Cooperative Behavior; Mood
罗旖颀(通讯作者),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13602654771@163.com。
苏方国,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余子逸,南卫理公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630056)资助。
■责编 / 罗文豪 E-mail:chrd_luo@163.com Tel:010-8838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