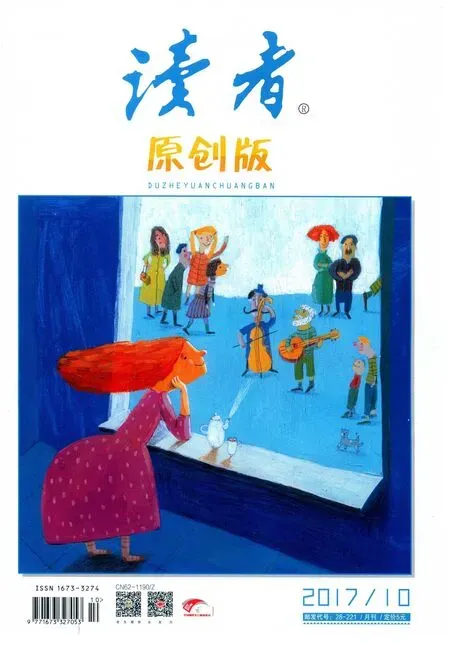一首甜美的短歌
文|张悦芊
一首甜美的短歌
文|张悦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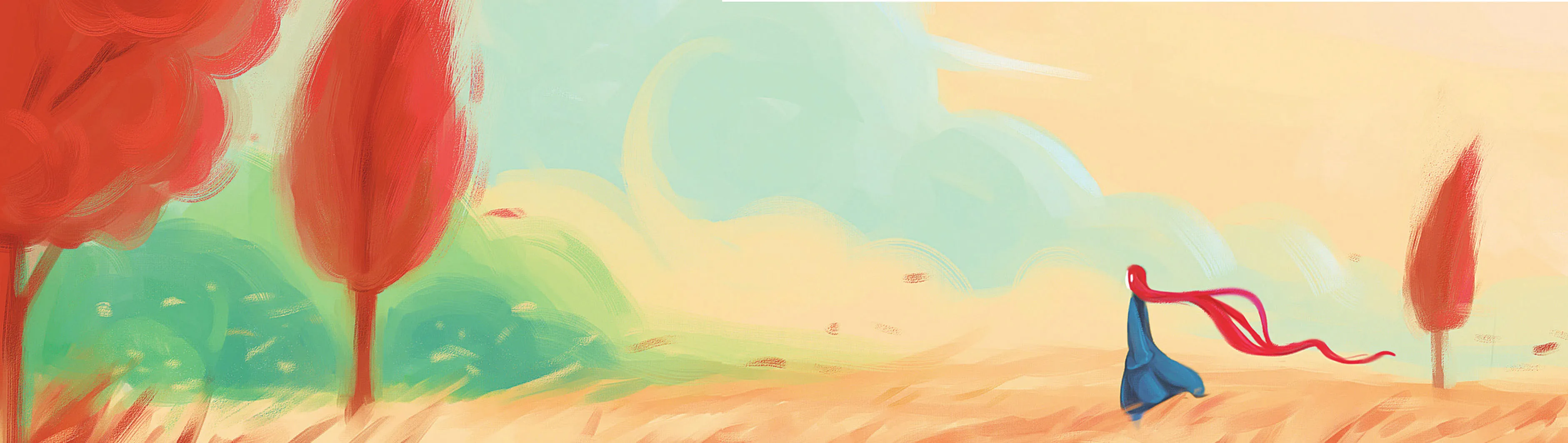
我的东欧之行始于一张不到二十欧元的廉价机票,从巴黎到华沙。
四月,春假的第二天,我拖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辗转来到巴黎,又搭顺风车来到郊外的机场。暮春时节,似乎整个欧洲都在下雨,但这并没有影响飞机上乘客的心情—在欧洲搭乘廉航仿佛坐公交车,永远都是吵吵嚷嚷的。
当窗外出现一片片绿意盎然的田野时,我意识到,波兰近在眼前。
一
前一天去青旅放行李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小哥躺在床上,看他在玩手机我就没说话,朝他笑了下,继续低头收拾东西。
叠到第三件衣服时,小哥问道:“你从哪里来呀?”
于是,本打算重温下《辛德勒的名单》的我,和小哥窝在青旅大厅的沙发上乱侃起来。
小哥名字里有个“Min”,所以当他问我他的名字用中文怎么说时,我敷衍地说:“就叫你小明吧。”他非常开心地把“小明”二字抄下来,然后发在了Facebook上。
小明在华沙上学,这学期来克拉科夫实习,找到房子前先在青旅过渡一下。他是个很厉害的程序员,现在在微软的X-box实习。虽然小明今年才大二,但已经做出两款在Google Play上架的游戏了。后来,我和朋友们分享他做的游戏,一群人沉迷于这个类似“开心消消乐”的游戏无法自拔。
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聊到午夜,考虑到明早他要上班、我要去玩,于是决定去睡觉。
小明的床铺正对着我的,我看他上床后还在发信息,正打算翻身睡去,手机开始震动。
小明发信息说:“‘我喜欢你’用中文怎么讲啊?”
我回复:“我喜欢你。”
小明发来一个又蠢又大的笑脸表情,还有一句从谷歌翻译软件上复制来的:“我也是。”
不知怎么的,那晚我睡得很甜。
二
第二天我送小明到车站,他说下班后要带我四处逛逛,我说好,然后从老城广场出发,四处溜达。
前一天我经过了一所名为雅盖隆的大学,校园里人来人往,但非常安静,有好看的红墙和对称的拱形圆柱。
于是,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并走进学校内部的博物馆一览其详。博物馆的顶部画了蓝天白云,一层长廊上的壁画,笔触看起来很稚嫩,但和阴天的灯光在一起相得益彰。
逛完一圈走出校园时下起雨来,我躲在学校外面的屋檐下避雨。忽然,手机连着震了好多下,拿出来一看,是小明发来的。
他问:“晚上去哪里找你?”
我想了想说:“就在‘大头’那里吧。”
这并不是什么黑话,而是我唯一能叫上名字的地标—没错,那时候我还没记住圣玛利亚教堂的名字,也不能大概说出来某个广场,唯有前一天导游说到的“Big Head”记忆深刻。
那个“大头”似乎是某位克拉科夫先锋艺术家的作品,被安置在克拉科夫市中心的广场上。
小明说:“好啊,我五点半下班,六点的时候我们在‘大头’那里见吧。”
雨小了一些,我赶往约定的地点。路上,我忽然想到,这样老派的、定好时间地点的见面方式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大约只在初中没有手机的时候会这样口头约定,再后来都是靠微信实时定位。
路过一家陶瓷店,里面零零散散摆着许多小玩意儿,我挑了两只杯子,又看到一只蓝色的小鱼挂件,打算买下来送给小明。
送这个礼物给小明是因为昨天聊天儿的时候说起我的记忆力不太好,而中国有个说法是金鱼只有七秒的记忆。
他说:“啊,那你是真的很像鱼。”
我在旅途中时常遇到不同的人,有的活泼健谈,整个旅程都在说话;有的沉默寡言,其实内心有趣、生活丰富多彩。他们给我的感觉,无一例外都是稍纵即逝的。
年少时不懂萍水相逢就该微笑作别,总对一些注定要分别的人念念不忘。
没有人教我该如何辨别注定只是嬉笑一场、明朝就离去的人和一生知己,只是这样不愿松手而狼狈挣扎的时刻多了,就慢慢习惯将新遇到的人都假定为他们即将离开。
但我依然隐隐期待那些类似灵魂撞击的相遇里,能有一些持续得久一点儿的羁绊。
即使是健忘的我,也还是想让不那么健忘的你,多记得我一些啊。
小明看到我拿出小鱼挂件时有点儿纳闷,我稍加提示,他便高兴地反应过来,非常亲热地推了我一把。我被他推得往后退了几步,咧咧嘴,心想:“他要是会中文,应该要说几句‘厉害了’‘666’吧。”
天色尚早,我问他:“你要带我去哪里逛啊?”
他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神秘又期待的神色,用右手牵起我,然后用左手指指天说:“哪里都不去,我们向上走。”
我并不知道,“大头”后面窄窄高高的塔是可以爬上去的。
顺着十分狭窄而陡峭的楼梯攀爬上去,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展示内容—这里仿佛是一个纵向的博物馆。
到了塔的顶端,景色一下子开阔起来。
我向来喜欢登高,喜欢站在高处俯瞰城市,俯瞰万家灯火明明灭灭,汇成蜿蜒的长河。但在真正俯瞰克拉科夫时,我还是惊叹了一下:“这就是我用整整两天走过的城市啊!”我几乎路过了它所有的建筑,走过了所有的街道,在飘着雨的清晨、午后和傍晚,仰望它的恢宏、精致或奇幻,而今天我站在云端俯瞰这座城市,换个角度,它们依然这么美。
三
我就这样趴在窗前拍照,探头探脑,又发了很久的呆之后,忽然发现小明也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又不想显得太刻意,于是搜肠刮肚地想出一个有关波兰的话题打破尴尬:“你读过辛波斯卡吗?”
他摇摇头:“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她有什么有名的诗吗?”
我想了想:“有一首《企图》我很喜欢。”
我从包里掏出日记本,翻到前几页。大学的时候收到友人赠予的一本《辛波斯卡诗集》,很喜欢这首,就抄在了日记本里。
我绞尽脑汁逐行翻译给他听:
哦,甜美的短歌,你真爱嘲弄我
因为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能。那毋庸置疑
我企图生出枝叶,长成树丛
我屏住呼吸—为求更快蜕化成形—
等候自己开放成玫瑰
甜美的短歌,你对我真是无情
我的躯体独一无二,无可变动
我来到这里,彻彻底底,只有一次
我们在塔顶聊天儿合影的时候,小明和我说了很多过去和未来的事情,谈到了他的上一任女朋友、爸妈的职业,甚至还有大一的平均分,畅想了关于未来的职业、生活和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些现状的坚持。
我一直在想,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来,我一定早就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他为什么这样傻、这样天真,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啊?而我竟然每一句都听了进去,并且都给了“好棒”“很好啊”之类的正面反馈。
我们说了很多对未来的畅想,最后当我们走到塔楼入口处时,他忽然看着我的眼睛说:“以后的生活,要是你在就好了。”
那时,我刚好翻译到《企图》的最后一句:“我来到这里,彻彻底底,只有一次。”
我开始艰难地向他解释我现在的想法,断断续续说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的句子。我说:“小明同学啊,我当然喜欢你了,我喜欢你半夜聊天儿时还给我泡茶、拿饼干,我喜欢你做的游戏和满屏我看不懂的代码,我也喜欢你对未来的畅想,尽管已经很久没人跟我说过这些话了。可是我们只是萍水相逢啊!明天一早我就要去布拉格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
他听着我讲,没有说话,忽然靠近我,轻轻地吻了我的额头。
我没看他,转过脸,吻了他的唇。
后来他说:“我以为你那么说,是在拒绝我。”
我说:“可能是吧,但我现在意识到,假如我因为明天要走就和你分开,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四
第二天清晨,我依旧坐上去布拉格的汽车,开始了在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旅程。
回到法国之后,我们仍然每天聊天儿、一起远程看电影,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咯咯笑个不停。
五月的时候我本想去波兰看他,但突然身患恶疾,难以成行,遂没有再见。七月时知道他来年可能来天津做交换生,还帮他填了中英双语的留学生申请表,但他因为成绩不够好而落选,继续在华沙读书。
那时的我已经在北京。收到他的信息的时候,我心想:“要是你能来,多好啊!”
我们依然断断续续地联系着,在视频这端我看到他搬了新的公寓,也看见他在Facebook上发布了他的又一款游戏在Google Play上架的消息。前两天他和我说,准备和朋友一起搞一个创业项目,明年二三月可能要去硅谷。
我说:“好啊,到时候去看你。”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我在塔楼上读的那首诗,我觉得他没有改变我,我们只是在某个微妙的时刻达成了和解。
对于我们分别后所有的期待都是真的,但谁都没有被期待改变方向,也不为期待落空而过分失望。
他的出现让我意识到,离别是所有同行者的必然结局,但若因此畏首畏尾就太愚蠢了。
你来到这里,只有一次,但这一次遇到的冒险、美好和爱,都是真实的,都值得为之疯狂。
期待你—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美好了。
我们认识一周年的时候,他发来一个视频请求,连通后他开始唱一首莫名其妙的歌。
我大概听到副歌才反应过来,他唱的是邓紫棋的《喜欢你》,而那些奇奇怪怪的歌词,是他学的蹩脚的粤语。
我一边听一边想,实在是太难听了。但回过神来时,我已泪流满面。